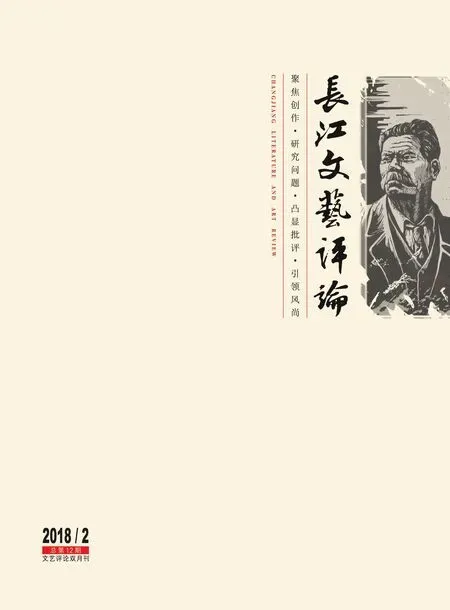搬演的魅力
——评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
◎陈全黎
法国探险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 说 过,“The impossible missions are the only ones which succeed(只有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才能取得成功)。”许扬导演的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6)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悖论。“从我的帐篷的门里,我可以看到营地或村落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对田野工作的经典描述。在薅草锣鼓消失多年之后,导演当然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到20年前的“换工搭伙”时代,甚至40年前的集体化时代,去拍摄一部“真实”记录宜昌薅草锣鼓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编号Ⅱ-27)的纪录片。要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只能采用情景再现的方法——“搬演”。
为了生动再现宜昌薅草锣鼓的历史现场和演唱流程,导演精心挑选了4位“演员”,他们是薅草锣鼓艺人袁国本、李光平、李光虎、肖世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锣鼓艺人是最理想的“演员”。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自己“扮演”自己。与其他“搬演”的音乐表演纪录片不同,《宜昌薅草锣鼓》没有舞台,也没有摄影棚。如果非得说有的话,那就是夷陵区天坑村的一块玉米地。在这块真正的“田野”上,导演为观众依次呈现了从早到晚按时序登场的各类薅草锣鼓号子。
正如保罗·休利所说,“现在假如有人拍摄民族志电影,他当然不再相信摄影机镜头可以记录客观‘科学’的资料。”即使是360度全景摄像获取的民族志素材,也必须经过导演的剪辑和重组,才能成为一个可以“观看”的故事。布莱恩·温斯顿指出,民族志电影的里程碑作品——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就有“造假”的嫌疑。例如“冬天之后”的北极天空居然没有变暗,还有那个只有一面墙壁的雪屋(Igloo),居然出现在电影中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按照布莱恩·温斯顿的说法,《宜昌薅草锣鼓》也许可以称为“真诚而正当的情境再现”。所谓“真诚”是指导演已经明确告诉观众,薅草锣鼓已经成为消逝的历史,锣鼓艺人的表演属于“搬演”。所谓“正当”是指导演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严格按照锣鼓艺人所说的“规矩”再现演唱流程。在纪录片中,锣鼓艺人既是表演者,又是口述者。作为表演者,他们击鼓,他们歌唱,他们用身体再现历史。作为权威的受访者,他们是讲故事的人,他们用记忆建构历史。借助于“搬演”和“口述”,薅草锣鼓由盛转衰直至消亡的历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在《宜昌薅草锣鼓》中,导演正是用这种真诚的态度,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实的虚构”,为纪录片如何重构过去的历史树立了标杆。
但导演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试图将《宜昌薅草锣鼓》拍成一部有思想深度和学术高度的纪录片,“一部理解中国小农生存之道的社会学纪录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纪录片中插入叙事者的声音,也就是导演的理论阐释。
在导演看来,薅草锣鼓只是纪录片的“毛”,它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制度,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用这种“皮毛论”或曰经济决定论,来解释薅草锣鼓这种具有高度实用功能的艺术形式的兴衰,似乎问题不大。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皮”。一种观点认为,薅草锣鼓衰亡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乡村从集体化向土地承包、分散经营的经济转型。在集体化时期,薅草锣鼓是生产动员的重要手段,自然盛极一时。而在集体经济解体之后,薅草锣鼓就只能成为一种表演的仪式或审美的艺术。事实上,集体化只是薅草锣鼓历史上一段非常短暂的插曲。从唐代的“耘田击鼓”开始,薅草锣鼓一直贯穿于中国上千年的个体小农经济时代。正是从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出发,导演认为,小农经济时代“换工搭伙”的潜规则和组织制度,才是薅草锣鼓依附的真正的“皮”。
米兰·昆德拉说,“事情总是比你想的更加复杂。”而在村民的眼中,我们总是故意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薅草锣鼓的敌人究竟是谁?锣鼓艺人袁国本以一种哲学家的口吻说道:
“现在由于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把农药一打,没得草扯,没得草薅,不需要这么多人,何况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还有更生动的描述。村民李培明说:
“春天种了打乙草胺,草籽刚刚生了,打百草枯,打一道。把苞谷扳了又打一道草甘膦。”
这就是村民的答案:除草剂。最简单,又最深刻。这使我们想到50年前的蕾切尔·卡逊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再也没有鸟儿歌唱?为什么春天如此寂静?蕾切尔·卡逊的回答是:杀虫剂和除草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宜昌薅草锣鼓》不是一部关于薅草锣鼓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及时记录“后蒿草锣鼓时代”中国农村生态和农民心态的纪录片。在除草剂的潜在危害仍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当下,这部纪录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介入了现实。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杰作,一部散发着浓郁诗意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记录。”这是格里尔逊对弗拉哈迪《莫阿拿》(1926)的评价。《宜昌薅草锣鼓》同样是一部充满诗意的纪录片。电影开篇,观众看到的是深切的三峡和高耸的百里荒,这是叙事展开的地理空间;接下来,导演用30分钟的叙事时间,再现了上工、歇工、收工的一天。劳动的场景,与不同功用的锣鼓号子精确对应:清晨,催人奋进的鼓点,奏响劳动的序曲;午后,高亢激昂、节奏明快的“扬歌”,掀起劳动的高潮;傍晚,悠扬舒缓的“送郎”“煞鼓”,宣告劳动的结束。这些相对松散的音乐片段组合起来,正好隐喻和暗示了薅草锣鼓的一段兴衰史。
“难舍难丢”,曲终人散。在电影的尾声,锣鼓艺人李光平回忆说:“我记得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我还在外村给别人打了一天锣鼓,那就是最后的一次打锣鼓。”而就在这次拍摄之后不久,49岁的李光平离开了人世。他给观众留下的,是一段苍凉的声音,一个消失的背影。
多少次看见
你穿行在百里荒的小径
清晨的三叶草
打湿了你的解放鞋
一锣一鼓
是你生命的全部
多少次聆听
你激越的鼓点洪荒的嗓音
铿锵的节奏
是劳作的最高律令
矫健的舞步
是乡村最美的风景
多少次追问
锄头为什么休息
百草枯为什么是绿色
歌声为什么变成拖拉机的轰鸣
骄傲吧
你的名字 再也不像你的祖辈
仅仅刻上墓志铭
你渐行渐远的背影
已被纪录片定格为历史的瞬间
(献给那些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无数民间艺人)
注释:
[1]【英】E.E.埃文斯 - 普理查德:《努尔人》,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页。
[2]【英】保罗·休利:《民族志电影:技术、实践和人类学理论》,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8页。
[3]【英】布莱恩·温斯顿:《纪录片:历史与理论》,王迟、李莉、项冶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97—98页。
[4]张建民:《从薅草锣鼓中追寻传统农业时代的节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
[5]【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2页。
[6]【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贾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