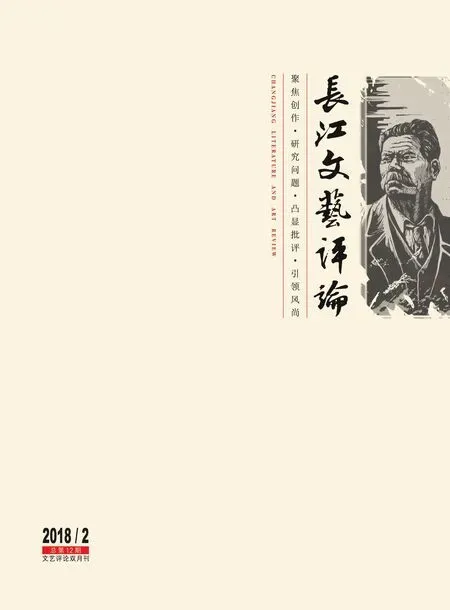论刘艳的叙事学批评
◎张 均
青年学人刘艳近年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异军突起,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不但许多前辈学者对她寄予厚望,同辈学者也多为她的才华与勤奋叹佩不已。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固然得力于她对《文学评论》长期推重的“学理性批评”的积极而有效的实践,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她在这些新鲜、敏锐的批评文字里,所显示出的博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一格的批评体系与文体风格。后者,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当代文学叙事学批评上的专业、精细与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学理论陆续进入大陆学界,但外来叙事学理论如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开花结果”,始终是有待解决的学术难点。这并非指当代文学批评未能有效借鉴西方叙事学的视角、叙述者、叙述声音等新概念,而是指在建立当代文学“中国叙事学”方面,仍然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批评实践。
然而,刘艳的“学理性批评”让人看到久已期待的学术努力。我不能判断刘艳在她“精耕细作”式的批评中是否已经在有意识地形成、完善自己的叙事学解释体系并努力“成一家之言”,但从她对陈晓明、申丹等前辈学者的虚心吸纳上,从她对萧红、严歌苓、赵本夫、北村等现当代名家文本“抽茧剥丝”式的精细解读中,是可以读出较成体系的叙事学分析框架的。倘以逻辑顺序而论,隐含作者、叙事结构、叙述视角(尤其限制性视角)无疑是刘艳展开叙事学分析的三个相互支撑的“着力点”。由此三点着力,刘艳巧妙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了自己繁复而深刻的叙事批评,并将最终问题集中在“文学性何以可能”之上。
“隐含作者”概念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西方叙事学理论从“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自我调整的结果。西方叙事学本身是从“结构主义诗学”内部发展起来的,它对“叙事语法”的寻找主要集中在文本形式层面,而有意排斥叙事与繁杂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的事实关联。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叙事学文本分析的深度及有效性,但介于真实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就有效地将形式分析与作者所置身的历史语境建立了关系。所谓“隐含作者”,是指读者从作品中推导和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它并非真正的作者,而是作者在文本中体现出的“第二自我”。可以说,由于时代语境与作者自我处境的流变,同一作者在不同作品中的“第二自我”未必是相同的。由此,刘艳将“隐含作者”列为了她的叙事分析的始发点:“(隐含作者)决定着文本的叙事结构及文本所遵循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负责场景和事件的选择和组合,即整体叙事结构、叙事节奏、主体行为方式和意义层面等各方面的安排。”不过对于隐含作者在叙事中的实际功用,刘艳却是以辩证眼光目之的。在她看来,隐含作者与作者、叙述者存在难以分割的关联,怎样将此关联处理得“恰当”,则是对作家叙事能力的挑战。在此方面,现当代文学堪称经验与教训并存。她引以为教训的,是“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们的“私小说”写作,如郁达夫之“自叙传”小说,“(其)主人公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出场,都熔铸了作家太多的主体形象和心理体验,连主人公的长相、穿着、气质、心理,简直就是郁达夫本人的翻版。”这初看起来,是叙述者和人物丧失必要的距离,细究起来则是作家虚构意识严重欠缺,以致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人高度混同。如此叙事处理,最后结果必然是文本缺乏必要的视点转换,在丧失叙事丰富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意义层面的丰富性。作为经验,刘艳则认为萧红、迟子建、严歌苓等作家在此方面处理分寸得宜,方法多样,并由此造就了丰沛的文学性,如严歌苓的《芳华》不仅“压缩了‘我’在小说叙事出现的频次和所占的份额”,而且将第一人称“我”分解为交替出现的两种眼光,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时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类处理,很灵巧地“避免了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人的一种高度混合性和过于全知叙事对于小说艺术真实感的伤害,并令小说产生足够的艺术真实性和可读性。”
由隐含作者延伸到叙事结构分析,刘艳又为当代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绾合”。相对于陈晓明借用坂井洋史“歪拧”概念来分析贾平凹、莫言等“50后”作家有关融合传统小说、戏剧经验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经验的特殊方法,刘艳则以“绾合”概念来处理当代文学新的叙事探索。她在严歌苓的《上海舞男》中,发现了与“套中套”结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新的结构方法:“(其)‘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已经不是与外层的叙事结构构成‘歪拧’一说,而是翻转腾挪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自始至终与张蓓蓓和杨东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嵌套,不只是互相牵线撮合——绾,还要水乳交融,在关节处还要盘绕成结——绾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这不但是结构上的交相映照,更是叙事上的互为动力要素,不能不说是作者苦心孤诣的创造。在赵本夫新作《天漏邑》中,刘艳也发现“宋源、千张子等人的抗日英雄传奇及其延伸性叙事,并不是被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包裹在祢五常及其弟子的田野调查和当下生活中的叙事,两套叙事结构在自己的时空维度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各自发展,逐渐揭示出真相”,“却因共同的空间结构‘天漏村’,而发生关联、彼此嵌套,最终绾合在了一起。”应该说,对于当代文学这种“绾合”结构的发现,在刘艳之前尚不见有具体阐释者,它是否在“文学性”阐释上具有长久有效性,还有赖于刘艳进一步的丰富。
与叙事结构、隐含作者相比,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是刘艳使用最多、最娴熟的叙事分析概念。据我的印象,她近年几乎每篇重要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限知视角问题。这样做,与她对李洁非的一个看法的共鸣有关:“小说这种东西,在文学中其实类乎兵法,‘兵者,诡道也’,小说叙事本质上就是计谋化过程,太单纯、太明澈、太纯朴反而不行,必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何况兼以笔下人物形色各异,作者绝不宜执于自己的‘一念之本心’,反而应尽量去除自我,使一己分身为芸芸众生、三教九流。”对此,刘艳颇为感叹:“这真是击中了当代小说写作的软肋和七寸之处,当代小说的叙事谋划中,不乏九九乘法表还背得七嘴八搭的人常常去做了线性代数。而不能够‘去除自我,使一己分身为芸芸众生、三教九流’,那是自现代以来就一直盘踞于中国作家小说叙事上面的积弊:无论谁在叙述、哪个人物在叙述,都难脱全知视角叙述的窠臼;作家很难放下身段,只用人物的视角叙述或者常常是人物限制视角的转换不够自如、捉襟见肘;而作家主观性的介入过多,不可避免带来对小说叙事和真实感的伤害。”由此,刘艳的叙事学批评就具有明显“后现代”时代的特征:她对转换自如的全知叙述兴趣不浓,而对出现在各类现代作品中的限知叙述大为青睐。这当然与行家深知的可“用限制视角来获得‘感觉’的真实”,“靠限制视角来加强小说的整体感”的叙述革命有关。她的限知视角分析,无疑以《呼兰河传》的解读最为出色。刘艳认为,《呼兰河传》是典型的采取限知视角的限制性叙事,这既体现为成人视角(如小团圆媳妇婆婆),更体现在非成人的儿童视角“我”之上。她发现,通过儿童“我向思维”的引入,《呼兰河传》真正告别了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小大人”现象:“儿童视角的遭遇性、无规划、直接性、随意性和无目的性,反而更容易洞见成人世界的真实,对充斥于成人世界的荒谬、不合理处乃至人性的扭曲,别具一种透视和艺术表现的力度。”而在《上海舞男》中,刘艳也通过限知视角的分析发现了严歌苓的“计谋”所在:“没有什么比‘我’的‘看见’和叙述角度,更加能够带来现场的真实感了,还可以有效避免传统全知叙事的平铺直叙和对真实感的伤害。借助‘我’的叙述角度,严歌苓方能够自如开启她的‘五度’叙述空间。但叙述之难,也在于对于‘我’的叙述角度的叙事所占分量的拿捏,包括什么时候该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什么时候该自如切换到其他视角的叙述,这都是有着玄机和一定之规的。”这腾挪跳跃的叙述“玄机”,无疑隐藏着隐含作者理解世界的方法论。
而且,刘艳之于限知视角的叙事分析,还延伸到固定人物限制性视角和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之上。譬如,通过对《呼兰河传》中农业学校校长儿子掉水坑一事发生后呼兰人众口纷纭的议论的呈现,刘艳探究了转换性人物有限视角的叙事功能:这种有限视角虽然如西蒙·查特曼所言“并不解决任何特定的问题,也不展开一个因果链”,但“叙述人是贴着呼兰河这里的每个人物的感受去写的,叙述人、人物与隐含作者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水平发生了剥离,我们很明白作者、隐含作者对于农业学校校长儿子掉水坑子的原因,都不会是这些段落所呈现的这样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和道德评判标准”,由此“缝隙”,叙述更能客观呈现出中国荒芜的世相人心。而在对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固定人物有限视角的分析中,刘艳更流露出了难以抑制的艺术喜爱:“叙述人、人物与隐含作者、作者,都天然拉开了距离,人物的心理、思想意识、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等,都是人物自己的,人物绝没有充当隐含作者的传声筒,而且在这种距离拉开的叙述手法中,人物的真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和展现”,“整个事件的反讽意味和悲剧性并存,让人在对人物的理解之同情当中,又对小团圆媳妇的被虐待致死和施虐者不失朴拙但又愚昧并且兼具人性恶与各种人性复杂性之外还对自己所犯平庸之恶毫不自知,而感到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纠结与无力感,纠结与无力当中还对美好生命的被虐杀而倍感痛入心髓之痛,审美意蕴可谓繁富无尽。”《呼兰河传》的“文学性”何以具有如此久远而幽深的魅力,刘艳几乎作出了最佳的形式解读。
以上限知视角、叙事结构、隐含作者三项,是刘艳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三大分析“着力点”。此外,她对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分析,也很令人称道。不过,恰如贾平凹所言,刘艳这些“精耕细作”的大文,是不适宜“闲读”的,而应有端正之心、庄重而读。然而在刘艳自己,她恐怕并无把“学理性批评”写成高头讲章的兴趣。恰恰相反,她的叙事分析都出自丰富细腻的审美体验,她有关《呼兰河传》《妈阁是座城》《芳华》等作品的解读,实在又是旖旎生姿、温润动人的。果断清晰的逻辑,体贴入微的“同情的理解”,在她这里融冶一体、相得益彰。可以说,即使在批评文体上,刘艳也是存在自觉探索意识的。
当然,刘艳这些年的进步与成绩并不局限于叙事学分析,诸如女性意识、存在论意义上的孤独感,对先锋文学转型及其当下新的可能性的思考,对乡土小说与柳青传统的思考,对学理性批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对“70后”创作与批评的思考,等等,在她近期和以前的研究中也时有可见。无疑,她面对的是一个广阔而开放的学术世界。但多年以来,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叙事学”期之久焉,尤其希望觅求到将叙述视角、隐含作者、叙述者等经典叙事学概念融入广义的“实践叙事学”的途径,而这点“私心”,也构成了我习常研读刘艳叙事学批评的持久动力,当然也构成了我作为“同代人”对她未来的期待:以我目见,国内治现当代文学而又专精于叙事学者不过寥寥数位,刘艳无疑是其中年轻并充满希望的一位;未来的“中国叙事学”的形成,或许就在寥寥数人之间,对此,我抱以乐观态度。
注释:
[1][2][9][11][12]刘艳:《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3]刘艳:《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
[4][6][7][10]刘艳:《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
[5]刘艳:《诗性虚构与叙事的先锋性——从赵本夫〈天漏邑〉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方法》,《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4期。
[8]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