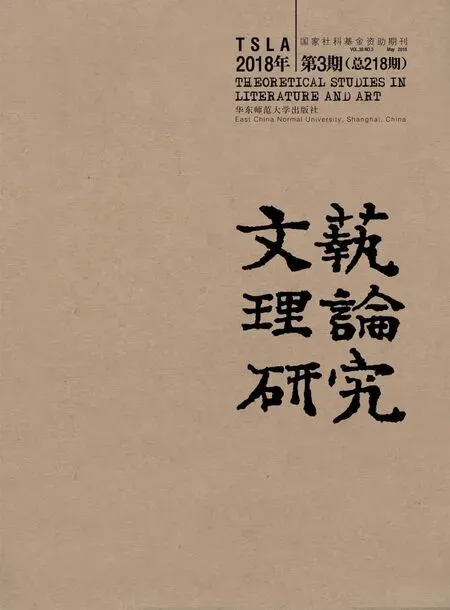时间与空间中的特殊性
——论格林布拉特著作中的历史主义精神
王 柱
一、历史主义的定义
要讨论新历史主义中的历史主义精神,则首先需要对“历史主义”这一名词作一概念上的厘清。提到“历史主义”,可能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名著《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在该书中,波普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历史主义”这一广泛存在于学术写作中的概念。在导言部分,波普尔便对他理解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作了明确的界定,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将历史预言作为主要目的的方法,它以可通过对历史演变中的‘规律’(或‘模式’)和‘法则’(或‘趋势’)的发现来达到这一目的为前提”(Popper 3)。不难发现,波氏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更接近于以黑格尔、斯宾格勒(Spengler)、汤因比(Toynbee)等为代表的所谓“玄想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派,而与之对立的英美历史哲学中的另一派则为“批评的历史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这二者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所注重的乃在于历史知识之成立如何可能,换言之,即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为真实不虚”,而前者“则注重历史事件之本身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并如何能解释全部历史进程为一必然之归趋”(余英时 235—37)。由此可见,波普尔所使用的“历史主义”以历史具有必然的规律为前提,且声称对这一规律的掌握使得我们可以对历史作出预测。这也就是上述玄想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中的所谓“全部历史进程为一必然之归趋”。
历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施密特(Frank Ankersmit)在其近著《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实和指称》(Meaning,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中着力于为“历史主义”张目,并试图将其用现代的学术话语进行重新表述。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便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对“历史主义”的理解有别于波普尔。在安克施密特看来,兰克 (Leopold von Ranke)、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著作也应被包括进历史主义的范畴,而“对玄想的历史哲学的摒弃为兰克和洪堡对历史主义的构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Meaning 1)。根据安克施密特的观点,历史主义实际上不仅应包括狭义的玄想历史哲学,而且应该有着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安氏随之阐明,其对于这一名词的理解为“认为某一事物的本质在于其历史的观点”(Meaning 1),更随即引用了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的论述来具体说明这一观点。大致说来,历史主义认为:对一事物的理解、认识不能与其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割裂开来,即不能将这一事物置于一个超越了历史时空的环境中,然后再去分析其结构或者特点,并认为这一结构或特点是永恒不变、具有普遍真实性的。与之相反,历史主义所提倡的是要到具体的某时、某地中去寻求事物的本质,因为它认为只有在具体的背景中人们才有可能把握住事物或现象的根本意义。如果说安氏对赫尔德、狄尔泰的引用给了读者对历史主义的宽泛定义的一个大概了解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对曼德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引用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定义。而为了准确把握其论点,我们在此有必要回到曼氏原书,在具体语境中考察此论点。
在其代表作《历史、人和理性》(History,Man,and Reason)中,曼德鲍姆追溯了十九世纪的主要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书中一个重要观点即为对历史的兴趣是十九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鲜明特点。曼氏认为:虽然人们常常将赫尔德、黑格尔等思想家与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系统间有着很多根本的不同之处,因此对历史主义的定义就需要将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找出来,而这些特点又需要足够精确,以与前人的思想区别开来,以标出本时期思想的独特之处。经过对上述种种因素的考虑,曼氏最后给出了他认为大致可以接近这一目标的定义:“历史主义是一个信条,它相信对任何现象的本质的准确理解和对其价值的准确评价需要考虑到这一现象在历史进程中所占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Mandelbaum 42)。将这一定义与波普尔的定义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波普尔所强调的“历史预言”和历史演变中的“法则”“规律”等因素并未出现于这一宽泛的定义中。而曼德鲍姆的这一定义则着重在于将现象置于一定背景中,离开了这一具体背景,则无法准确理解特定现象的本质,也无法对其价值做出正确的评断。当然,黑格尔等人的玄想历史哲学也主张将历史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只不过其最终归宿在于试图说明历史有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在其它形式的历史主义中,这一对必然规律的寻求则被摒弃了。因此,只有根据曼德鲍姆的这一较宽泛的定义,我们才能理解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在波普尔的著作之外的语境中的应用。
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指出:在对人进行定义时,人类学家之所以会避免探讨文化的特殊性,是因为他们都怀有“一种对历史主义的恐惧”、“一种害怕迷失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漩涡中的恐惧”(43)。不难发现,格尔茨所说的“历史主义”近于上文所述的曼德鲍姆的定义,都是一种突出特殊性而非共性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任何对事实的探寻都必须以尊重具体情况为前提,即必须考虑到现象在不同地域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唯有将现象置于历史中的具体位置之后,我们方能把握这样的一个现象对于整个历史发展的意义,也就能更为正确地理解它为何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产生。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格尔茨本人在其研究实践中所奉行的乃是一种“共时”(synchronic)的方法,而非通常意义的历史主义的“历时”(diachronic)的模式,他也不是历史主义者。格尔茨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历史主义,是因为其相信人类学家们将特殊性与历史主义联想到了一起,因而尽力要避免过多地探讨文化的特殊性,以免自己陷入历史主义或者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中。而之所以人类学家会有这样的恐惧,是因为他们和许多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一样,相信对特殊性的强调会导致研究结果只具有仅适用于某一特定时间和地域的“局部有效性”(local validity),而不能拥有“普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而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后者才是一个学科可作为真正的科学而存在的前提。
二、格林布拉特的历史主义精神:对抽象理论建构的摒弃
在对历史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定义进行总体的回顾后,我们对这一概念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而只有在具备了这种理解后,我们才能对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中的历史主义精神进行真正的讨论。虽然在历史学传统中,历史主义最初是用来指代十九世纪的史学著作和深受其影响的某些二十世纪史学家(如克罗齐、科林伍德等)的研究理念,但以这些史学研究为范例的精神却仍在今天存在着——虽然其具体形式可能已改变。正因为此,保罗·汉密尔顿(Paul Hamilton)才会将新历史主义称为“在今天最有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义批评实践”(Hamilton 130)。在二人合著的《实践新历史主义》(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一书的引言中,格氏与凯瑟琳·加拉赫(Catherine Gallagher)回应了某些学者对于新历史主义缺乏对理论的成熟建构的批评,并指出:二人都对“应该构想出一个抽象的系统再将其应用到文学文本中”的说法表示怀疑,且对“去建构这样一个独立于我们自身所处的时间、地点和我们所感兴趣的具体对象外的系统”的可能性也持有相同态度(3)。显然,从这一宣言来看,不管是加拉赫还是格林布拉特,都秉持将考察对象置于一定时间和地点中的历史主义精神。职是之故,二人都很难同意应该去建构一个抽象的、超脱于具体历史位置之外的系统的观点。而格林布拉特在自身的写作实践中,则充分地诠释了这样的精神,即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中,我们应该建立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发现贯穿于其著作中的便是一种不断在具体探索中得到结论的精神。
首先,与其他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一脉相承的是,格氏也常在著作中探讨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或历史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如在《摩擦与虚构》(“Fiction and Friction”)中,他就试图讨论文学写作和医学写作的关系。文章一开始便直指主题地叙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十二夜》的情节,指出剧中人物先有可能遭遇一个“危险境地”:即婚姻双方性别相同且本属于不同社会阶层。而在一系列阴差阳错后,这些在当时无法被接受的“丑闻”又巧妙地得以被避免。随后,格氏又以轶闻的形式讲述了医生雅克·杜瓦尔(Jacques Duval)书中关于变性人马兰(Marin le Marcis)的故事。故事中的马兰本名为玛丽(Marie),在此前一直是以女性身份生活。在与一位名为珍妮(Jeane)的女性一起时,马兰向对方坦露自己其实本为男性,随后又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与其同居,并发生了关系。之后二人试图以举办婚礼的形式获得世俗认可的夫妇身份,却遭到逮捕并差一点处以重刑。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专业鉴定后,马兰的男性身份得到证明。而根据当时一般的法律程序,马兰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终生不得改变的性别。在结束了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马兰的故事的分析后,格林布拉特指出马兰的故事的诸多主题,如一段公开后会让主人公遭受生命威胁的恋情、聚焦在变装上的身份的混淆等,实际上也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主要情节,而这二者的相似更绝非偶然。格氏随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存在于医学实践和戏剧实践之间的联系“不是因和果或者来源和文学表现的关系”,而是“一种共享的准则,一系列紧密连接的转义和比拟,这些转义、比拟不仅充当着表现的对象,更是作为其条件”(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86)。格氏所要说明的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之所以充满着这些医学实践中的主题,并非是因为莎士比亚受了医学写作的直接影响,而是由于“紧密连接的转义和比拟”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得二者具有相似性。正如克莱尔·柯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所言,新历史主义所信奉的是:“文本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不能由一个预先想定的理论给出;相反,文本和世界之间、文本的物质性和其所创造的意义之间以及艺术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成为每一个批评实践的调查对象”(26)。在此处格林布拉特所提供的便是关于文本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具体实例:莎士比亚的剧作和(见于医学写作的)医学实践之间的联系。二者由某种准则、某种转义和比拟联系在了一起,这些转义、比拟不仅在戏剧和医学的表现中作为被表现对象出现,它们更是决定了这些表现能得以被实现的条件。
接着考察另一个关于文本与世界的关系的例子:在第一部重要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中,格林布拉特通过莫尔(Thomas More)、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怀亚特(Thomas Wyatt)等的事例,以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对自身的塑造为主题,详细地讨论了文本、人、社会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如在关于丁道尔的部分中,格氏就探讨了这位宗教改革家的圣经翻译对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在丁道尔生活的十六世纪早期,社会对于体制和他者的定义正在发生改变,而这些定义则决定着人对自我的塑造。丁道尔认为包括主教和枢机主教等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国王的臣民,并通过将圣经新约翻译成英文和呼吁从字面上来理解经典,有效地削弱了本为教会所独有的对经典的解释权。这一系列活动的后果则为:社会公民原本对教会的认同和对教会以外的机构的怀疑都发生了变化。而因为公民对身份的塑造本依赖于其对自我、他者的定义,原本稳固的认同一旦发生变化,身份塑造也会随之而变。由此看来,丁道尔的翻译就绝非仅是单纯的文学实践,其对社会现实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丁道尔的自我塑造也在其实践中得以完成:其自身转变为了圣经中上帝的声音,这也象征了从个人主义到一个更宏大的确定性(即在上帝中找到自身的主体确定性)的转变(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111)。因此,在此处格氏向我们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圣经的翻译的双重社会影响——即其不仅对社会中的人,也对译者自我的塑造发生了影响。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作为文本的英语版圣经之间已非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实是一种有机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
三、历史纵深与空间扩张间的对立
上述的两个例子都很好地例证了格林布拉特的一个基本态度——即拒绝抽象理论建构而倾向于在具体实践中发现结论,而这和历史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中获得意义,且在不同阶段会扮演不同角色的观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不过,颇有论者指出格林布拉特对于社会现实的描述仿佛更加着重于社会的宽度,而忽略了对历史纵深的探求。如在其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读本》中,哈罗德·维瑟(Harold Veeser)便借用了莫顿·怀特(Morton White)的历史主义和“文化有机主义”(cultural organicism)这一对概念,指出新历史主义“让其有机主义削弱了其历史主义”(Veeser 10)。
同样,要准确理解怀特的概念,很有必要回到其原文。在其出版于1949年的著作《美国的社会思想:对形式主义的反叛》(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中,怀特便在紧接在引言后的章节里追溯了美国思想史上对于“形式主义”的反叛,并指出由杜威等主导的这场反叛带来了两大思想上的积极因素,即上文提到的两个概念。怀特更随即给出了他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我所说的‘历史主义’是指试图通过以前发生的事实来对事实进行解释;而我所说的‘文化有机主义’则是试图在社会科学而不是在首要考察的对象中来寻找解释和相关材料。历史主义向过去回溯以期说明某些现象,而文化有机主义者则将触角伸及其身边的整个社会空间”(12)。然而,如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对思想史上人物的“刺猬”(即用一总持的理念去解释一切)和“狐狸”(拥有很多不同且时不时互相矛盾的信条)的划分一样,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且在同一个人身上大可以兼而有之:柏林之所以写作本文就是想说明托尔斯泰从根本上说是一只“狐狸”(他的天赋是“狐狸”型的),却信奉“刺猬”的信条,并将自己诠释为了“刺猬”型的人物(Berlin 4)。在借用柏林的概念去分析戴震与章学诚两大思想家时,余英时也相信原本只有很少纯粹的“狐狸”和“刺猬”,一般人都是兼有这二者的特征(余英时 95)。而怀特也认为多有在同一人身上兼具“历史主义”和“文化有机主义”的例子(Morton White 13)。然而,如维瑟所言,格林布拉特的“历史主义”相比于其“文化有机主义”仿佛不甚明显。如在《隐形的子弹》(“The Invisible Bullets”)中,格氏以“测试”(testing)、“记录”(recording)和“解释”(explaining)三种策略作为主线,将英国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殖民统治与莎士比亚的“亨利国王”系列剧以及作为莎剧历史背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格氏将远隔重洋的殖民统治与在英国本土的戏剧表演及君王的统治融为一炉,可谓颇具广度。然而,从历史纵深上看,格氏却并没有阐述这样的一种策略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有呈现不同的面貌。如此看来,维瑟等学者的批评应是不无道理。
然而,格林布拉特对于事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是否就真是付之阙如了呢?在《社会能量的流通》一文中,格氏试图分析艺术作品为何可令人产生喜悦或焦虑。格氏进一步提到自己希望能够了解这些艺术品是怎样被赋予令人动容的力量,而可以在时隔几个世纪后仍让读者和观众感受到这种力量。接着,格氏论述道:“这是否说明像《李尔王》这样的剧作的美学力量是从莎士比亚时代直接传送到我们的时代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一剧作及其原本置身的环境一直以来都在持续地改变着,而且常常有极大的改变”(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6)。格氏对于在历史进程的同一事物的不断演变的看法在此处得以言明,这也是一种和历史主义相一致的态度。不过要指出的是,一旦对事物的演变中各阶段的不同进行过分夸大,则作为考察对象的事物就会变成一系列碎片,而无法维持其作为一个整体在演变中始终为同一事物的地位。因此安克施密特提到:“在这里采用的对历史主义的定义必然包含了对历时性的暗示,而这一历时性则会使得某一历史实体在其历史中所经历的一系列连续性阶段相互间脱离开,从而导致共时性产生”(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133)。换言之,如果对不同阶段中的同一事物的不同进行过分强调,则该事物很难再被视作是同一事物了。专注于描述事物在某一阶段的特殊性不仅可能使历史断裂为一个个分离的阶段,更有可能导致研究者的考察工作停滞于同一时期,从而演变为一种共时性研究。上文所引的格尔茨对特殊性的倡导恰可以说明其人类学研究为何表现出鲜明的共时性特征。
格林布拉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接着指出: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作者和其所处的文化消亡很久后也仍存在,这一“生命”就是“一开始编码进这些作品中的社会能量的历史后果”,不管这一后果“如何转变和如何得以被重新塑造”(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6)。格氏在这里强调了,虽然经过持续的且常常是巨大的改变,文学作品的“生命”这一实体仍然贯穿于历史中,也由此避免了把这一整体的每个发展阶段割裂开而成为碎片的命运。而在访谈中,格氏也曾表明自己“越来越努力地将文化流动性(cultural mobility)这一现象实际上是什么理论化,某个事物怎么可能从一个地域和时间移动到另一时间而能够保持某些文化身份,或者仍旧能与其始源力量保持着某种关联。”
尽管格氏时时表现出对历史进程的注意,其在具体实践中却往往更专注于向空间的广度延伸,而非追溯历史的发展演变。如在上文提到的《隐形的子弹》《虚构与摩擦》等处,格氏用政治策略和聚焦于变装的身份混淆等主题,将原本很难发生关系的三者——即莎士比亚剧作和当时英国的政治历史现实以及远在重洋外的殖民地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其丰富的想象力令人印象深刻,而其对包括纪实文档在内的文本的深入细读也有令人击节之处。不过在其文学批评实践里,格氏对这些策略或主题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表现是否有不同却的确鲜有考虑,而更多着力于对相似性的描写。在总纲性文章里对历史进程中的演变的考虑如同昙花一现一般,让读者在具体批评中便难觅其踪迹了。
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不可分割
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一文中,格氏对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两大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作了分析和评论(2—6)。首先,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将美学领域与其它社会领域分开,从而将其“私人化”,从而损害了我们对于时间和变化的思考。与之相反,利奥塔认为,通过对一种单一的语言和网络的使用,资本主义试图把种种名称从历史和地理中驱逐出去。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不管是詹姆逊还是利奥塔的理论都失之于无法“接受资本主义的明显相互矛盾的种种历史效应”(5)。对格氏而言,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单一性的邪恶原则”,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在其中对社会的划分和对其向单一性的推动是同时发生(或者在二者间摇摆得极其迅速,以至于给人以同时发生的印象)的(6)。正是对这一复杂性的关注,使得格氏对发挥总纲性作用的宏大理论建构持有保留态度。格氏曾对自己理解的“传统历史主义”或“旧历史主义”提出商榷:在他看来,旧历史主义“倾向于单一化,即关注于发现单个的政治愿景,而这一愿景与被认为是整个知识人阶层或所有人所共同拥有的愿景通常是一致的。”格氏所理解的旧历史主义的特点就是将历史单一化,从而将历史的复杂性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单一图景。
格氏对于旧历史主义的描述的矛头自然是直指提利亚德(E.M.W.Tillyard)。这位著名的批评家在其代表作《伊丽莎白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中提到:“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用三种主要的形式来描绘宇宙的秩序:一条链,一系列相互对应的平面和一场舞蹈”(Tillyard 25)。随后提氏分别论述了这三个形式的历史:如在关于巨链的部分中,提氏就提到这一观念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到中世纪以至于十八世纪的传播,并通过斯宾塞、莎士比亚等人的具体作品来例证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地存在(26—36)。提氏的主要观点即为:这三种形式自从其诞生起便长久而广泛地存在于知识人的观念里,而他所分析的文本都是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提氏所强调的为某一观念在历史演变中仍然保持的一致性,而并未考虑到即使是同一具体时期也存在着种种的复杂性。因此,对于更倾向于福柯式的“新史学”的格林布拉特而言,这样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自然是很难令人接受了。并且,提氏甚至提到“在这里发现的对于存在之链的说明一定是十六世纪的欧洲共同财富”(27)。这也与格林布拉特在描述旧历史主义时提到的“单个的政治愿景”这一概念若合符契。也就是说,提氏将自己的观念想象为一种客观存在,以为这个观念是当时的所有知识人共同持有的,而提氏所引用的作品则都是这样一种观念得以形诸笔墨的例子。
关于对连贯叙事的建构和在具体时空点上探寻的两种方法的对比,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的策略》(“Formalist and Contextualist Strategies”)一文中有详尽而系统的讨论。怀特将这两种策略分别定义为:“努力去建构对社会形式和过程的形式上的整体表现”和“努力对具体时间和地点语境中的社会现象做出诠释般的理解”(44)。而怀特随后通过对语境主义的分析,指出由于其将对科学的构想视作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占主导的社会文化状况的一种功能,语境主义体现为了某种历史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时,由于社会学家渴望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超越具体语境的(即上文中提到的“新康德主义”式的)知识,因此其对于这样的一种语境主义的策略总是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偶尔以语境主义的形式表现出历史主义动力的时候,这种动力都是以结构主义(struturalism)而不是源流主义(geneticist)的形式出现的。怀特随之作出解释:源流主义以社会文化语境和在其中存在的实体间的因果关系为前提,而结构主义则只是以社会文化整体中的所有因素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为前提。社会学家在研究中所采取的结构主义的语境主义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语境主义,而有着对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间的矛盾进行“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ing)、“去历史化”(dehistoricizing)的特点(47—48)。此处怀特的观点与上文中引到的格尔茨对于人类学家避谈文化特殊性的做法的批评一致,都同属对倾向于做整体结论的形式主义的诘难。
不过,在怀特看来,格尔茨本人的研究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表现:即其研究能详尽分析社会中一切因素,却不能说明其社会意义(48)。而如果仔细分析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我们会发现其似乎更偏向于结构主义而不是源流主义。如上文提到的格氏对于医学实践和戏剧实践的关系的阐述所示,格氏要建构的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这二者作为社会现实的两个因素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即二者通过共同的准则联系在了一起。格氏之所以会避免建立这样的因果联系,大概是因为其对于传统的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等同于对历史的反映的做法抱有怀疑态度。格氏曾在著作中列出词典对于“历史主义”的定义,更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多数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都坚定地反对这些立场”(Learning to Curse 220)。然而,正如于尔根·皮特斯(Jürgen Pieters)所说,格氏并没有必要将历史主义全盘否定。毕竟,这一概念是如此地指代不清,它能包含兰克等人的史学,也包括黑格尔一派的玄想历史哲学。
在今天,历史主义这一名词含义颇为广泛,它能指代所有将事物置于一定时间空间中去考察其特征的做法。而格氏的许多观念,如对脱离具体语境的理论建构持保留态度等,恰好为历史主义这一本身就具有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概念作出了新注脚。正如皮特斯讲到的那样,通过将过去建构在史学家的史学写作层面而不是历史真实的层面,格氏的新历史主义将历史主义从兰克、洪堡等人的“形而上的现实主义”(metaphysical realism)中拯救出来,实际上是一种“更新的”“更真实的”历史主义,一种安克施密特所说的“叙事历史主义”(narrativist historicism)。因此,在皮特斯看来,格氏对于自己的写作完全不属于任何形式的历史主义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总体来看,虽然格林布拉特不能接受那种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历史主义的说法,但他的批评著作却时时体现出一种历史主义的精神。虽然在具体实践时,格氏的方法偏向于在空间维度上的积极扩张,而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中的回溯和探究则不是那么明显。然而,如上文所示,在对其批评理论的总纲性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格氏对于事物在历史发展中的进程也有着自己的考虑。不管格氏的新历史主义是否如皮特斯所言是一种更新的历史主义,或者是否如安克施密特认为的那样在所谓新、旧历史主义间并没有什么重要而有意义的分别,格氏的新历史主义都与历史主义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虽然格氏对理论的系统性建构持保留态度,但是在批评实践中其对于方法论的强烈自我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大概是受波普尔的名著的影响,在英语学术界“历史主义”一词有时会给人可怕的联想。因为对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并无完全了解,格林布拉特始终不愿与其有任何联系。尽管如此,如本文所示,格氏的著作时有历史主义的痕迹出现——虽然这种历史主义精神并非在其文字里“一以贯之”,而仿佛总是在一些断裂处如弗洛伊德式的口误般表现出来。格氏的新历史主义与现在使用的定义较为宽泛的历史主义,实是不可能分割的。如果我们不将“历史主义”这一概念限定于波普尔的诠释,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就不必持有格尔茨所说的那种对历史主义的“恐惧”了。
注释[Notes]
①此书在中文中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辑、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翻译。这里要指出的是,波普尔使用的historicism,意义上比较接近历史决定论,即西方学术语言中常用的historical determinism。而波普尔用了另外一个词(historism),来表示把社会科学学派等与某个历史时期的偏好联系在一起以解释这些学派之间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见Karl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7.)。然而,波普尔对于historicism一词的定义在英美学术写作中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如汉密尔顿(Paul Hamilton)提到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的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时,仍将其译为The Rise of Historicism,而梅尼克所讲的也不是波普尔的 historicism(见 Paul Hamilton.Historicism.26.)。而如下文所示,曼德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等人所用的historicism一词也与波普尔不同。关于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参见 Georg G.Iggers.“Historicism: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Ter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56.1(1995):129-52.
②参见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1-2.
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主义在德国遭遇了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的挑战。争论焦点即为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历史主义不能提供超越时空的绝对道德真理,因此无法对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类发挥指导作用。参见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5.
④参见Georg G.Iggers.“Historicism: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Ter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6.1(1995):129-52.
⑤参见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21-65.
⑥这里安克施密特使用的是historism而非historicism,然而在《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实和指称》一书中关于historicism的讨论中,安氏也提到同样的问题,并在注释中标明请参看此处关于historism的部分。参见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10.这也说明,虽然安氏曾建议分别使用historism和historicism来指代以兰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两种风格的历史著作(Frank Ankersmit.Aesthetic Politics: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375-76),但在后期的写作中其对这两个名词至少是没有进行严格区分的。
⑦参见《智性的拷问-当代文化理论大家访谈集》中关于格林布拉特的部分。生安锋编著:《智性的拷问-当代文化理论大家访谈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79页。
⑧ 参见 Stephen Greenblatt.“Introduction.”The Forms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Renaissance.Ed.Stephen Greenblatt.Special Issue of Genre5.1(1982):5.此处转引自 Jürgen Pieters. “New Historicism: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Narrativism and Heterology.”History and Theory 39.1(2000):25.
⑨在福柯看来,以往的史学都竭力避免“非延续性”在历史中出现,而在当今的史学中它却已然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要素之一”。参见 Michel 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A.M.Sheridan Smith.New York:Random House,2010.8.
⑩ 参 见 Jürgen Pieters. “New Historicism: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Narrativism and Heterology.”History and Theory 39.1(2000):23-27.
[11] 参见 F.R.Ankersmit. “An Appeal from the New and the Old Historicists.” History and Theory 42.2(2003):269.安克施密特在这篇文章中论证了格林布拉特对于传统历史主义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在传统历史主义中,对于战争、意识形态上和宗教的斗争的描写也能被找到。因此我们不能说传统历史主义就是只有“单一愿景”而没有对历史的复杂性的关注。在安克施密特看来,格氏对于传统历史主义的不熟悉才导致了他看到新、旧历史主义间的本不存在的区别。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nkersmit, Frank.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
Colebrook,Claire.New Literary Histories:New Histor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Gallagher,Catherineand,and Stephen Greenblatt.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Geertz,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New York:Basic Books,1973.
Greenblatt,Stephen.Learning to Curse:Essays in Early Moder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07.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 “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Ed.H.Aram Veeser.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1-14.
Hamilton,Paul.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1996.
Mandelbaum,Maurice.History,Man,and Reason: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
Popper, Karl.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57.
Tillyard,E.M.W..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New York:Random House,1959.
Veeser, Harold. “The New Historicism.”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Ed.Harold Veeser.New York:Routledge,1994.1-33.
White,Hayden.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White,Morton.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Yu,Yingshi.On Dai Zhen and Zhang Xuecheng.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