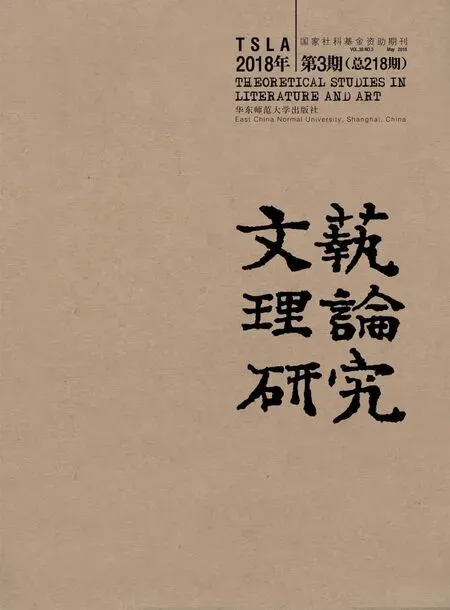“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
——从阿甘本到青年马克思
王行坤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论(Science Studies)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推进,在自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都出现了所谓的posthuman转向。这就决定了posthuman的内涵是多元的,因此在汉语学界的翻译也不可能统一:一般有“后人类”“后人文”以及“后人本”等用法。本文在细致辨析posthuman的多元内涵之后,会着重处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区分问题。阿甘本对“动物问题”的处理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以及阿伦特等思想家的影响,针对的是政治领域中人如何沦为动物的机制——“人类学机器”,这似乎与 posthuman的问题域关联不大。
但本文要强调的是,阿甘本关于人的动物化论题在当下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揭示了人本主义的虚妄——我们从未人类过(we have never been human),现代以来人类生命越来越动物化,越来越贫乏,但阿甘本那种囿于政治和哲学的非历史化的思考不可能真正叫停“人类学机器”,并且达成人性与动物性的和解。本文旨在回到青年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对人的动物化所进行的思考,重新阐释其“类本质”的概念,旨在提出一种真正达成人性与动物性和解、从而真正解放生命的生命政治。
一、posthuman研究的三种路径
本文之所以保留posthuman的英文形式,是因为这个词的汉语译法不一:有翻译为后人类主义、后人文主义、甚至是后人道主义。这也反映了这个术语内涵的复杂多元性。
posthuman的译法虽则众说纷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posthuman的哲学社会内涵,以及相关的文化与自然、人与非人(自然、技术、动物)、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一般认为关于posthuman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路径,如“动物研究”的领军人物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所指出的:一是福柯在《词与物》中对人之死的宣告;二是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发明,人类在意义、信息和认知的问题上等同于系统模型(Wolfe,What is Posthumanism xii)。前者可以说是遵循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而产生的哲学上的后人本主义思想;后者是基于科技进步认识到的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从而产生的后人类主义思想。而在生态思想家露易丝·韦斯特林(Louise Westling)看来,后人类主义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美国科学论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文学批评家N.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的技术或赛博格后人类主义(techno or cyborg posthumanism),探索的是人类与技术的共生;二是德里达、哈拉维和卡里·沃尔夫为代表的词语动物后人类主义(animotposthumanism),研究的是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与我们的伴侣物种的交互关系,旨在解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25—47)。另一位论者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提出了posthuman研究的三种取向:第一种来自于以纳斯鲍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后人类境况的回应性(reactive)研究;第二种源于科学论对人和生命的地位的反思,其代表人物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布拉伊多蒂看来,这是posthuman图景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第三种源于反思主体性哲学采取的具有反人本主义立场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38—54)。因为纳斯鲍姆秉持的是一种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立场,所以并不能将她归入到posthuman研究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posthuman研究主要是两种路径:一种是从科学论的角度出发,反省人类——到底何为人类,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的研究,我们可以将这种取向称为后人类主义研究;另外一种是从哲学角度出发,来反省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尤其是从动物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与动物关系,最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要属德里达的研究(Derrida,The Animal),我们可以将这种取向称为后人本主义的“动物研究”。
但我们要提出第三种研究路径,那就是阿甘本从西方哲学的内部,从人在政治和法律上沦为动物的现实境况,来反省人本主义(“人类学机器”)的研究。我们会通过第三种路径,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动物以及类本质概念,来探索解放生命、实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和解的真正途径。
当然这三种路径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质疑人的中心地位。
科学论视野下的后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拉图尔和哈拉维等,前者用超越人与非人的行动者(actant)来取代专指人类的行动者(actor),在本体论层面消除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是一种本体性混合的状态。皮克林对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我们应该把科学(包括技术和社会)看作是一个人类的力量和非人类的力量(物质的)共同作用的领域。在网络中人类的力量与非人类的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对称的,两者不互相逊,平分秋色。任何一方都是科学的内在构成,因此只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11)。在拉图尔等人看来,自然以及实验室的仪器都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参与到了对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自然所为、仪器所为、科学家所为彼此交织、相互强化,三者地位等同,没有预先存在着主次、先后(邢冬梅 毛波杰 13)。
哈拉维虽然也属于科学论的阵营,但是她更多是从女性主义和社会的视角来看待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哈拉维用赛博格(cyborg)——即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来解构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自然与非自然等传统二元对立。随着技术的发展,外界的技术越来越渗入甚至是融入到有机的身体中,从而打破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界限,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赛博格。正如哈拉维所写:迄至20世纪后期——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成为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赋予我们政见(Haraway,Manifestly Haraway 7)。什么样的政见呢?那就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即人和动物严格界限、超越男性与女性界限的后人类和后性别的政治。虽然哈拉维并没有使用posthuman这个词,但她解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努力,质疑人的纯粹性的做法无疑与后人类思想是一致的。
可以看出,这种取向的posthuman研究旨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因此我们将其翻译为后人类主义研究。有论者甚至认为,人类其实从最开始就与技术共同进化,技术一直内嵌于人类的生活中,因此就像拉图尔所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样,我们也从未人类过——我们天生就是赛博格(Clark 3)。
另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身体和智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因此在技术和思想领域中出现了超人本主义(transhumanism)的取向。这种取向其实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的无限完善性等观念,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在心灵和身体上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从而成为外在自然与人类自然(生命)的主宰。被视为“文艺复兴宣言”的《论人的尊严》可以说最好地体现了超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帝对人类的代表亚当说:
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抉择决定你的自然,我们已把你交给你的自由抉择。我们已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你更容易凝视世间万物。[……]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型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米兰多拉 25)
超人本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技术乐观主义色彩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在追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后指出,“超人本主义的根在理性的人本主义那里”(2)。或者正如如卡里·沃尔夫所说,应该将超人本主义视为人本主义的强化(What is Posthumanism xv)。超人本主义并没有质疑解构人本主义,只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推进了人本主义思想,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从科学论角度研究后人类主义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但汉语学界有研究者却混淆了这两种思想,将超人本主义也视为后人类主义的组成部分。
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视角下的“动物研究”因为哈拉维和德里达的开创性著作而成为后人本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旨在消解以人类为至高无上(sovereign)存在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这种观念认为除了人类之外,其他动物不应该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人类对其他动物并没有道德责任。
德里达正是从边沁的“动物是否会感受到痛苦”问题出发,来论述人类对动物的道德责任。在德里达看来,动物保护主义者对动物权利的探讨仍植根于传统哲学话语中,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与动物的关系(庞红蕊,“德里达”36)。德里达的立场更为激进:他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出发——自己赤身裸体面对一只猫,认为动物(一只猫)也可以引起人类(德里达)的伦理回应。因此对德里达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吃不吃动物的问题,而是哪些杀戮算罪行,哪些不算。德里达就这样解构了动物不具有伦理道德能力的观念,从而解构了人类主体与动物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同时,如注释④所言,德里达也解构了动物的一致性和单一性,强调动物的杂多性和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这可以说是德里达“未来民主”(democracy to come)思想的应有之义,那就是将包括动物在内的绝对他者都包纳进来,从而形成一个更好、更包容的共同体。
哈拉维则使用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来强调人与动物之间一直以来的共同居住、共同进化关系。在哈拉维看来,人与动物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两者都处于生成之中,且是与……共同生成(becoming with)(Manifestly Haraway 221)。
当然,这种后人类主义思想与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中的反人本主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很多理论家也承认这种传承关系。但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解构人的中心地位和永恒人性,而前者主要从技术的角度认识到,人从来就不是人本主义所规定的人,因此也要将非人要素(技术、动物、自然)纳入到伦理和政治的维度中。
最后是“例外状态”下的人的动物化研究。在后人类/人本主义看来,“我们从未人类过”,也就是说,人类主体总是去中心化、与外界的技术、动物和自然共同生成的,我们应该积极接受这一现实;但另一方面,阿甘本却忧虑甚至绝望地告诉我们,人类从来就有沦为动物之虞,这似乎是更为现实且危险的处境。
阿甘本并不属于典型的后人本主义“动物研究”领域,因为他主要还是从人的生命状况出发,来考察当下日益普遍化的例外状态。但阿甘本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阿伦特和福柯等人的解读,系统梳理了当下人类生命动物化即人沦为非人的困境。如果说哈拉维和德里达是从生物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来反思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解构物种主义,建构一种更为“人性化”和民主化的物种间关系——两位思想家没有明言的是,人本主义对待动物的方式会将殖民地、欠发达地区的他者动物化,正如卡里·沃尔夫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在制度上想当然地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可以因为非人类动物的物种而系统性地利用和杀戮它们,那么关于物种的人本主义话语就可以用来支持某一部分人残害另一部分人,用来支持对无论什么(whatever)物种或者性别、种族、阶级以及性差异中的社会他者施加暴力(Wolfe,Animal Rites 8)——那么阿甘本则是从哲学与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政治如何将某些人类动物划归入动物的范畴,从而使其沦为“赤裸生命”。因此今天我们固然要思考人类对于动物的伦理责任,但我们要认识到,解构物种主义的后人本主义动物伦理并不能让我们摆脱沦为动物的命运,因此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生命政治,或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的分离
在后人本主义的“动物研究”看来,是人本主义话语以及相关的物种主义制度(institution of speciesism)造就了动物被宰制的地位,而这种宰制关系有可能造成人类中的某些他者(如有色人种、异教徒、女性或者性少数等)也被动物化,从而也沦为被宰制、甚至被消灭的地位。但是如果说后人本主义的动物研究关注的是人本主义思想所确立的人与动物的边界如何造成了某些人的非人(动物)化,那么阿甘本则通过追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如何因为区分人类内部的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而将某些人类划入到动物范畴,从而造就杀人行为的非罪化。正如阿甘本所指出的,在我们(西方,笔者注)的文化中,主导所有其他冲突的决定性的政治冲突是人类内部的动物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西方的政治从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Agamben,The Open 80)。
生命政治在福柯那里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具体指的是西方18世纪出现的权力技术——福柯也将其称为生命权力,因为权力不再只关注个体生命(这是规训权力的任务),而是作为整体的群体,即人口,以人口的福利为旨归,其操作手段由人口统计学负责,来对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进行规划。现代权力不是直接的压迫性权力,它通过优生优育等人口政策来对生命进行组织,通过社会机构对群体进行管治,从而取得更为深入的渗透。这是一种“主动使人活”的权力,但正如后来相关的理论家所指出的,这种权力与死亡权力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福柯早已指出: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93)。言下之意,生命政治的存在势必让某些生命成为不合时宜的存在,因此他们的生物性存在要受到威胁。
阿甘本从这个论述得到启发,追溯古希腊以来的政治哲学观念,发现早在西方文化的开端就已经出现生命-死亡政治的机制。西方政治之所以从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其原因在于政治的主权必然要决定例外状态,于是出现主权禁令(ban)将某些人抛弃,褫夺他们的政治生命,让他们只剩下岌岌可危的生物生命,从而成为赤裸生命(即福柯所说的生物性存在受到威胁的生命)。这些人并没有被抛出城邦之外,因为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邦,但是城邦的任何法律对他们都失去效力。相应地,他们失去了法律的保护,成为赤裸生命,在“野外”孑然一“身”地去面对神祇。在属于神的意义上,他们是神圣的;而在其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施加暴力的意义上,他们又是被诅咒的(damned,accused)。这种机制既是排斥——排除在法律之外,同时也是吸纳——限制在城邦内,这正是通过主权例外来实现的。所谓例外,不是简单的排斥在外,而是带出(taken outside,ex-capere),在排斥的同时,也有吸纳。
他(那些被排斥在法律之外的人——引者注)的整个存在被化约为赤裸生命,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人人都可得而诛之,而没有犯法之虞;他只有不断地流亡或去国离乡,才能存活下去。但是他与那个将他放逐的权力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是纯粹的生物生命(zoe),但是他的生物生命本身又为主权禁令所掌握,必须时时刻刻面对这个主权。(Agamben,Homo Sacer 183)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西方哲学传统将人类生命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zoe和bios,前者指的是自然的、生物性的生命,在古希腊是在家庭(oikos)内的生命;后者指的是政治性的、质性的生命,即不是单纯为了活命而存在的生命,在古希腊是城邦(polis)内的生命。城邦是人作为复数性的独一体(singularity)在其中展示自我的公共空间,是人们进行交往协商的场所,换句话说,这是追求善与正义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古希腊的奴隶属于前者,而公民属于后者。但公民作为生命,也会因为犯罪而被褫夺政治生命,从而成为生物生命,阿甘本引了公元2世纪古罗马文法学家庞培·菲斯特斯(Pompeius Festus)的一段话:
牲人就是因犯罪而受到人民审判的人。这种人不能被用于献祭,但是杀他的人却不会因为杀人罪而受到惩罚;事实上,在第一条护民官制定法(tribunitian law)中就可以注意到,“根据平民制定法(plebiscite),如果某人杀了牲人,并不算是杀人。”这就是为什么按照习惯,会把坏人或不洁之人称为神圣的。(Homo Sacer 71)
阿伦特在分析集中营和难民营中所造成的纯粹存在时,认为这些难民因为失去了民族国家的保护而失去公民权,进而彻底丧失人权——人之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于是人被逐出了人类(humanity)之外,这“比起古代和中世纪的放逐习俗来,后果要严重得多。放逐(当然是‘史前法律能造成的最可怕的命运’)判定,犯法之人的生命可受到所遇之人的任意处置”(“极权”396,译文有改动)。也就是说,当难民失去公民权即因为政治生命而带来的权利时,其因为生物性的自然生命而带来的人权也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从而沦为赤裸生命。阿甘本正是沿着阿伦特的思路分析了纳粹集中营的穆斯林,并且认为现代人的生命随时可能被主权权力所捕获,从而造成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的分离。例外状态随时都可能出现,集中营成为现代(生命)政治的范式,“我们几乎全部都是神圣人(homines sacri)”(Homo Sacer 115)。
三、人类学机器,或人的动物化与动物的人化
阿甘本用生命政治解释了某些生命如何沦为赤裸生命,在他后来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中,则借用“人类学机器”的概念来分析某些人如何被动物化。在阿甘本看来存在两种人类学机器,现代的与古代的,前者将人类内部的某些群体作为非人类的排斥出去,也就是说,将人类动物化,将人类内部的非人要素隔离出去:不会说话的哑人(homo alalus)或猿人,例如犹太人就是人类内部制造出来的非人,或者脑死亡与过度昏迷的人,他们是从人体内部分离出来的动物;后者与前者具有对称的机制,通过吸纳外部来生产内部,通过动物的人化来制造非人,例如人猿,野孩子,愚人(homo ferus)(林奈指认的几乎不具有人类智能的人种,笔者注),但首要的还是奴隶、野蛮人和外邦人,这些都是以人类形式出现的动物形象(The Open 37)。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甘本的研究与后人本主义的动物研究之间的殊途同归:两者都认识到,因为现存秩序的排斥性吸纳的机制,绝大多数人类“从来都没有人类过”(Calarco,Thinking Through Animals 64)。但阿甘本认为这种排斥性吸纳的机制源自于主权暴力,而后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人本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并且认为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从而走向后人本主义就可以走出这种困境。例如有些理论家认为,更为民主开放的人与动物关系会导致更为民主开放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反思人的动物化的根本是要更人性化地对待动物。但这是成问题的推断。例如纳粹德国有非常完善的动物保护法案,而纳粹在道德上将动物提升至很高的地位,并且主动认同它们,结果就是人的动物化。纳粹受到尼采“金发碧眼的野兽”的观念的影响,因此推崇人类的动物根源和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充满生命力的人类动物和动物都受到推崇,即凡是充满生命力的动物都是健康的、高尚的。因此很多纳粹领导人都呼吁要回到与动物相亲近的前基督教的野蛮人状态,而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的虚弱的人类,纳粹则欲除之而后快(Arluke 138-40)。
当然,在尼采那里充满生命力意味着对此在世界的肯定,意味着主动的力量(active forces),而非受动性的(reactive)力量,前者意味着主人的、健康的、强大的行为方式,后者意味着对此在世界的否定(如犹太-基督教),是奴隶的、病态的、虚弱的行为方式。在尼采看来,“金发猛兽、猛禽和主人都是未经奴隶道德所驯化的生命,是保存其原本面貌的生命,是自然(取‘自然’的原初义‘生生不息’)的生命。而羔羊、家畜和奴隶都是奴隶道德驯化的产物,是失去了其本性的生命,是反自然的生命。他在哲学领域打破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庞红蕊,“当代西方”69)。在这个意义上,尼采以及后来的纳粹基于生命的强度提出了一种打破人与动物界限的后人类思想,关键的是生命强度,而非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差别。
这是后人本主义的动物研究所欢迎的观点吗?当然不是,因为无论尼采也好,纳粹也好,都没有真正摆脱物种主义,坚持从生命力的角度来判定动物的高低等级,而在纳粹看来,那些低等的虚弱的动物是不值得存在下去的生命。但纳粹的动物思想对后人本主义的动物研究无疑提出了巨大挑战。
德里达使用carno-phallgocentrism来指代西方吃肉的(carno也带有“牺牲”意味)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而他用“不可吃性”来确立一个界限,那就是有些绝对的他者(剩余物remainder)是无法被我们所解读的,是永远与我们相异的(2009)。这是将列维纳斯关于绝对他者的伦理推到了动物范畴(在列维纳斯那里只限于人类)。但我们如何看待那些善待甚至崇敬动物的纳粹?例如希特勒本人就是素食主义者,是动物之友。纳粹对待动物的伦理态度为何会导致对某些人类群体的不人道?纳粹主动认同动物——当然是那些“有德性的”,“纯洁的”,“无畏的”动物,但他们会将其他群体如犹太人视为“粗野的”“肮脏的”动物,为了维持社会生态的健康纯洁,就必须将那些“肮脏的”群体消灭殆尽,而人的动物化就为这种消灭奠定了基础。
德里达认为希特勒没有将自己的素食主义作为典范(Derrida,“Eating Well” 119)。在他看来,首脑或者头(chef)必然是个食肉者,不可能公开推广素食主义,去规定哪些物种不能吃,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不可吃性”。但谁来决断“可吃性”与“不可吃性”,或者“可杀性”与“不可杀性”?这种决断就涉及到了主权政治,而这是德里达伦理思想所忽视的,因为他的“未来的民主”、“对动物的激情”(Calarco,Zoographies 103-49)没有决断即政治的维度(王行坤 夏永红 46—49),而只是一种伦理态度。阿甘本通过施米特(Carl Schmitt)认识到主权权力的重要意义,并指认出决断“可杀性”与“不可杀性”的是主权权力所确立的例外状态。某个社会群体如犹太人或者移民因为无法被彻底吸纳,处于混沌不清的领域(zone of indistinction),一旦主权者宣布例外状态,这些群体则必须被抛出来,成为赤裸生命,要么被系统性消灭,要么成为其他群体攻击发泄的对象。
在生命政治下,所谓的人权或者人类价值基本失去意义,因为人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正如阿甘本所说:如果人总是那个不断分化(divisions)与停顿(caesurae)的位置——同时也是其后果,那他到底是什么?更为紧要的任务是处理这些分化,去追问在人之内人如何与非人相分离,动物如何与人类相分离,而非在那些大问题上站队,如人权和人类价值(The Open 16)。所谓人之内的人与非人的分离,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动物性的生物生命与专属于人的政治生命的分离,在阿甘本看来这种分离是(生命)政治和主权权力所造就的。
对阿甘本来说,应对之道不是将更多的人或非人纳入到人的范畴,让人类学机器变得更具包纳性,而是彻底打破人与非人、人与动物的分化,打碎人类学机器。正如阿甘本所说,如果某一天要抹去人的科学在历史的海岸上所塑造的“沙滩上的脸”(这是福柯在《词与物》结尾处关于“人之死”的经典论述,笔者注),那么我们将看见的就不再是重新获得的人性或动物性(The Open 92)。言下之意,人性和动物性概念因为人类学机器的失效而失效了。那么如何让人类学机器失效,从而造就一种可以让人和动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的状况?阿甘本转向了本雅明。
本雅明的“救赎之夜”(saved night)和“定格的辩证法”(dialectic at a standstill)意味着人类学机器的完全失效,因为对本雅明来说,拯救之夜意味着自然完全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人类历史的参与,因此是无需修复(irreparable)与无需救赎的(unsavable)(The Open 81),这时人类与动物的之间的辩证法就会“定格”。关于无需修复者,阿甘本在《来临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中做了解释:“无需修复者即是某物以这种或那种模式是其所是,无需补救就被托付给它们的存在之道。不论是什么样的事物,它们的状况都不需修复:无论悲伤或是快乐,人神共愤还是蒙受神恩。你是什么样子,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无需修复者”(89)。其结果就是:
人类学机器不再分辨自然与人类,从而通过对非人的悬置和捕捉来生产人类。也就是说,这个机器被叫停了;“定格”了,而随着人类与自然的相互悬置,在救赎之夜,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我们或许还没有命名、既非动物、亦非人类的某物,并且在得到驾驭的关系中维系自己。(The Open 83)
所谓得到驾驭的关系指的不是人驾驭自然或者自然驾驭人的关系,而是指驾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各得其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摆脱人性与动物性的二元对立。
四、劳动动物与生命政治
《历史哲学论纲》补遗中,本雅明有这样一句话: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也许恰好相反。也许,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即人类——所进行的一场努力,去启动(activate)紧急刹车(Benjamin 402)。
本雅明就是要拒绝历史的连续统一体,拒绝空洞、同质的时间,而这就需要等待微弱的弥赛亚从窄门侧身而入。这时的时间就为当下时间(Jeztzeit,now-time)所充满和圆成,而这被圆成同时也是废除。换句话说,新天新地必然伴随新的时间,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时间(王行坤 203)。这里所表现出的“弥赛亚主义”与“救赎之夜”异曲同工,也为阿甘本所接受。
我们可以看到,阿甘本追求的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政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将福柯的生命政治观念去历史化,从而将集中营视为现代政治的范式——西方民主政体、法西斯主义或者极权主义政体以及社会主义政体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主权权力总会通过例外状态(通过人类学机器)将处于含混不清区域的群体抛出去,让其既内在又外在于共同体,在人类内部制造人与非人的分化。于是,他不是从当下物质生产条件即市民社会去寻求解放的可能,而是诉诸于神学。除了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之外,阿甘本在《至高的贫穷》(The Highest Poverty)中考察放弃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内的一切所有制形式、共同使用财物的圣方济各式的修道院,希望以此来作为社会组织和生命-形式的模式来对抗“例外状态”。但是“阿甘本用奠基于‘共同使用’的抽象的‘贫穷’概反对一切形式的所有制——无视经济结构和利益,其结果就是将真实的贫穷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浪漫反抗,而非视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所造成的剥削的结果”(Wilkie 46)。
阿甘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劳动成为财富的源泉(洛克和亚当·斯密),作为生物生命的劳动动物走向前台。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的结尾部分哀叹“劳动动物的胜利”:今天,在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劳动甚至变成了一个如此崇高,如此有抱负的字眼[……]现代——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254—55)。所谓“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就是劳动状态,而劳动动物在阿伦特看来,的确是地球上的一个动物物种,充其量是最高级的一种罢了(63)。
阿伦特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劳动动物不能归入人类的范畴。另外,阿伦特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劳动是在家庭内所进行的痛苦的、繁重的和毫无创造力的活动,这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工作是作为自由民的手艺人所进行的手工制作活动;而行动则是公民在城邦内就公共事务进行探讨和协商的活动。前两个领域受制于自然必然性,没有自由可言,只有在行动即城邦-政治(政治来源于城邦polis)的领域,才有进行协商和自由活动的余地。因此从事前两者的都属于劳动动物,唯有后一种属于亚氏所说的政治动物即真正的人的活动。
《人的境况》出版于1958年,作者认识到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本可以彻底摆脱劳动,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受雇于某个雇主的“职业人”依然是现代人的根本规定,其结果就是现代人的生命越来越接近动物生命,而非真正的人类-政治生命。阿伦特认为这是某些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马克思)推崇劳动的结果,因此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这无疑和阿甘本一样犯了忽视历史的错误。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条件推崇劳动(“劳动光荣”),但阿伦特注意到,马克思本人也主张消灭劳动,即消灭自然的必然性,从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动物生命取得胜利,以至于在人类内部,绝大多数人口都成为劳动动物,只有少部分人成为政治动物?与其他“动物研究”相比,这或许是最为根本性的动物问题。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出现,绝大多数人沦为雇佣劳动力和无法受到雇佣、生命岌岌可危的剩余人口。工厂内的劳动力因为异化劳动完全失去自主性和能动性,成为笛卡尔意义上的机械的动物,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5)。作为雇佣奴隶,他们与古代的奴隶-非人并无本质不同,在生产空间毫无自由,只能按照雇主的意志和机器的要求去改变客体,其结果就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 55)。马克思所认为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拥有主动且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后者只是出于本能完成自身的活动,因此前者可以通过各种对象性活动来表现自身本质的多样性和无限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存在先于本质”),而后者只能通过固定的活动而表现固定的本质,如蜜蜂筑巢,蜘蛛结网。异化劳动在生产空间内剥夺了人的这种特性,使其沦为受制于必然性的动物生命。
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动物并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就的人类生命的沦落;正如在阿甘本那里,人类动物也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人类学机器”通过排斥-吸纳机制所造就的后果。但阿甘本就现代的人类动物所给出的例子是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医院里脑死亡和重度昏迷的人、关塔那摩羁押的犯人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却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外部的殖民地人民和内部的劳动动物,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盲点。就殖民主义来说,“被殖民者被动物化,因为赤裸生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而变得面目模糊,其权利永久性地遭到悬置”(Hudson 1665)。
无论是殖民地的动物化还是工厂内的动物化,其根本机制不在于主权的例外状态,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德里达试图解构吃肉的-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主体,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主体并非人类个体或者整个人类,而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这种体制为了剩余价值就必须将作为劳动力的生命力——如果劳动力不是生命力又是什么?——吞没、牺牲掉(吃肉必然伴随着牺牲)。德里达寄希望于“不可吃性”或者不可被吸纳或吞没的绝对他者,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他者(无论是人类动物或者其他任何动物)都要作为劳动力被吞没。在维尔诺(Paolo Virno)和奈格里看来,阿甘本赤裸生命的概念具有神秘化和失败主义色彩,赤裸生命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捕捉的劳动力,或者说,无产阶级(Virno;Henninger 160-61)(Vrino文章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英文版只在网上发表,网址已在“引用作品”中标出)。因此我们必须从劳动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生命的动物化问题:“我们不仅要在伦理、法律政治的领域去考察人类的动物化,而且也要在生产行为过程中考虑人类的动物化”(Hudson 1675)。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叫停“人类学机器”,而且也要叫停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机器”,因为只要后者存在,我们作为劳动者就必然是劳动动物,就不是真正的人,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146)、“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183)这样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话。现代劳动动物几乎不再是可以享受公民权利的政治生命,而是命运岌岌可危的动物生命,正如福柯所说,数千年来,人依然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一个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而现代人则是这样一种动物,他的政治让他的生物性存在成为问题。只不过其根本不在于福柯-阿甘本所说的生命政治,而在于对劳动力的身体-生命进行管制的治理技术。
结语:作为后人类/人本主义概念的类本质
“1844年手稿”直到1932年才出版,之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风靡一时,出现了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对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潮。但是在阿尔都塞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下,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异化”和“类本质”即便不是被彻底抛弃,也成为非常可疑的看法。但正如威瑟福特(Nick Dyer-Witherford)所指出的,近年来如大卫·哈维、斯皮瓦克和贾森·里德(Jason Read)等人又重提类本质的概念,试图将其从本质主义的概念中解放出来(3)。
在阿尔都塞看来,青年马克思向人性回归的说法预设了人的本质的概念,这种概念在“认识论断裂”之后便被马克思抛弃。“类本质”概念来自于费尔巴哈,的确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术语。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性的类本质恰恰没有预设人的本质,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人的本质只能在历史尤其是社会生产的历史中得到体现,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我们可以概括出类本质的特征:潜能或者潜在性(virtuality),社会协作性或者普遍性(universality)(Dyer-Witherford 6),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所谓普遍性就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通过社会交往、协作而让自己的主体性不断越过自己,从而让自己与他人更加容易交流通约,因此我们可以将类本质视为跨个体(transindividual)(Dyer-Witherford 7)。这种“跨”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是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组合协作,因此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机器式主体(Machinic Subjects)(Hardtand Negri 107-23),这是有待实现的作为潜在性的主体。
这种去中心化的类本质观念与斯宾诺莎-德勒兹关于身体力量的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并非封闭的原子式的个体,我们的力量也并非限于我们自身的身体之内,而是取决于我们影响(affect)他人以及受到他人影响的能力。在斯宾诺莎看来,身体是由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些部分的数量和内容是可变的,因此我们不能将身体视为实体,而应该视为关系。当身体中出现新的关系,身体会更广大;当有关系破灭,身体就会萎缩或解体(Hardt 210)。因此斯宾诺莎强调能够对我们造成积极影响从而增强我们力量的愉悦的相遇。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异化劳动,工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处于孤独无助的地位,其身体无法与外界形成任何关系,因此变得虚弱无比,其类本质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工人只能沦为无知无识的劳动动物。
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抛开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等,去激发人的类本质。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等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如何思考人机互动,如何思考对人的能力的强化(超人本主义),如何思考人与动物以及自然的关系(动物研究和生态科学)?福山和哈贝马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维护人性的纯洁性,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超人本主义思想某种意义上与尼采“金发碧眼的野兽”观念不谋而合,两者的根本问题都在于只注重少数强者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利用新兴科技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进行增强,而尼采所要恢复的,是贵族式的释放本能和生命力的任性而为。尼采在某种意义上认识到了现代性以来的问题,那就是生命力的萎缩,但他没有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动物的大规模出现。我们如何恢复劳动动物的生命力?
斯宾诺莎关于身体的论述或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凡能支配人的身体,使身体可以接受多方面的影响,或使身体能够多方面地影响外界物体之物,即是对人有益之物。一物愈能使身体适宜于接受多方面的影响,或影响外界的物体,则那物将愈为有益(201)。但这种物如何寻到?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已经对人造成巨大的压迫,似乎物具有了能动性,而人只是被动的生物。
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根本区别在于他对于生产实践的重视,因为人的类本质是在劳动的过程即改变外部世界从而与他人结成关系纽带并改变自己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58)。巴迪欧坚持认为自己通过数学得到的“类性”(générique)概念与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是相通的:“马克思将处于自我解放运动之中的人性称为‘类性的人性’,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个名称——则是在其肯定形式下类性的人性的可能性名称。对马克思来说,‘类性的’这个词命名了人的存在的普遍性的生成,而无产阶级的历史职能就是给我们提供人的存在的类性形式。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真理位于类性这一边,从来都不在特殊性这一边”(45—46,译文有改动)。这里的类性就是前面所说的通过生产历史与协作而达到的普遍性,而作为类性的人性就在这样的进程中得到实现。
正如鲁维恩克(Gerda Roelvink)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类本质的论述可以为后人本主义思想提供丰富的资源(67),因为后人本主义思想不是关于后人类或者什么人类之后的存在——人类总要存在下去,而是关于人本主义的自主性幻象,强调的是与他者(包括机器)的相互依存。因此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如何与他人、动物以及机器建立关系纽带,从而增强所有生物的力量,并且让人类的类本质得到最大范围的发展,让人更具普遍性即更为全面的发展,这或许是最为根本的任务。
注释[Notes]
①也翻译为科学元勘,指的是从文化角度如哲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去研究科学知识,意在揭示科学知识的构建性。
② 相关文献可见,冉聃、蔡仲:“赛博与后人类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0(2012):72—76;梁晶:“当后人类社会成为一种可能”,《中国图书评论》,7(2010):30—33;刘鹏:“拉图尔后人类主义哲学的符号学根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5):22—28;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33.6(2013):4—11;夏永红,“环境人文学:一个正在浮现的跨学科领域”,《国外理论动态》1(2015):37—45。其中夏永红认为,伴随着“人类世”出现的是一个后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也需要一种后人类的视角来面对这个后自然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环境人文学”。
③卡里·沃尔夫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Posthumanities系列的主编,该系列至今已出版45部相关著作,沃尔夫的这本书也是出自此系列。相关信息见:〈https://www.upress.umn.edu/book-division/series/posthumanities#〉。
④“animot”是德里达自创的词汇,其法语发音听起来像“animaux”,法语“动物”的复数形式。德里达希望人们能从“animot”这个单词中听到复数性的、多样性的动物生命,因为当我们说动物时,我们指的好像就是与人不同的所有物种,这些物种本身的差异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而德里达用“animot”就是要表达动物生命的多样性。在“animot”中,每一生命个体都保持了它们自身的独特性。另外,“animot”中的“mot”是“词语”的意思,这个法语词由动物-词语组合而成。古代西方哲学认为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语言”,而德里达通过这个词来解构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类与动物的区分机制(Derrida,The Animal 37-41)。
⑤本文将西方近代以来哲学观念上的humanism翻译为人本主义而非人文主义,以与西方之前的神本主义相对应,因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的中心地位。transhumanism翻译为超人本主义,因为这是加强版本的人本主义,而哲学意义上消解人类主体中心地位的posthumanism和anti-humanism则翻译为后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
⑥例如赵柔柔将超人本主义视为后人类主义的一个支流,见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10(2015):82—90。另外有学者写道:“后人类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最后10年以来,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富裕国家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大脑科学、神经药理学、生物克隆技术、基因修复技术、直观人类工程、人工超智能、人体冷冻技术、纳米技术、太空技术等的新发展为基础,希望借助于这些技术的巨大潜力,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物质和精神世界,最终变人类自身的自然进化为完全通过技术实现的人工进化的社会思潮和实验性探索活动。”完全将超人本主义等同于后人类主义,见佘正荣:“后人类技术价值观探究”,《自然辩证法通讯》30.1(2008):95—100。另外可见张之沧:“‘后人类’进化”,《江海学刊》6(2004):5—10;刘魁:“超人、原罪与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困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8.2(2008):39—44;曹荣湘编选:《后人类文化》。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宋秋水:“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4(2005):31—34。
⑦相关文献请见,Kalpana Rahita Seshadri.HumAnimal:Race,Law,Langua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Michael Lundblad.The Birth of a Jungle:Animality in Progressive-Era U.S.Literature and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Mel Y.Chen.Animacies:Biopolitics,Racial Mattering,and Queer Affect.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David A.Nibert. Animal Oppression and Human Violence:Domesecration,Capitalism,and Global Confli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Debora Amberson and Elena Past.eds.Thinking Italian Animals:Human and Posthuman in Modern Italian Literature and Fil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Margo DeMello.Animals and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Nicole Shukin.Animal Capital: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Stanley Cavell,et al..Philosophy and Animal Lif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以及本文所提及的沃尔夫和卡拉柯(Matthew Calarco)等人的作品。
⑧分别见Habermas,Jurgen.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Trans.Hella Beister and William Rehg.London:Polity Press,2003;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⑨affect这个词既可以作动词,表示影响他人行为,同时也被他人所影响;也可以作名词,表示情感或情动的意思。
⑩感谢蓝江教授让笔者注意到巴迪欧这个说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gamben,Giorgio.Homo Sacer.Trans.Daniel Heller-Roaz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The Coming Community.Trans.Michael Hard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The Open:Man and Animal.Trans.Kevin Attell.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Arendt,Hannah.The Human Condition.Trans.Wang Yinli.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Trans.Lin Xianghua.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8.]
Arluke,Arnold.Regarding Animal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6.
巴迪欧:《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李佩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Badiou, Alain. The Enig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Trans.Li Peiwen.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2017.]
Benjamin,Walter.Selected Writings.Vol.4,1938-1940.Eds.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Jennings.Trans.Edmund Jephcott et al..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2003.
Bostrom,Nick.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14.1(2005):1-25.
Braidotti,Rossi.The Posthuman.Cambridge:Polity,2013.
Calarco,Matthew.Thinking Through Animals:Identity,Difference, Indistinction. Stanford: Stanford Briefs,2015.
---.Zoographies: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 from Heidegger to Derrid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
Clark,Andy.Natural-Born Cyborgs:Minds,Technologies,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Derrida,Jacques.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More to Follow).Trans.David Will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Eating Well,’ 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ubject: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Who Comes after the Subject.Eds.Cadava E.,Conor P.,Nancy J.L..New York:Routledge,1991.96-119.
Derrida,Jacques,Daniel Birnbaum,and Anders.Olsson“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on the Limits of Digestion.” E-flux.January 2009. 〈http://www.eflux.com/journal/02/68495/an-interview-with-jacquesderrida-on-the-limits-of-digestion/〉.
Dyer-Witheford,Nick.“1844/2004/2044:The Return of Species-being.”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4(2004):3-25.
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Foucault,Michel.The History of Sexuality.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
Haraway, Donna. Manifestly Harawa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
---.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
Hardt,Michael, “The Power to be Affec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Society 28.3(2015):215-22.
Hardt,Michael,and Antonio Negri.Assembl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Henninger,Max.“From Sociological to Ontological Inquiry:An Interview with Antonio Negri.”Italian Culture 23.1(2005):153-66.
Hudson,Laura.“A Species of Thought:Bare Life and Animal Being.”Antipode 43.5(2011):1659-7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Marx,Karl.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Trans.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
米兰多拉:《人的尊严》,顾超一、樊虹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Mirandola,Giovanni.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Trans.Gu Chaoyi and Fan Honggu.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
庞红蕊:“德里达的动物问题”,《求是学刊》41.2(2014):31—38。
[Pang,Hongrui.“Animal Issue of Derrida.” Seeking Truth 41.2(2014):31-38.]
——:《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动物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Anim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Ph.D.Diss.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2014.]
皮克林:《实践的冲撞》,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Pickering,Andrew.The Mangle of Practice.Trans.Xing Dongmei.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4.]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Spinoza,Baruch.The Ethics.Trans.He Li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3.]
Roelvink, Gerda. “Rethinking Species-Being in the Anthropocene.”Rethinking Marxism 25.1(2013):52-69.
Virno,Paolo. “General Intellect,Exodus,Multitude.”Trans.N.Holdren.2018年3月26日访问。〈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virno2.htm〉。
王行坤:“生命、艺术潜能——阿甘本的诗术-政治论”,《文艺理论研究》02(2014):200—208。
[Wang,Xingkun. “Life,Art and Potentialities:Agamben’s Concept of Poetics-Poli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02(2014):200-208.]
王行坤 夏永红:“情感转向下的爱与政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4(2017):39—53。
[Wang,Xingkun,and Xia Yonghong.“Love and Poli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Turn.”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31.4(2017):39-53.]
Westling,Louise.“Literature,the Environment,and the Question of the Posthuman.”Natur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s on Ecocriticism.Eds.Catrin Gersdorf and Sylvia Mayer.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06.25-47.
Wilkie,Rob. “Giorgio Agamben’s ‘Cenobitic Communism’and the Limits of Posthumanism.”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5.1(2015):42-51.
Wolfe,Cary.Animal Rites:American Culture,the Discourse of Species, and Posthumanist The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nd ed.2003.
---.Before the law:Human and Other Animals in a Biopolitical Fra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What is Posthuman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
邢冬梅毛波杰:“科学论: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5):8—15。
[Xing,Dongmei,and Mao Bojie.“Science Studies:From Humanism to Posthumanism.”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201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