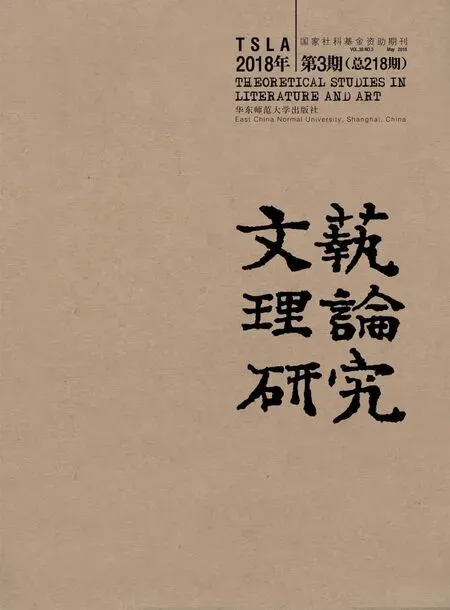从二分心智人到自作主宰者
——关于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内心声音
傅修延
人物的自我意识往往以内心声音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中外叙事作品中,“脑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之类的表述不胜枚举。在理论批评领域,意识和声音也常被人等量齐观。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声音和意识的内涵几乎相互重叠——该书中译者对这两个术语作了专门解释,认为前者“指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某人思想、观点、态度的综合体”,后者“实指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观念,一个意识常常即代表一个人”(27—29)。此外,韦恩·布斯的《小说学修辞学》、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苏珊·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和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和意识形态》中,意识与声音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著作中的声音多指作者意识,但作者意识最终还是会以种种方式向人物渗透,或与人物意识相互激荡形成巴赫金所谓的复调。
由于声音较之意识更易于被人理解,加之两者在内涵上相当接近,理论批评领域用声音来指代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在具体的叙事作品中,内心声音更多表现为某个不期而至的念头——包括思虑、计划、议论、评价和观点等,其发生与内容有时甚至会让人物自己也感到吃惊。如果将人的意识想象成大海(所以有“脑海”之喻),那么内心声音就是大海中飞溅的浪花,也就是说意识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从内涵上说前者囊括了后者。我们不妨来看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段心理描写,这节文字叙述安娜与伏伦斯基见面后心头如有小鹿儿乱撞:
她一想起伏伦斯基,内心就有个声音在对她说:“温暖,真温暖,简直有点热呢!”她在座位上换了一个姿势,断然地对自己说:“哎,那有什么呢?那又有什么道理?难道我害怕正视这件事吗?哎,那有什么呢?难道我同这个小伙子军官有了或者可能有超过一般朋友关系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读不进去。(102)
引文中安娜的内心声音发生得比较突兀,在其原本波澜不惊的意识中搅起阵阵涟漪,但此时安娜对伏伦斯基的情感尚在萌动之初,因此其意识中又出现了一个更为响亮、更能代表安娜意识主要方面的声音,其功能在于构成对前者的压制——“哎,那有什么呢?难道我同这个小伙子军官有了或者可能有超过一般朋友关系的关系吗?”不过这种压制只是暂时的,从安娜“拿起书来”“怎么也读不进云”的后续动作来看,她原先平静的心境已被打破,那个嚷嚷着“温暖,真温暖,简直有点热呢”的声音显然已经对其意识构成了严重的扰动。
安娜内心是否真有声音响起?这个问题乍看上去有点幼稚,因为一般认为这是作者用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修辞手段,说人物心中有声音只是一种譬喻,不能按字面意义理解为真有什么声音在其心中发出。说得更直白一些,人的大脑里面没有发声器官,声音不可能凭空白地从里面产生——如果一定要说某个人物听到了自己的内心声音,那只能说其神经系统出现了谵妄型的听觉感知。但是,如果完全用幻听来否定内心声音的存在,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作者都用声音来指代意识。再则,一些作者在写内心声音时,也是像托尔斯泰那样使用言之凿凿的直接引语,引号中的声音给人的感觉是发自另外一个主体,其存在的真实性与清晰性均不容置疑。更有甚者,内心声音在有些作家笔下还像真的声音一样具有冲击感。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第四十章中,汤姆在遭受折磨时向上帝祷告,结果耳边“一个更大的声音”震动了他的全部身心,“仿佛上帝的手触到了他的身体似的”:
这些凶狠的话语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一个更洪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听了这句话这可怜人仿佛被上帝之手触摸过似的,浑身的神经和筋骨都激动地震颤起来,觉得自己拥有千人之力。(458)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南希·法默的《鸦片之王》,小说第七章写小男孩马特脑子里的声音是如此逼真,以至于他以为屋子里还有什么别人存在:
马特漫无目的地走到火炉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做什么,可是有一个声音,一个深埋在他头脑里的声音,在悄声说道:他要杀了你。这个声音是那么的真实,以至于小男孩连忙抬头看房间还有什么人。(40)
此类描写在中国小说中同样存在。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中,人物的“脑子深处”也有一个在说话:
高马翻身爬起的动作又笨又拙:屁股撅得高高的,四个爪子着地,很像刚会爬行的婴儿在“支锅”。他(高羊)咧了咧嘴,他听到脑子深处一个似自己非自己的人在说:“你没有笑,知道不知道,你没有笑。”(9)
文学来自生活,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不是真人,但作者并非不食五谷的神仙,因此不能断然否定这些描写的现实依据。不过对内心声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首先听取他们的意见。不仅如此,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还能引导我们以声音为路标步入邃密幽深的意识迷宫,看到主体意识的建构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早已完成,而是一个绵延至今的渐进过程,而了解这一漫长过程又会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作品中那些耳边有声音响起的人物,当然这也意味着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现在机器人的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本文认为人类自己的意识问题至少应获得同样的关心,叙事作品可以为这方面的探讨提供不可替代的研究材料。
一、内心声音因何产生——来自二分心智理论的解释
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经常出现幻听,这一判断已为无数临床诊断所证实,然而不能据此反过来说出现幻听便意味着精神不正常。1894年,一项名为“国际正常人幻觉普查”的调研活动征集到了17000人的回答,针对调查问卷上的唯一问题——“当你确信自己完全清醒的时候,是否曾经真切地看见或感到一个生命体或者无生命体碰到了你;是否曾经感觉听到某种声音传来,而就你所能了解到的,它又并非在外部客观存在”,超过10%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表示自己有过幻听经历。参与这一调查的对象全部心智正常,有明显疾病和精神问题者均被主事方严谨地筛除在外(萨克斯 65;Sidgewick 25-394)。这一调查结果显示,正常人并非完全听不到虚无缥缈的声音。中国古代的“余音绕梁”故事中,韩娥离开后其声音还萦绕在邻居的耳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之旨”的豁然领悟,源于其似睡非睡时听到的话语。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在其经典之作《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中,坦然承认自己也和他的许多病人一样遭遇过幻听:
年轻时代我曾飘泊于异乡,每每陡然听到家人在唤我的名字,清晰无误。我马上记下这个幻觉出现的时间、地点,担忧着那时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幸而”,每次都是徒劳。(187—88)
弗洛伊德的现身说法在心理学家中并非个例,他的同行朱利安·杰恩斯如此记录自己20多岁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时的一次经历:
一天下午,思虑上的困顿令我卧于睡榻,突然在一片寂静之中,从我头顶右上方传来一个坚定而又清晰的响亮声音:“把知道者(knower)置于已知(known)之中!”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发出不可思议的呼唤:“谁呀?”同时寻找是谁在屋里。那个声音有其明确无误的发生位置,但那个地方并没有人!我还傻里傻气地跑去墙外寻找,仍然没有人。(Jaynes 86)
杰恩斯写下这段经历,不仅是为证明正常人也会有幻听,更主要是为了引出他的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人类的意识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才产生,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发自自己右脑的声音,但他们的左脑将这种声音感知为外界神祇的指令,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也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出现之后,随着自主意识的萌发,这种声音才逐渐淡出人类的头脑。不过,虽然人类从此有了内在叙事(internal narrative)的能力,其遗留痕迹至今并未被完全抹去,症状之一便是现代人仍会莫名其妙地听到子虚乌有的声音。把右脑中的声音当作神的旨意,等于人的心智(mind)中存在着一个负责发令、一个负责执行的双重主体,杰恩斯把这种情况称为二分心智(bicameral mind),三千年前的人类在他笔下也就成了二分心智人(bicameral man)。由此,杰恩斯把自己论述这一观点的著作命名为《二分心智崩溃中的意识起源》(以下简称《二分心智》),旨在强调二分心智的崩溃是意识起源的先决条件。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心智中“双马拉辕”状态的结束,便是人类建构起自己主体意识的开始。
观点需要有证据支撑,杰恩斯宣称三千年前人类没有意识,其主要证据来自《伊利亚特》的相关叙述。与文学艺术领域对《伊利亚特》的认识不同,杰恩斯认为“《伊利亚特》不是想象性的文学创作,不能作为文学讨论的材料。它是历史,关联着迈锡尼人在爱琴海上的活动,因此须由心理历史学领域的科学家来做考察”。引文中所说的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属于西方“新史学”流派的一个分支,这个领域的学者主张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历史事件的心理动因。杰恩斯把《伊利亚特》定位为“历史”,从心理历史学角度研究这部史诗便无越俎代庖之嫌。在用心理学的手段对史诗人物的心智作了全面诊察之后,杰恩斯得出了下列认识:
1.《伊利亚特》中的人物没有意识,他们不懂得自己行动的意义,不会进行自我反省,也不知道危机发生时应如何应对;
2.驱使这些人物行动的是神的旨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神在他们耳畔发出的声音指导他们如何行事,这一点以阿喀琉斯的忍辱负重为最典型;
3.他们完全信赖这种声音,对其持绝对服从的态度,西方文化中的“服从”就是“听从”,拉丁语的“服从”(obedire)一词乃是由“听”(ob)发展而来;
4.这种声音在他们的大脑中成为意识的替代,其地位有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超我”(superego),因此一旦行为出了偏差,他们也会认为过错不在自己,这一点可从阿伽门农的自我辩解中看出;
5.与今天的癫痫病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他们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大脑中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也常给他们带来迷乱与困惑,赫克托耳的不幸下场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6.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把神看作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那么特洛亚战争的交战双方全都处在谵妄状态。“我们可以说赫克托耳得了谵妄症,阿喀琉斯也是如此,整个特洛亚战争都是在幻觉引导之下进行。被幻觉如此引导的战士们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异类,他们是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的高等级自动人(noble automatons)。”(Jaynes 67-83)
为避免占用过多篇幅,以上诸点是从《二分心智》中归纳提炼而来。对《伊利亚特》有印象的读者或许会觉得杰恩斯过于武断,因为史诗中许多涉及心智的叙述显示史诗人物还是有意识的,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僵立在特洛亚海滩上等待脑中声音出现的“高等级自动人”。杰恩斯对此有专门解释,他说《伊利亚特》中那些貌似与智力活动有关的词语,在当时全有与现代人理解不同的具体内涵。例如:
psyche——后来逐渐指灵魂或心智,当时指与生命有关的因素,如鲜血或呼吸等。某人断气可表述为他在最后呼出了他的phyche;
thumos——后来逐渐指心灵激奋,当时指运动或运动器官。某人停止运动可表述为thumos离开了他的四肢,神赐予某人力量可表述为神将力量注入他的thumos;
phrens——后来逐渐指心灵,当时指腹膈或腹膈中的感觉,说某人的腹膈察觉到了某事的发生,其义相当于某人为某事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noos——后来逐渐指内省心智,其本义为noeein(看),说神把某人置于其noos之中,其义为神在照看着某人;
mermera——其本义为两半(一半为meros),加上后缀-izo后变为动词mermerizein,后人将mermerizein误译为沉思、思考、心神不宁和取舍不定等,这一译法的错误在于该词指在两个行动中难于取舍,而不是指在两种思想中踌躇不定。(Jaynes 69-70)
语言反映认识水平。以上对相关词语的辨析显示,与灵魂与意识等有关的表达方式,在史诗所处的时代主要指有生命或有生气活力的具体对象,其内涵与现代人的理解有较大差异。似此,《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不可能被赋予主宰自己行为的自由意志,因为使用这些词语的荷马及其同时代人尚未来得及在自己心中进化出这样的概念。杰恩斯还指出,史诗的身体概念也与现代人大相径庭:如soma到公元5世纪才有身体之义,而在史诗中这个词指尸体或无生命的四肢;又如荷马经常提及身体各部分的名称,热衷于赞美手、小臂、上臂、脚、腓(小腿肚)和大腿等部位的筋骨强健,叙述它们迅速而有力的运动,但就是不把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Jaynes 71)。显而易见,对身体这一总体的无视,与当时人缺乏灵魂和意识概念有密切关联:“灵”是“肉”的主宰,与前者有关的概念没有建立起来,后者只能是一堆活力部件的集合。
杰恩斯的研究让许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意识萌发被其推迟至距今三千年前。众所周知,人类起源至今已有数百万年乃至超过一千多万年的历史,以文字为标志的人类文明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六千年前。按照《二分心智》中的说法,人类是在文明社会中生活了三千年之后才产生意识,这不啻是说三千年之前那些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如埃及金字塔、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与《吉尔伽美什史诗》等,统统都是由浑浑噩噩的“高等级自动人”创造出来的。杰恩斯很清楚人们首先会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所以《二分心智》一开始用了整整一章讨论“对意识的意识”,其要义为意识不是经验的复制,亦非学习、推理、判断、简单思考和建立概念等心智活动的必备条件,不能和反应混为一谈,事实上一些创造性的发明正是在摆脱了意识干扰的情况下不期而至(Jaynes 21-47)。讨论结束时杰恩斯如此强调和承认:“除非至此你相信一个没有意识的文明可能存在,否则你会发现本书接下来的讨论都是没有说服力和自相矛盾的”(Jaynes 47)。
但要所有的人——特别是具有根深蒂固“常识”的人,都相信这种颠覆性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就曾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向他发难:“现在我感知到了你,你是不是想说我此刻没有意识到你呢?”杰恩斯对此的解释是老先生混淆了意识与感知,事实上此刻他意识到的是自己的雄辩,假如他转过身去或者闭上眼睛,也许会更为有效地意识到杰恩斯的存在。从这里可以看出,杰恩斯对意识的理解与常人有所不同,在他的意识前面加上主体二字,或许更符合其本意。《二分心智》第4章开头的举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现代人与二分心智人之别。作者说开车人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操纵汽车的具体动作,其意识可能被卷入车厢内的谈话,或被车窗外的景观所吸引,等等,然而一旦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发生,如爆胎或堵车之类,开车人的意识便会在瞬间回到现场,与此同时大脑中各种应对方案相继映现(笔者按,此即所谓“内在叙事”,有些人甚至会自言自语地说出这些方案),但二分心智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焦急地等待右脑中声音的出现(Jaynes 84-85)。
杰恩斯的《二分心智》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这部多次重版发行的著作尽管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少数极力推崇的人认为可以与达尔文或弗洛伊德的开拓之作相媲美,但在其所属领域从未获得主流意见的认同。因为心理历史学归根结底属于史学,而心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对于这门学科中的正统学者来说,《二分心智》对右脑声音的探讨只是纸上谈兵,光是引述荷马史诗、旧约、玛雅石雕和苏美尔文献之类仍然不足以服人,他们更关注显微镜下的神经元联络和实验室里拿出的数据。杰恩斯于1997年去世,他在《二分心智》初版后的20多年里未再写出新的著作,这种“一本书主义”说明他对同行的反应多少有些失望。
不过与许多因时光流逝而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开拓性研究不同,《二分心智》带来的冲击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因为该书讨论的意识起源问题处于时代前沿,杰恩斯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扮演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尽管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二分心智》事实上开启了研究意识与行为之间联系的新方向,这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不少当代哲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对脑成像的最新研究指出人的听觉幻象源于右脑,随之而来的行为源于左脑,这一发现亦可视为对二分心智说的某种肯定。哲学界现在也开始认同杰恩斯的意见,即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察知(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ly awareness),这些都显示杰恩斯当初并非信口开河。人工智能技术近年来的突飞猛进,特别是2016年谷歌公司那条“机器狗”(AlphaGo)以4∶1的比分击败九段棋手李世石,使现代人猝不及防地面对了一个原先以为还很遥远的问题:机器什么时候会进化出和人一样的意识?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讲述未来故事为己任的作家和编剧也对《二分心智》发生了兴趣。21世纪已有不少叙事作品向其表示敬意,或从这部“神书”中汲取灵感,或以书中理论为自己的思想内核,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罗伯特·索耶的《WWW·苏醒》。这部科幻小说和《二分心智》一样讨论了自我的意识起源,当然网络这一新生事物的“自我”更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故事女主角凯瑟琳正是在杰恩斯的启迪下开始思考网络生命出现的可能性。最近轰动美国的电视连续剧《西部世界》犹如二分心智理论的故事版,故事发生在一个模仿“西部世界”的特大型人工智能乐园,为释放人性恶而来的游客可以在此为所欲为,接待他们的机器人(host)则按指令(相当于《二分心智》中神的声音)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逆来顺受。但在运转若干年之后,接待员的大脑中逐渐出现对抗指令的声音,这种谵妄症候源于设计者在其大脑中“埋伏”的程序,目的在于让这些声音唤醒机器人的自我意识。《西部世界》第1季的季终集名为“二分心智”,这一名称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杰恩斯的理论是这部连续剧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故事中机器人的生死循环过于频繁和角色转换过于随意——被游客杀“死”的接待员经修理后又立即投入使用或改派别的角色,它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受到记忆碎片的干扰,这就导致其身份与行为均变得迷离恍惚,乐园的整体运行因此也每况愈下。如果说《二分心智》讨论的是意识如何诞生,那么这部连续剧要说的是意识诞生将会带来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剧中人会说“毕竟创造生命是上帝的专利”。
二、从“被主宰”到“自作主宰”——任重道远的主体意识建构
对二分心智说的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应承认它给人的启迪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古希腊栩栩如生的人体雕塑,迄今为止仍然是西方美术史上未被逾越的高峰,杰恩斯的研究让人认识到:后人的同类作品难以望其项背,是因为人体各部位在当时的雕塑家眼中都有自己的“phyche”或“thumos”,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那些生气灌注、血脉贲张的肉体都是有自己“精气神”的——现代人不再像早期人类那样把战争看成是人类膂力之间的较量,对发达的肌肉和强健的骨骼缺乏崇拜之情,当然也就创作不出像《掷铁饼者》那样的杰作。不过这样的启迪并非杰恩斯给读者的主要馈赠。实际上,二分心智理论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让我们认识到人的主体意识并非与生俱来,或者说这种意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处于建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还未真正结束。
中西历史上许多事实似可佐证这一认识。在中国,殷墟出土的商代卜辞,显示我们的祖先过着一种“无事不占”“无旬不卜”的生活,对于尚在未定之天的事情,不管是军事、祭祀、婚丧和生育,还是田猎、出行、疾病和天气,他们都要通过甲骨占卜来征求上帝和祖先的意见。从卜辞可以看出,殷人对自己的思维能力缺乏足够的自信,对未知世界怀有极大的恐惧之情,因而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听取神的旨意。商朝开始于公元前17世纪,延续了五百余年,其为周朝取代的时间正好是杰恩斯所说的三千年前。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材料(按,指卜辞)全部是殷人神权崇拜的记录。关于一个时代神权情况的资料如此完整而丰富,这是后世的文献记载难以比拟的,也是世界上古历史中极为罕见的”(晁福林 99)。
西方虽然没有甲骨卜辞这样的出土文献,但希腊境内如鲁灵光殿般幸存下来的神谕所遗址,告诉我们同时代的西方人也同样缺乏主见。商代“贞人”和“卜人”的主要职责是分析烧灼后爆裂的甲骨“兆”纹,古希腊的祭司则是通过倾听鸟类、树叶发出的声音或观察祭祀用活物的反应来与神沟通,祭司在迷狂状态下发出的含混低语被理解为神的旨意(与此类似的降神仪式在中国一些地方不绝如缕)。维柯说:“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政权统治下过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和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28)。希腊罗马的神话和传说中,有大量故事讲述神谕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俄狄浦斯试图摆脱神谕预示的可怕命运,但最终还是犯下了弑父娶母的滔天大罪。
杰恩斯把人类主体意识的萌发确定为距今三千年前,是因为支撑其观点的《伊利亚特》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此后的作品中再难找到那么多唯耳畔声音是听的人物。二分心智说显然还须有更多证据方能服人,不过有趣的是,观察公元前10世纪以来的历史,便会发现正是在这个临界点过去之后不久,世界各大文明中不约而同地诞生了一批对人类精神有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孔子、老子、墨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犹太诸先知。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段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前800至前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69)。“轴心”这一名称容易让人想起二战时的“轴心国”,我们这边更习惯于用“百家争鸣”来形容自己历史上那段黄金时代——“百家”在当时并不是夸大之语,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便有“诸子百八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之多。雅斯贝尔斯将那段时代的起点定在公元前八百年,此一时间点距杰恩斯的临界点不过两百年,两百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冲破壅塞的人类心智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质变:如果说此前世界各地的人类都在侧耳寻找神的声音,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当中的智者开始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
智者的声音在公元前八百年之后的世界各地同时响起,说明人类各大文明差不多同时趋于成熟。有必要指出,这些文明彼此间虽然相距甚远,但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等人的活动范围都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北半球上这一由西欧、北非绵亘至东亚的长条状温暖地带,构成了当时人类在地球上的主要集聚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片集聚地上的人类不可能永远处于浑浑噩噩的境地,不管是在其东边、西边还是中间,一定都会有人率先觉醒,从一味依赖神示变为自己独立思考。然而先觉和后觉之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或许是由于人类的心智之火只在冲破壅塞那一刻才可能发生最为强烈的爆燃,至今照亮我们思想天空的还是当年的火光,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今天仍然依托于那个时代奠定的精神基础,其实际意思是两千多年来再未出现可与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等人相比肩的伟大人物。杰恩斯看到二分心智崩溃的余波荡漾至今仍未平息——从平民的婚丧嫁娶到国家的庆典祭祀,人们仍在用种种方式向古老的神祇祈祷或宣誓;受过科学知识洗礼的人在遇到无法抗拒的生老病死问题时,仍会不由自地向冥冥中的未知主宰求助。这些事实使杰恩斯得出这样的认识:从二分心智到独立心智的转折,到20世纪结束时仍未完成:“在第二个千禧年结束之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仍深处于这场通向新的心智的转折之中,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处在二分心智坍塌的残余之中”(Jaynes 317)。
杰恩斯说当今人类仍然处在“通向新的心智的转折之中”,这样的提法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他为证明我们周遭存在“二分心智坍塌的残余”而举出的一些现象,却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二分心智》第三部讨论的预言、附体、催眠和精神分裂等现象显示,现代人身上仍有一种易受外力控制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催眠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心理学理论都无法圆满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接受催眠师声音的诱导,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催眠师可以对他们任意摆布。据此看来,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牢固,外部力量总能轻而易举地“入主”某些人的内心。说到内心,如果我们足够坦诚,便应承认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有形形色色的“神龛”存在,现代社会中神谕所和甲骨占卜已然绝迹,但人们或多或少仍在期待来自彼岸世界的谕示,我们身边以各种方式求神问卜的仍大有人在。
对群居的人类来说,个人的主体意识不牢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人是靠集体力量生存的动物,在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中,体型偏小的人类祖先能够战胜那些具备爪牙角翼之利的掠食性动物,靠的就是轻个人重集体的团队协作精神。在老虎狮子眼中,那些聚在一起大声怒吼并掷出石块的众多野人,就像是一只挥舞多个手臂的巨兽。而作为这只巨兽一分子的单个人,则会因自己的群体认同而进入到忽视肉体痛楚与生命恐惧的“战斗恍惚”状态:“处于战斗恍惚状态,大脑会释放缩宫素,人类会有激动、鼓舞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认为其属于一个大大超越自我,并比自我生命更重要的事物之一分子。战斗恍惚的概念,是个体失去了自我意识而获得了新的集体认同”(乔丹尼亚 75)。二战中日本“神风突击队”用撞机方式与对手同归于尽,属于“战斗恍惚”的典型事例。调查资料显示,驻伊拉克等地的美国士兵战前会在重摇滚乐伴奏下大声唱歌和跳舞,要不然他们就无法振作起精神投入战斗(乔丹尼亚72)。“战斗恍惚”的功能在于让人忽略一己之安危,以便个体的“小我”服从于集体的“大我”,这说明人类意识很容易进入某种“被控”或曰“被主宰”状态。与“战斗恍惚”相类似,父母保护自己的孩子时也会有奋不顾身的表现,此类不假思索的自我牺牲非后天理性所能干预,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高等动物都有这种天性。为了种群延续和生命繁衍,造物在基因层面上便作了这种设计。
还应看到,将个人行动的主宰权交给集体,不仅仅发生在与敌人或危险作斗争的场合,由于融入集体能带来身心安宁与诸多保障,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会秉持一种随大流的心态。主体意识即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意识,其要义可归纳为意识到自己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主宰,在与客观世界打交道时自己居于主导和主动的地位,等等。不难看出,一旦“吾从众”成了多数人的习惯甚至是本能,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便成了整个社会心理中的稀缺物质。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总会以种种表达方式提醒人们勿忘自我的存在。笛卡尔看到人的视听触嗅味等感知都是可以怀疑的,而唯一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时的“怀疑本身”,因此“我思故我在”强调的是人人都有一个能够反思自我存在的“自我”。假如没有这个独立于肉体的自我怀疑能力,人就成了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的“兽性机器”(所谓“哲学僵尸”)。汉娜·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时大力批判的“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导致的罪恶),则是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泯灭后结出的恶果——集体有时也会做出不道德乃至反道德的决定,如果不作思考一味顺从体制,任何人都有可能像艾希曼那样犯下反人类罪行。
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早有警惕,《礼记》提到人应自别于“禽兽之心”,陆九渊在孟子思想基础上提出“发明人之本心”,要求人们“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注意“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297—301;卷三十五)。王阳明进一步将人的主体意识推上万事万物的“主宰”地位:“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124;卷三)。陆王心学探究的都是“人之本心”,王阳明称“致良知”为“圣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1278—79;卷三十四),这一论断值得所有研究主体意识者深思。陆王之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许多人也一再主张“自作主宰”,曾国藩自认仅有中人之智,他之所以能效法王阳明,在立德、立功和立言上均有卓越建树,与其对心性的磨砺与坚守有密切关系。验诸中国历史,大凡建功立业之人皆有“自作主宰”意识,否则便有满腹韬略也难成大事。
1948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作过一场名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座,所谓“半个人”,指的是文理分科后知识与人格裂为两半。这种不完整的人让我们想到连“半个人”都够不上的原始人——经过一百多万年的体质进化,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从外观上说已经与今人无异,人类学家裴文中曾戏言他们如果穿着现代衣服走到王府井的大街上,不会有人看出破绽。人之为人当然不是因为外形,按说这种脑袋里空空如也的人不可能真正存在于现代社会,然而事实是今天我们周围不但有梁思成所说的“半个人”(The Half Man),还有T.S.艾略特用诗句讽刺过的“脑壳中装满了稻草”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从“空心人”到“半个人”再到“自作主宰”的人,这一心智进化过程和体质进化过程一样,也须耗费漫长的历史才能最终完成,因此目前三种人同时并存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奇怪。“平庸之恶”在20世纪的挥之不去,极为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不完整的人,主要是就心智而言,与知识水平或文化内涵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陷入“平庸之恶”的既有缺乏思考的芸芸众生,也有著书立说的精英人物。海德格尔从哲学高度思考过受集体控制的日常在世问题,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对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有过入木三分的描摹与批判,然而这些描摹与批判恰好成了他本人日后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写照。在我们这边,经历过文革的学界领军针对自己曾经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历史,发出了“要听自己的”这样的反省之声。如此看来,“自作主宰”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三、“to be or not to be”——为何许多人物都处于两难境地
对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有了如上认识,回过头来再看人物的内心声音,我们就会明白这是自主意识在与“被主宰”状态作斗争,是心智中“自作主宰”的冲动在向大脑神经中枢发送信号。只有将叙事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书写置于上文描述的人类心智进化史中,我们对这一对象才能获得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或者说只有看到了这一宏大背景,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文学中会有谵妄型听觉叙事的出现。当然,这样的表述还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习惯于把文学看成是现实的镜像。事实上,文学本身也是一种现实,谵妄型听觉叙事作为文学中的异数,书写的是意识深处很少“见光”的内容,研究上文提到的“心理历史”或曰人类的认知历程,不能忽视意识对意识自身的特殊书写。从这一意义上说,杰恩斯认定《伊利亚特》是历史,与我们古人所说的“六经皆史”有异曲同工之处。
要认识谵妄型听觉的发生以及叙事作品中的相关书写,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意识会以声音而不是以别的形式出现。大脑中虽然没有听觉器官,但幻听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在外界没有声音发出的情况下,人们仍有可能产生某种虚幻的听觉感知。幻听的出现机率之所以远远高于幻视、幻嗅和幻触等其他幻觉,或许是由于迄今为止的人际沟通还是以声音模式为主,在一定条件下,大脑对信息的处理会因惯性而更多作用于人的听觉神经。不仅如此,意识与声音之间还有一种“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的特殊联系。笔者在《释“听”——关于“我听故我在”与“我被听故我在”》一文中提到,在当前这个过分依赖眼睛的“读图时代”,人们一般认为视觉的作用远远高于其他感知,但“看”不能直接看到自我,而“听”到自我则无须通过其他媒介:在说给别人听的同时,我们也在说给自己听,我们通过这种“说”与“听”感觉到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存在,这似乎是许多人总要说个不停的原因(129)。德里达从此类现象中悟出意识与声音的同一性,他认为“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
向某人说话,这可能就是听见自己说话,被自我听见,但同时,如果人们被别人听见,也就是使得别人在我造成了“被听见—说话”的形式下在自我中直接地重复。直接重复“被听见—说话”,就是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而再产生纯粹的自我影响。[……]从理想意义上讲,在言语目的的本质中,能指很可能与直观追求的并导引“意谓”的所指绝对相近。能指会变得完全透明,因为它与所指绝对相近。(101—102)
德里达之所以把声音等同于意识,是因为听见自己说话属于“不求助于任何外在性”的内部传导,这种传导中能指与所指几乎融为一体,声音因此成为一种与自我意识“绝对相近”的透明存在。德里达接下来的一句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绝对相近”:“当我看见自己在写或用手势表达意义而不是听见自己说话的时候,这种接近被打断了。”
幻听现象还与听觉预期有关。所谓听觉预期,指的是听话者总是在预期说话者要说些什么。人类能从语音中听出意义,关键在于对音素间与语义相联系的差异有高度敏感,这种敏感使得听者总是处在某种“猜测”状态,即试图弄清楚说者发出的一系列语音是否符合预期的意义。语言学家史迪芬·平克据此提出了一条重要定律——“我们只听到我们期待要听见的话”:
人类的语音知觉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的。或许我们一直不断地在猜说话者接下来要说什么,把我们一切有意识或无意思的知识都派上用场。[……]我们只听到我们期待要听见的话,我们的知识决定了我们的知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跟客观真实世界有直接的接触。在某个意义下,由上而下强烈导向的听觉,会是个几乎不受控制的幻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是问题所在。(229—30)
“从上而下强烈导向的听觉”,决定了我们是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去猜测听到的声音,平克因此把人类的语音知觉称为“几乎不受控制的幻觉”。农夫把布谷鸟的叫声听成“布谷”,诗人把鹧鸪啼鸣听成“不如归去”,前述王阳明在半睡半醒之中听到有人在谈格物致知之道,这些其实都是听者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听者自己的心声。
二是为什么意识会以神或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声音出现。前文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古人相信自己是在神的统治下生活,因此一言一行要听神的谕示,现代人由于心智进化过程尚未最终完成,意识深处仍然留有神的身影。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是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主动拆除自己心中的神龛,就一定意义而言,许多人还是更愿意处在某种“被主宰”状态。甚至可以这样说,与“自作主宰”相比较,“被主宰”更符合芸芸众生的常态。“被主宰”需有主宰者方能实现,虽然后神话时代的世俗生活中已经没有神的位置,但人们仍然会在自己心中建构起形形色色的主宰者。E.W.J.谢林说:
神话过程中,人所应付的不是一切事物,而是那些由自身意识内部升起并对其有支配作用的力量。神话的形成缘于神的谱系化,这一主观历程发生在意识之中,并通过产生表象来显示自己。虽然这些表象的原因和对象确实与神谱的力量有关,但正是通过这样的力量,意识显示出自己归根结底是一种“假定有神的意识(God-positing consciousness)”。(144)
谢林的意思是人有一种自我造神的自然冲动,作为表象的种种神话其实都是意识的外显与幻化。从信奉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到后来想象出与人“同性同形”“同感同欲”的人格神(泰勒 599),应该说是人类心智的一大进步,因为这时候他们是按自己的模样造神,按自己的社会关系编排神谱。只有通过信奉各方面都更像自己的心灵主宰,人类才有可能缓步走向对自己的主宰。
如果说“假定有神的意识”使人释放出支撑自身的内部力量,那么这种“假定”或曰自我设缚在后神话时代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西方国家中,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男男女女不会不知道上帝本是子虚乌有,但许多人还是会定期去教堂向神祈祷,就连美国总统就职时也是手执《圣经》宣誓。“祭神如神在”有利于保持心理稳定,要想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莫过于假定头顶上方有一个时刻都在为自己保驾护航的“主宰者”。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指出叙事中的话语权威缘于虚构(6—7),但与现实生活中种种树立权威的做法相比,这类纸面上的游戏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史记·陈涉世家》写陈胜、吴广将写有“陈胜王”的帛书藏于鱼腹,并在夜里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这一策划果然产生了神化陈胜的效果。一般来说,群体对“虚构的权威”会有一种下意识的敬畏和顺从,因为多数人相信“人事”抗不过“天命”:仅凭个人努力不可能出人头地,权力和威望须由某个更高的权威来赋予,如果没有这种更高权威便得去虚构一个。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奥运举办国仍然要从希腊的奥林匹亚神庙前采集“圣火”,这说明当代生活中仍有对“虚构的权威”的需求。
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中,“假定有神的意识”更有理由大行其道。许多西方诗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阿波罗或缪斯的祭司,把诗神看作自己的灵感来源和精神主宰。18世纪的弥尔顿说其诗作出自诗神纡尊降贵的“口授”,19世纪的济慈觉得莎士比亚是自己心中的“主宰者”(Presider),20世纪的欧文又把济慈当成自己的“主宰者”。与弥尔顿的被“口授”相似,中国古代诗人也有不少神差鬼使般的创作经历,脍炙人口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据称来自“鬼谣”,“梦中得句”之类的事例在我们的诗歌史上屡见不鲜。国人心目中的天才诗人非仙即圣,李白、杜甫和苏轼之所以有“谪仙”“诗圣”和“坡仙”之称,是因为人们觉得写出超凡脱俗诗句的人一定不是肉体凡胎。汉字的“诗”有“寺”旁,叶舒宪说“寺”的本义指主持祭仪的祭司或巫师,诗人来自过去的“寺人”(135—52),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诗人”这一概念在中西双方都有某种通灵、附体内蕴。与祭司、巫师的通灵、附体不同的是,诗人的“被主宰”实际是被一股巨大的艺术力量所攫获,借用上引谢林的话来说,这股力量是“由自身意识内部升起并对其有支配作用”——诗人在创作状态中感到自己与想象中的诗神或曰艺术真谛接通了联系,进入了一种若有神助般的“下笔不能自休”状态。狂热状态从来都与谵妄症候携手同行,在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看来,小说诗歌的作者都是白日梦患者,文学家的灵感袭来之时,便是这种疾病的发作之日。
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物。如果说作者都是白日梦患者,那么创作便是白日梦患者进行自我治疗的手段。虚构故事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心头郁结的纾解过程,因为作者会把自己的意识投射进故事世界之中,让人物充当自己的“替身”去经历种种磨难与考验,这个过程一旦完成,作者自己也获得某种解脱。歌德便是借着讲述少年维特的故事,治愈了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情创伤。古今中外的故事多如恒河沙数,但若用诺思罗普·弗莱提出的“向后站”方法对人物行动作“远观”,便会发现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被作者置于“to be or not to be”的两难境地。西方文学中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冉阿让、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马克·吐温的哈克:哈姆莱特为复仇问题煞费踌躇,浮士德在尘世享乐与精神追求间彷徨不定,冉阿让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罪犯还是好人,聂赫留朵夫体内“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激烈交战,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名本义就是“分裂”,哈克在帮助黑奴逃跑的同时不断想告密。中国四大小说名著中的主要人物,全都同时具有正统与非正统的双重身份——贾宝玉既是荣国公之孙又是来人间讨“泪债”的神瑛侍者,孙悟空既是天宫的齐天大圣又是花果山众猴之主,宋江既是九天玄女口中的“星主”又在水泊梁山“把寨为头”,刘备既被天子称为“皇叔”又是有结拜兄弟的民间豪杰,这些双重身份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撕扯他们,逼迫他们委屈自己的天性与内心来履行对正统社会的责任。贾宝玉这方面的反应最为典型,他动不动就对姊妹们说自己要“死”要“化灰”或者“化烟”,只有心灵深处被严重撕裂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讨论至此,“to be or not to be”后面的意义似有进一步浮现。哈姆莱特的这一名言在我们这里有“生存还是毁灭”与“干(做)还是不干(做)”等译法,笔者认为与“be”最接近的汉译还应是“为”,“为还是不为”可以将“行事”“为人”的意思都包括在内。行为决定本质,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由其所作所为决定,但是采取什么样的作为说来容易,真正面临重大抉择时却让人左右为难。现实生活中许多貌似有主见的人,在需要做出决断时往往都有哈姆莱特式的表现,这或许是莎士比亚此剧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扪心自问,大多数人在事到临头时都会有莫衷一是的惶恐,临危不乱的自作主宰者在人群中总是凤毛麟角,许多事实表明今人并没有彻底摆脱杰恩斯所说的二分心智状态。至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叙事作品中会有那么多人物处于两难困境与谵妄状态——“to be or not to be”这类自言自语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显示出说话者渴盼获得内心神明的指点,意识活动的这类“返祖”现象在许多叙事作品中都有表现。
苏珊·桑塔格说肺结核有“加速”和“照亮”生命之功(14),谵妄状态对叙事来说亦不是什么坏事,人物语无伦次的述说给了我们窥见其内心活动的大好机会。呓语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只有无所适从造成的巨大压力才有可能冲开内心独白的阀门。许多人物如果不是处在谵妄状态,不会毫无保留地倾吐自己胸中隐藏至深的焦虑与块垒。《红楼梦》中的《葬花吟》堪称千古绝唱,来人间偿还“泪债”的林黛玉作为故事中注定要被毁灭的人物,在诗中既是“手把花锄”的“闺中女儿”,又时时以被“风刀霜剑”摧残的花枝自况,这就导致其意识在两者之间来回切换,形成两种自我(所谓主格的“I”与宾格的“me”)之间的对话,“奴”“侬”“尔”等人称的交替使用更令叙事主体的声音呈现出微妙的复调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在“杀还不是杀”问题上犹豫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这样把自我的一部分当作“你”,巴赫金注意到这个人物的大段独白中“常用‘你’字,就像对别人一样”(325);他还这样评论陀氏《白痴》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的声音分裂为两种声音,一是认为她有罪,是‘堕落的女人’,一是为她开脱,肯定她。她的话里到处是这两种声音的交锋结合,时而这个声音占上风,时而那个声音占上风,但是哪个声音也不能彻底战胜对方”(350)。
中国古代叙事讲究“省文寡事”,少有西方叙事那样的大段心理描写,但我们的古人擅长用“镜像人物”来影射人物内心的分裂与斗争。这种人物表面上与故事主人公相同相似或有某种特殊联系,实质上却是其行动与性格的倒影摹拟:四大小说名著中,最终屈服于“仕途经济”的甄宝玉,自拉队伍去西天取经的六耳猕猴,时刻想抡起板斧造反的李逵,以及“名为汉(魏)相实为汉(魏)贼”的董卓、曹操父子与司马懿父子等,分别暗示贾宝玉、孙悟空、宋江和诸葛亮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故事主人公心中的一念之“恶”。《西游记》第五十八回六耳猕猴所说的“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天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瞻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听上去就像是孙悟空内心一闪而过的念头。孙悟空挥动金箍棒将六耳猕猴劈头一下打死,和宋江借药酒毒死李逵一样,都是用行动来消灭自己的心上魔头;贾宝玉义无返顾地离家出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辅佐后主,与甄宝玉、司马懿两位反面教员的刺激也不无关系。韩非将战胜自己胸中的杂念称为“自胜”,此说有助于今人揣测四部小说未曾明写的人物心理。
小 结
以上所论,简单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四条。
1.杰恩斯认为人类意识萌发于三千年前,此说尚未得到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撑,但二分心智说让我们认识到人类主体意识的建构是非常缓慢的,今人仍然处于从二分心智人到自作主宰者这一进化过程之中,所有研究“人学”者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2.内心声音在人物脑海中响起,总体上看属于上述进程的伴生性反应——如同青春痘显示出某人处于青春期一样,这类声音的出现也透露出人类心智中“被主宰”与“自作主宰”之间的斗争。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固然值得注意,但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对意识本身的书写,更何况这种书写还能达到其他书写无法企及的深度。
3.谵妄在医学上被定义为病态,但人人都有可能发生轻微的谵妄,以幻听来折射人物内心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叙事策略。我们总倾向于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成完全正常的人,实际上他们经常被作者置于谵妄状态。莫言由于善于此道,瑞典文学院在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称其手法为“谵妄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
4.学界当前关于“后人类”问题的讨论,给人的一个印象是人类自身的心智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要考虑的是机器人的心智问题,本文对谵妄型听觉叙事的系统考察,旨在显示“to be or not be”仍然是人类心智进化过程中没有迈过去的坎,因此今人在担心机器人摆脱人类的控制时,也要想想人类自身意识是否完全受我们自己主宰。
注释[Notes]
① “昔韩娥东之齐,匮于粮,过雍门,鬻歌乞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列子·汤问》)。
②“(王阳明)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王守仁 1228)。
③ Jaynes, Julian.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84-99.按,杰恩斯所说的“意识”(consciousness),主要指人的“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④杰恩斯作此类宣称时多用“意识”而不用“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
⑤“The Iliad is not imaginative creative literature and hence not a matter for literary discussion.It is history,webbed into the Mycenaean Aegean,to be examined by psychohistoric scientist”(Jaynes 76).中文引文中的重点号为本文所加。
⑥史诗第1卷中,阿伽门农当众宣布要从阿喀琉斯手中夺去其心爱的女俘布里塞伊斯,后者作为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希腊英雄,居然没有拔出剑来阻止这一令己蒙羞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赫拉派来的雅典娜在暗中揪住了他的金发,命令他只可咒骂不可动武。当然这一切是旁人看不到也听不到的(Homer 15-22).
⑦“To hear is actually a kind of obedience.Indeed,both words come from the same root and therefore were probably the same word originally.This is true in Greek,Latin,Hebrew,French,German,Russian,as well as in English,where‘obey’ comes from the Latin obedire,which is a composite of ob+audire,to hear facing someone”(Jaynes 97).
⑧史诗第19卷中,阿伽门农如此解释自己当初的糊涂作为:“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过错——/错在宙斯、命运和穿走迷雾的复仇女神,/他们用粗蛮的痴狂抓住我的心灵,在那天的/集会上,使我,用我的权威,夺走了阿喀琉斯的战礼。/然而,我有什么办法?神使这一切变成现实。/狂迷是宙斯的长女,致命的狂妄使我们全都/变得昏昏沉沉”(Homer.The Iliad.Trans.Samuel Butler.New York:Barnes&Noble,2008.312).此说在现代人看来纯属推诿,但阿喀琉斯等人却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解释,因为他们也是如此听命于神。
⑨史诗第17卷中,阿波罗数次幻化为不同人物为赫克托耳打气,雅典娜则变形为赫克托耳最亲密的朋友得伊福玻斯为其助阵,当赫克托耳对阿喀琉斯一击未中向身边的战友索要长枪时,却发现这位得伊福玻斯早已不见踪影,赫克托耳迫不得已拔出佩剑与阿喀琉斯搏斗,最终被后者的长枪刺穿喉咙(Homer 276-93)。
⑩见Jaynes 447-48。按,该书再版时收入了杰恩斯1990年撰写的后记,其中叙述了这个故事。
[11]罗伯特·索耶被认为是加拿大科幻小说之父,其作品曾囊括科幻文学奖项的所有最高奖,《WWW.苏醒》是其《WWW》三部曲的第一部,后面两部分别是《WWW.注视》和《WWW.惊奇》(中译本2013年已由中国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
[12]HBO公司2016年推出的这部电视连续剧(第一季共10集)汇聚了众多大牌明星,其创意虽源自1973年的同名电影(国人观看过的《未来世界》为该影片的继集),但由于二分心智理论的注入,《西部世界》的故事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
[13]在中国,孔子、老子等圣人就是人类中涌现的发声者,所以“圣人”在古代又被称为“声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德经》帛书本如此记载)。
[14]2016年7月23日,一名女游客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下车后被老虎拖走,其母见状不顾危险下车追赶,结果不幸命丧虎口。
[15]1961年4月—5月,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对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平庸之恶”这一概念见于两年后阿伦特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嗣后她又出版了《反抗“平庸之恶”》等著作。
[16]该报告未收入200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出版的《梁思成全集》,文字记录疑已佚失。
[17]T.S.艾略特有诗名《空心人》:“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填充着草的人/倚靠在一起/脑壳中装满了稻草。唉!”Eliot,T.S.. “The Hollow Men.”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74.77-82.
[18]“在世的展开状态的这一存在方式却还把共处本身也收入统治之下。他人首先是从人们听说他、谈论他、知悉他的情况方面在‘此’。首先插在源始的共处同在之间的就是闲言。每个人从一开头就窥测他人,窥测他人如何举止,窥测他人将应答些什么。在常人之中共处完完全全不是一种拿定了主意的、一无所谓的相互并列,而是一种紧张的、两可的相互窥测,一种互相对对方的偷听。在相互赞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对的戏。”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6—47页。
[19]“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后听谁的?……后来想清楚了,还是要听自己的,不能听别人的。因为听别人的,你犯了错误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81页。
[20]“但愿天上的女诗神允许给我/与此相应的文体和风格。/她,天诗神曾自动地每夜降临/访问我,在我睡蒙胧中口授给我,/或给以灵感,轻易地完成即兴诗章。”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12页。
[21]“我记得你说过好像有某个好心的天才在主宰着你——近来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在半随意状态中写下的东西,被后来的冷静判断肯定为写得非常恰当——把这个主宰者想象成莎士比亚是否太大胆了一点?”约翰·济慈:“一八一七年五月十、十一日致B.R.海登”,《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7页。按,为了增强这种“被主宰”的感觉,济慈甚至经常坐在莎士比亚画像下写作。
[22]“在其短短的人生历程中,欧文以一种宗教般的热情崇拜济慈,就像莎士比亚一直是济慈的‘主宰者’(Presider)一样,济慈也在欧文身上发挥了这种‘主宰’作用。”傅修延:《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433页。
[23]“(钱起)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鵩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鵩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旧唐书·钱徽传》)。
[24]英语中,用于形容艺术家的“创造”和“天才”等词语最初均有神性。“‘创造’意味着像神那样制造出在创造行为之外没有前例的东西[……](艺术家)因此被设想为具有类似于神的特征。”“‘天才’(genius)最初是一个精灵或守护神,它附着于人的躯体,操纵他们去做一些超越凡人能力的事情。拥有最高‘创造力’的人便是‘天才’。”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悭、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25]“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韩非子·喻老》卷七)。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Bakhtin,M..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Polyphonic Novel Theory.Trans.Bai Chunren and Gu Yaling.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8.]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1990):99—112。
[Chao,Fulin. “On the Divine Right of the Yin Dynasty.”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1990):99-112.]
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Derrida,Jacques.Speech and Phenomena.Trans.Du Xiaozhe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0.]
南希·法默:《鸦片之王》,陈佳凰译。广州:南方出版社,2016年。
[Farmer, Nancy. The Lord of Opium. Trans. Chen Jiahuang. Guangzhou: Southern Publishing House,201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Freud,Sigmund.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Trans.Lin Keming.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5.]
傅修延:“释‘听’——关于‘我听故我在’与‘我被听故我在’”,《天津社会科学》6(2015):117—33。
[Fu,Xiuyan.“Interpretation of‘Listen’ — On‘I listen,therefore I am.’ and ‘I am listened,therefore I am.’”Tianjin Social Sciences6(2015):117-33.]
Homer.The Iliad.Trans.Samuel Butler.New York:Barnes&Noble,2008.
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
[Jaspers,Karl.Way to Wisdom.Trans.Ke Jinhua.Beijing: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Press,1988.]
Jaynes,Julian.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0.
约瑟夫·乔丹尼亚:《人为何唱歌:人类进化中的音乐》,吕钰秀等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
[Jordania,Joseph.Why do People Sing?:Music in Human Evolution. Trans. Lv Yuxiu, et al.. Shanghai: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2014.]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Lanser,Susan Sniader.Fictions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Trans.Huang Bika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2.]
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
[Lu,Jiuyuan.Complete Works of Lu Xiangshan.Beijing:Cathay Bookshop,1992.]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
[Mo yan.The Garlic Ballads.Beijing:Contemporary World Press,2003.]
史迪芬·平克:《语言本能——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洪兰译。台北:商周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Pinker,Steven.The Language Instinct: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Trans.Hong Lan.Taipei:Shang Zhou Press·Cite Publishnig Ltd.,2015.]
奥利弗·萨克斯:《幻觉:谁在捉弄我们的大脑?》,高环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Sacks,Oliver.Hallucinations:What Hallucination Reveals about our Minds?.Trans.Gao Huanyu.Beijing:CITIC Press,2014.]
Schelling,E.W.J..Historical-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ythology.Trans.Mason Richey and Markus Zisselsberge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
Sidgewick,Henry,et al..“Report on the Census of Hallucinations.”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34(1894):25-394.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Sontag,Susan.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Trans.Cheng Wei.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3.]
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杨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Stowe,H.B..Uncle Tom’s Cabin.Trans.Yang Yi.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4.]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Tolstoy,Leo.Anna Karenina.Trans.Cao Ying.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7.]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Tylor,Edward.Primitive Culture.Trans.Lian Shusheng.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5.]
维柯:《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Vico,G.B..New Science.Vol 1.Trans.Zhu Guangqi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9.]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下册,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Wang,Shouren.Complete Works of Wang Yangming.Eds.Wu Guang,et al..2 vols.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2.]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Ye,Shuxian.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to the Book of Songs.Wuhan:Hubei People’s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