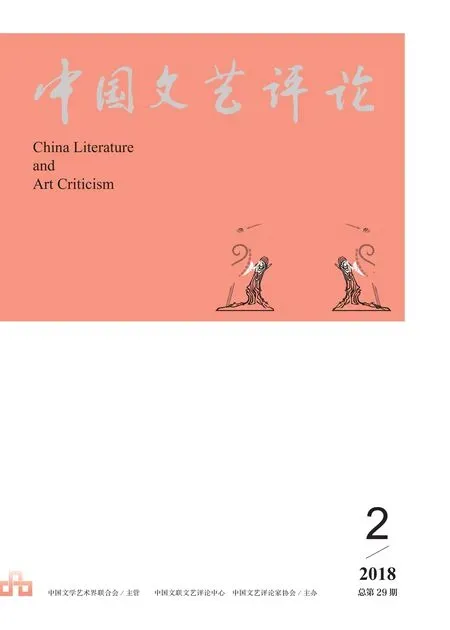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话语体系的价值与路径
夏燕靖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所谓“话语体系”,其定性有两点:一是构成话语体系内涵、定位和功能的明确性;二是话语体系具有完整表达的方式方法,这是话语体系对应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据此,在讨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同时,对于其理论建构之当代阐释话语体系的追踪探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理由十分明确,即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在数千年积淀传承中,虽说发挥了令人惊叹的历史作用。但在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它根植的社会文化土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完全改变,遂使得这一理论进入到一个传承命运多舛、艰难且尴尬的境地。曾经无论是推崇备至、更替继承,抑或贬损否定、弃如敝履,到如今如何延续其文脉则成为又一次需要慎重思考的现实问题。自然,从现实角度来说,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阐释话语体系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一理论成为过去式,而是在传承中不断获得发展,被赋予其应有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能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认清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话语体系的定位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话语体系如何在当今条件下形成自己的特色,抑或是打开新的局面,这是学界关注的问题。这实际上关系到弘扬古典艺术理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更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大问题。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一种理论意识的自觉,或者说是一种研究境界的突破,以求在新的历史交融点上达到一种新的理论创新。至于说到现实文化建设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现实文化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纳入其中,使之转化提升为适应新要求、新任务和新内容的艺术理论;另一方面在提倡重视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定位,即明确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的“源”与“脉”,以及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主体部分。
换言之,在当代语境下讨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阐释话语,可以说与当下社科界开展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讨论有较为直接的关联性。“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探讨的问题都是关注当今学术发展进程中对于学术话语的建构。进言之,这种建构意味着一种学术自觉性的增强,即对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具有批评性质,以批评的方式检讨学术话语的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带有建设性质,以建设性姿态来探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当然,需要特别阐明的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涵盖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阐释话语。这样的话语体系,不是表面的、纯粹的形式议题,亦不是某种话语的表述问题(虽然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需要深入到话语体系内容当中去理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其核心就在于,如何能够真正契合,或者切近当今的中国问题,开启新的思维,从而使这样的学术话语以学术的方式被理解和运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深植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当中而被建构,因而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全部探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其现实问题真正地展现出来。由此推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阐释话语有一个基本尺度,即对其话语体系建构有一种现实的定向。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阐释话语,一方面是和话语体系与学术自立有关,体现该学术话语体系与整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和走向的契合度,另一方面体现出其自身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创新,再有就是内在和外在的勾连与借鉴。进言之,学术反映的是一种思想,即学术是以一定的指导思想为其理论基础。举例来说,从中国历史观来讲,有研究者概括认为:“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大的跨越,即从古代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再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起来,并在50年代后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因此,探索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从学术思想上看,不能不考虑唯物史观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应该考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发展,揭示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是从旧学到新学的跨越,也是从低级不断走向高级而有规律的发展进程。这其中特别是涉及对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文化遗产与当代学术话语的建构问题,引发学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联系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理论发展进程的现实来看,这一时期也是被外来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潮左右最多的历史时期。
这里,以笔者撰写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学史》为例,书中将此历史阶段分期列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至1978年为一个大的历史划分阶段;另一个历史阶段则是1978年至今。与本书讨论话题相关的前一个历史阶段,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78年,属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学的酝酿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和艺术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当然这离不开“西风东渐”的影响。根据现存资料来看,作为学科名称的“艺术学”提法可追溯到1922年俞寄凡翻译的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自此,“艺术学”这一学科称谓在中国学者的文章著述中多有出现。这里仅举书中两例,宗白华从德国留学回国任教,即1925年曾以“艺术学”为题做过系列讲演,并留下系列讲稿,两篇讲稿基本都是围绕来自德国的艺术学进行的传引。宗白华对艺术理论的认识有许多是接受德国批判艺术史家或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观点,诸如,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in)的艺术风格学、李格尔(Alois Riegl)的艺术意志观等。对照之下,宗白华的观点在当时是以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为基础,导致他在认识艺术问题上,总是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除宗白华外,同一时期,上海美专教授张泽厚于1933年在光华书局出版了《艺术学大纲》。该书引用“文化”拉丁语词源作立论,“用以指称人类所以优越自然的一切努力的成果,所以完成生活的劳动及思维底一切成果。”更为关键的是,张泽厚将艺术归之为文化形态的一种,主张“在我们用科学方法来说,艺术是从头至尾,彻底都是表现人类底实生活的!因为艺术是和人类实生活结合的一种文化形态”。就艺术与其他科学的关联,张泽厚也进行了详细论述,包括与宗教、哲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并没有脱离前人的窠臼,而是创新性地将艺术与社会科学关系也纳入讨论的范围。既然社会科学被视为“研究社会现象——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一种科学”,由此观之,“艺术是社会底意识形态之一种(此种意识形态是精神的。如宗教,哲学一样,同是精神的)”。张泽厚强调,艺术不仅与宗教、哲学及社会的基础经济有关,它与政治、法律、道德、风俗等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张泽厚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受西学影响至深的艺术理论观念。
“今天,当我们以国际的视野来看艺术学研究的当代进展时,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诞生一百多年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艺术学的研究,与艺术自身多样化形态的迅猛发展相比,无论是从具有创新性的艺术学研究成果、代表性的理论大师还是从推动这一学科递进发展的理论等方面来看,都相对逊色得多,尚没有形成具有整体性的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尤其是艺术学及其研究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诸多探索也还没有与中国传统具有独特审美理想和评价标准的艺术理论交融和对接。“由于尚不具本土生命力且自身理论基础薄弱,到上世纪40年代末,我国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陷入沉寂。”及至新中国成立,一批以重要的艺术理论家、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在艺术理论研究、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领域成果颇丰,但由于“文革”时期,左倾主义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端化,导致这一时期反映艺术规律和体现科学方法的整体性的艺术学研究根本无从谈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少学者重新开展并推动中国艺术学研究,呼吁确立艺术学的学科地位。由此可见,需要确立这样的建构基点,即明确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古至今有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逐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另一方面是与治学方法论的介入有关,即在当代语境下所谓的学术问题,不仅需要在问题意识上形成自觉,更要在方法论上形成自觉。所谓的“问题意识”,包含两个因素:“思维”与“问题”。人们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学习经验、社会经验对各种情况、问题进行总结,最终提炼出各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通过提出问题,给予思维以动力,使人们以疑惑为出发点,以探究为路径,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积极思考,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对树立“问题意识”的认识已不局限于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上,更重要的是针对问题能够有适应的方法论来作支持。比如说,现在讨论最多的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问题,自然离不开方法论的自觉,即自觉坚持以“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是方法论所起到的支撑作用。如此说来,所谓治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一定有其现实意义。比如,学界一些不善于联系现实考量的学者治学,往往用西方理论教条来解释中国问题,以致引起严重误导。经济学界有识之士归纳出一种现象,叫作“‘要理论不要实践,要外国不要中国’的‘盲从西学’现象”。其实,艺术学界也或多或少存在此类问题。在艺术学理论界此风也有盛行,诸如,一股片面追求以西学阐释问题的现象,以致中国话语被边缘化,在学术研究中“失语”“失声”,特别是在构建当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过程中,大量直接使用西方艺术理论来作依据,或是用西方话语来作分析,套用西方理论范式诠释和解释中国问题,甚而不加以中国化的重构或改造,结果只能是生搬硬套,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说,理论研究在今天重视方法论的运用,其本身就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必须是针对现实需要的方法论。
从上述分析来看,话语体系本身就是学术立场,自然也是学术思想的真实体现。试想,如果我们的学术没有自己科学合理的话语体系,那么,必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丧失话语权。不容置疑,话语体系是由一整套学术支撑才得以确立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由此而论,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不仅承载着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阐释两个“承载”的价值诉求,而且关乎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设的现实转化,是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认清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方法论及运用,在当代语境下如何阐释,是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一项重要且紧迫的课题,也是构建有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的关键。学界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或者涉及“话语符号理论”的探讨,已然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论,是学科与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用学界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人文学科日益“科学化”。比如,运用现象学视角来分析和探讨艺术理论的“悬置”问题,就有多位学者主张在借鉴与超越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从而依据现象学“朝向实事本身”这一命题拓展,即通过一种“直接认识”加以描述现象的方法进行研究,以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来分析问题和阐述论点。而“现象”总是以更多的富有背后重要性的意义给人以启示,由之,必须有方法获得确证的理解,这里的“现象学”研究便是通向认识与启示的重要途径,这样的现象学方法论就属于人文学科“科学化”之一种,这对于艺术学的学科化建设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举例来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套独特的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理论思维特色的范畴体系。“它既是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历代艺术家用以进行艺术批评与鉴赏的认识工具。”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是一部“艺术范畴”的文本研究,无论是从学科性质上,还是从研究对象的特性上说,都非常有必要加强对古典艺术理论的范畴问题进行研究。从现象学角度分析来说,针对文本研究关心的首先是文本范畴的现象。那么,我们能够研究的现象是什么呢?用胡塞尔一生所关心的问题来推论,就是“精神”(Geist)和“意识”(Bewusstsein),而现象正是研究“精神”和“意识”的真对象。此时,现象这个概念就被赋予极大的意义。然而,仅仅以所谓的“现象学”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仍然是有局限的,尤其是涉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话语体系”的论题,则多少带有特定的地域和时空上的认识差异,如果硬要以现象学方法论的阐释路径来作依据,的确会是强行阐释,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任何方法论都需要我们以辩证的方式来对待,诸如,备受当今艺术理论界关注的符号学理论,在为人文与社会学科研究提供话语“武器”的时候,其自身的弊端也导致了自身发展的危机。如过于注重语言逻辑分析,甚至将符号学当作数理逻辑那样进行定理推论,美其名曰以精确的要求来衡量语言表达,这便是一种形式化的危机。事实上,就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理论而言,这些其实都是实践的产物,即话语和符号都是为表达思想与目标而确立的“符号”意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大自然物象的敬仰与崇拜一直延续至今。较为典型的是对自然物象的敬仰与崇拜,在艺术创作理论中极为常见。自然物象被作为崇敬的对象,并非是“超验”存在,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可“游”、可“赏”、可“化身”的审美对象。诸如,鲲鹏之美,在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有多种表达,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这里表现的事物,无不是意象的表达,是中国特有的感知方式“观物取象”的叙事方式,是中国艺术话语体系的特色与标志。很显然,构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必须要以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话语体系为根基,任何脱离话语实践活动的所谓纯粹理论探讨,都解决不了中国艺术的真实问题。对于符号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如此,对其他西方理论亦是如此。立足于“中国立场”,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阐释话语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为其构建提供有效的方法论,这应当是方法论研究和运用的当务之急。
其实,对于方法论的认识在中国古已有之,如孔子就有方法论的阐述。《论语·子罕》有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分析来看,就是讲的方法论。孔子以“叩其两端”为回答,即主张应该从问题的两端展开探究,而强调“竭焉”,可以理解为是追问,寻找到终极答案为目标。况且,孔子还突出表达了方法论的应用,就是对问题的认识,可以从“无知”到“有知”,而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又有“空空如也”“叩其两端”和“竭焉”三个步骤或三个环节。方法论说到底,犹《庄子》“庖丁解牛”之说,掌握其原理便运斤成风。所以说,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不同的文化产生的意识观念、研究方法自然就带有各自显著的特征。因此,中西方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各自的特点,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学和西学在各自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进行发展。尽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在解读不同文化之间学术观点时也大都会扩展到文化理解的范畴。然而,东西方学术差异是始终存在的,从而导致中西学术本质上的差异,连带着中西方的话语体系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而不是一个主体意义的表达系统,以至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更是不同。然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西学伴随着经济扩张拥有绝对话语权,不少国内学者深受其影响,主张全盘接受西学观念和方法论,导致部分学者治学时总是戴着西学的有色眼镜来打量中学。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西方思潮对历史、文化、艺术甚至传承千年的伦理观念等问题上有不同程度的同化现象。传统的价值观逐步被破坏,人文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受到冲击,虚无主义者开始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最终否定有中国特色的全部理论基础,成为西方价值观的维护者。因此,“在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理论任务就是正本清源,廓清价值观上的迷雾”。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符合“中国立场”“中国话语”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学术自信的源泉。
三、古典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决定其方法论的独特性
这里讨论的关涉中西治学方法论比较,以及构建中国学术有效方法论运用的问题,应当说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大背景的问题。恩格斯曾说过,文化植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具有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所经历的特殊历史命运而形成的,决定了这一民族只能走适合其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学术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共同构筑起我们的精神家园。
进言之,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决定其方法论的独特性,王充提出“为世用”的原则,即可理解为是一种方法论,曰:“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这表明,自古治学之道于方法论而言,以“为世用者”先。当然,王充的观点有其先决条件,这便是“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王充又说:“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这是富有辩证观的方法论。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认为,诗上可“裨教化”下可“理性情”,曰:“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白居易还认为,褒贬之文惩劝善恶,美刺之诗补察得失,强调云:“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劝惩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可见,中国古代文论中体现出来的方法论,是“教化”与“明达”合一。相比较西学方法论,立于概念“范式”,针对“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直接阐释有所不同,更多是“为世用”的自由裁定。恰如,清黄子云所主张的诗有裨益于世教人心,谓曰之:“由《三百篇》以来,诗不绝于天下者,曰:美君后也,正风化也,宣政教也,陈得失也,规时弊也,著风土之美恶也,称人之善而谨无良也。故天子闻之则圣敬跻,大夫闻之则訏谟远,多士闻之则道义明,匹夫匹妇闻之则风节厉而识其所以愧耻矣。”
对照西学而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各个层面的论理学说,其方法论运用是多样化的。如果系统而深入地加以探究,就会发现所谓的范畴及其体系,以及阐释意义都有独到的方法论给予揭示。也就是说,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积累了一套独特的范畴与概念,它不仅构成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特色,集中体现出论理思维的特性和艺术品鉴的价值,形成其独到的阐述方式。当我们对古典艺术理论中的概念和范畴加以整理和研究,分析其理论体系构成的来龙去脉,在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内涵、特征,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往往既维系着“中国古代艺术之甲令,同时又与传统文化之圭臬紧密相连,是传统书画、音乐、舞蹈等所要追寻的终极价值目标”。当然,我们在认识这些范畴、内涵、特征及规律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方法论的介入,明晰古典艺术理论思想与审美的特定意义,不能在方法论解析概念上一味追求与西学画等号。也就是说,艺术的、文化的,乃至哲学的概念均有“中国式”的独特性,不可以用所谓西学方法论将其全部涵盖,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丰富多彩的思想、审美等概念狭窄化。所以说,我们在探究中国古典艺术理论问题上,要“洋为中用”,自然也要“古为今用”。
比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诸多范畴概念,就是伴随着文论被不断出现的新方法释读而形成新的语义,或是传统语义有了新的演变,或是进入到一个新的语义系统,即语义场,“将相互关联的词汇和短语组织起来,显示其间的新关系和新认识”。就“感悟”范畴概念说,在《汉书·刘向传》中曰“上感悟,下诏赐肖望之爵关内侯”,是有所感触而醒悟或领悟之意;《后汉书·丁鸿传》云“鸿感悟,垂涕叹息”,是指受感动而醒悟。自晋代陆机以来的文学创作论中,“感悟”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表达的是创作主体在特定环境下被偶然激发的创作冲动,如“感兴”“天机”“妙悟”等,表达的多为此意。从心理机制上讲,感悟是创造性思维过程中认识发生飞跃的心理现象,感悟与想象、感悟与体验,可谓是主观情志超乎有限达于无限。其实,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范畴概念,都有如此演变过程。有研究者归纳总结认为:“道、气、中和、阴阳、刚柔、象、文质、通变、形神、自然、才性、境界等范畴,最初都属于哲学范畴,后来被引入文学理论批评,并且随着文学理论批评意识的自觉,而愈来愈被赋予确切、具体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意蕴,从而也就具有了自己区别于作为哲学范畴时的特殊内涵,即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美学含义,亦有了自己特定的使用范围。但是,这些文论概念范畴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哲学思想对它的影响制约,随着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些文论概念、范畴也往往随之而发展变化,从而又增添了新的内涵成分,并且对于文学理论批评产生新的影响和渗透”。同此道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阐释,或是针对其话语体系的探究,都可说是方法论构成的新意。
就上述列举的“感悟”概念进一步分析,可列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方法之一种,如今有学者将之作为“直觉”或“经验”的方式来对待,将其视为中国治学的独特思维方式,以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区别。但“感悟”并非等同于“直觉”或“经验”,其背后是高度抽象的中国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理解“感悟”有“开悟”之意,与“心境”和“心力”有直接关系,是理性经验的揭示,这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传统哲性思维中尤为突出。如《周易》可说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源,其描述方法就是“感悟”。在《周易》中,但凡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伦理、心理、审美和文艺之道的论述,多是通过卦象推演来表达的,即对事理的阐释似乎是具体且形象的,可细读深究起来却又极其抽象,这种思维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领域,使得“感悟”成为解读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方法论。
正因为包括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在内的古代文论都具有“感悟”性特征,也就造成了其解释范畴及内涵的游移不定。所以,在解读或是阐释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尤其是建构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话语体系中,对于方法论的认识与把握十分关键。由于近代以来学术发展受西学方法论影响至深,论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不可谓不注重详细的分析,可针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而言,套用这样的关系论证,却不一定能让人有明朗、清晰之感。即便是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学理论,有些论断也是游移不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很难厘清,如“神思”“兴会”“妙悟”等。文学理论尚且如此,借转而来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更是如此,在阐释过程中多少存在着不清不楚,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的特点。在研究古典艺术理论关键概念时会延伸出众多观点,这些观点相互交错,不免造成阐释的一定难度。如《庄子·外篇·知北游》所云:“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以辩证观点比照出美的相对性。话说开来,如果以作为美的观点之一的“以奇为美”来阐述中国古代艺术的奇美价值取向,可延伸出诸如:正、雅、贞(此三者看似与奇对立)、逸、悲、静、远、轻、俗、幽等概念。不难看出,这些概念很难单独予以讨论,研究“奇”之美不能脱离正、雅、贞这些美的中心观念。“奇”之所以美,无不因为它的“奇”而有正、雅、贞。
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纳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之多,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若以西学范畴概念来作界定,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有的可能仅带有随意性地出现于某篇文论,倘若在使用时,未作概念内涵的界定,很难说会有连贯使用的意义。像这类范畴,是概念抑或是术语呢?另外,在中国古代文论,抑或古典艺术理论中还有过专题论述的“诗言志”“诗缘情”等,有研究者将其当作范畴,也有研究者认为只是文论短语,或许可以当作一个完整的文论观点,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复杂问题,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对范畴概念作界定,来明确其研究对象,但有些则难以作具体界定。借学者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一书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辨析来看,对于“范畴”与“概念”的关系,他认为,“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概念是对各类事物性质和规律关系的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那种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更大,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对此,又举例说明,“范畴指超越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譬如‘格律’之和谐、精整,‘结体’之遒劲、疏朗,这‘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是概念、范畴,而‘格律’‘结体’则不是。”对“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他认为,“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上述‘格律’‘章法’属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绘画,‘飞白’之于书法。概念和范畴则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属性的特殊名称,与术语一旦形成必能稳定下来不同,它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冲动,它的规范现实的标准越精确,意味着思维对客体的理性抽象越精确。”
据此来看,将古代文论范畴概念作过于泛化处理自有不当,极可能产生随意阐释;但完全遵从西学分析逻辑来作判断也未必妥当,有时会适得其反,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似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例如,庄子的“心斋”“坐忘”之说,无疑是对古典艺术理论的审美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庄子本意并非是作为美学论理来阐述的。事实上,庄子所谓的“静虚”,源于道家始祖老子。老子有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乃至宇宙鸿蒙,一切都起源于所谓的“道”,并受其支配。“道”性乃虚极静笃,致虚者,天之道也。守静者,地之道也。尽力使心灵的虚寂达到空明宁静的状态,与“道”和谐。故而,庄子的虚静说,以及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都是力求达到虚静大明境界。客观地说,“静虚”不应属于美学的范畴概念,而只是一种古代哲学概念。“虚静”被古典艺术理论列为审美观,甚而被作为创作新理论,是对庄子学说的转化与汇通。只要论说有据成理,符合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阐释就不属于牵强附会,没有必要以西学方式强制否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价值观念,应当有诸多此类的方法论概念作支撑,除上述列举“感悟”外,还有“经验”“评点”“品评”“鉴赏”等诸多艺术理论阐述的方式方法。此外,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有强调“道进乎技”的观念,以及人的主体性与经验性等认识,通过这些概念来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话语体系注入新的精气神。回本文讨论的主题,可将上述观点落实在中国学术话语的维护功能上,这也是中国当今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主题。就学术研究而言,一个成熟的话语体系理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这是承载特定学术思想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和条件。如果将此话题提升来看,则关乎中国学术话语是否具有独立性的大问题。进言之,话语体系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有无独立的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倘若没有就只能跟随西学(“它者”)的话语体系,原有的话语体系甚至会被它者体系所肢解与重构,丧失其原有话语体系,最终只能沦为它者的附庸。就此问题来探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路径,可说是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阐释话语体系的先决条件和基础。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研究项目:“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5ZSTD008)课题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