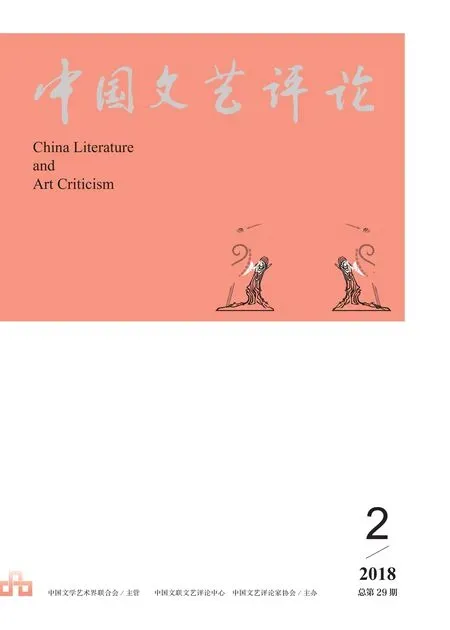“宫斗”题材电视剧的文化阐释
孟 梅
“宫斗剧”这一概念目前在学界尚无明确的界定。顾名思义,“宫斗”题材电视剧应该指的是呈现“宫廷斗争”的电视剧。但是从2004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出品的《金枝欲孽》开始,“宫斗剧”这一称谓渐渐约定俗成,仅指以后宫为“主战场”、以皇后嫔妃之间的争斗为主要叙事线索、后妃的成败直接影响剧情走向的电视剧。概言之,“宫斗剧”专指“后宫争斗剧”。
一般认为,《金枝欲孽》为“宫斗剧”的肇始之作。此后,《至尊红颜》《美人心计》《宫》《后宫》《美人天下》等望名便可知意的“宫斗”题材电视剧层出叠见,尽管屡有诟病之声,甚至出现“边看边骂,边骂边看”的现象,但十几年来经久不衰。2012年的《后宫·甄嬛传》更是以跌宕起伏的结构、精良考究的制作横空出世,创下“收视奇迹”,引发又一轮荧屏内外的“宫斗热”。随后的《芈月传》《武媚娘传奇》等剧,虽然从剧情到制作明显呈现质量下滑之势,但播出收视率也一时风光无两。2016年将“争斗范围”扩展到尚书府内宅的《锦绣未央》,因抄袭问题饱受争议却依旧雄踞收视率前三位。本文以近几年受众关注率较高的《后宫·甄嬛传》《武媚娘传奇》《芈月传》和《锦绣未央》为主要样本,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宫斗剧”,并对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阐释和反思。
一、“宫斗”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研究
在没有影视剧之前,正史或野史中也记录着一些“宫斗”事件: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将戚夫人做成“人彘”(《史记·吕太后本记第九》);广川王刘去的王后阳成昭信以诬陷手段杀死陶望卿、荣爱等宠妃(《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旧唐书》说武则天“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涂之骨”。其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言之凿凿地写下武则天扼杀亲生女儿、残害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行为;楚怀王的王后郑袖以“(王)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的说辞,害得魏美人被楚王割去鼻子的阴谋更是因为《战国策》被广泛流传……
以上这些“后宫争斗事件”,无论是被正史堂而皇之地记载,还是在稗史中被津津有味地渲染,都是为了抨击和鞭挞,用以维护“月星并丽,岂掩于末光;松兰同亩,不嫌于并秀”的“妻妾纲常”,所以叙事结构相对简单,基本上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势的王后欺害嫔妃的模式,被伤害者往往没有反抗的机会或能力,不会形成你来我往报复仇杀的“宫斗”局面。
当这些“后宫罪行”被现代人或原封照搬、或借用由头加以点染,放置在“宫斗”电视剧情节当中,因为话语视角和预期受众审美认同的大相径庭,也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叙事范畴。
1. 白雪公主/灰姑娘的“逆袭”:“宫斗剧”的叙事模式
白雪公主、灰姑娘的故事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美丽善良的少女受尽欺侮迫害,最终在王子帮助下,战胜了阴险恶毒的后母,得到属于自己的乐土。现代心理学认为,类似的童话故事都隐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竞争。综观十几年来的“宫斗剧”,绝大多数是线索复杂化了的白雪公主或灰姑娘故事。
除了《金枝欲孽》属于多主角剧情之外,“宫斗剧”一般只设置一位女主角,她必然有白雪公主式的纯洁善良、灰姑娘式的任劳任怨,当然还拥有童话故事中女主人公都具备的令人一见倾心的美丽——虽然剧中男性英雄宣称引发他们强烈情感的是善良或才学等与外貌无关的因素,但是从演员的选择,到服装、化妆以及剧中其他人艳羡、倾慕或嫉妒的表现中,都足以体现女主角的稀世容颜。和童话的开场一样,所有“宫斗剧”中的女主角最初都是以纯真的目光打量世界,相信人性的美好。她们志向高洁,不慕权贵,不谙于也不屑于参与后宫争斗。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势能”的概念,认为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在“本体势能(内在)、位置势能(外在)、变异势能(内在和外在结合而生变异)”的合力之下,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人物的命运走向。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读童话故事和“宫斗剧”的叙事结构。
“宫斗剧”中总有一位跋扈狠毒的专宠后妃,一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姿态的“皇后”或“皇太后”,以及一个开始同甘共苦逐渐分道扬镳最后反目成仇的姐妹——在童话中,她们是“女巫”和“女巫的跟随者”——她们是女主角本体势能的“受害者”,也是变异势能的引发者:女主角的光环遮掩住她们,夺走了她们的荣宠或爱情,使她们因为痛苦而痛恨,不择手段地对女主角进行攻击陷害,最终“帮助”了女主角的“成长”,引发女主角的报复。当然女主角身边还会有至高无上的皇帝、英武倜傥的亲王、侠肝义胆的将军、足智多谋的文士、妙手仁心的太医等“王子”式的男人,以及对她忠心耿耿的贴身义仆(恰如童话中的小矮人或仙女教母),他们都是女主角势能的“被吸引者”,或出于爱慕怜惜,或因为感激赞赏,成为女主人公无怨无悔的辅助者,在关键时刻扭转她的困境,保护她逢凶化吉。
童话以象征的手法讲述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欲望、梦想以及道德选择,它利用魔法的幻想来解除困境,并最终一定会捧出“幸福结局”给人以强大的心理满足感。美国心理学家谢尔登·卡什丹认为,童话中的“女巫一定得死”,因为“女巫的死亡象征美德战胜邪恶,象征自我中正面的力量取得上风”。“宫斗剧”袭用了童话式的叙事模式,显然契合了现代人置身于多元并存却还未取得和谐状态的文化语境中,因为进退失据产生拒绝长大、退守童年的逃避心理,女主人公一路“打怪升级”的过程,则是永恒的“成长主题”的现代延伸。需要指出的是,和童话中“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生活” 的完美结局不同,虽然在“宫斗剧”中,所有与女主角对抗的“女巫”——争宠的“姐妹”(皇后、别的嫔妃)以及险恶的“后妈”(皇太后)最终确实都失败(“死”)了,但是“女巫”的幽灵还在后宫继续游荡。观众会发现,无论是牵着儿子的手走上朝堂的芈月、甄嬛、冯心儿、窦漪房,还是先做了皇后、太后最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媚娘,胜利之后的“公主”成为了“皇后”或“皇太后”,她们的城府心机和“宫斗经验”注定会成为另一批新入宫少女生命中的“女巫”。
“女巫”一直存在,“宫斗”一直持续,这个沉重的现代生态话题被包含进看似荒唐甚至可笑的“宫斗”剧情中。所以在很多“宫斗剧”里,最初以“呆萌女孩儿”形象出现的女主角们,在故事的结尾,已经到了美人迟暮,她们以苍凉虚无的情绪回忆走过的道路,对曾经的行为充满不确定感。恰如《母仪天下》中终于坐稳太后宝座的王政君说:“我不愿意争斗,可我又不得不争斗。……我真的赢了吗?可我又为什么有止不住的哀伤呢?”——这当然不再是白雪公主的城堡中或者灰姑娘的南瓜马车上发生的故事,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后宫故事,而是现代人充满现实焦虑和自我怀疑的内心世界的镜像折射。
2. 阴谋与爱情:“宫斗剧”的叙事逻辑
“宫斗剧”,“宫”是名词,限定了叙事空间;“斗”是动词,组成了剧情的结构框架。
在后宫富贵祥和的表象之下,时时处处充斥着“阴谋”的气息:香料、佩饰、宫扇、鲜花都有可能成为毒药或瘟疫的媒介,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孕、流产、疯狂或丧命;故意散播的流言蜚语、别有用心的小道消息、包藏祸心的内奸、忘恩负义的奴仆,甚至巫蛊邪祟、毒蜂病鸟……“宫斗剧”中的每个人都处在阴谋的连环套中,既是别人的棋子或目标,也时刻谋划着去利用和伤害别人,必要的时候连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也用作筹码:《芈月传》《武媚娘传奇》《甄嬛传》《锦绣未央》等“宫斗剧”中均有以自己或儿女为圈套引人入彀的桥段。
中国人对兵法谋略的推崇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卷帙浩繁的史传典籍以激赏的语气对智囊人物进行记录和膜拜,民间流传的各种“智斗”“智取”故事,充分体现出权谋文化的深入人心。基于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权谋”常常被用来作为谍战、商战、历史、悬疑等影视剧重要的叙事元素。与其他类型剧相比,“宫斗剧”既没有家国大义的指涉,也不呈现政见分歧或忠奸矛盾,于是实施权谋的行为和动机就都指向了“爱情”:女主角遭到嫉妒陷害的原因是因为爱情;逢凶化吉、走向王权宝座的动力与助力,也全部来自爱情。母仪天下的王后、艳冠群芳的宠妃为了爱情可以舍生忘死、背弃道德伦理;英明神武的王侯将相、英雄豪杰也动辄为了爱情不惜放弃王霸大业、前程性命;连侍女仆从的爱情都能促成剧情的突转……
《武媚娘传奇》中武如意对徐慧说:“既然我已经进到宫里来了,我也就认命了。我想,纵然陛下是一个秃头大胖子,我也要争取他的宠爱吧?只有这样我才能帮我娘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且不评判这句台词是否符合唐代的语言风格和审美标准,单就字面意思来分析:如果皇帝真的外形猥琐心智昏庸,嫔妃们各施手段争宠夺爱,倒也确实能让观众感到后宫中人深切的悲哀和无奈,凸显出“宫斗”本身的荒诞和蕴涵其中的批判性。然而,不论是《武媚娘传奇》中由张丰毅扮演的李世民、李治廷扮演的李治,还是《芈月传》中赵文瑄扮演的楚威王、方中信扮演的秦惠文王,《甄嬛传》中陈建斌扮演的雍正……被“争夺”的男主人公从外形和气质都自带“光环”,使绝大多数的后宫争端,尤其是女主人公 “遭受陷害”和“实施报复”的原因,全部成为在“爱情”牵引下的“情不自禁”,完全化解了“王权富贵”对人性的压迫扭曲。
当爱情成为唯一的叙事伦理,亲情淡化成可有可无的背景,友情则更多时候蜕变成不触及彼此“爱情底线”前提下的利益联盟。“爱情至上”的逻辑不仅将丰富多元的人类情感演绎得狭隘失真,还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对善恶的评判:甄嬛、芈月、武如意等女主角的谋权夺位手段,必然因为叙事视角的原因被赋予忠贞正义的光环。就连刻薄寡恩害人无数的“反派人物”,也会因为“深情”被镜头语言所美化:《甄嬛传》华妃被赐死之前,镜头多次近景呈现她的满脸痛泪,辅以如泣如诉的背景音乐,将华妃定格成“为情生、为情死”的悲剧形象,似乎她“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的言行也理直气壮起来;《武媚娘传奇》中徐慧在李世民去世后从容自杀殉情,她逼迫太子谋反、杀死贴身侍女、多次欲致武媚娘于死地的种种恶行都在武媚娘捧着手镯哭唤“徐姐姐”的时候得以消解。类似的还有《锦绣未央》中的李常茹、《武媚娘传奇》中的罗玉姗和殷德妃等等,这些“凄美”的情节和镜头掩饰着一种荒诞的理念:只要是以爱情为名义实施的阴谋或暴行,哪怕造成血债累累,都可以获得同情和谅解。
对爱情的讴歌和向往,古今中外,概莫如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艺作品中,也有数不胜数、异彩纷呈的经典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否得到现代人的理解,都努力以端庄得体的姿态,传递着对忠贞、良善、真诚的期许。当代“宫斗剧”却是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阴谋以爱情为名义,爱情以阴谋为手段,女主人公借助来自三个以上男人的爱情,利用“恶行”来战胜“恶行”,一步一步走向“事业的巅峰”,既抹杀了古代女性在或为家国、或为生存、或为尊严而奋斗时真实存在过的隐忍坚强和雄才大略,也没有实现对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识的深刻探讨。
二、“宫斗剧”收视热潮的文化阐释
在2015年底《芈月传》播出之后,曾有人预测此剧“或许代表了一个传统电视‘宫斗时代’的结束”。“《芈月传》只是一次非体面的谢幕。”然而,“宫斗”剧却并没有就此谢幕。继《芈月传》斩获“上海电视节”“金鹰节”各类奖项之后,2016年末《锦绣未央》以“台网双爆”的态势热播;2017年《甄嬛传》作者流潋紫的另一部“宫斗”小说《后宫·如懿传》也已经被改编成电视剧即将播出;另有《女医明妃传》《寂寞空庭春欲晚》《秦时明月美人心》等“类宫斗剧”(叙事模式和叙事逻辑不变,“争斗背景”不再局限于后宫的电视剧)纷纷上映。可见,即便是题材严重同质化、剧情编排漏洞百出、演员表现乏善可陈,“宫斗剧”依旧拥有大量拥趸。概其原因,“宫斗剧”中“宫”的历史怀旧元素、“斗”的权谋悬疑元素、“剧”的视觉娱乐元素,能够同时满足受众的多重审美期待。
首先,“宫廷”题材的电视剧满足了受众对“内院”的猎奇心理。在中国长期“内外各处,男女异群”的儒家礼义规范中,“内宅”近乎与世隔绝,除了一家之主的男性之外,就连成年后的子侄、兄弟无事都不得擅入。身处内宅的女眷严谨地遵从着“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唐·宋若莘《女论语》)的闺范律条,她们的姓名、生辰、日常言行都被幽闭在闺阁之内。《红楼梦》中林黛玉责怪贾宝玉把她写的诗拿给外人看,贾宝玉赶忙申辩说:“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薛宝钗也说:“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红楼梦》第64回)后宫,作为皇家的“内宅”,更是充满了隔绝与禁忌。这种“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苏轼词)的隔绝刺激着“墙外人”的“窥视”欲望。古代大量的摹写后宫嫔妃侍女或豪门贵族妻妾生活、情感的“拟古宫词”“拟闺怨词”,以及《赵飞燕外传》《梅妃传》《长生殿》等小说戏曲的传抄流布,足以说明民间对“深宫内宅”的兴趣和想象。
其次,后宫中众多女性等候皇帝垂青宠幸的性别格局,暗合了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众多贤才俊彦等待当权者提拔任用的仕途格局。古人常以“美人香草”寄寓君臣关系,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屈原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明确指出其中的比喻意义:“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金枝欲孽》播出之后,网络上出现很多诸如“《金枝欲孽》争宠术VS职场大黑招”“《金枝欲孽》之职场五大伎俩”“《金枝欲孽》——大学生就业必看的职场宝典”等文章;《甄嬛传》播出之后,更是有连篇累牍的关于“《甄嬛传》与职场法则”的比附文章。这种比附虽然颇有牵强附会或扭曲价值观之嫌,但是,“在后宫被皇帝选中”与“在科场被主考官选中”和“在职场被领导选中”,三者之间确实会产生异曲同工的心理效应。无论是古人书写“香草美人”意象的诗词,还是现代人坐在家里观看“宫斗”电视剧,都有“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情感意识在其中。
其三,“宫斗剧”以“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白雪公主/灰姑娘逆袭”的叙事模式,承载了现代人打破平庸生活的梦想。梁启超认为“人生趣味的源泉”之一就是“他界之冥构与蓦进”:“对现在环境不满,是人类普遍心理……就令没有什么不满,然而在同一环境之下生活久了,自然也会生厌。不满尽管不满,生厌尽管生厌,然而脱离不掉他,这便是苦恼根源。然而怎样救济法呢?肉体上的生活,虽然被现实的环境捆死了,精神上的生活,却常常对于环境宣告独立。或想到将来希望如何如何,或想到别个世界……”对于现代人来说,电视剧就相当于“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的自由天地”。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认为:“我们在剧场、电影里或在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戏剧,是一种精心制造的假象。可是同其他产生假象的艺术相比,戏剧(戏剧脚本的演出)有更大很多的真实成分。”观众在收看“宫斗剧”时,伴随着所认同的角色,在一波三折的阴谋与爱情、圈套与悬念中分享着“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尊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深情,虽然明知无稽,却也能在“真实的假象”中满足女性的“后宫/公主梦想”和男性的“君王/英雄梦想”。
此外,观众在自家客厅或卧室里近距离观看“后宫故事”,对剧中人物的行动、剧情走向乃至演员的表现、影像的优劣等问题进行品评谈论。电视重播和网络播放还能够满足观众反复回放寻找“线索”或“漏洞”的优越感,这也是“宫斗剧”吸引观众的魅力因素。
三、结语
2000年前后,也正是美国“女性电视剧”迅速繁兴的时期,各家电视网纷纷推出诸如《欲望都市》《绝望主妇》《口红丛林》《绯闻女孩》《邪恶女佣》等电视剧,塑造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形象鲜明、主体意识高涨的女性群象。“宫斗剧”以及与“宫斗”类似的“女主剧”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井喷之势,将本来隐藏于历史背后身影模糊的古代女性拉进屏幕,以现代人的视角关注、阐释她们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足以说明女性主义意识在全球范围内对文艺作品的影响。
遗憾的是,大多数跟风出品的“宫斗剧”所引导的审美体验既与真正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大相径庭,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相悖离,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创新的断裂和错位:形式上以历史为叙事空间和素材源泉,在人物语言行为、价值理念的处理上却与历史貌合神离;内容上似欲彰显女性的独立自强,却总在情节语言中流露出对“英雄救美”的艳羡赞叹;在向“一生一代一双人”的古典爱情致意的同时,又摆脱不掉多元婚恋观带来的泛情倾向。《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说:“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甄嬛传》中悲惨的人物命运感受到强烈的批判精神,不再把阴暗吃人的宫廷当作向往的地方,不再被某些宫廷戏误导想要穿越回古代。”就演员表现和制作的精良程度而言,《甄嬛传》毫无疑问算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但是如果从对受众审美诱导的层面而言:美轮美奂的华服艳饰、温文尔雅的谈吐举止、随时产生爱情的良辰美景,如果说以《甄嬛传》为代表的“宫斗剧”是以“揭露批判”为目的的话,那么这些在“揭露批判”的过程中时时通过影像呈现出的迷恋和艳羡则很大程度上消解甚至颠覆了初衷。
纪伯伦曾经感慨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当前的“宫斗电视剧”恰恰印证了这句话。电视剧以“后宫”为外壳,装载爱情、悬疑、谍战、权谋等各种类型因素,注重娱乐快感,追求商业利益,原本也无可厚非。只是,如果不在艺术品质和叙事伦理方面加以提升,以现代人的高度和理性去挖掘、呈现中华民族传统中最宝贵的也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道德文化底蕴,一味追求视觉狂欢和市场效益,势必会因为对爱情和权谋毫无节制的消费引起受众的反感和抵触。到那时,娱乐也好,利润也罢,一切都将因为无所依附而归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