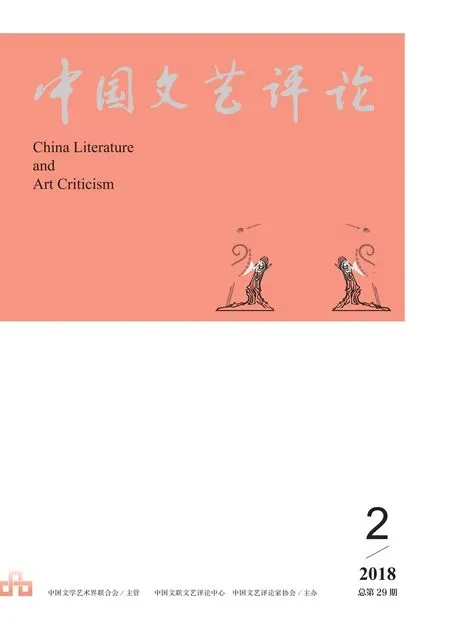1950至1970年代台湾社会剧的拓展与丰富
胡星亮
社会剧是1950至1970年代台湾剧坛常见的三大话剧类型之一,是指那些描写当时当地台湾社会人生的戏剧作品。
1950至1970年代台湾当局的主导政策是“反共复国”。1950年台湾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号召文艺家“自觉地以战斗姿态,在精神上武装自己,在行为上发扬民族主义,安定人心,肩负起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1951年台湾又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重金奖励那些“能应用多方面技巧发扬国家民族意识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义者”。处于如此时代大潮中的社会剧创作自然带有“反共性”。学界长期以来也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是当年的参与者说:那时包括戏剧家在内的台湾文艺界“一致反对灰色和黄色的文艺,一致参加反共抗俄的战斗文艺运动”,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评论:那时的文艺创作“进入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台湾的各种戏剧也被全面收编,汇入反共抗俄剧运动的激流”等,大都持这种看法。
然而实际情形不完全是这样。以1956年国民党“中央”为推动话剧运动,成立“中央话剧运动委员会”,发表“实践战斗戏剧,贯彻精神动员”宣言,而大力开展的“新世界”剧运为例。两年间共演出16台戏,除《万丈光芒》《儿心关不住》《维新桥》《音容劫》《春归何处》带有明显的“反共”“战斗”意识外,其他如《汉宫春秋》《乘龙快婿》《黛绿年华》《清宫残梦》《还我河山》《锦上添花》《新红楼梦》《碧血黄花》《蓝狐狸》《十二金钗》《红楼梦》等,或为历史剧,或为描写台湾普通生活的社会剧,或为改编外国的喜剧,都不属于“反共抗俄的战斗文艺运动”,没有“汇入反共抗俄剧运动的激流”。以至于剧运中途有人批评:“除《万丈光芒》和《儿心关不住》外,无一是配合反共剧运的创作。”
仔细梳理也不难发现,1950至1970年代的台湾剧坛,在描写当代台湾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注重“反共”意识灌输的作品,演出较多的只有李曼瑰的四幕剧《时代插曲》(1955)、张永祥的四幕剧《悲欢岁月》(1963)、吴若的四幕剧《天长地久》(1965),以及赵琦彬的《翠竹苍松》(1962)、丛静文的《凤凰》(1967)等独幕剧。创作更多也更有影响的,是为学界所忽视的另两类社会剧:一种注重揭示社会问题,一种注重表现人生价值和伦理道德。
一、在现实描写中揭示社会问题
着重在现实描写中揭示社会问题的社会剧,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赵之诚的三幕喜剧《八仙过海》(1951)是较早出现的批评不良社会风气的剧作。描写战乱中从大陆去台湾的一群人,由于环境改变做不成“仙”,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与新环境冲突而带来很多笑料,揶揄中包含着批评的锋芒。作者的四幕喜剧《新红楼梦》(1957),立意与《八仙过海》相似,批评“红楼梦型”男女青年在现代社会中无法适应而出尽洋相,最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而走向时代。赵之诚戏剧影响较大的是1954年创作的四幕喜剧《花好月圆》,尖锐嘲讽结婚铺张浪费、图虚荣讲排场的社会不正之风。此剧搬演一幢公司宿舍楼里几户人家的生活,其中,张玛莉和周振华、吴海英和唐圣聪、范杰民和阿兰三对年轻恋人准备结婚。张玛莉好虚荣,周振华又打肿脸充胖子,他们没有钱却要结婚风光排场,并且盘算这样可以收很多礼,一定能赚钱。他们不顾自己和同事的实际生活情形,也不顾倡导节约、一切从简的社会改造运动,首饰、家具、礼服、酒席大肆铺张,最后亏空太多债台高筑才深深悔悟,表示要改过重新做人。吴海英和唐圣聪原打算从简结婚,受到张玛莉和周振华影响,吴海英也开始爱慕虚荣,是这场教训使他们改变想法而准备公证结婚。范杰民和阿兰也从中吸取教训而参加集体结婚。作者巧于构思,随着剧情发展,张玛莉和周振华由结婚的喜庆走向烦恼、忧愁,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焦头烂额、痛哭流涕,运用喜剧笑声对这种爱慕虚荣、排场浪费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剧中还有几对也是同事的中年夫妇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如梅家惧内、董家怕丈夫、徐家相敬相爱等,也写得颇富喜剧情趣。
奢靡享乐的生活观念也是“问题”社会剧批评的对象。丁衣的独幕剧《尼龙丝袜》(1952)、张英的独幕剧《殊途同归》(1956)、丛静文的四幕剧《绛帐千秋》(1959)等,都是批评这种社会现象。《殊途同归》写姐妹俩暑期一个去香港游玩,一个去金门参加军中服务,姐姐从香港带回洋烟洋酒、首饰衣料、尼龙丝袜等奢侈品被海关没收,妹妹去金门军中服务学会洗衣、做饭、缝补等生活能力,姐妹俩从不同路途回家产生了人生观念的冲突,剧作对追求享乐奢侈的生活作派予以了严厉批评。《绛帐千秋》则是批评父母的奢靡享乐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不良后果。王家事业有成生活富裕,妻子整天吃喝玩乐追求享受,丈夫饱暖思淫欲在外勾搭女人,直到家中幼子也学会赌博、偷窃、打架,父母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尼龙丝袜》是从正面宣传政府减少外汇、增加生产的经济政策,强调奢侈享乐必须加以节制。
1950年代的台湾,还有一种陈旧落后的社会风俗——“养女”制度——也被搬上舞台受到批评。丛静文的四幕剧《春风吹绿湖边草》(1954),就是写一酒家老板白兰花,为了赚钱买来一批养女,她们被环境所迫过着任人蹂躏的生活。剧作一方面描写台湾流行的“养女”风俗,和家主借此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无恶不作,批判了“养女”制度的罪恶;另一方面,又怀着悲悯的人道同情,描写了香妹、玫瑰、珍珠、玉娟等女性遭受蹂躏后或被贩卖、或被摧残致疯、或与家人生离死别的非人生活。剧终,政府决定废除“养女”制度,开设工厂收容这些“养女”去做工,使她们真正成为一个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赵之诚的《新红楼梦》等剧,也有关于“养女”制度的描写。
第二,对少年犯罪、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当代台湾严重的少年犯罪现象,所谓“十三太保”“十三太妹”等不良青少年困扰着台湾社会,这个问题同样在戏剧舞台上呈现出来。较早反映此类问题并获得强烈社会反响的,是刘垠1953年创作的四幕剧《鼎食之家》(又名《黛绿年华》)。台北某工厂厂长覃净斋出身于书香世家,家庭富有,前半辈子靠祖宗留下的产业过着优裕生活。是抗战之后的社会动荡使他懂得个人事业与国家兴衰的密切关联,懂得人生的艰难、疾苦是充实生命的过程,所以他严格教育子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走上社会,他有感于自己专心事业而忽略家庭管教、使子女教育出现问题,而要把家业捐给社会办学以培养更多的人才,由此引起激烈的家庭矛盾。覃净斋有二子二女,长子覃烁、次女覃泓读书用功且能辨别是非、明理尚义;长女覃洁、次子覃焜却不读书不求上进,覃洁整天跳舞、看电影、交男朋友,覃焜则在家偷钱、在外打群架,是典型的“十三太保”“十三太妹”。剧作赞扬覃烁、覃泓的积极上进,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批评覃焜、覃洁不读书不做事,依赖家庭而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覃净斋怒斥他们是“跟社会增麻烦,跟国家添败类。”覃焜、覃洁后来在误入歧途的瞎混中感到人生的严峻,逐渐走上人生的正道,生命展现出光明的前景;覃净斋的妻子开始溺爱子女、不理解丈夫,后来看到覃焜、覃洁的人生转变,看到丈夫对自己的爱,也转怒为喜,支持丈夫的事业。《鼎食之家》的“家庭教育主题,正针对着当前如火如荼的少年犯罪问题,而且也对着当前一般十三太保十三太妹的家庭而发的”,故多次公演都广受欢迎。
少年犯罪、家庭教育是当代台湾戏剧关注的普遍社会问题,刘硕夫的《梦与希望》(1959)、徐天荣的《啼笑良缘》(1964)、吴若的《点铁成金》(1969)等剧对此都有表现。李曼瑰的五幕剧《淡水河畔》(1967)也是写“太保”“太妹”问题的,但其视角和内涵要宽阔、复杂一些。剧作主体是太保型“太空帮”和太妹型“月亮帮”不良青少年困扰台湾社会的严峻问题,而其故事载体,则是父母、子女两代人的情感纠葛,是台湾、大陆两个社会的政治纠葛。剧中因为复杂的情感关系而经常聚在同一屋檐下的夏成仁、温淑慎、张汉生、邓玲玲几个男女青少年,夏成仁爱温淑慎,而张汉生要夺其爱,夏成仁遂因爱生恨走上邪路,联络几个社会青年组织“太空帮”,要“创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1960年代由香港逃来台湾的大陆少女邓玲玲,她爱夏成仁而夏成仁却不爱她,也因爱生恨,利用色相和金钱分裂、拉拢“太空帮”成员组成“月球帮”,撒谎、欺骗、偷盗什么坏事都干。年轻一代的矛盾,又引出张方正、王美英、陈美德等父母一代复杂的情感纠葛。最终,夏成仁因为父母一代情感纠葛导致母亲自杀而醒悟,认真思考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从而走上人生正途,也获得温淑慎的爱情;而邓玲玲却因为本性邪恶且不思悔改,在偷盗后企图偷渡外逃时被警察缉拿归案。剧中还写了张汉生去美国就和一美国女孩订婚,王美英要儿子抛弃落难的温淑慎而攀上某董事长的女儿,对这对母子身上表现出来的崇洋心态和嫌贫爱富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第三,反映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关系和族群矛盾。
族群关系和族群矛盾在当代台湾,因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和“国府迁台”带来大量大陆移民,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政治高压的1950至1970年代,这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在戏剧舞台上正面展现出来,但还是有一些侧面描写的创作。
主要有两类戏剧描写。一类是以寓言形式表现族群矛盾,更希望不同族群能够同心协力建设家园。杨逵是此类戏剧描写的代表作家。杨逵1955年创作的台语街头剧《光复进行曲》《胜利进行曲》表现了台湾从荷兰、日本侵略下回归祖国的欢乐情感,其四幕剧《牛犁分家》(1956),则借一个兄弟不和、牛犁分家而家庭沦落的故事,表达了对“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社会发展的期望。他说:当时“在‘光复’后不久,我认为大家要沟通,才能重建一个新的时代,因而有感而发”,写了这部“寓言”式的作品。该剧写日据末期,林耕南带领家人开垦荒地准备春耕,虽艰辛但全家和睦,不想日本警察强征儿子大牛、铁犁去打仗。林耕南和儿媳拼命劳作仍生活困窘,无力交税又被税吏牵走耕牛,他只得自己当牛拖犁。战后儿子回来,大牛秀兰夫妻努力劳动,铁犁被媳妇金枝拉着到处玩耍,林耕南教训儿子却被金枝蛮横顶撞而气死,妯娌斗气又分家。然而数日后,牛、犁分家的两个家庭都不能耕作,兄弟妯娌这才想起父亲常说的要“宽量”“容忍”,而渐渐消除隔阂,团结协作建设家园。杨逵作为本省作家,因为“二二八”事件后起草《和平宣言》而坐监,然而即便是在牢狱中(此剧在狱中创作演出),他仍然坚定信仰和追求,站在百姓的立场表达民众的心声和愿望,《牛犁分家》在普通百姓的生活描写中承载着社会政治的深层寓意。剧作家期望经历这次悲惨事件,外省人和本省人作为兄弟“应该宽量、容忍”,就像该剧主题歌所唱的:“废除界线心相应,除掉障碍血交流”“勇往直前迈向复兴建设道路”。
另一类戏剧描写可以外省作家高前的三场剧《高山上》(1959)为代表,表现迁台的国民党政府帮助居住在高山上的土著族群,山地族群也在走向进步和文明,他们的生活在改善,整个社会在发展。此剧通过外省青年医生方志杰和医疗站护士、山地少女李康萍,以及与李康萍青梅竹马的山地青年林阿土之间的情感冲突,写政府派各种专业人才帮助山地族群改善环境卫生、提高生活水准,写山地族群的忠厚淳朴和落后愚昧,及其在实现定居定耕、改掉不良习俗、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消除了与外省族群的隔阂,表达了对于政府的感恩:“我们要争气,要求进步……我们要诚恳地接受政府的领导,不求进步就会被淘汰,永远被别人看不起,说我们自甘堕落。”在男欢女爱中还是可见社会消除族群隔阂的努力。
批评不良的社会风气,关注少年犯罪、家庭教育等问题,反映当代台湾的族群关系和族群矛盾,上述剧作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当时台湾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与“反共”社会剧相比较,这些“问题”社会剧更多关注当代台湾的现实人生,贯注了戏剧家揭示问题、变革社会的创作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其不足主要有三点:一是为了教育社会和宣传思想,这些“问题”社会剧在最后,剧中所揭示的问题和矛盾都要得到解决,所以,有些性格刻画和情节安排就不大合乎情理。比如《鼎食之家》剧终,让原先要离婚的母亲突然良心发现而与丈夫和睦恩爱,让原先被父亲骂为“流氓、土匪、瘪三、十三太保”的败子立马回头,让原先“太爱虚荣、性情浮躁”的逆女迅速改变并获得有为青年高载扬的爱情,就有草草收场之嫌。二是注重人物的外在冲突和外在动作性,性格描写生动,但性格的深度和丰富性不够。仍以当年多获好评的《鼎食之家》为例。剧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冲突构成剧情主体,故有时为了有戏,就着意渲染外在动作的戏剧性,如第一幕结尾覃焜听说父亲要送他去警局就耍赖装死,第三幕结尾覃洁被父亲训斥后跑进厨房喝醋而家人以为她要自杀乃乱成一团,以及覃焜为了教训马毕克欲黑灯瞎火揍他一顿却又误打家中老仆,覃洁误会妹妹与自己争爱引发姐妹吵嘴打架闹得不可开交等,都使其变成喜闹剧而冲淡了剧作主题。三是说教的东西比较明显,有时还带有“反共”的说教内容。如《花好月圆》写普通百姓婚恋生活,也强调“要军民一体,共渡难关,目的在消灭共匪,光复大陆”;批判台湾“养女”制度罪恶的《春风吹绿湖边草》,也鼓吹“我们去做工,为国家生产,为反共抗俄而努力”。那些“反共”社会剧更是如此。因为当时创作“必须在剧情进行当中,插入刻板的教育性的主题台词”,这就影响到剧作内涵挖掘的深度。
当然,上述“问题”社会剧创作最大的不足,是它们不敢直面台湾现实,揭示当时台湾的高压政治、白色恐怖等尖锐严峻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表现人的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
着重表现社会生活中人的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的社会剧可称为“人生”社会剧。在生命意义、人格操守、人性良知等方面有突出表现。
李曼瑰抗战时期就关注现代女性的生命意义问题,撰写《创造妇女的新史实》等论文,创作《天问》(1955年修订改名《女画家》)等剧作,主张妇女应该牺牲自我、努力工作而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专才;更应培养人格,完成中国妇女的最高德性。1957年创作的四幕剧《尽瘁留芳》是其关于女性生命意义探索的继续。剧作虽然是以1947年“国大”代表竞选为背景,但它所描写的正义与邪恶交战的社会人生,人们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人生选择,却可见当代台湾的现实;而主人公漆若兰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一生勤俭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女画家》中史坤仪以高尚行为描绘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李曼瑰所彰扬的女性的人生价值。漆若兰善良、纯真、朴实,她捐出祖宅开办医院悬壶济世,成立妇女会以推进妇女运动,为社会、为病人、为孩子耗尽了精力和生命,却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攻击和诬陷;她性情温柔却心力强大,独自承担命运带给自己的一切苦难,总是牺牲自我而成全他人。这是一位靠心灵而伟大的完美女性。刘硕夫的三幕剧《萤》(1964)的主人公施淑莹也是作者所歌颂的女性。剧作一方面批评丈夫彭鸿丰,在功成名就的人生晚年吃喝玩乐乃至金屋藏娇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着重描写妻子施淑莹在知晓丈夫事情后,竭尽全力一边扶助丈夫的事业,一边维护家庭的安稳,终于以其贤慧善良、温婉明达唤醒丈夫的愧疚和良知。“虽然萤火虫是个微小的动物,可是它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从自己身上发出光芒的动物!唯有它才不会让你在黑暗中迷失!”这是作者借剧中人之口对萤火虫般的施淑莹的生命意义的颂扬。
姚一苇此期的现实题材剧——三幕剧《来自凤凰镇的人》(1963)和四幕剧《红鼻子》(1969)——也是探讨生命意义的。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意义何在?这是姚一苇着重思考的问题。《来自凤凰镇的人》搬演三个来自凤凰镇的人的一段感情和生活,及其关于人的生存和生命的思考。《红鼻子》的主人公神赐念过大学,父母和妻子都对他很好。生活在这个“可以什么都不必做,什么都不必想”的家庭里,他说:“但是当有一天,我问我自己,我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我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我问我自己:你究竟能做些什么?你究竟要做什么?想着想着我就不安起来了。”神赐因而离家出走。之后他教过书、做过推销员,当过记者也摆过地摊,可是都没有做成。后来到一个杂耍班子里戴上红鼻子面具当小丑,他才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戴上红鼻子面具的神赐,能够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社会人生,并且还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尽管后来神赐又陷入牺牲自己却不能真正救助世人灵魂的困惑,但是,当别人需要他的时候,他仍然像他所崇拜的耶稣、释迦牟尼、吴凤那样,献出他的一切甚至生命:或是为了救助世人而献祭——牺牲自己而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或是献出自己而让世人警悟和觉醒。
所谓人格操守,是指一个人要坚守做人的人格、信念和责任感等,这也是人生价值的重要方面。刘硕夫的三幕剧《旋风》(1963),就是描写在人生“旋风”当中,主人公罗衡立为了保持人格完整而坚守的故事。动乱时代像一阵巨大旋风,“人们必得把自己锻炼得像钢铁一般的坚强;还得把那些人性上的缺口,心灵里的缝穴,全部都堵塞起来;也许我们才不会被这巨大的旋风摧毁。”罗衡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罗衡立是一位优秀建筑师。早年在战乱中与未婚妻走散,一个人去台湾,收养了三个孤儿,如今事业和家庭都令人宽慰。但是陡然间生活发生巨变:特强台风使其建筑工地损失惨重;已经与人结婚的未婚妻韩云霓来台,带给他情感痛苦;孩子长大离开家使他觉得孤独空虚;原先住在家里的至友、诗人姚文方也因人生观念分歧而搬走。罗衡立的人生遭遇了“旋风”,但他坚守着人格、信念和责任感。终于,他变卖家产使事业转危为安,韩云霓也认识到人生责任而回香港帮助破产的丈夫重振家业,孩子们离家独立但很恋家、很尊敬他,姚文方准备成家,与他依然友谊深厚,而一直钦佩他的侨商之女潘婷玉来到他的身边。人生有悲有喜,就像有台风也有风和日丽,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人格操守,才能根基牢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真正的人。
钟雷三幕剧《长虹》(1965)的主人公许家骏同样是具有人格操守的人。不同的是,罗衡立所遭遇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在家庭和公司内,而许家骏所面对的,是既有来自家庭、更有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为了发展经济,台北市郊某乡镇要修“固本堤防”以防低洼洪灾,建“光陆大桥”以便利交通,却因为需要征用拆除一些房屋地产而遇到巨大阻力。青年工程师许家骏是这项工程的设计者,为了建桥修堤,他得罪了舅母、也是女友的母亲林太太,得罪了居于楼上的商人蔡老板。林太太抓住亲情无理取闹,蔡老板贿赂不成便竞选下届镇民代表“要改变这建桥修堤的计划”,还有流氓趁机造谣、诬陷、敲诈,无所不用其极。许家骏有理想有抱负,做事认真且有正义感责任感,在女友支持下“运用正义的力量,去跟他们作战”,最终邪不压正,大家同心协力奔向美好前程。剧作背景是写台湾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但作者主要不是揭示问题,而是要彰显一种代表社会正义的人格力量。邓绥宁的独幕剧《日月光华》(1955)也是这样。此剧也是以某钢铁厂建设中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作为背景,表现厂长兼总工程师陆云平刚正不阿,严拒董事长秘书等人想套取外汇弄钱的贪污行为,崇法务实,埋头苦干,其人格操守如“日月光华”体现出一种精神和希望。
人性良知其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天然或本分。然而社会环境改变人、扭曲人、异化人,所以保持人性良知,同样是追求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平陵的三幕剧《幸福的泉源》(1958),就是通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和几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来阐述剧作副题所标示的“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人生真理的。助人或互助是人类的天性。成功商人曹福元热情帮助积极上进的年轻人,把助人看作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赢得人们尊敬和社会的爱戴。女儿曹纯英与何松年、冯志航交往,何松年英俊聪明即将去美国留学,但其人生目的为偏激狭隘的出风头,难以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情;冯志航是平凡普通的海军军官,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且乐于助人,与曹纯英志同道合而获得爱情幸福。儿子曹飞龙及其女友洪霞信奉有钱就有一切,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些人的生活遭遇都说明:“世界上只有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人,才能得到朋友!才能得到真正的爱!”在现实面前,尽管也有执迷不悟者如何松年,但更有良知发现者。曹飞龙在感情受到欺骗之后省悟自新,要到部队熔炉去锻炼自己,又在知道洪霞的家庭困境后让母亲去拘留所作保帮助她回家照顾。交际花洪霞在人生歧途得到别人帮助和关爱,也让她懂得:“善良的人,才能得到朋友的帮助!真诚的人,才能得到朋友的爱护!”从而悔改重新做人。
不同于《幸福的泉源》是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激烈碰撞中,人性良知最后获得了胜利,张永祥的三幕剧《风雨故人来》(1963)是在一场爱情的春风化雨中,真、善、美感化假、恶、丑而带来人性复归和良知发现。顾君毅是一个上进拼搏却工于心计的年轻人,在台北商界闯荡多年。他长期利用公款与人合伙往来香港做生意,这一次,他们雇佣的那条船突然失踪,对方说是海上失事,他知道是上当受骗却没有证据。事发后,他来到台湾南部当年读大学的老师丁教授家想暂时躲避一个时期;随后知道公司报案自己被通缉,他又想利用陪教授长女亚琴去美国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机会逃去海外。丁亚琴善良美丽,虽然身体有残疾,但在心灵上她是完美的、圣洁的。她不愿别人为她吃苦所以她不肯去美国治疗,她爱顾君毅哪怕他犯法坐牢都会记挂着他,但她不强求顾君毅为她作出牺牲。是丁亚琴的善良圣洁和纯美爱情使顾君毅深受感动潸然泪下:“我真该死……过去我一直没有真正关心过别人,我以为也不会有人关心我……以后但愿我不再那样孤独了!”他真诚地向亚琴求婚,又给公司写信主动投案认罪。剧终,丁教授和师母仍然肯把女儿许给顾君毅,也代表社会对于改过自新者的鼓励和善待,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和社会的美好。王生善的三幕剧《春晖普照》(1969)也主要是在家庭矛盾中表现人性的良知。剧中的儿子陈永培忠厚温雅,恪守孝道;媳妇欧阳美美漂亮热情,个性倔强;年轻就守寡的陈母(婆婆)坚毅固执,慈爱却守旧。陈永培在母亲和妻子的冲突中,不能说服妻子顺从母意留在家中相夫教子,也不能让母亲尊重妻子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亲情与爱情的两难困境中,他只得遵从人性选择孝道,给自己也给子女和家庭带来痛苦。而在多年之后,同样感受骨肉思念之苦的欧阳美美良知发现回到这个家,也是戏剧家对于人性的肯定和期望。邓绥宁的三幕剧《书香门第》(1969)也是在家庭亲情和矛盾中表现人性良知的。
这些着重表现人生价值的社会剧,大都是在男女爱情、家庭亲情的故事框架中彰显生命意义、人格操守、人性良知,基本上没有“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思想内容。较之“反共”社会剧和“问题”社会剧,其艺术审美也有新的探索。最突出的,是它既有外部性格、人生观念的激烈碰撞,又有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挖掘,人物性格描写趋于丰富深刻。因为人的生命意义、人格操守、人性良知,不仅是从剧中人与外部环境及与人的冲突中体现出来,更是剧中人与自我的内在世界冲突而显示的精神内涵。这就促使戏剧家朝向人的内在心灵进行深入开掘。漆若兰(《尽瘁留芳》主人公)的尽瘁留芳表现在为了社会事业与邪恶势力的斗争,更表现在她为了女儿而压抑自己生命和爱情的内心痛苦。《风雨故人来》的剧情结构和矛盾冲突,就是围绕逃犯顾君毅的举止不安、内心反常挣扎、事情败露痛心疾首、心灵彻悟悔过,来展开性格描写和人性良知的开掘。其次,这些戏剧对于生命意义、人格操守、人性良知等的揭示,与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人伦情感有更多联系,渗透着戏剧家更多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因此较为真切感人。有些剧作带有自传性质就更是如此。王生善的《春晖普照》就融入了自己悲剧性的婚姻故事,有切身的体验和真挚的情感,写得生动细腻。《尽瘁留芳》是李曼瑰为纪念亡友伍智梅女士而作,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非传记剧却具有浓郁的真实性。王生善说:“注入了真感情的作品,才能够感动人,使观众与你同悲同喜。”它赋予此类社会剧独特的魅力。再次,是这些戏剧在社会生活描写的基础上,还运用象征手法表现出具有哲理意味的戏剧意象。如《红鼻子》《旋风》《风雨故人来》《长虹》《萤》《日月光华》等剧的情节和立意都富有象征味,有助于深化戏剧的社会人生内涵,并启发人们对于戏剧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思考。姚一苇的剧作总是留下问题让读者/观众去思考。“红鼻子”意象是象征性的,剧作的情节立意也是象征性的。戏剧结尾,红鼻子走向大海象征着什么?作者说:“我把这个问题留下一个大问号:他是去救溺水的舞娘?自杀?或另有用意?他会死吗?他会不会回来?……这个诠释,我们完全交给观众,端看个人对生命经验的领悟了。”
三、戏剧现代化的艰难拓展和突破
不难看出,上述1950至1970年代台湾的社会剧创作,真正表现“反共抗俄”“反攻复国”内容的作品不多。所以有台湾学者说,当年有“许多社会剧也无非只是将反共的场景由国家缩影到家庭而已”,这是不大准确的。
关于这一时期台湾的社会剧创作,还有以叶石涛、夏志清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叶石涛尖锐地批评当时大陆去台作家主导的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创作,“压根儿不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和人民,也不想了解此块土地上台湾民众真实的现实生活及其内心生活的理想和心愿,更不用说和民众打成一片。一个作家的根脱离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悲苦和欢乐,他们的文学无异是空中楼阁”。作为台湾本土学者的叶石涛,其学术和政治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此期台湾社会剧中那些揭示社会问题、表现人生价值的作品,虽然不能说其社会生活描写达到怎样深刻的程度,但是它们在努力表现当代台湾的社会人生,这是无疑的。
夏志清则认为此期台湾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说:“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确有别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共文坛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夏志清笔下的台湾“文学的新时代”,主要指当时那些强烈“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创作,也包括描写当时台湾社会人生的作品。作为随“国府迁台”的学者,夏志清学术和政治的偏颇同样是非常明显的。夏志清更看重当代台湾文艺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那一面,但正是在这里,包括戏剧在内的当代台湾文艺创作都成为了政治宣传品。此期台湾社会剧中那些揭示社会问题、表现人生价值的作品,也正是突破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模式,才取得程度不同的成绩。
显而易见,上述三种看法注重的其实都是包括社会剧在内的此期台湾戏剧中“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内容描写。它们也可以代表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台湾戏剧的基本观点。就社会剧创作而言,这种观点遮蔽了此期台湾社会剧创作的多层面发展。
关于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剧创作中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倾向,白先勇有一段话,分析了当年此类作品所呈现的创作者的心态。他说:“国民政府迁台之始,即提出响当当的‘反攻复国’口号,从火车站到酒瓶标纸上随处可见,可谓无所不在。这官方的神话正好代表了流放者的心态:从大陆逃来的人,不过以台湾为临时基地,好发他们的美梦,希望有一天回到海峡的彼岸。国民政府统治台湾初期,这种神话在人民的政治心理上根深蒂固,没有人敢怀疑;当时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反映在这方面,不免产生麻醉的作用。”当年台湾社会剧创作出现上述主题的作品也是自然的事。
然而社会剧创作突破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八股模式。戏剧家把眼光转向他们所生活的台湾那片土地,关注当代台湾的社会人生,而把创作视野扩展到对于当代台湾现实中多种社会问题的揭示,扩展到对于生命意义、人格操守、人性良知等人生价值的表现,推动了当代台湾社会剧创作的发展。出现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戏剧传统的艰难传承,同时,它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台湾戏剧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即便是在张扬“反共抗俄”“反攻复国”最激烈的1950年代,当局要求“战斗戏剧”,都是“要一方面激发反攻必胜建国必成的战斗信念,坚定民族自立自信的心理;一方面发挥戏剧正人心移风俗的功能,改进社会风气促进精神动员”。社会剧中着重“反共抗俄”“反攻复国”内容的当属前者,着重揭示社会问题、表现人生价值的乃是后者的创作。在把“反共抗俄”“反攻复国”当作主导政策的1950至1970年代的台湾,正是这些剧作的出现拓展和丰富了台湾戏剧,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台湾戏剧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不过严格地说,尽管上述社会剧突破“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八股模式而呈现出戏剧创作的新生面,但是,在包括台湾在内的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曲折。诚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描写社会人生的传统,可是在更大程度上,由于当时的戒严体制和思想控制,这一时期在整个台湾文艺界,“中国三十年代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文论和台湾在一九三〇年前后的左翼作家、作品和文论的传统,都被强权禁刊和抹杀”,“五四”以来中国戏剧和文学的启蒙精神、批判精神、人学精神、创新精神等,都不可能真正地传承下来。这就造成此期台湾社会剧描写社会人生的一些严重缺失。首先,它们大都是揭示伦理道德、不良青少年等社会问题,而不敢直面政治专制、白色恐怖、族群冲突等当时台湾严峻、重大、尖锐的社会矛盾。无论是夏志清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还是杨逵所说的台湾的中国新文学“远离梦境,面对现实,对腐蚀社会的根源,追根究底,进而给予纠正”的传统,很大程度上都已然失落。其次,是这些剧作表现台湾社会人生的视野和格局都不够宏阔,就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展开描写,而少有人学层面的关于生存、生命、人性等深层内涵的揭示,以及与人类共同命运结合起来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再次,是有些戏剧家的现代意识单薄,影响到剧作反映社会人生的深度和力度。尤其是《尽瘁留芳》《萤》等剧歌颂女性的所谓牺牲精神,与现代女性的个性解放意识形成冲突。施淑莹(《萤》主人公)宽恕丈夫在外寻花问柳,她觉得这是命运——“这个世界是男人的”。所以她有个比喻:“男人就好比挂在堂前的那盏明灯,女人就好比那长年埋没在炉底的火种;堂前的那盏明灯,虽然光芒四射,明亮夺目,说不定吹来一阵野风,它就会熄灭的!可是那并不要紧,只要那埋没在炉底的火种不灭,那盏灯立刻就可以再燃亮起来。”女儿听后为女人感到冤屈,施淑莹进而又劝说女儿要恭顺隐忍。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剧描写女性伦理道德的,大都持这种传统的思想观念。
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剧除姚一苇的《红鼻子》等个别作品外,绝大多数创作其艺术审美都少有探索,仍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话剧译介过来的“易卜生—斯坦尼”样式,甚至进一步,简单化到用“易卜生—斯坦尼”样式讲故事去宣传意识形态的地步。196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的借鉴西方的现代派尝试,在戏剧界更是没有反响。这是为什么呢?此乃戏剧在当代台湾文坛的特殊情形所决定的。“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当局”总结现代社会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形式和技术上认识了抓住剧场运动的重要性。1950年以后,台湾剧场受到最严苛的‘安全’监视。中国三〇以迄四〇年代民族·民众剧场充满活力的传统在台湾中绝。国民党党、军文工团体包办了台湾剧运。”而国民党政府当局着重宣传,是反对戏剧的现代主义探索的。1952年张道藩就强调:“纵情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文艺形式,非我们目前所需要。属于新浪漫主义的唯美派、颓废派、象征派、神秘主义、享乐主义等文艺形式,和超现实主义的文艺形式,尤非我们目前所需要。”不仅如此,社会剧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反共抗俄”剧,因其现实题材的意识形态性也被管控得甚为严格。所以,运用“易卜生—斯坦尼”样式演绎故事,以宣扬意识形态、阐释伦理道德的创作比较多,而对于人的关注比较少,更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精神情感的深刻描写和挖掘。它同样影响到戏剧反映社会人生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