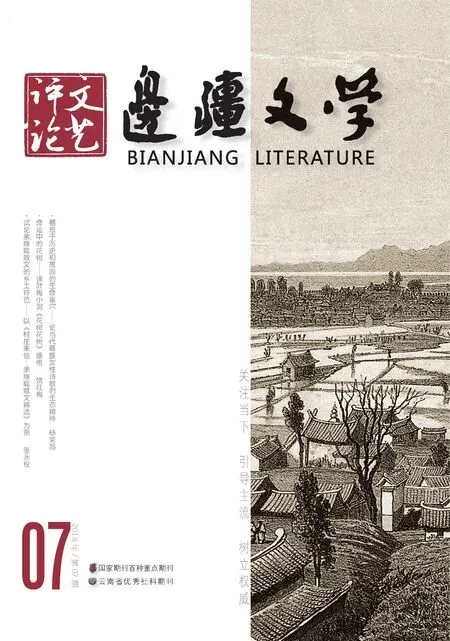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读郑山明《乡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
沈德康
《乡愁的滋味:那年·那事·那人》是郑山明先生创作的一部散文集。此书语言简洁、流畅,笔触细腻、节制。作者饱含深情的追忆,让“湘南故园”的风俗礼仪、世态人心、鸟兽虫鱼在读者心中熠熠生辉。
每一个人都有令他魂牵梦系的故园。郑先生笔下的故园,有难熬的春荒与秋旱,有糯米酒里氤氲出的醇香、“花喋婆”中飘出的闲适,也有舂水河畔的乡民们直面生存困境、挑战无常命运时表现出的勇敢、坚韧与善良。
当然,郑先生的乡土之思,并不全然是一种个人化的追忆。实际上,若换一种眼光来看,郑先生的乡愁也是近百年来国人在这旷日持久的“转型期”里、在“城市化”(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几代人的乡愁。更进一步说,郑先生笔下的故园亦可谓是古今中外所有对人性还持有信心、对未来还抱有希望之人心中的“桃花源”,因而这里的故园既是“生我养我的故园”,也是令世人向往的“理想人性的家园”。一言以蔽之,这故园是坐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田之上的故园,这故园是对现代人浸淫其中的“技术时代”的超越与理想化。
一、“薄暮时代”的乡愁
在郑先生平实、质朴的文字里,饱含着对故土的眷念。这眷念,根植于郑先生早年与土地的交道。在这“薄暮时代”,太阳西下,灯光升起,群星溺死在城市绚烂的“光污染”中。此时,恐怕只有农人才能真切地体味到那蕴含在“大地母亲”这一类比中的深情厚意,恐怕也只有像郑先生一样从农村走出的游子才会萌发出刻骨铭心的思乡之情。
乡愁是写给大地母亲的诗,其间包含着一个明媚的意象:“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我们来到春天的田野,漫山遍野的晨露在朝阳中闪耀,透过圆润、婉转的露珠——这些大自然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柔嫩而悠长的蔓草沁人心脾的绿,这是大地母亲的心意。于是,在毫不起眼的野草中,我们“看”到了春天,难怪郑先生也会如此写道:“从来没有人比农民更能接近春天,从来没有什么活儿比割草更能感知春天。”
事实上,农人挥舞镰刀割草时,是心怀感激的,这跟城市里的园丁像清除垃圾般用割草机一丝不苟地为草坪剪一个标准的“平头”不一样。在莫名的感激中,草儿更绿,春意更浓,大地母亲也似乎更宽厚、更深情。其实,比大地还要深情的是割草的人。当把碧绿的狗尾草或开着小白花的“马儿杆”割下、捆扎起来背回家一把把喂给家里饲养的白兔、马驹、牛羊或鸡鸭,此时此刻,你的心里会升起一种唯有当过母亲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温柔与充实。
农人的生活的确艰辛,在郑先生笔下,“双抢”“抗旱”“打石灰”“挑煤”等营生让每一个劳动者遍尝生活的苦楚。如郑先生所言,在“双抢”时节,“割禾是很累的事。连续几个时辰弯腰劳作,腰板又酸又胀,伸一下腰就能听见腰椎嘎嘎的爆响声。” 但是,那种与春水、山风以及默默奉献的泥土打交道的过程,确实又饱含着城市人很难体会到的浓浓“诗意”。这种“诗意”根源于农人的生存境遇:在无限而神秘的长天与大地之间,在无数个寒来暑往、朝晖夕阴的轮回中,农人领会并确认了那“生于大地又归于大地”的宿命,他们默默地接受大地母亲丰厚的馈赠,也默默地承受突如其来的洪涝、饥馑与死亡,他们对人的处境以及人在天地间理应占有的位置具有远比城市人更恰当的领会。
尽管“进步主义”的观念已让世人习惯了俯视甚至蔑视那个业已衰败了的农业时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进步主义”的逻辑不过是维护着现代人尊严和信心的一种“独断论”。想一想我们的老祖宗是如何用“大同社会”“黄金时代”“桃花源”等理想以及尧、舜等前圣来锚定他们“退步主义”与“永恒复返”的历史观,我们或许就能洞悉作为一种“偏见”的“进步主义”的“偏见性”。
郑先生的文字让我想起了西方18到19世纪如卢梭、雪莱、海涅、华兹华斯、爱默生、梭罗等浪漫主义、超验主义思想家和诗人,也让我想起了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海子、顾城等诗人以及如莫言、刘亮程等小说家、散文家,这些“时代的歌者”,尽管时殊境异,但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们对自然人性与淳朴人情的珍视,对山川湖海、大地苍穹的热爱,对无限宇宙的景仰与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剧烈变动时代的种种不适应以及在遭受时代浪潮的冲刷、打击之下对理想人性的憧憬与坚持。所以,正如一位潦倒的诗人所言:全世界的诗人都在诅咒城市而歌颂乡村。这说法虽有些言过其实,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现代社会特有的现实困境和思想危机带给世人的那种深层次的困惑、焦虑与虚无感。
由此可见,郑先生的乡愁具有时代性、普遍性,绝非孤例。任何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不得不修正或放弃传统道德或信仰的人,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怀念那个业已消逝了的、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的、闪着金光的世界。
事实上,忍不住地思念,根源于难以忍受的现实。因为不安,所以憧憬。哲学家说这是一个“悬于深渊的世界”,是漆黑的“夜半时代” ;诗人说“我们的习惯意识越来越局促于一座金字塔的顶尖上”,因而全然忘记了“我们是‘不可见者’的蜜蜂”这一实情 ;小说家则认为现代人的幸福都是“被幸福” ……因而,我们已很难体会到生命的神圣或神秘,也很难体会到“命运”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薄暮时分,这蔚蓝的星球已沦为浩瀚星海中一艘迷惘的“航船”,旅人像晚风一样疲惫和落寞,即使乘上银色的翅膀追赶太阳,可在这无尽的虚空里,何处是那安顿心灵的家园?
二、何处是家园?
何处是家园?诗人荷尔德林回答道:“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通过荷尔德林的诗句,我们或许能对几个世纪以来飘荡在大地之上的浩荡“乡愁”会有所理解。
如哲学家所言,一味地、单纯地“筑居”只意味着现代人拥有了物质的、现实的“居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居所”便是“家园”。 “家园”是什么呢?“家园”不仅仅是用来遮阴避寒的栖身之地(生存),它还是思念的方向,是浩荡乡愁的策源地,是一开始就树立在心田上引导我们不断抵近理想人格的路标(伦理),是将天地四方的神灵与大地之上的有死之人建立起联系的无比强烈的希望与诗意的想象(信仰)……一句话,“家园”不只是安顿人“肉身”的“家园”,它还是安顿人“良心”的“家园”,它更是安顿人“灵魂”的“家园”。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读懂郑先生笔下湘南农人在建房时“立门”“上梁”“封顶”等仪式中显出的神圣性。此时,笔者也想起了湘南传统民居庭院中常见的采光、采雨的“天井”,还有村落中不可或缺的“祠堂”,以及祠堂门口半月形的“池塘”中亭亭净植、香远益清的“莲花”。从乡村孑遗的古迹中,从天、地、神、人水乳交融的格局中,从风雨临庭、家燕栖梁、荷香四溢的意象中,我们才能明白何为“家园”。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诗人荷尔德林喃喃自语。肉身是“沉重”的,生活“充满劳绩”,而苦难则是生活之舟必须负载的“压舱石”。正因为人还能以“诗意”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有限与不幸,所以我们明白把“大地”称为“母亲”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也能够在想象中强烈希望,而正是这希望为人的生活镀上了意义的金色。
“家园”是金色的,是等待收割的稻田,是“天堂的桌子” ,鸟群不时从中窜起,是农人感念的“谷魂”。望着这“金色的餐桌”,挨过了春荒的农人仿佛已尝到新米的滋味。“家园”的确是一种滋味,在郑先生细腻又充满韵律的文字中,我们可发现“家园的味道”并不仅仅驻留在舌尖,而是需要我们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参与、去欣赏才能获致。对此,笔者以郑先生的一段文字为例:
“豆腐师傅把石膏碾成粉末,和点豆浆存放在一个大缸里。看着锅中的纯豆浆煮开了,立即将其装入两个木桶里,两个青壮劳力提起木桶站立在大缸两侧,豆腐师傅用手搅动缸里的石膏浆,速度越来越快,搅得石膏沾满缸壁时突然将手抽出,大喝一声‘倒’,两个木桶的豆浆顷刻冲入缸中,‘啪’的一声将大缸盖好。几分钟后,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豆腐师傅慢慢地掀起缸盖,将浮在表层的泡沫除去,原来液体状的豆浆已变成晶莹白嫩的豆腐脑。”
从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可以发现,人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美好,如此令人留恋,那是因为——人不仅活着,更关键的是人还能用欣赏的姿态来审视生活,用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反思生活。正是在这样的审视与反思中,我们拥有了“诗意”与“思想”。郑先生笔下的豆腐师傅让我想起了庄子文章中解牛的庖丁、斫垩的匠石。不论是庖丁还是匠石,甚或是湘南村中的豆腐师傅,与其夸赞他们的技艺如何精湛,还不如说他们已经学会了用一种超越性的、非功利的亦即诗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事实上,唯有能试着以这种方式看待生活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正是在此意义上,庄子表达了“逍遥”的人生境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尼采才会说:“唯有用审美的眼光打量生活,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家园”何在?按郑先生的意思,“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故我们的“家园”必然也是生长“爱”的沃土。如同大地与农人的关系,父母对儿女的呵护,这种天然的情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润着“善”的萌芽,并最终长成了挺拔的“德行之树”。所以,家庭是人的“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初的教师,孩子在这里学到的绝不是“知识”“技术”,而是远比“知识”“技术”更为重要的“道德”。对此,郑先生深有同感,他在书中这样写道:“那时,学生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装知识的容器,而是作为一个个完整的有灵性的人来培养的……那时读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始终没有脱离大自然,没有脱离日常生活,也没有脱离简单质朴的家庭关爱。” 古人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这是极为深刻的论断。当我们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感到忧虑时,有谁可曾想到如今不堪的道德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恰是因为我们的“第一学校”(家庭)受到了代表社会、国家的“第二学校”的严重“挤压”?
现代文明是高度社会化、集约化的文明。文明的两大支柱——“人的生产”(生育)与“物的生产”(经济)——在我们时代都是十足计划性的。如学者所言:“机械化(机械技术)和严格的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技术),这两者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新花样,新的仅是这种机械化和严格管理现在已是有计划地、有形地在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整体主义”和“激进主义”倾向的“计划”中,与过去相比,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位置是极大地下降了,或者说传统家庭葆有的“德育”的内涵被时代的浪潮侵蚀掉了。于是,“德”也在世人对“才”(工具性的知识与技术)的狂热追求中丧失其作为“帅”的主导地位。故而我们时代的缺憾,用郑先生的话来说即:“他们没有学到比父辈更多的东西,却丧失了许多祖辈传承守望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郑先生笔下不时施展“杨梅爪”的父亲,想起了为了儿女的安危而忧心惙惙的母亲,我还想起善良、坚强的秀秀,为人师表的“高长子”以及尽职尽责的“驼子”……我们不难意识到,秉有传统教育观念的严父、慈母对于儿女健康人格的养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郑先生在书中所言:“每隔一两个月,我就会抽空回老家看看他们,陪父亲喝两杯,和母亲说说话,看到他们幸福愉悦的样子,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由此可见,我们的“家园”是“爱”的象征,是从伦理道德的维度指向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坐标。
三、烟波江上的“返乡之思”
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技术时代”。在所谓“现代化”这一潮流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磕磕绊绊又匆匆忙忙地几乎走完了西方四五百年走过的路。换句话说,“中庸”了数千年的国人对“技术”的倾情拥抱已经让我们对“革命”这个概念所秉有的“激进主义”性质安之若素。所以,发生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所有“伟大的革命”——无论是“社会技术”层面的还是“机械技术”层面的,甚或是“身体技术”层面的——对我们而言似乎都具有“绝对价值”。在这种“绝对价值”的背景下,那种浪漫主义的“乡愁”往往因其保守主义的倾向而被视为不合时宜。但是,如学者所言:“浪漫主义所代表的理想的力量是现代文明的必要组成元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把它转换成可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模式。” 所以,在郑先生的书中,所有那些对家园的美好追忆其实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华,追忆过去则是为了更好地憧憬未来、创造未来。
在这个逐渐泯灭和混淆“人性”与“物性”之本质差异的“技术时代”,“社会技术”在各个层面都“机械技术化”了,人和由人构成的社会失去了应有的神性(不可剥夺的尊严),人们以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人们以操纵一台机器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对于这个时代,《共产党宣言》做出了大体准确的诊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当我们读懂了这本关于我们时代的“病历”,我们对郑先生书中的美好追忆才能有深切的体会。
在郑先生的追忆中,我们的“机械技术”还没有“高级”到把一个有尊严的人变成单纯的“交换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书中描绘出的作为嫁妆的呜呜吟唱的旧式纺车上看到。在纺纱织布的同时,含辛茹苦的父母也将一曲关于乡愁的歌谣送到了数十年后的游子耳畔。在那个“没有使用农药的年代”,田里种的是高梗水稻,圈里喂的是土猪,所谓的“良种”还未大行其道,人们在河里摸鱼、田里抓鳝,感受到“煎鱼送饭,锅底刮烂”的生活况味。此时,人们为在草丛中偶遇一丛天鹅菌而高兴,为酒坛子飘出的枫叶气味而喜悦,听着糯米酒发酵时在坛中清脆的嘀咕声而满怀希冀地进入梦乡。在这“故园”,为了过年,人们不仅“杀猪”,还“杀豆腐”,人们尊奉“亥日不杀猪”的禁忌,也从炸豆腐中嗅到了浓浓的年味儿。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机械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拥有了无数的工具、商品,可是它们带给人的“幸福”却远不如从前那些简单的事物。对此,我们的学者指出:“若把现代和历史做一比较,可从提供丰富、舒适安定的现代经济的社会关系加以考察。在听到人们把这些称为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社会关系却牺牲了人类的精神价值,把所有的尊贵和美都牺牲了。” 的确如此,在这个崇奉“商品拜物教”并将“工具理性”视为至高价值的时代,我们把“物”的位置放得有多高同时也就决定了我们把“人”的位置放得有多低,我们把测度、加工和评价“物”的方式视为至高价值,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然以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对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却尚未“自觉”的悲惨状况,郑先生书中对传统手工技艺的诗意描写就像是一剂解毒剂:
“这时补锅匠左手拿一块叠了好几层的小布块,迅速从地上掏一层草木灰在上面,大拇指在灰上面压一小坑;右手用铁钳夹一个小泥勺,把炉中的铁水舀到左手的小坑里,形成一粒圆圆的铁水球。左手平稳迅速地移向那只铁锅,把那粒铁水对准铁锅的裂缝,往上一抬,铁水挤进裂缝变成了月偏食的模样;右手放下铁钳,快速拿起一支用破布扎成的布柱,将布柱蘸上水对准那粒‘月偏食’压下去,‘滋’的一下布柱被灼热的铁水烧出一道火苗。”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诗意的劳动者,还有诗意的观赏者。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价值。劳动值得赞美,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在功利算计的层面赞美。我们是人,我们不仅活着,我们还要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故此,我们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吃喝拉撒,我们还通过劳动去实现自己追求的那种人生意义——这即使是一个幻觉那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完全不用伦理的、审美的眼光看待劳动,那我们就跟非人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诗人才始终强调:“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
在郑先生用文字搭建的“家园”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尚未被“机械技术”磨蚀殆尽的“诗意”。但是,在“社会技术”层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经过几十年激进的“革命”,极少数像“木鱼脑壳”那样“脑袋空洞嗓门大、四肢发达一根筋”的激进分子的确是“昧了良心”,而大多数人则已麻木不仁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在农民上交的“公粮”变成了“救济粮”“救命粮”时他们错愕的表情中看到,也可以从“把守在圩场的各个口子的基层民兵的吆喝声”中听见,还能从“停课闹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吃肥肉的’受制于‘吃瘦肉的’”“四类分子”“现行反革命”等历史名词中读出。还是听听我们的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吧:“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都是技术的随从。” 事实上,人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技术”,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技术”的过度发展亦即技术对人与物的普遍强制毫无疑问是一种“病”,浩荡的“乡愁”则是其症状,就像发烧之于感冒,在本质上是“社会有机体”免疫功能的自动强化。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田里有“嗷嗷待哺的禾苗”,苍天之下则有“嗷嗷待哺的农人”。如郑先生所言:“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对得失已显得有些麻木,他们不去抱怨苍天,也不想去与社会抗争,他们只是用自己的韧劲去诠释一种生命的意义:人活着的价值就在于劳动。” 事实上,远不止是“劳动”,人的价值不能仅仅从他者的角度被测算,它必须建立在一种主观主义的对生活的信仰(热爱)上,所以人的价值还在于用“诗意”的眼光审视和反思自己的“劳动”。对于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多次谈到。但是,笔者此时还是非常愿意用郑先生对美好生活的畅想来印证这个看法:
“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男人又在火塘上架起桌子,取一块腊肉切成薄片,和青蒜、辣椒一起烹炒,肉和大蒜的清香夹杂着酒香袅袅飘飞在雪后初霁的湛蓝天空。一壶酒,一场雪,一个咸淡的冬季。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