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如水(二题)
曾耀文
母爱如水,给我浓浓的柔情,水之所处,无微不至,滋润着我成长的道路;母爱如涓涓细流,连绵不断,永远不求回报,无私付出,无私奉献。
——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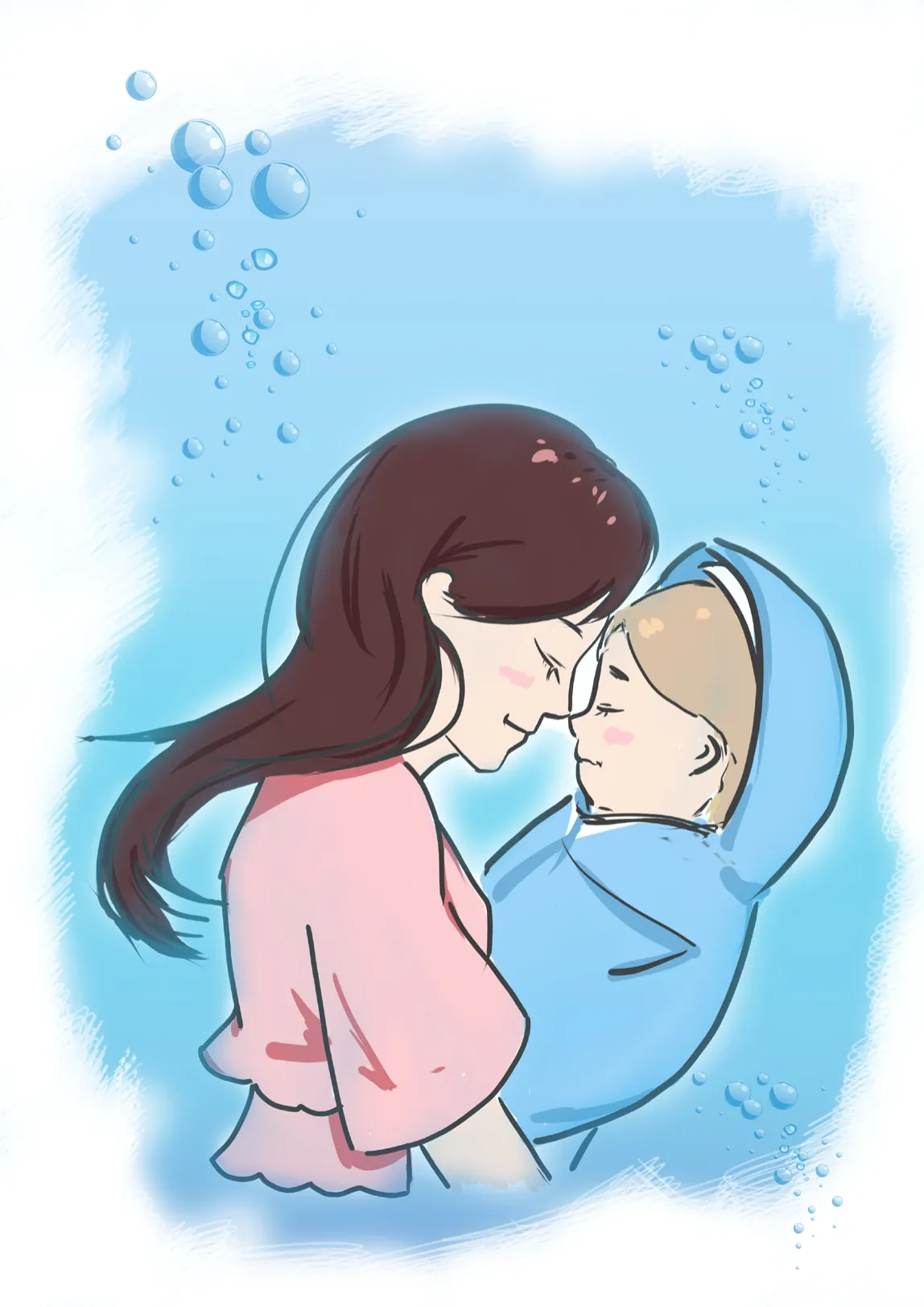
那些土鸡蛋
母亲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家,她晕车厉害,很少来城里。每当我回乡下去看望她,她总会给我带回一大箱土鸡蛋。有时家里土鸡蛋多了,母亲也会打电话叫我回家去拿。
母亲,一个很少走出乡下的老人,用她一生一惯的勤劳俭朴,用最原始的方式喂养着鸡,用这样的方式关爱着她的儿女。我每次回家,都发现母亲有明显的变化,一次比一次老了。头发全白了,耳朵背了,牙齿也掉得差不多了,背驼了,走路一瘸一拐,尽显蹒跚之态。她患有糖尿病,饮食受限制,生活也必须要有规律。八十多岁的老人,干不了农活,却一直忙里忙外,对养鸡情有独钟。我不知跟母亲说了多少次,叫她不要养鸡了,万一摔倒那就麻烦了。母亲说什么自己喂养的鸡下的蛋有营养、味道香甜呀,城里都买不到,说了一大堆话。结果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每次回家看望母亲后要回城时,母亲早已精心包装好土鸡蛋。这些装土鸡蛋的包装盒五花八门,鞋盒、饼干盒、罐头箱,母亲都留意保存下来备用,专门来盛装鸡蛋。一粒一粒土鸡蛋用报纸包好,再放在箱里、盒里,然后再用包装绳捆紧,做得那么认真、细致,生怕不小心碰坏了。这些土鸡蛋,蕴藏着母亲对儿女的疼爱,倾注着对儿女的牵挂和思念。尽管坐车一路颠簸,到城里打开包装,鸡蛋都完好无损。提着母亲亲手包装捆扎好的土鸡蛋,看着母亲佝偻、瘦弱的身体,我的眼眶早已湿润了。
我们家虽很少买鸡蛋,却从不缺鸡蛋,家里冰箱里的鸡蛋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变着花样吃,煮、蒸、炒、煎等,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吃惯了母亲的土鸡蛋,只要到外面吃饭,我总挑剔别人的鸡蛋,没有母亲的土鸡蛋味道香甜。月是故乡明,鸡蛋还是母亲亲自喂养的鸡下的土鸡蛋好。天底下的母亲都是倾其所有对子女深沉、无私地关爱,直至生命终老。而做子女的呢?我感到渐愧!
母亲的石磨豆腐
现在豆腐已经成了老百姓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食品。然而,在我童年岁月的记忆里,豆腐却是一种仅次于鱼肉的奢侈品,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红白喜事,除了鱼肉,桌上还要有豆腐和芋头,这些是平时很难吃到的。
做豆腐的前一天晩上,母亲会从缸里量岀二三筒黄豆,在水中浸泡一晩上。第二天,我和母亲、姐姐挑着浸泡好的黄豆和木桶到婶婆家,借用她的石磨磨豆腐。母亲和姐姐先把石磨清洗一下,各个角落都要清洗,姐姐力气大,掀开石磨的磨盘,我舀水冲洗。接下来,母亲把木杵套进石磨,我舀一瓢黄豆和水进石磨的小洞,母亲和姐姐先推后拉木杵,石磨开始一圈圈乖乖地转起来。看,在石磨的转圈下,滴滴牛奶般的液浆缓缓流出,汇聚成一股细流沿着石磨的凹槽流进桶里,带着白白的泡沬。木杵刚从我眼前转过,我眼疾手快伸手舀豆和水倒入石磨洞中,经常是豆少水多。我记得大人说过“多水多豆腐”。母亲看岀我的心思,笑骂道:“傻孩子,哪有多水多豆腐?没有豆只有水,哪来的豆腐?”听了母亲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地傻笑。看着石磨一圈一圏,把豆碾压成琼浆流出,我突然想起大人说的一道谜语:“一垄田园圆滚滚,种豆种麦不会翻身。”我对母亲说:“我知道那道谜语的谜底了。”母亲笑了:“是什么呢?”“是石磨。你看,我一瓢一瓢把豆舀入石磨的洞里,瞬间碾压成白白的泡沬。我‘种下’的豆当然不会发芽‘翻身’了。”“孩子,你真聪明,谜语靠想象是想不出来的,要多观察生活多实践。”受到母亲的夸奖,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
折腾了两个小肘,才磨完半桶豆浆。回到家后,母亲一会儿也没歇,生火煮豆浆。煮开后倒入纱布过滤豆渣,把盐卤倒入汤勺,汤勺在过滤后的豆浆里慢慢转动,变魔术似的,豆浆出现豆花了,母亲把豆花倒在纱布上把水份过滤掉后包好,上面压个重物,过一会儿打开就是白花花的豆腐。豆腐洁白无瑕,母亲把鲜鲜嫩嫩的豆腐,切得有棱有角,方方正正地码进生活中,家中便热气腾腾的,空气中也弥漫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和豆腐的清香!
母亲做的豆腐细滑、鲜美,酥软到令人陶醉。出门在外,吃过无数次豆腐,怎么也品尝不出母亲做的豆腐的那股清新香味,以及那股熟悉的母亲的味道、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