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不到的“麓山”:小镇夏记
李 勇(Li Yong)

《球场01》 李勇 布面丙烯 30.4cm×40cm×2 2018年
历史还是历史,只是当下才可能成为你的历史和未来的机遇。
年初应成都麓山美术馆总监田萌的邀请,约定今夏去他们馆里驻留一段时间,想必可以暂时远离重庆火炉一般的夏日煎烤,于是爽朗答应。成渝虽然很近,但其真正生活于一段时间的体会还真是没有。带着对益州蓉城的人文历史和所谓新一线城市排名第一的的想象,在1小时的高铁速度下到达了成都。当地铁又越走越远地把我拉到五环郊外的一个小镇时,面对一个被修建10年的别墅区,我发现先前的想象无法一一对应。其实想象归想象,一切都是新的,正是这样的落差和不清晰让一切变得可能,或许工作的路径就在空间的缝隙之中。
很难说这是一篇关于驻地创作的日记心得,因为这样的写作也将成为二手经验,难以复制的同时也非对在地的入微描述。如何谈体会和经验都难以再现日常中那种鲜活的现场和切身的关切。艺术家写的创作日记大多来自一种自我系统下的安全记录或者偶然之得。应当说,不是艺术,恰恰是写作又重新把我拉回到那个昏沉沉的小镇夏天。
艺术家在一处地方待久了,往往会陷入一种窠臼,创作变成被一种体系(所谓的文化经验)包裹的长期的惯性动作。我必须警惕这样的惯性。驻留,恰恰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作方法,通过在异地陌生的环境中处理一种临时状态的关系,借由新鲜感带来的刺激和感召,重新激活艺术家对于作品的思考。
可能最早的驻留,是源于过去画家和文人知识分子在达官贵人家寄住的借居生活,但那样的借居大多只是为了闲时雅集的主题创作需要和应酬显摆,而非出于一种主体性的文化自觉意识。古人的创作应时应物,当然也很讲空间。当骑驴转山或是途遇荒村破庙还是山溪舟桥,当感慨人生际遇和政治抱负时多半就是创作的集中表达和涌现,就连城外送别朋友也会折几枝柳条来赋诗作画。所以在我看来,艺术驻留的意义,在于如何在陌生的空间中重新去激活一种身体内部和文化意识的活性因子。于对象和自身的一种可及关系和移步换景,我也相信艺术还是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下的文化生产。
麓山属于成都平原,处于华阳和万安两镇交界处,又有些起伏的坡地,因此被后来的地产开发商起名为麓山。我驻留的地方名为麓山国际社区,又名天府基金小镇。也是开发商取的名字。这跟我的想象其实是不符合的。在我到麓山小镇之前,我希望能够在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找到它有可能的历史上线,以为这样的痕迹可能会有成为工作的入口。所以我最先借用了《楚辞·九章》的形式结构试图制定一个在地方案。我原非一个对地方志和史料感兴趣的艺术家,我想它也不完全是去做田野考据和知识考古,而驻留刚好可以在差异现场提供一种不同的经验。尽管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差异越来越小,甚至不复存在。
我原本也想在麓山社区驻留的这段时间,做一次关于十二首诗的绘画与写作的尝试。我倾向于更多使用一种关于写作方法的编织,把驻地一切我所看所听的素材,如同诗歌里面的文字编排一样,运用现场调研,历史考据,文化研究的方法在麓山这个区域展开工作,甚至每一个声音都会成为我创作的素材,每一个生活现场之物都被重新调度出它的具体之物的想象和他者之间的一种语义链接,成为新的语意场。它可能由一些碎片化的词句构成,是一次不一样的在地写生。它不是自然风景形态和社会风景形态的写生概念,它不是写实的描绘和再现记录,而是对麓山这个区域的一次历史勾陈的写作实验。它是在社会的现场中去观察和感知社会,采集社会标本来形成我对艺术进行重新构型和塑造一个关于这个区域的历史和当代的一个总体现实的文本编织。也许出现得更多的是声音对话、访谈小视频,或是居民和场所之间的互动,都是关乎生活和社会现场的具体之物,通过类似社会人类学的走街串巷的调研,通过对这些日常劳作之物的收集关注和分析研究以及讨论,得到一些可能性的关键词,并在艺术和驻地空间之间嵌入这种关键词,并以直觉来调度,在艺术、场域、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可见可感的关系,用小说的写作回到这个现场重建感受和想象,重新制造我们的语言,虽然它依然是不可见的。

麓山美术馆驻留画室的下午 摄影 李勇

麓山美术馆窗外景色 摄影 李勇

《小镇途遇02》 李勇 布面丙烯 60.5cm×60cm 2018年

《又爱又怕》 李勇 布面丙烯 60cm×60.5cm 2018年

《肉叙事》 李勇 布面丙烯 120cm×100cm 2018年

《导游》 李勇 布面丙烯 130cm×150cm 2018年

《那么深、那么轻》 李勇 布面丙烯 79.7cm×119.8cm×2 2018年
然而,当我来到麓山小镇,即便我把麓山小镇所在的华阳镇有可能链接的华阳国志找来阅读一通,依然一无所获。于是,我从对地方志的研究转向对麓山国际社区这个地产项目的了解,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的渣渣都不剩了。我眼前是一片几千亩地的别墅区,完全是一个当代地产景观。那些掩藏在绿树花园里的洋房别墅,在我看来空无一人,我不能够假定那些房子里真有人,事实上有些真就没有人,只有黄昏时分,带孙子的大妈们终于出现在歌舞的广场,我才意识到房子里有人。我和田萌说:这样的社区我是真不愿意在此生活,没人我慌,人多也慌。我也真的无法在这里获得对一景一物的认知。我必须重新开始,像一个突然闯入的游荡者,在闲逛和旁观中,慢慢去认识一个郊外小镇,去认识这个小镇夏天的各种闷热。

左·《上灰》(草图) 李勇

中·《上灰》 李勇 布面丙烯 80.6cm×100.2cm 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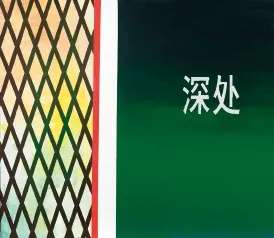
右·《深处》 李勇 布面丙烯 120cm×100cm 2018年
在这里,驻地与周围的景观层叠在一起,每个生活的现场既丰富、具体又碎片化。我很难整体地描述和再现什么现场经验,更多是体会到一种切身的在场感。我想到夜晚走出海昌路地铁站,在路边寻觅食物时的经验,那混杂麻辣烫的油腻气味和天桥的姑娘,令人难忘。还有骑着小黄车(共享单车,编者注)穿过周边每条街道。去过的城乡接合部的那些苍蝇馆子,都带给我弥足珍贵的图像记忆。如何再现和描述当时的感受呢?

《小镇途遇》 李勇 布面丙烯 150.2cm×180.3cm 2018年
我每天不间断地记录一些短句和词语:“一到中午,整个小镇仿佛就陷入了沉睡”“新的夜”“肉叙事”“那么轻,那么深”“上灰”“又爱又怕”。这些文字最终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没有线索,没有上下文,更没有中心。甚至还有更多的词语,我其实并没有找到能够对应的画面或者图像。对我来说,这些我在脑海中拾得的只言片语,可能更像一种即兴快感的记录,不是为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需要,而是为了在图像和文字之间形成一个暧昧模糊的灰色地带。也许正是这样的灰色地带让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在词与物之间显现一种诗意的存在,那是无法准确触及却又能感受到的真实——无法捕捉的充满了闷热和汗水的夏夜。于是,一次麓山在地驻留,变成了一篇夏日的途中影像。“大概宋画里那些在山水峡谷中骑着毛驴、坐着小船、抱着花瓶的行人,也不过如此吧,”我想。
在地,就是此时此刻的图文交汇和影像编织,最后去到哪里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认同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未来之书》(Le Livreàvenir)中关于“叙事开始于小说去不到的地方”这一句。我想我在麓山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大概是这次驻留去不到的地方。地方在变,经验在变,一直试图在接近,去抵达那个关于这个夏天与绘画之间的故事,只是空间一直在挪移和平滑逃逸。它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就貌似我每天穿过树林,快要达到小镇的那一瞬间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处,等待一种莫名和未知,哪怕是一块云或是一片灰,也许这才会是你需要真正接近和抵达的那一刻。只有那些被散落的和被记忆的可能才会是最初关于此地与艺术的最真实部分,只有那里才是你从未真正去过与抵达过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