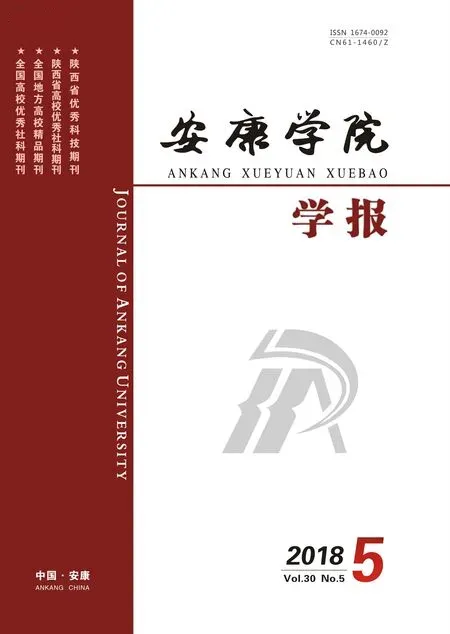《山有扶苏》的主题探析
唐 鹏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山有扶苏》是《诗经·郑风》中的篇章,讲述了盛夏之时,草木繁盛,女子归宁抱怨夫婿的场景。诗曰: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1]240
一、《山有扶苏》主题概述
略看文本,《山有扶苏》显然是一位女子的牢骚之辞。但梳理其接受史,我们发现其主题众说纷纭。大致有刺君王说、淫女戏谑之辞、巧妻恨嫁拙夫的抱怨和对爱人的俏骂等。
(一) 刺君王
在“通经致用”的观念影响下,儒生们认为凡大道理都应出自经书。“天不变,道不变”,经是道的记载,故《诗》往往被儒生们当作谏书来使用。
1.刺昭公忽
《左传》记载,“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2]113,忽以“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2]113辞之。后公子忽助齐败北戎,又请妻之,固辞。庄公卒后,忽立为昭公。新君上位,朝局不为所控,昭公为祭仲罢黜。因屡次拒娶文姜,而失齐援,遂逃奔卫。归国复位后,死与高渠弥之手。《山有扶苏》中的刺忽之说即是汉儒依据郑国的这段历史所提出的。《毛诗序》曰:“刺忽,所美非美然。”[3]299《郑笺》曰:“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3]299《正义》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郑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养之失所。笺、传意虽小异,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3]299孔颖达虽注意到《毛诗》与《郑笺》之解释有小异,毛以用臣不得其宜,而郑以用臣有所失,养臣有所失。其单一的把忽“所美非美”的主体、重点指向“臣”,这是孔颖达解释《毛诗》 《郑笺》“小异”的不明确之处。试比较《毛诗》 《郑笺》,我们发现毛、郑解释的细微差别在于《毛诗》的解释强调“秩序”“性质”,要求合乎其宜,其哲学范围更为广阔。此“所美非美”应是强调定物序、明物性。“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所指皆是物象,物各归其所“宜”。《正义》曰:“毛以为山上有扶苏之木,隰中有荷华之草,木生于山,草生于隰,高下各得其宜。”[3]300山上生木、生松,隰生荷华、游龙,万物生长一切皆从自然规律、法则,此为物序与物性。此刺忽者,应指昭公善易其性,行事违物序,不明物性。“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实际是昭公行为上违背物序与物性的具体表现。而《郑笺》把忽关注的范围缩小,其重点在“臣”,反映用人之理。《正义》曰:“郑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苏之小木,隰中有荷华之茂草。小木处高山,茂草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美德之人于下位,言忽用臣颠倒失其所也。忽所以然者,由不识善恶之故。有人自言爱好美色,不往见子都之美好闲习者,乃往见狂丑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贤者,反任用小人。”[3]300-301故曰:“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毛诗》 《郑笺》的这一差别在后世被诸家所承袭。
首先,承袭定物序、明物性者,如王夫之《诗广传》。王夫之认为:“不见则子都矣,见则狂且矣,无能必子都之非狂且,而狂且之不可子都也。悲夫!人之不能自定其性,见异则迁,而迁则异也,有如是夫?是以善审乎情者当之,宁狂且不见而疑乎子都,勿子都见而狎以狂且。”[4]740王夫之之言实际是强调定序与定性的重要性。子都与狂且莫辨,其根本是不明物序与物性。物序不定,物性不明,而“见异则迁,见迁则异(变)”,故“不能自定其性”,随风摇曳。
其次,承袭用人者,如陈启源认为:“喻昭公用人,贤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毛诗稽古编》);姚际恒认为:“《大序》意以若不类忽辞婚事,因云‘所美非美’,则‘用人’亦可通之,故后人多作‘用人’解”(《诗经通论》);牛运震认为:“狂且狡童,目昭公所用之人也。《序》以所美非美,妙得诗意”(《诗志》)。
2.刺文公踕
在乾嘉疑古思潮影响下,清儒对刺忽说表示怀疑。崔述曰:“考之《春秋》经传,昭公以前为庄公,射王,囚母,纳宋、鲁之赂而与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郑人不之刺。昭公之后为厉公,逐太子而夺其位,依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贪忍谲诈,背盟食言,是以谥之为‘厉’;然而郑人亦不之刺。独昭公较为醇谨,虽无驾驶之才,亦无暴戾之事,谓宜郑人爱之惜之;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岂郑之人皆扶人之性,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然绝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读风偶识》) 方玉润曰:“《小序》谓‘刺忽’,无据。《大序》谓‘所美非美然’,庶几近之,然不必定指忽也。”[5]214因而,魏源提出刺文公,诸锦提出刺(文公)朝楚。
《左传》记载,齐桓公首止会诸侯以拥周太子姬郑,周王派周公姬宰首止私会文公,许文公以王室卿士,诱其背齐亲楚,助次子姬带承袭王位。文公不听“三良”叔詹、堵叔、师叔的劝告,私自逃盟,同时派申候暗通楚国。宁毋会盟,因逃盟事,文公惧桓公加害于己,便令太子华前往宁毋。太子华为嫡夫人陈妫所生,文公初对陈妫宠爱有加,后陈年老色衰,文公再娶二夫人,陈遂失宠。太子华担心被废,借会盟之机谎称说:“郑国之政,皆出于叔詹、堵叔、师叔。郑伯首止逃盟,背齐向楚,皆‘三大夫’之意。若以君侯之灵,派兵伐郑,灭掉‘三大夫’,夺回政权,我愿让郑国长期服从齐国,比于附庸!”齐恒公听从管仲意见,把此事泄露给了郑文公,太子华遂被诛杀。刺文公说即是魏源、诸锦依据郑国的这段历史所提出。《诗古微》曰:“刺文公也。所美非美然。文公不从三良以亲齐,而宠申候以暱楚也。”[6]394文公不从“三良”之意,不亲齐,故有太子华宁毋会盟之祸。诸锦《毛诗说》曰:“刺朝楚也”,“齐桓卒而中国无伯,文公于是始朝于楚。然不知尊王,而从荆楚,是下乔木而入幽谷也。非特《春秋》所深贬,亦当时人心有公恶焉”。文公朝楚的行为遭到中原诸侯国厌恶,诸锦进一步解释到:“荆楚无王,不知礼义,故谓之狂也。山,喻中国,扶苏小木,喻伯主,见小木虽不足依,而犹木也。若荷之在水,其华虽艳,岂足恃乎?楚为泽国,故以隰喻。狡童,谓楚成王也。楚人性狡,而成王又以稚年在位也。乔松固无荫,然游龙虽大,尤不可依也。以喻见狡童之非”(《毛诗说》)。
(二)淫女戏谑之辞
宋儒站在教化的角度提出此乃淫女戏谑之辞。朱熹《诗集传》曰:“兴也。扶苏、扶胥。小木也。荷华、芙蕖也。淫女戏其所私者曰。”[7]67他认为这首诗以扶苏、荷华、乔松、游龙起兴,是女子欲望未能满足的淫乱之辞。理学大家朱熹的淫女之说,从者甚夥。如辅广《诗童子问》认为:“《山有扶苏》已得而其欲未餍之”,“餍”为满足之意,即指淫女之欲,未得满足。许谦《诗经名物传抄》解释说:“此诗恐是淫女见绝于男子而复私于人,乃思绝者之美好”,即女子倾慕男子之美貌,遭拒后再三纠缠,故称其为淫女。朱熹此解被诸家广泛采纳,如刘瑾《诗传通释》、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梁寅《诗演义》、湖广《诗传大全》等均采朱熹《诗集传》淫女戏谑之辞作解,可见各家对淫女戏谑之辞的赞同。
(三)巧妻恨嫁拙夫的抱怨之辞或对爱人的俏骂
从文学的角度解释《山有扶苏》,是近现代学者普遍认可的方法。
首先,王质《诗总闻》曰:“当是媒妁始以美相欺,相见乃不如所言,怨怒之词也”。出嫁女子本以为嫁了个如意郎,相见后却不如其意,女子对媒人的欺骗行为充满了愤怒与抱怨。陈子展先生《诗经直解》曰:“疑是巧妻恨嫁之拙夫之歌谣。”[8]259他进一步指出“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8]259可用袁枚之诗为此歌谣脚注,诗曰:“劣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做天莫做天”。周振甫先生《诗经选译》也提出:“当是一首民谣,写一个女子,悔嫁了一个品行不端的丈夫。”[9]86
其次,近现代的学者多认为《山有扶苏》是对爱人的俏骂。傅斯年先生认为此乃“相爱者之戏语。”[10]88高亨先生在《诗经今注》提出:“此乃女子戏弄她的恋人的短歌,笑骂之中蕴含着爱。”[11]117差不多同时的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里也说:“这诗写一个女子对爱人的俏骂。”[12]86现代学者陈戍国先生在《诗经图文本》中说:“其主旨只有一个,就是一对男女谈情说爱,不免有调侃情趣。”[13]65费振刚先生在《诗经类传》中说:“一个女子想找个健美的男子为侣,却只碰上一些坏小子,因而感到十分失望。也有很多人把这首诗理解成女子所说的反话,这么一来,就变成她对爱人的打情骂俏之词了。”[14]123郭芹纳先生在《诗经:精选本》中说:“这首诗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女子对其恋人的戏谑之词。”[15]118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们情真意切地相爱。有一次在山边约会,姑娘早早地如约而至,却迟迟不见小伙子的身影。爱而至极的姑娘遂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起兴,嘲笑晚到爱人像个‘狂且’‘狡童’。”[15]118可见,他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解释《山有扶苏》主题的。
二、《山有扶苏》主题解读
文学与经学两方面解读《山有扶苏》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文学的解读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巧妻恨嫁拙夫的后悔貌,是周民媒妁相欺的真实写照,是千千万万婚姻悲剧的缩影;另一方面则为我们呈现了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场景。经学的解读奉行“经世致用”的信仰,以具体历史事件为背景,评断君王、警醒后世。宋儒从教化的角度给出解释,批判淫女戏谑之辞。近现代学者从文学的角度诠释《山有扶苏》,其中王质、陈子展、周振甫三位先生的解读值得我们关注。其原因在于,他们在解读文本的同时为我们揭示了周人生活。通过对周人真实生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诗旨。
(一) 《山有扶苏》植物之小考
各家对“扶苏”之解读大同小异,均解为树名。如《毛诗正义》解为“小木”。《正义》曰:“扶苏,扶胥小木也”[3]300,朱熹、吕祖谦、吴闿生等从之。胥、疏、苏叠韵字,古通用。《诗》“疏附”,《孔丛子》作“胥附”。当知,“扶胥”即扶疏。“扶”又作“枎”,《说文》曰:“枎,枎疏四布也”。《释木》曰:“辅,小木”,小木即为木之名。钱大昕曰:“扶、辅声义皆相近,长言为扶苏,急言为辅。”孔疏言小木,而《释木》中不见,是其不知扶苏即辅故;又如,扶苏通作蒲苏,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曰:“暴桑,蒲苏桑也”。故“扶苏”又作“桑”解,吴夌云从之,《吴氏遗著》曰:“扶桑”,刘毓庆、贾培俊、张儒亦从之。《诗家百家别集考》曰:“窃疑‘苏’乃‘桑’之音转,苏、桑古同为心母字。在今晋方言中,‘桑’读如‘缩’,‘苏’读如‘搜’,二音极相近。‘扶苏’当为‘扶桑’之音转。‘桑’字在甲骨文中,即作木多杈桠之状,正与‘扶’之训枝叶四布同”[16]366;又如,作松柏、槐古解。《尔雅》曰:“如松柏曰茂。”郭注:“枝叶婆娑。”《尔雅》又曰:“如槐曰茂。”郭注:“言扶疏茂盛也。”马夌云曰:“下章曰桥松。桥,高也;松,莑也,言其木高而枝叶莑松也。然则松柏与槐古皆谓之扶苏矣。”(《吴氏遗著》) 《说文》曰:“扶疏四布也。”盖以茂盛义同松柏、槐树之茂合;又如,作唐棣解。《正义》曰:“扶胥,山木,宜生于高山。”[3]301潘富俊在《草木缘情》中说:“山坡地和山谷低湿地生态环境不同、土壤的生育条件有异,自然会生长不同的植物。山脊、山坡的植物耐旱耐瘠,而山谷低地的植物需水量大。《诗经》记载了当时北方植物的生态分布,如《邶风·简兮》篇有‘山有榛,隰有苓’,《郑风·山有扶苏》篇‘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及‘山有乔松,隰有游龙’等,可归纳出山坡地耐旱的植物有榛、唐棣(扶苏)、松……”[17]63-64概而言之,“扶苏”共有四种解释:其一,如《正义》之意,指“小木”;其二,扶苏同蒲苏,指桑树;其三,松柏、槐树之茂状比附扶苏之茂状,盖指松柏、槐树;其四,扶苏生于贫瘠的山脊,指唐棣。
“荷华”即芙蕖,也就是今天所指的荷花,无异议。“游龙”,即马蓼。《郑笺》曰:“游龙,犹放纵也。”[3]301“放纵”即繁盛貌。《尔雅》曰:“红茏古,其大者蘬。”《毛传》曰“龙,红草也。”[3]301红草似蓼,髙大而多毛,故谓之马蓼。《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游龙,一名马蓼。叶麄大而赤白色,生水泽中,髙丈馀”,无异议。“乔松”,《正义》曰:“毛作‘桥’,其骄反;王云‘高也’;郑作‘槁’,若老反,枯槁也”[3]301。郑枯槁之意有误,应从毛作高解。“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二句皆触物起兴,“扶苏”之茂,“荷华”之盛,“游龙”之放纵,草木繁盛之貌,唯夏季有之。诗人不可能在同一季节既看到草木之繁盛,又看到松柏之枯槁,故“乔”不当作枯槁解,而应作高大解。
概而言之,“扶苏”之茂、“荷华”之盛、“乔松”之高、“游龙”之放纵,皆为夏季之物象,故此诗当作于夏季。
(二) 《山有扶苏》乃盛夏归宁巧妻恨嫁拙夫的抱怨之辞
陈子展先生指出,《山有扶苏》“疑为巧妻恨嫁拙夫之歌谣”[8]259;周振甫先生也说,“当是一首民谣,写一个女子,悔嫁了一个品行不端的丈夫”[9]86。巧妻恨嫁之抱怨是在夫家还是娘家呢?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如若在夫家抱怨或会遭来更多祸患。情理上讲,女性只有回到娘家才敢抱怨,才有抱怨的资格。古代女性不得随意外出,回家省亲是为数不多的出门机会。省亲途中必要翻山越岭,涉河淌水。诗中既有高山,又有下隰;既有扶苏、乔松等树木,又有荷华、游龙等花卉,树木生于高山,花卉生于下隰。无论是从高山到下隰的空间变化,还是从植物的丰富性来看,皆可说明诗人处于行进之中。
女子夏季归宁之例,《春秋谷梁传》中有载,如“夏,夫人姜氏如齐。”《葛覃》中也有女子夏季“归宁”的记载,诗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1]6
“归宁”具有时间性与限制性。葛覃蔓延山谷之中,《韩非子·五蠹》曰:“冬日麑裘,夏日葛布”,夏日正是采葛制衣之时。又“萋萋”“莫莫”言葛覃茂盛状,故诗中女子归宁的时间应在夏季。《葛覃》中记载女主人有采葛制衣、浣洗衣物、勤俭节用等诸多事宜,故出嫁的女子需要在夫家无事时才可归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据《七月》载,将出嫁的女子各月之事罗列如下:

表1 《七月》所载出嫁的女子各月之事
如表1所列,一年中1月操练打猎、凿冰;2月修锄犁、搬冰入窖;3月下地耕种、取冰、祭祖;4月修理桑树、采桑;5月远志结籽;9月割芦苇、织麻、染布、织衣、收远志果实、打枣、摘葫芦、采苦菜、砍柴;10月筑打谷场、收拾秋麻;11月收稻、酿酒、庄稼入仓、筑宫室、割茅、打绳、修理屋顶、打扫谷场;12月猎貉、猎狐,为公子裘。3月至5月为春季,6月至8月为夏季,9月至11月为秋季,12月至次年2月为冬季。唯有6、7、8月赋闲,故正好与女子夏季归宁相印证。
“归宁”具有条件性。出嫁的女子已是夫家之人,需经夫家允许才能回娘家,不能随意“归宁”。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首先要告诉师氏,在征得夫家同意之后才可归宁,否则将会招来夫家的讨伐。如隐公二年,向姜未经莒子的同意,擅自归宁,“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葛覃》中记载的采葛制衣、浣洗衣服、勤俭节用等诸多杂务都由女子一人承担,可见女子在夫家的繁劳。而这些繁杂的家务丈夫并不与其分担,思念远方的家人还要受到诸多限制,所以《山有扶苏》中远嫁女子“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的抱怨就很好理解了。因夫妻生活不协而归宁抱怨之例,可见于《左传》,隐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向姜因不满莒国的生活而回到了向国,可谓开归宁抱怨之先例。
前文已述,归宁多在夏季,归途中见“扶苏”“荷华”“乔松”“游龙”之貌满心欢喜,暂时摆脱“狂且”“狡童”之纠缠,因而触物起兴。故《山有扶苏》篇可理解为盛夏时节诗人归宁途中登高山见扶苏、乔松,过下隰见荷华、游龙起兴而作的抱怨之辞。
三、结语
近现代学者从文学的角度解释《山有扶苏》获得了普遍认同,但他们只是简单地从文字层面看到巧妻恨嫁拙夫的抱怨,却忽视了诗歌抱怨中的深层内涵。《山有扶苏》中的季节判定帮助我们了解此诗乃是归宁途中巧妻恨嫁拙夫的抱怨之辞,而归宁这一风俗,对我们了解先民的生活习俗有不可小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