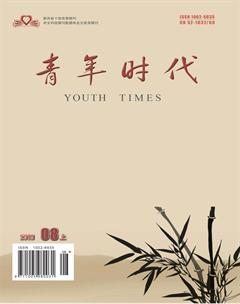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的天文学史研究简述
李玉鹏
摘 要: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Gaubil)于1722年到1759年在华,历经雍正、乾隆二朝,在历史、文学、民俗风情、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在华期间,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天文学史和历史纪年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西方天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耶稣会士;宋君荣;中国天文学
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改历的需要,传入了欧洲的天文历法知识,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历法、历史纪年等。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将中国的历史纪年以及天象记录介绍到西方,其成果很快被欧洲天文学家所引用,通过他们的介绍与传播,这些知识对17、18世纪的欧洲天文学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伏尔泰将中国古史纪年作为反对《圣经》的强有力的武器,并且在《风俗论》中说到“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①
从中国的方面来看,传统的学术如果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西方近现代学科的体系,适应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路将传统中国知识纳入近现代的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明末清初的汉学家们的研究实际上是第一步的尝试,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至今还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他们当时的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将有力促进中国的学术成为当今世界学术体系中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中国学者逐渐拥有世界胸怀。
(二)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宋君荣的研究大致是从对其著作、书信的整理发表开始的。海外的宋君荣研究要早于国内研究,在19世纪初,拉普拉斯(法)就曾在《时代知识》上发表了宋君荣关于中国天文学研究的若干文章,随后,雷慕沙、毕欧和布鲁克尓等汉学家或耶稣会士也相继发表了论及宋氏的文章,其研究和评价深度逐渐加深。到了20世纪,海外汉学界对宋君荣的研究更加深入,甚至出现了专门从天文学和地理学角度切入的研究。如1932年发表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的遗稿《中国纪年与周朝建立》,该文第二部分为《宋君荣年表》,其中论述了宋氏的天文学著作和其对于日食的看法;同时法国学者詹嘉玲的《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领域的接触》也从天文学入手分析了宋君荣的著作与研究。
国内对宋氏的研究大约是从20世紀开始,前期作品多是对宋氏的生平及其著作略有提及,篇幅较短,如莫东寅在其《汉学发达史》中就对宋氏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单的介绍,篇幅限制在一段以内。后期研究逐渐深入,曹增友先生的《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中宋君荣的天文学成就也指出了其所作推论中的一些谬误,韩琦先生也在《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一书中另辟一节,介绍了宋氏的天文学研究和他对黄赤交角的观点及研究。
由此可见,学界对宋君荣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与丰富,相信日后会有更加优秀的相关著作问世。
二、生平及著作
宋君荣(Antoine·Gaubil),字奇英,1689年出生于法国,15岁时进入耶稣会学校学习,并立志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721年,他获得国王授予的数学家敕书,前往中国传教。次年,到达广州。1723年应康熙之邀前往北京,截止到1759年宋氏死于急性痢疾,他一共在北京居住长达36年,逝后葬于北京正福寺法国人墓地。
宋君荣博学多识,知识渊博,在诸多领域都有所涉及和研究。方豪称赞他是“欧洲最博学的耶稣会士②”。宋氏在历史、文学、民俗风情、天文学和地理学上都有着丰富深厚的学识和出色的成就。他的汉语、满语和拉丁语都相当出色,来华后曾受命担当新来传教士们的翻译,还曾担任朝廷拉丁语翻译,协助理藩院处理与俄国的外交事务,在中俄就边界问题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大唐史纲》和《成吉思汗和蒙古史》,翻译了《诗经》、《书经》、《礼记》和《易经》,译词准确,中国色彩浓厚。宋君荣对制图学也十分擅长,曾绘制了北京城图,琉球和越南地图,在1727年写与盖亚尔神父的信中,他提到“十三御弟亲王曾多次明确表示,皇上对徐懋德、冯秉龙神父和我本人绘制的那副地图甚为赞赏” ③,其制图研究后被冯秉龙的《中国通史》所采用。雷慕沙称他为“18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宋氏研究领域广泛,著作众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将主要介绍他对中国天文学史的观测与研究。
三、天文学研究
欧洲一直对中国的天文历法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沟通交流上的缺乏,没有人能对这方面有着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即使有些耶稣会士曾撰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也有部分涉及此方面,但是由于缺乏各种专业知识,其中偏误较多,难以为证。当时要研究中国历法和天文学史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点能力:一、熟识汉文和满文;二、阅读大量中国天文学史著作;三、懂得欧洲古代和近代的天文学,熟练掌握各种理论和运算公式;四、善于发现问题,辨别是非。而宋君荣恰巧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来华前他已掌握丰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来华后为了传教,他又努力学习汉文和满文,在一位举人教徒的帮助下大量阅读中国文献,并经常向其他的文人请教问题,以此对中国天文学著作进行整理与分析。
中国历朝的正史中有历志专门记录天文历法,日月食情况及计算方法、各种天象记录等,宋君荣考察了《诗经》、《书经》等书中对日月食的记载及历朝研究者对其的评论和注解,并认真阅读了邢云路的《古今律历考》和朱载堉的《圣寿万历年》,梳理其中上千年的有关日月食的记录和计算方法。宋氏的天文学著作主要介绍了年代学的原理,帝尧时代的恒星记录,仲康日食,二至日圭影观测,中国古代关于黄赤交角的认识等等④。这些介绍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十分新颖,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也促进了他们对中国天文学的理解,避免断章取义,错误评判。
宋君荣写给法国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等欧洲各科学院及其亲友的信件中多讲述自己对中国古籍中的天文学史的研究和自己的天文观测。下面是宋君荣在北京所做的天文观测的部分记录:
1730年12月20日,用14法尺的望远镜,在北京测得木星的第四颗卫星的掩始是18时50分12秒。在巴黎,观测到的这同一掩始是在11时12分53秒。不考虑望远镜因素,这两地的子午差是7时37分28秒;
1737年12月4日,在北京用20法尺的望远镜,测得木星第一颗卫星的第一次复现时间是8时11分40秒。依据这次观测,该卫星在12月2日掩始的发生时间是13时43分38秒。
1738年12月21日,在北京用12法尺望远镜测得木星第一课卫星的第一次复现是在13时23分40秒。在巴黎,用16法尺的望远镜,测得的这次复现时间是早5时47分8秒。考虑到望远镜差异因素,两地之间的子午差是7时36分24秒。⑤同时,宋君荣还将他所做的观察与其他人在世界各地所做的观察进行比较分析,他把在北京所做的对木星的观测结果与在彼得堡、柏林、巴黎、维也纳、马德里等地所做的观测结果列表对比,发现了北京和法国天文台间的子午差在7时35分29秒或39秒与7时36分20秒或30秒之间。
除了对木星的细致观测,宋君荣对黄赤交角的变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时欧洲学者对黄赤交角是否变化的问题主要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黄赤交角不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腊羲尔和耶稣会士利酌理;二是认为黄赤交角随着时代变化而减小,主要支持者是科学家卢维勒和耶稣会士布迪耶。宋氏根据对古代观测记录的整理对其中黄赤交角的变化规律进行黄赤交角了深入探究,并得出了黄赤交角不断减小的论断,但是他始终认为这一结论并不确定,仍然保持黄赤交角不变的观点,从他的相关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观测与思辨期间他的内心的纠结与困惑。弗莱德曾在信中说道:
宋君荣神父在信中附了四页纸的关于黄赤交角变化的注解······看起来他的观测都有利于卢勒维先生的观点,反而与腊羲尔先生关于黄赤交角不变的推论相反。
在1734年7月宋氏写与德利勒的信中,他提到:
布迪耶神父相信,从他的观测中可以看出黄赤交角易变性的论据;您看一下我寄给您的中国圭影观测中可以看出什么结果。
此时,宋君荣已经从自己的观测和古代的观测记录中发现了黄赤交角变化的现象,但他仍然认为这一结论并不确切,坚持黄赤交角不变的论点。1750年和1756年,他分别在信中写到:
我自文献中看到的和我自己的观测都可以证明布迪耶神父的观点,但是我避免证明根据布迪耶神父的系统所得出的减小的数据和比例······
德利勒神父,我請问该如何测定黄赤交角呢?因为我有时发现它增大,有时又减小。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呢?⑥
虽然宋君荣始终认为黄赤交角不变,但这一论断与观测结果的违和也促使着他不断去研究中国古代二至日的圭影观测,也激励着他不断进行细致的观测与计算。
四、结语
在欧美早期汉学研究中,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宋君荣可称为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古代天象观测数据的整理分析及其自己所做的各项精准观测,对近代欧洲和中国的天文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 [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P74.
②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73,p84.
③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p169.
④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p78.
⑤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p55.
⑥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p78.
参考文献:
[1]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2]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M].中华书局,1973,p84.
[4]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5]张明明:《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研究史概述》[J].时代教育,2011.
[6][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M].商务印书馆,1995,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