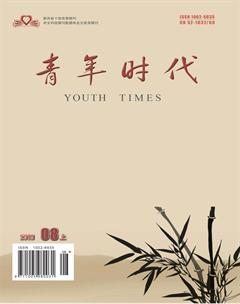浅析《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意义
郭扬
摘 要:《去中国的小船》于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四月公开发表于文艺杂志《海》,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昭和五十八年该作品经改稿后被收录进同名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此次改稿涉及叙事、人物对话、叙事者心境等的细节表现。而后,1990年9月在第一次改稿的基础上经再次修改,收录在讲谈社出版的《村上春树作品全集》。本文以200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少华译本《去中国的小船》为阅读文本,尝试分析小说中“中国”的意义和特征,为解读此篇作品及村上春树的中国情结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记忆;存在感;疏离感
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以主人公的记忆为线索展开,依据时间先后讲述了三十岁的自己在不同年龄时期邂逅的三位中国人,逐渐形成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对生活的思考。“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主人公内心的“中国”是怎样的世界与现实的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有怎样的联系呢,依据文章脉络,本文将分别分析三段邂逅,从每段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心里出发,尝试找出“中国”的含义。
先行研究:山根美惠的《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论-对社会意识的觉醒》一文从潜意识中的“差别意识”层面展开论述并将小说定位为《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天黑之后》等村上关注社会问题系列作品的原点。浅利文子在《村上春树的中国-以<去中国的小船>为视点》中提到这篇小说是村上春树作品的中国元素的起点,“我”通过与三位中国人的相遇触发了内心对“中国”的向往并寄托期待。
中国研究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于小说中的中国人的虚与实、与村上春树的战争观等方面。
一、模糊的记忆与“记忆符号”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这篇文章将从可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开始。”“我”记不清小学时代的事,唯一可以回忆起来的两件事中的一件便是去中國人小学参加考试,遇到中国监考老师。我的记忆是模糊的,通过努力搜寻记忆残片想起“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因此到图书馆对照体育年表便可以知道我遇到第一个中国的具体年份。但翌日,当“我”来到区立图书馆时,突然疑惑“阳光充足的阅览室桌子上的旧新闻年鉴同我之间,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种因素吗”,于“我”而言记忆中的往事与现在图书馆中的历史年表是两码事,我想展现的是记忆、记忆中的“中国”、“中国人”而不希望把这与历史、现实联系的过于密切,它是区别于现实也区别于现在而言的历史。但这段记忆又不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村上在1998年接受台媒采访时表示:他的父亲在大学时代被征兵调至中国大陆,人生发生很大改变。在他小时候父亲对战争绝口不提,但常常讲中国的风土人情。由此得知在村上的记忆里“中国”是伴随他成长的存在,潜藏在记忆之中,是记忆中的一个符号。加之年少时他所生活的神户地区有很多华侨,同学中也有华侨子弟因此中国对于村上不仅是记忆中的,有想象空间的,也是并不虚无缥缈的存在。中国是其记忆中的不可抹去的符号,与现实的中国区别又相互联系。而小说便是村上记忆中的“中国”的浮现。“记忆中的存在”随着三段相遇变得清晰。
二、与中国的邂逅
(一)小学时期
1.有距离感、与想象相反的“中国人小学”
“我之所以到位于港街的高地上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模拟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考场分好几处,而我们学校被指定去中国人小学的唯有我自己,什么原因不清楚,估计是某种事务性差错造成的,因为班里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场。
对于这个过去并不了解的中国人小学充满距离感。想象的中国人小学也是“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等两个星期来在我脑海中随意膨胀的图像”。真正来到“中国人小学”后才意识到现实的环境与“我的想象”形成强烈反差:“外表上与我们小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清爽得多”“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2.中国人监考老师:有板有眼、自豪感、尊重
对于中国人老师的认知可以通过我记忆中老师的讲话来解读:“试卷发下以后,请扣在桌上别动。等我说好了,再翻过来答题。差十分到时间时我说最后十分钟,那时请再检查一遍有没有无谓的差错。我再说一声好了,就彻底结束,就要把试卷扣在桌上,双手置于膝盖。听明白了么?”提及考试老师是严肃的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注意: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今天早已忘了。我能想起的,唯有坡路上行走的小学生和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记忆力不好的我为何对此对念念不忘呢,浅利文子认为这里的自豪感是文章第一节中“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的“灰土”的同音词,实际上则暗示着中国人的自我怜悯,是被日本社会排斥的在日中国人自我表现的过剩反应。笔者也注意到了多次出现的“自豪感”,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存在感。当时的“我”听中国老师讲话,受到鼓舞,才满怀自豪感这是作为个体的存在感,才能至今难忘。而前文的“灰”则是这一时期的“我”,寻找存在感的我对于周围环境的判断和寻找自我存在过程中的正面心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涂鸦,在中国人老师的口中是随意的、不尊重的表现。高三那年得知女友与我同一考场时我明知女友可能并不记得却反复追问当时桌面是否有涂鸦,最后头脑中还浮现发现涂鸦的中国少年像。涂鸦充满负面意义代表不尊重、伤害。“我”多年后反复的确认和最后脑海中的想象反而突出我怕留下涂鸦、伤害的紧张感,不想伤害那滑溜溜的桌面的以及那里的一切,因此涂鸦反应的是“我”是紧张过剩、罪意识强烈的表现与第二段相遇的女大学生的心理相似。
第一段相遇的中国从想象中的黑暗变成现实中的整齐干净,第一位中国人是充满自豪感的有板有眼的形象,而作为人,个体的我在这一时期找到了存在感。但我对中国(或者异境)的罪意识及负罪感让我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距离。
(二)与中国女大学生的邂逅
“我”遇见的第二个中国人是一起打工的中国女孩,她有如下特点:沉默寡言的,干活非常热心: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变得干活儿热心,可我们的热心不同,我是普通的热心,而女孩却有种“紧迫感”仿佛她周围所有日常活动都因了这热心而得以勉强合为一束并得以成立。她会因为作业顺序乱而陷入精神危机。后来“我”与女孩熟悉,约她喝酒,彩灯下的她看上去同在仓库时判若两人,乐淘淘的。后来我送女孩儿回家,时候才发现将其送到了相反方向的电车上,而我还意识到原本方向相同可以一起回去的。女孩所属的类型是:一旦坐错车便一直坐下去。最后找到女孩时她说“即便你真的弄错了,那也是因为实际上你内心是那么希望的”这种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可以了。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女孩为何会这样说呢:从来没回过中国的中国人,基本也不会说中文,在日本长大却还是中国人的身份(区别于日本人这个群体的存在),在东京的舞台里,她不仅仅是大都市中的漂泊者,她还是挣扎在日本人社会边缘的,不会中文的她也疏离于在日中国人的圈子。因此更为孤独,无法找到存在感的她过于紧张、敏感,会陷入自卑、崩溃变得逆来顺受、麻木。所以被送上相反方向的列车,即使发现也不愿下车改变方向。她深刻地明白“这里没有她的位置”而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最后我将写有女孩电话的火柴盒也不小心扔掉,此后经过寻找也没能见到女孩。山根在研究中指出,这是我无意识地远离“中国女孩儿”的表现,换句话说我无意识地远离那些“少数”,因为我并不属于“少数”所以根本无法理解这类群体。浅利文子在研究中也表明认为我对女孩犯下的两次错误都是“我潜意识”在行为上的表现。而笔者认为文中的我明确指出“舞台转至东京”这说明“我”也同样背井离乡成为都市的漂泊者,“在东京我完全孑然一身,没有像样的朋友,大学里的课又枯燥无味。”由此可见“我”也是孤独的。“我没有办法向你很好地解释我这个人。我时常闹不清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虑什么如何考虑,以及追求什么。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都稀里糊涂。这种事一一细想起来,有时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十分自私,从而伤害别人,尽管我并不愿意。所以,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人”这段独白倾诉了作为都市漂泊者的孤独及迷失。“我”通过与“中国女孩儿”的邂逅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
(三)与高中中国同学的相遇
记忆模糊的我与记忆及其清晰的高中同学形成对比,但无论是为了刻意记住而忘记还是想忘记却依然记得,我们都活在当下。
当下的状态: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脸也是那样的气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现出的表情却好像是为了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推销百科辞典的职业,他的受众仅限于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都拜访过了就只能转向推销别的比如保险,总之是要对付活下去的。作为生存在日中国人、社会边缘的人为了生活,棱角被磨平,曾经的个体存在感被渐渐打磨。
而被磨损的也正是我自己:重逢时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这些全都是在这个无可捉摸的巨型城市里进行的。在这个大都市的“我们”看似拥有表面的都市生活的一切、但实际上是被都市变得孤独、迷失自我的,因此后文指出看似拥有一切的我们实际上什么有没有。这里的我不仅从“中国”中看到自己,也仿佛是与之共存的。
三、与“中国”的相遇·理想化的自己
小学时代第一次与中国邂逅,那时的我找到了存在感和“自豪感”。
第二次我已经来到东京与女友关系疏远、并觉学校无趣,孑然一身。遇到身份特殊的中国女孩从孤独敏感崩溃的她身上看到空虚、找不到位置的痛苦。第三次与高中中国同窗的相遇看到的是“磨损”的人,是在都市边缘磨损着的人。三十岁的人生里分别在小学、大学、结婚后不同阶段与“中国”相遇,有自豪感的中国老师,找不到位置的中国女孩,彻底被磨损、接受成为生活在都市边缘群体的高中同窗像影子一般使我发现自己:有存在感的自己-找不到位置渐渐迷失的自己-埋葬希望与痛苦的自己。因此中国的存在中国人的存在像是一面镜子,折射着是自己,与中国的相遇便是与自己的相遇。
最后三十岁的我终于意识到:倘若再一次在外场追球时一头撞在篮球架子上,再一次头枕手套在葡萄架下苏醒过来的话,这回我到底会说出怎样的话呢?或许我将这样说: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对外界的认知与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中国”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象征着美好的自我世界,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逃离现状的与谬误,找到出口达到那个美好的“中国”就不能失掉遥想、仍然要以无所畏惧、不畏崩坏与孤独的方式去追寻“中国”尽管它过于遥远。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的意义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自己,同时也是理想化的自己理想化的自我世界。并不是地球上黄色标记的地方,可以是任何地方。由于小时候父亲的影响村上记忆的中国是个遥想的世界,本篇小说从都市文学的角度通过都市中“我”的孤独,迷失,与社会的疏离赋予了中国非现实化的意义。但三段与中国的邂逅描写“中国”也带有现实中国,带有历史痕迹的意义比如监考老师的性格使中国读者感受到某一时代的中国精神。而无论哪也一段邂逅,其中的中国人都是生活在日本社会边缘的,是疏离于日本社会、日本人的存在,这也一定程度上反应客观现实以及历史。
四、总结
本文依照阅读文本、对照先行研究通过分析主人公与“中国”的三次相遇,尝试解读“中国”在小说中的含义,笔者认为这是村上春树都市文学中的一个短片,着重体现的是村上的人生观。但也融入了作者的观察及体验(记忆),其中也可以找到现实意义的中国及中国与日本的社会历史痕迹。以此为起点,今后将收集更多的文本、资料希望进一步了解村上春树的中国观,中国情结。
参考文献:
[1]山根由美惠『村上春樹「中国行きのスロウ·ボート」ー対社会意識の目覚めー』 近代文学試論(40).2002-12.
[2]浅利文子.『村上春樹の中国ー「中国行きのスロウ·ボート」ーという視点から』 異文化論文編(11)2010-04.
[3]安倍「村上春樹論の試みー短編二、三の解読をめぐって」ー[Z].紀要 第22号 神戸学院女子短期大学 1989.
[4]王海藍.论村上春树的战争观--由“死使我想起中国人谈起”.文学评论.2013.04.004.
[5]吕周聚.论村上春树的中国情结与创伤记忆.社会科学辑刊,2015 第4期.
[6]林少华译.去中国的小船.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