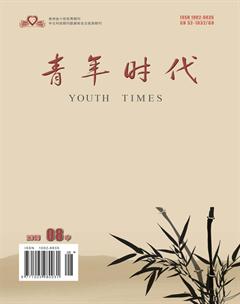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跨族裔两性关系”中的 文化内涵
姜安琳
摘 要: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她将东西方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思考,以平和宽容的心态看待文化差异,并期待实现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与理解融通。从其新移民小说中的跨族裔两性关系中,我们不难窥见严歌苓对移民母题“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歌苓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之间,在男性社会与女性自我之间,努力寻找两端沟通的可能性,彼此的冲撞常常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沟通与理解,从而寻求文化间的共融或共存。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文化内涵;共融
严歌苓是当今海外华文文坛上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前往海外求学,之后移民美国,成为美籍华人。她创作了很多反映华人移民生活的作品,譬如《少女小渔》、《扶桑》、《栗色头发》、《太平洋探戈》……
陈贤茂将新移民文学定义为“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①,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在跨文化背景下,关注整个移民群体的命运、思考并探求在异域生存环境下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复杂生存条件下人性的彰显等问题。跨文化视野使她对移民母题“东—西”方文化关系持有强烈的关注。
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表现男女关系的大部分作品都把不同种族的两性置于不同的文化中加以呈现,作家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对跨族裔两性关系加以考量,也就是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位置和关系加以考量。本文以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为研究范围,聚焦于她笔下表现跨族裔两性关系的作品,试图从中窥见严歌苓对移民母题“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绎。
一、隔膜与冲突: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
身处异域环境中,移民最先遇到的就是语言的隔膜。在严歌苓的短篇小说《簪花女与卖酒郎》中,东方女子齐颂在被美国姨妈卖掉前,被扔在路边,偶遇了一个卖酒的墨西哥小伙子卡罗斯,语言不通的二人却能很迅速的由陌生走向亲近。然而,当姨妈回来后,她凭借流畅的英语,进行着“歪曲本意”的翻译,硬生生将两颗靠拢了的心分开。最终卡罗斯只能眼巴巴看着女孩被那老女人带走。这两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仍能产生真挚的爱情足以说明,爱情是超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的信念,但是即使是两性吸引这一纯粹的人类情感也无法规避语言形式独自前行,反映了东西两种文化理解沟通的艰难性。毕竟“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人物的失语不只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而且还来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误解。”②
除了语言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严歌苓还描写了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差异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隔膜。在《太平洋探戈》中,东方女子阿翠与白人青年罗杰的婚姻之所以渐行渐远,正是因为二者在各自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价值观念的不同。罗杰认为朋友们一起吃饭完全可以AA制,但阿翠却觉得应该主动付钱,更有面子。罗杰认为自己相对父母而言是独立的个体,会选择跟父母借钱然后归还,而阿翠却觉得父母给子女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还。阿翠认为自己作为女性理应接受男性的追求,罗杰却觉得二人是平等独立的个体……多次冲突过后,两人的感情也消失殆尽。
罗杰和阿翠无论是在内在的价值观念,还是在外在行为方式上都显示出较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东西方文化在互看的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火花,也是东西方文化關系对抗性的表现。这种对抗与冲突在《橙血》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和激烈。
《橙血》中,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玛丽迷恋上仅有14岁,来自遥远东方的阿贤。在三十年的岁月里,玛丽把阿贤视为个人私有财产,要求阿贤必须维持着她心目中的那个美好中国人的形象,她将自己放在圣母的位置,居高临下地控制、占有着阿贤的一切。她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一直是俯视、轻蔑东方文化的,他们的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而当阿贤“做中国人”的信念被唤醒,决定要离开玛丽的时候,他被有意地当做小偷而遭到枪杀。
阿贤和玛丽的关系隐喻了东西方文化所处的文化地位,在这种强弱悬殊的文化冲突中,东方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卑下、孱弱、落后的代表,西方文化以鄙夷和把玩的态度来对待这种被扭曲了的弱势文化。
二、拒绝与宽恕:强弱势文化间的博弈与转化
有学者指出,“在第三世界国民向第一世界移徙而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男女划分已不仅停留于性别层面,而且还延伸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赋予男女区分以特别的含义。”③也就是说,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性别文化政治学层面已被置换成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往往体现为西方男人对东方女人的征服与拯救。
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西方男人”和“东方女人”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中绝大多数已经超越了西方男人征服、拯救东方女人的范式,她在文本中以东方女性的拒绝和出逃,拆解了西方男性高高在上的姿态,表现出解构殖民主义的创作姿态。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男士都希望有一位东方妻子,或者对东方女性充满了爱恋和欣赏,譬如《栗色头发》中的“栗色头发”,《扶桑》中克里斯……然而他们的青睐并没有换来东方女性们的投怀送抱,相反,她们独立而自得的活着,哪怕身份低微,生活艰难困窘。
在《栗色头发》中,“我”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接受了栗发男子介绍的一份模特工作,并在相处的过程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尽管互存爱慕,但当我发现他对“我”的倾慕带着东方主义的目光,“我”还是决然的选择离开。令“我”更加无法接受的是他对中国人的诸多偏见。比如他模仿中国人吐痰的姿势以博取周遭观众一笑,再如他在与“我”聊天时提到“我”的牙齿真美,但随即又武断地说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这种带有歧视的偏见,使得“我”与“栗色头发”最终分道扬镳。
《扶桑》中,虽然扶桑身上依然具有殖民者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建构东方形象的多种要素,如小脚、长辫、马褂、长袍等等,但作者更为着力描写的是她身上“地母般的雌性”。她如同从人类的洪荒中走出来的地母,浑身散发出“古老的母性”。
扶桑是一个有些痴傻的中国妓女,却被严歌苓赋予了高贵的灵魂,她原谅了那个在反对华人的暴动中轮奸过她的白人男孩克里斯,那个从12岁起就迷上她试图拯救他但最终深深的伤害了她的白人男子,也是她唯一爱过的男人。由此严歌苓颠覆了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传统意义上强弱关系。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评价的:“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④扶桑宽恕了来自克里斯的侵犯,“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居高临下者”⑤。
在严歌苓笔下的跨族裔两性关系中,东方女性以拒绝和宽恕,拆解了西方男性的征服与拯救。她对以拯救者自居的西方进行了嘲讽,使东西方文化既定的关系得到了扭转,被拯救者不仅拒绝被拯救,甚至成为男性的宽恕者与救赎者。
三、理解与融通: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期望
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严歌苓如实地描写了东西方文化间的隔膜、冲突与博弈,但是其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二元对立的中西文化冲突模式有所超越。“两性关系”以及“爱情”在严歌苓的笔下成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栗色头发》中,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种种情感隔膜使“我”与“栗色头发”分道扬镰,但当“我”看到他刊登的“请给我回个电话”的寻人启事时,“我”决定,“某一天,我会回应,那将是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作者在此處设置了一个希望的尾巴,两性之间微妙的感情使人们愿意冲破自己所属文化的藩篱,达到沟通交融的境界,或许“我”与“栗色头发”实现理解与沟通的那一天终将到来。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文化思考是饱含希望的,小说寄予了她对东—西方文明互相借鉴、彼此受益和平等对话的愿望。她在小说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副美好的图景——只要人类有共同的情感与共通的品质,中西文化最终走向理解与融通。
要融通,而且要平等地进行融通,在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中,小渔用假结婚骗取绿卡,这项勾当,是由在居留国没有身份的小渔与有身份的意大利男性老头共同实施的,这种合谋已把双方身份差异的强弱势奇妙地扯平了,他们同处于“弱势”,共同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挣扎,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男女两性以及东—西双方在内在文化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
为了应付移民局的检查,小渔搬到老头家,与老头相处了一年。她努力适应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时用传统东方的包容去迁就老头。当“丈夫”生病后,小渔一直陪伴、照顾老头,最终用善良和宽恕的美德唤起了老头的良知,最后还将火车月票送给了她。在这对“夫妻”的跨国界交流中,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相互影响。
“文化冲突”在这里已经辗转变体为“文化融通”了。正如霍米·巴巴所言,坚持文化的固有原创性或“纯洁性”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对立”⑥。
总之,严歌苓一方面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不同种族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强弱势文化间的博弈与转化,另一方面又力图证明对于人类这个广博的范畴而言,民族、种族的差别微不足道,而文化隔阂也终究会在进一步探求人性的过程中悄然消解,实现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交流,优势互补,走向真正的融合。
注释:
①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②李亚萍:《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华文文学》,2003年03期,第62页。
③吴奕锜,陈涵平:《从自我殖民到后殖民解构——论新移民文学的女性叙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1期,第73页。
④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上海文学》,2003年09期,第27页。
⑤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扶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版 ,第159页。
⑥霍米·巴巴:《献身理论》,《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