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如何面对死亡时刻
文 《法人》特约撰稿 李伟长
《暮色将至》里的故事选取了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等这些伟大作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说是一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作者是美国作家、记者凯蒂·洛芙
美国作家,记者凯蒂·洛芙经常为《纽约客》写稿,被称赞为行文优雅且力道惊人。她的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凯蒂·洛芙受过母亲一些影响,不过在《暮色将至》里,她显得还是比较克制。力道惊人的效果,来自于她裁剪和组合材料,以及叙述的能力。她将寻常可见的材料重新叙述,使得它们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从内容而言,《暮色将至》是一本灰色调的书,但并不让人沮丧。我曾经听一位经历病痛的大学者讲,35岁时他就想通了生死的问题。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陷入生死纠缠的契机。换我们常人,面对死亡,总不免担惊受怕,无非是想活得久一点,至于质量如何,也不重要。
这本书的主题讲的就是死亡,所谓大作家的暮色时间,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美国作家、诗人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英国作家、诗人狄兰·托马斯(1914—1953)和美国作家、插画家、艺术家莫里斯·桑达克(1928—2012)等,面对死亡降临时的反应和表现。在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真的没有本质区分。当死神来敲门,有人会拖在门后久久不肯开门,而有人会提早打开门,迎着死神进门。
苏珊·桑塔格:“没有了我,万事万物如何存在?”
苏珊·桑塔格在71年的生命中三次确诊癌症。前两次,她都挺过来了。她在16岁的时候曾经写下:“对我来说,不再活着如何可能没有了我,万事万物如何存在?”这种对待死亡的近乎天真的发问方式几乎贯穿了桑塔格的一生。她无法设想自己的死亡。她的生命意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完全不接受自己的死亡。
她所迷恋的是活着这一事实本身,为此,她甚至可以不在乎生命的质量。为了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她以70岁的苍老身躯承受着化疗、移植、试验性药物所带来的种种痛苦。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主张的,她拒绝赋予疾病任何浪漫化的、阐释性的隐喻意义。在她自己被疾病侵扰折磨的经验之中,她始终将疾病作为生命的敌手,而将自己视为一名抵抗侵略的战士。
桑塔格像平常人一样怕死,她期望活得久一点。写桑塔格的部分,让我想起了桑塔格的儿子写的随笔集《死海搏击》,记录了他母亲患病之后的岁月,展现了桑塔格如何渴望在死亡的忧伤之谷展开双翼,试图再次飞翔。他不但呈现了自己母亲的不平凡——向死而生,相信理性,倔强自信。更重要的是,他也呈现了一个母亲的平凡——害怕死亡,渴望生存,看不透生死,参不透命运,如常人一样,因病焦虑,寻找偏方,遍求名医,期盼幸运降临。
相比而言,这本《暮色将至》写得更加冷静,也就更为触目。因为不用避讳亲人,作者叙述了桑塔格对生命的不舍和眷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机体希望以自身的样式死亡”
与苏珊·桑塔格不同,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一直以来都深信自己命不久矣。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进行了大量临床案例的研究,这其中还包括他自己。他热爱他的事业,所以当他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时,他要求自己做到绝对地清晰,如此才不负其事业中的诗意与科学。为此,即使在病痛之中,他仍拒绝服用止痛药,甚至他的死亡都是由他自己做出安排的:在读完巴尔扎克《驴皮记》的最后一页后,他向他的私人医生表示希望给他注射吗啡,让他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1.狄兰·托马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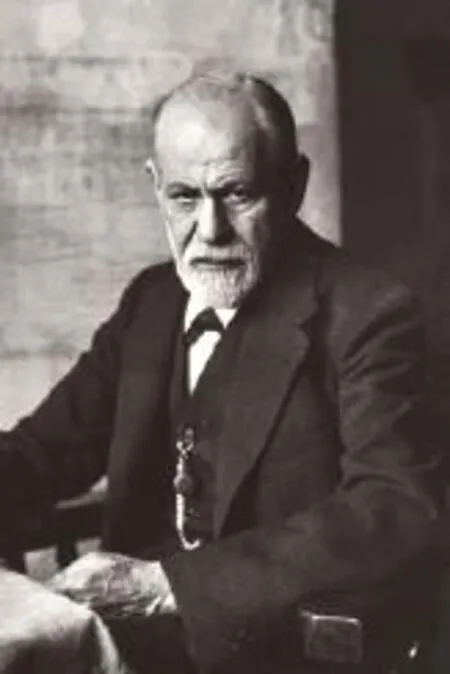
2.约翰·厄普代克

3.莫里斯·桑达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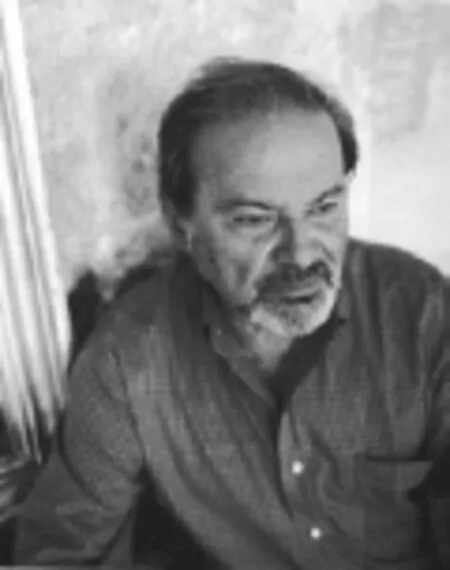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5.苏珊·桑塔格
在他的研究中,他提出人对死亡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向往,这就是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他甚至说“所有生命的目的都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克制,他可以毫无怨言地承受几十次痛苦的口腔手术。他唯一未能克制的行为是抽烟,即使抽烟不断加重他的病痛,他也无法放弃抽烟。抽烟之于弗洛伊德仿佛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成为他具体的生命中的一项本能。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连抽烟都是他自我安排的一部分。“有机体希望以自身的样式死亡”,他以惊人的控制力完成了自己的死亡。
弗洛伊德用吗啡结束了生命,狄兰·托马斯死于18杯鸡尾酒。他们似乎比桑塔格看上去要通透一些,也无畏生死一些。他们就是打开门等待死神做客的人。尤其是狄兰·托马斯,这个劝人“不要温柔地走入那个良夜”的诗人,自己却主动地走进了良夜。
对这个诗人来说,生与死之间似乎并没有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生死就像邻居一样。酒精给了他灵感,也给了他伤害。围绕他周围飞舞的女性们同样如此。狄兰·托马斯的去世简直就像一首诗,令人猝不及防,又似乎在意料之中。尤其令人感怀的是,从一开始写诗,从一开始学者了与酒精相伴的生活,生死相接的地方大概就是狄兰·托马斯最为熟悉的情境,似乎并不惧怕。喝醉,然后醒来是他的日常。终于喝醉,却没能醒来,也是一种日常。不得好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诅咒人的话。得好死就是善终,死于杯中物,死于可能的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狄兰·托马斯的结局也是善终。作者凯蒂·洛芙,展现了惊人的材料组织能力,通过她的叙述,狄兰·托马斯的生命结局早已注定,倒有点慷慨赴死的感觉。
约翰·厄普代克:活着固然可喜,但是不活也是可喜的
面对死亡,美国作家、诗人约翰·厄普代克说,我准备好了。他的暮色时分尤其令人感慨。这个几乎痴迷于用性冒险完成自我救赎的小说家,性对他而言是强大的发动机,在76岁那年,厄普代克被检查到了肺癌晚期。我们已经无法推测厄普代克的真实想法,当绝症真的降临时,他内心深处的波动。至少那意味着性这件充满能力的事情将彻底告一段落。
死亡一直是厄普代克畏惧并试图超越的对象。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通过疯狂的性和出轨获得的生命燃烧,来对抗对死亡的恐惧。被死神宣判的厄普代克,这回终于需要直面死亡了。书中写了一个细节,具有小说般开阔意识的细节。住院期间,厄普代克的前妻来病房看他。这个被厄普代克抛弃的第一任妻子,并没有沉湎于对过去配偶的怨恨和自我保护式样的反讽。她觉得没有必要证明厄普代克本质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蛋,她对他依然有着一种既现实又温柔的情感。
等死神来到了厄普代克的面前,所有曾经的恐惧和焦虑,以及为了逃避焦虑而进行的身体冒险和欲望释放,都变得不再有意义起来。对厄普代克来说,写作曾经是慰藉、逃避和庇护所。死神来到了面前,躲无可躲,逃无可逃,庇无可庇,写作也变得更为纯粹了。据说去世前,厄普代克的诗变得更好了,不为什么的写作会自然抵达一种化境。有这样几句诗:活着固然可喜/但是不活——被拖下来,依然/向太阳伸展——也是可喜的。
我喜欢这句诗。我甚至偏执地认为,这句诗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活与不活,都向太阳伸展,这大概是最自然也最倔强的样子。中国古语讲,不知生焉知死,说来何尝容易。真的想通生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中,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审判,就说过关于死亡,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是黑暗的地域,还是鲜花铺就的世界,没有人知道,没人能够说得出来。既然不知道是怎样的,那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和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呢?苏格拉底的想象,在今天依然有价值。被死神宣判之后,如何安然度过,变得如此困难,甚至变得不堪,这种现象总是在发生,大概还会继续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