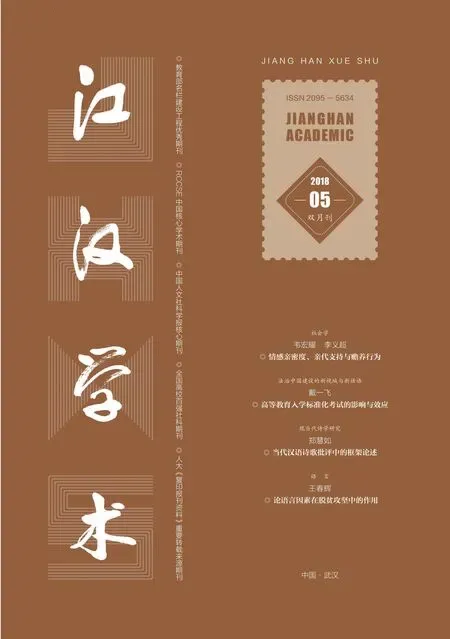论戴望舒诗歌“青”色世界的三重意蕴
叶琼琼,马红雪
(1.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 430063;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隐喻是诗的基础之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诗歌从理论到实践都对隐喻有着高度重视。中国晚唐诗、美国意象派、法国象征派等都是擅长使用隐喻的流派。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布鲁克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1]西方现代派对隐喻的推崇对20世纪初成长中的中国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920年代的象征派、1930年代的现代派,都反对“直说”和“狂喊”,主张诗歌多用暗示的手法。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提倡新的诗歌抒情原则,“将生活中常见事物本来的意义模糊化,赋予这些事物以一种超生活本意之上的喻指意义。”[2]“诗人以在接受与迂回中游走来呈现现实。隐喻是语言的迂回,却是呈现诗性的直径。现实不只是被动地被‘反映’,也被‘反应’。”[3]戴望舒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更在诗歌创作上身体力行,创作出大量含蓄多义的诗歌。他擅长用颜色词语构造意象存续的空间,通过隐喻手段让理想女性、故土家园与现实世界聚集,将现实完美地融合和反应在隐喻创造的时空中[4]。本文欲从一个小切口——“青”色词隐喻内涵角度切入,探讨戴诗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
一、戴望舒诗歌颜色词的使用
所谓颜色词,就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的光波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5]。汉语颜色词基数大,构词方式灵活,分类标准多。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颜色词为例,叶军针对现代汉语颜色词中的部分静态成员,把《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颜色词分为具体颜色词(包括基本颜色词和普通颜色词)和抽象颜色词两个大类,通过统计分析来管窥汉语符号系统对客观世界的表记功能[6]。叶军的研究所依据的《现代汉语词典》具有规范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加上其研究采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因此本文较为赞同其分类。为更全面、准确对颜色词进行分类,本文在其分类基础上增加含彩词,将颜色词大致分为基本颜色词、普通颜色词、抽象颜色词、含彩词等四类。基本颜色词一般指红、黄、蓝、白、黑、绿、紫、灰八种;普通颜色词指除了基本颜色词以外的其他颜色词,大多数情况下是基本颜色词派生出来的复合词;抽象颜色词则通过抽象的感知,激发人们对色彩的感觉,引起相应的听、触、味觉及心理感受。含彩词中的色彩语义由基本颜色词的颜色意义构成或参与,一般不直接表示颜色概念,但对于形成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具有重要作用。颜色词不单纯表示颜色,而往往与人类特定的意识、观念及情感相关联。如红色表示热烈奔放,绿色表示生机勃勃,蓝色表示宁静深思。颜色词与特定情思之间是如何建立起对应关系的呢?这源于隐喻的经验基础,“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在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7]18。经验基础包含身体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等。人的视觉机制包含感觉和知觉两种,当光波进入人的视野后,人能够感觉到色彩信息,然后会自觉地将色彩信息与过去的经验、所处的背景进行整合,构建对于色彩的知觉。比如燃烧的火焰会发热,人们可以用火烹饪食物、驱赶野兽,因此红色常常与温暖、热烈等情感联系起来。春天万物复苏,小草、树叶等植物都呈现为绿色,因此绿色常被认为富有生机与活力。当一种颜色具备了表情达意的功能时,它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学概念,而被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带有人文标记的审美符号,人们可以通过颜色词去表达或理解某种情感、体验、经历,甚至思想。“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7]3古今中外诗人用五彩缤纷的颜色词表达丰富的文化内涵:“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江南春》),一“绿”一“红”活现春光的明媚与人的神清气爽,心旷神怡;“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徐志摩《再别康桥》),若是没有“金”“艳”,诗人那心醉神迷、万分留恋、依依不舍等种种复杂难言之情不会如此跃然纸上;“人群中这些面庞的闪现;湿漉的黑树干上的花瓣”(庞德《地铁车站》,赵毅衡译),这首意象派扛鼎之作若是没有“黑”树干作为背景,便无法凸现花瓣的鲜艳明丽,无法形成猝然的对照,而此诗众说纷纭的内涵正是在这对照中形成的。颜色词的存在让诗歌明丽多姿,诗味隽永。戴望舒现可收集到的101首诗作中有明确颜色词的诗作高达58首,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颜色词是戴望舒诗歌赖以表达情思的重要写作策略之一。而在这些颜色词中,青色系列出现的频率最高,它在戴望舒诗歌中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隐喻内涵,破解其中奥秘是破解戴望舒诗歌艺术密码的途径之一。
关于戴望舒诗歌颜色词的使用情况分析,本文并不精确地按照语言学的分类进行阐述,而基本上采用普通颜色词和含彩词的颜色内涵对诗歌中的颜色词进行抽离,并进行归纳、总结。之所以不采用语言学的精准分类,是因为,一方面本文所做的研究是关于隐喻内涵的分析,关于颜色词的分类若过于精准,有可能一部分颜色词无法包括入内,从而会影响隐喻的内涵理解和隐喻内涵变迁的分析。另一方面,文学的语言是诗人寻找与自身感情最契合对应的语言来传情达意、表达所思所感的产物,在选择词语的时候诗人更注重于它的表达效果,而非是否合乎语言学规范,因此语言学的分类并不总是适用于诗作的分析。
颜色词的色彩概念有时候并不那么清晰,在古汉语中,青与苍、碧组成一个色彩系列,彼此之间虽有分别却能混用。本文将青色、绿色、天青色、碧色、玉色等归为同一色系(青色系),将珠色、绛色、赤色、粉色等归于同一色系(桃色系),戴望舒在诗歌中使用的颜色词可以大致分为青色、桃色、白色、金色、紫色、黑色和极少数的彩色、黄色、土灰色几类。戴望舒带有明确颜色词的58首诗歌中颜色词共出现135次,其中青色系的词语出现45次,占颜色词出现率的33.3%,出现的几率最高(见表1)。可以看出,戴望舒有浓重的尚“青”情结,他用“青”织出一个清新朦胧凄迷伤感的复杂世界。
二、戴望舒诗歌青色词的隐喻内涵
戴望舒为何如此偏爱“青”色?首先我们尝试从物理属性中寻找答案。作为自然色的一种,青色的波长界限模糊,色相和波长均在绿和蓝之间,不易辨别。物理学上的可见光的波长范围是400纳米到700纳米,波长越小越不容易被感知。蓝色波长为450,绿色波长为500,青色波长只能确定在470—500之间,波长范围向小值接近,所以青色的界限并不明朗,以青色为底色的事物也就显得迷离而朦胧,在人的视网膜中形成的色彩信息偏淡,在人脑中结合色彩经验和视觉效果形成的知觉信息也就不够浓烈,呈现出素淡的色调。青色波长虽然偏短,但是视觉效果却最为澄澈,一是因为青色的明度和纯度较高,青颜色的明暗范围更接近明,形成青色的主波长更单一,因此青色自身的色彩就比较澄澈①;其次,根据人的温度经验,火焰、太阳是暖色的,而天空、大海、树叶是冷色的,青色系的颜色一般被认为是冷色系的,冷色的色调更能给人以澄澈的感受。

表1 戴望舒诗歌中的颜色词使用情况

(一)(1)53款步(二)(1)54夜蛾(1)55寂寞(2)56我思想(1)52款步黑白不分、红帽子白帆1 57狼和羔羊(寓言诗)(3)58断章(1)1 1 1总计:58首(135)青、绿(包含天青、碧、苍翠、玉)45;桃色、红(包含珠色、绛色、赤色、粉色)29;白2 0;金7;紫2;黑16;其他(包含银色、黄色、土灰、彩色)16苍翠的松柏鲜红(嘴唇)彩色的大绒翅青春的彩衣彩翼1 1 1 1 1 1
同样是青色,但内涵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仔细分析青色内涵的流变,可以从中深入戴望舒复杂的情感世界,感知他情感波动的脉络。
在传统诗文中,青便有丰富的涵义。青色象征着生命和生长,如“青青河边草,一岁一枯荣”;“青”还有吉祥如意、和谐美好的意味,如“青鸟殷勤为探看”;“素女青娥”之“青”有素雅清淡之意,“青灯古佛”之“青”含着淡淡的孤独,“青裙布袜”之“青”暗喻清贫、清冷,而“青云之志”的“青”则有飞黄腾达之意;“青”还可表丑陋凶恶脏污之意,如“青面獠牙”。“青”不但意义多变,其指代的颜色亦是多变的,“青山绿水”的“青”指绿色,有碧绿茂盛之意;“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青”是黑色,指头发乌黑发亮;“青眼有加”的“青”指黑色,意指正眼看这个人;“青云之志”中的“青”指白色,喻光明的前途;“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青”则是蓝色,喻天空晴朗明媚。在传统诗文和口语中,青色与它所对应的内涵之间有比较明显、固定的关联。如青山、青天、青眼、青梅、青云、青面等。因此传统“青”的隐喻是常规隐喻,随着各种内涵的长期使用和广泛接受,“青”熠熠生辉的创造性特点逐渐被湮没,成为死隐喻。
在戴望舒的诗歌中,“青”主要蕴含三重意蕴:一是悲喜交织、苦乐相融、患得患失的爱情体验;二是对永恒精神家园的向往与追求但求之不得的怅惘与苍凉;三是对祖国和民族光明前途的乐观肯定与由衷赞美。“青”深深地烙上了戴氏个人气质和时代色彩,呈现古典与现代情感艺术交汇特征。
用色相与波长均模糊不定的青色隐喻复杂多变的爱情体验是戴望舒诗歌独特的创作策略。在《路上的小语》这首情诗中,青色让爱情如此明丽、清新,还微带一丝青涩:“——给我吧,姑娘,那朵簪在你发上的/小小的青色的花,/它是会使我想起你底温柔来的。∥……——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你的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这里的青色如梦似幻,它让你想起最甜的蜜和最醇的酒,饮一口就醉了。然而如此美好的“青”却又是捉摸不定、若有若无的,让诗人满溢着爱意的心充满了忧伤。透过这清新袭人的“青”,我们看到了初坠爱河中的诗人跃跃欲试,甜蜜陶醉,但又羞怯畏缩、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态。在《我的恋人》中,诗人陷入热恋,燃烧的爱火在他的心里起了奇特的化学反应:“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此时的天青色散发着圣洁的光芒,有着天青色眼睛和心灵的恋人是纯洁无暇、至圣至美的。天青色成为理想爱情的象征。然而,热恋很快就走向失恋,笼罩上一层浓重的忧郁、凄切的阴影。青色的模棱两可最适合表现绝望中隐隐升起希望,感伤中隐约有快乐的回音,凄冷中似乎还有一点温暖的矛盾、综合的情感。作者从青的“冷”色调与“活力”中找到了情绪“冷”与“热”的契合处,形成对复杂情绪的隐喻。
戴望舒对青色隐喻内涵极富创造性的开拓还表现在怀乡主题中。在面对城市的不接纳和现实的黑暗时,他化身失去家园的乐园鸟,希望融入自然的怀抱,获取肯定感和归宿感。因此这个主题的青色系列词汇隐喻着故乡的纯净明丽和包容接纳,寄托了漂泊的灵魂对永恒精神家园的渴望和向往。《游子谣》中的“青”浸染了诗人在追寻家园的过程中孤单清冷和现实重压下的迷茫无助。诗人感受到时代和生活的重压,作为“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8]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生命的欲望正在苏醒和要求勃发,但是又那么容易受到各种阻挠和压抑,不得不缠绕在灰色的日常生活中”[9],寂寥的诗人渴望在故乡的怀抱里得到心灵永恒的安宁。《对于天的怀乡病》中诗人审视自己的内心:“我呢,我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我啊,我真是一个怀乡病者,/是对于天的,对于那如此青的天的”,这里的青色是母亲慈爱的笑容和手掌的温暖,给诗人受伤的心灵带来莫大的慰藉。“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乐园鸟》)家园被毁的乐园鸟极其疲倦和寂寞,唯有那温存宁静的湛蓝青空或许能给它些许安慰。“青”带有无尽的包容性,让诗人在现实的苦闷中得到抚慰。“青”既隐喻现实生活的无奈和彷徨,内心深处的迷茫、寂寞与凄凉,也隐喻对永恒精神家园的渴望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诗人在“青”这个颜色上寄予无尽的情思,深深烙上现代知识分子思维的印记。
抗战爆发后,诗人在民族危亡面前走出了小我世界,走向广阔的大世界,融入了时代的洪流。诗人彷徨不安的内心世界终于明朗坚定,纤细感伤的絮语变成了深沉嘹亮的吟唱,忧郁朦胧的“青”被鲜亮明丽的“绿”代替:“泻过草地,泻过绿色的草地,/没有踌躇或是休止,/把握住你的意志。”《流水》这首诗赞美了集体力量,肯定了英勇的反抗,赞颂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革命终将取得胜利有坚定的信心。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戴望舒抛弃掉个人的悲戚哀怨,用诗歌语言为民族歌唱,描绘未来,用绿色隐喻在压迫下仍追求信念、乐观向上的中华民族。这里的绿,是青色的变体。
通过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戴望舒笔下的青色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颜色,它既明净又朦胧,既安静又忧郁,既生气勃勃又迷茫绝望,它是“情”与“思”的结合体,是对个体与社会存在状态的俯瞰与反思。青色隐喻内涵的变化纤毫毕现地勾勒出诗人情感变化的脉络:最初虽然无法摆脱晚唐纤细的哀伤,但个人情绪整体上是清新明亮的。个人感情经历的失败和时代的风云变幻让天性脆弱敏感的诗人逐步走向失望、忧郁、哀怨。他无奈又彷徨,想从文学的象牙塔中,在自然和回忆的家园中寻求抚慰。面对民族危亡,诗人投身救亡图存的战斗,诗歌风格开始深沉阔大。这时,他笔下的“青”又恢复了勃勃的生机。“青”的隐喻“已经扬弃了一般比喻的明晰性和语意关联上的对应性,而带有了抽象的甚至含混的特征。也正是因为它有着这种抽象与含混的特征,它又往往将诸如生命、死亡、爱、意志、欲望甚至存在本身等等这类原本属于形而上范畴的东西接纳了进来,使之具有非常浓厚的‘思’的色彩乃至于某种神秘的意味”[10]。戴望舒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并将这种独特的存在体验投射到青色中,成功地实现了传统与外来诗歌艺术的交融。
三、个人、古典与现代的融汇
戴望舒笔下的“青”为何可以容纳许多相异甚至相反的情感?其奥妙在于诗性隐喻的核心特征:无穷尽的创造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突然性、新颖性、美学性等[11]。隐喻的意义是模糊不定、多向散发、不可穷尽的。这种多义性的产生源于三个原因,一方面是喻体可以跟不同的本体结合产生不同意义;二是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个喻体会有基于本民族本时代本地域的喻旨;三是年龄、性别、性格、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使不同的读者对同一喻体会产生不同的联想,选择不同的意义去解读。诗歌犹如能拼出无数隐喻图形的魔方,在每一次转动中获得发展。而隐喻的每一次创新,都丰富与扩展了人类的语言系统,推动着语言的发展[12]。莱考夫指出:隐喻有两种,一种是建构我们文化普遍概念系统的隐喻;一种是常规概念系统之外的隐喻,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隐喻。这样的隐喻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的经验有一种新的理解……它们能够让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知识和信仰有新的意义[7]129。莱考夫把后一种隐喻称之为新隐喻,诗歌隐喻是新隐喻家族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之一。诗歌隐喻有一些属于“远取譬”,在看似不相关事物之间发现、创造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某些特征,抑制另一些特征,从而展现一个新的与内心情感吻合的世界。青色是多种颜色和内涵的集合体,当诗人情感的潮水流到明朗的区域时,清新的绿色就脱颖而出,清新、欢乐的情感便浮现出来;当诗人的心绪忧郁感伤时,明丽鲜亮的绿色便消隐而去,黑色、墨绿等暗色系便粉墨登场,默默诉说凄凉与忧伤;当诗人孤单和寂寥时,宁静深思的蓝便遮蔽了绿和黑。当诗人的心情变幻不定,若悲若喜,青色便在绿、蓝、黑、白之间变幻不定,暧昧不清。酷爱“青”的戴望舒手握隐喻这个万花筒,不断开拓“青”的隐喻空间,流转自如地创造新的意义,大气魄地开创一个显现新的审美风格和诗学意识的诗歌时代。
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深刻的现实。如果新隐喻进入我们赖以活动的概念系统,它将改变由这个系统所产生的概念系统、知觉、活动。许多文化变革起因于新隐喻的引入和旧概念的消亡[7]134。
戴望舒创造了一个梦幻的青色世界。隐喻语言“通过心灵构形,创造人类的精神性结构”[12]。吴晓东对此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当一个‘辽远的国土’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的范型,从而无法具体地进行描述的时候,诗人只能采取一种幻想性与比喻性的方式来呈现。这时的诗歌在语言维度上就无法脱离譬喻和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派诗歌的语言是一种隐喻和象征化的语言。批评家瑞恰慈认为:‘所有的语言终极都具隐喻的性质。’如果说这是从终极的意义上界定语言的隐喻性质,那么现代派诗歌则是在实践性和具体性层面印证着语言的隐喻性。”[13]作为现代派诗歌的领袖,戴望舒正是从“青”的这个词汇来印证现代诗歌语言的隐喻性。
戴望舒何以对“青”一往情深?这是因为“隐喻对一个人产生的意义一部分由文化决定,一部分与我过去的经历相关联。”[7]132。穆时英认为戴望舒“非常清楚地了解着自己的矛盾和自己的二重人格”,一方面爽直、钝感、无聊,近于白痴,失去理性,是只有“赤裸裸的本能的现代人”;另一方面,有着“羞涩、锐敏,近于女性的灵魂”[14]。这种人格的二重性就是他诗作的源泉。20世纪上半叶,民族多难,国家动荡,人们生活艰辛,“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15]。戴望舒就是一个寂寞入髓的人,如影随形的寂寞让他时时陷入忧郁和感伤中。“羞涩、锐敏、近于女性的灵魂”让他羞于狂放地倾诉,绿色、蓝色、黑色、白色等含蓄内敛的冷色调很自然地成为诗人的选择。虽然同是冷色调,但是其中的内涵因视觉感受和深浅浓淡的不同往往相异或相反:如绿色代表活力与希望,黑色却代表死亡和绝望;蓝色代表宁静,也代表忧郁。青色是这众多颜色的集合体,自然而然地蕴含着二重性。戴望舒性格中的二重性在“青”这个颜色里得到最恰当最适宜的表现。“尚青”是戴望舒天性使然。
戴望舒钟情于青色的第二个原因是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潜意识中促使他选择这个传统文人喜爱的颜色和意象。戴望舒对晚唐朦胧梦幻凄艳的情调尤其迷恋,他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16]682晚唐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李商隐,他的诗歌忧郁缠绵,晦涩多义,带有青字的诗句比比皆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李商隐将忧郁、惆怅、欣喜、怜爱、憧憬种种情愫都揉进了“青”这个色相模糊的颜色中。这种写法突破了古典文学感物抒怀的传统,闪烁着现代性的光芒。“这样的诗的情感蕴涵,传达方式和审美效果,区别于传统的‘白话’诗,也区别于五四之后流行的直白描述的现实主义、袒露呼喊的浪漫主义新诗的抒情模式,正是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在晚唐诗词中所要寻找的东西。”[17]“尚青”是戴望舒对古典文学传统的遥遥呼应,是对古典诗歌艺术传统创造性的吸收和借鉴。
第三个原因是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象征主义者在诗歌常常是晦涩含混的。这是一种故意的模糊,以便使读者的眼睛能够远离现实集中在本体理念上”[18]。它特别重视诗歌情调的暗示性,追求晦涩朦胧的表意模式,重视色彩与音乐性。戴望舒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倡导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观点,他认为诗歌是诗人“隐秘灵魂的泄漏”,诗的动机“在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他强烈反对“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倾向[16]50。戴望舒曾经翻译过保尔·福尔的《我有几朵小青花》:“我有几朵小青花,我有几朵比你的眼睛更灿烂的小青花。”其创作的《路上的小语》:“——给我吧,姑娘,那朵簪在你发上的/小小的青色的花,/它是会使我想起你底温柔来的。”在意象的选择、诗歌思维方式、诗歌的结构、隐喻的运用上都受到前者强烈的影响。他在中国古典诗歌提倡含蓄和西方象征派诗重视暗示的艺术传统中找到了相通之处,而隐喻便是通往含蓄和暗示的坦荡的大道[16]50。
戴望舒认可传统诗歌,积极借鉴和吸收传统诗歌的长处,以“回返”的方式站到了新诗艺术的前列,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其对诗歌隐喻语言创造性的把握和运用。霍克斯认为:“隐喻的主要用途在于扩展语言……并列在隐喻中的诸因素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为它们双方都带来了一个新的意义范围,因此当然可以说隐喻创造了新的现实,当然也可以说隐喻把这种现实限定在语言之内,从而使运用语言的人易于接受。”[19]戴望舒深谙隐喻与诗歌语言之间玄妙的关系,对诗歌隐喻语言的创造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创造性运用。对“青”多种隐喻内涵的赋予便是戴望舒这种语言探索的体现之一,其实质是对“现代诗质”的探寻。这种现代诗质的探寻,“一方面,是体认现代经验的性质,寻求诗歌感觉、想象方式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把诗歌外在形式灵魂化的追求,从而使‘新诗’弥合现代语言与现代意识的分裂,真正成为一种新的感受和想象世界的艺术形式”[20]。戴望舒诗歌显示了新诗自白话诗派、浪漫派以及格律诗派之后新的审美尺度,改变了诗歌感受和想象世界的方式。
注释:
① 迷离是因为波长范围和界限不明朗,澄澈是从另一个角度,即明暗和饱和度特点来讲,二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