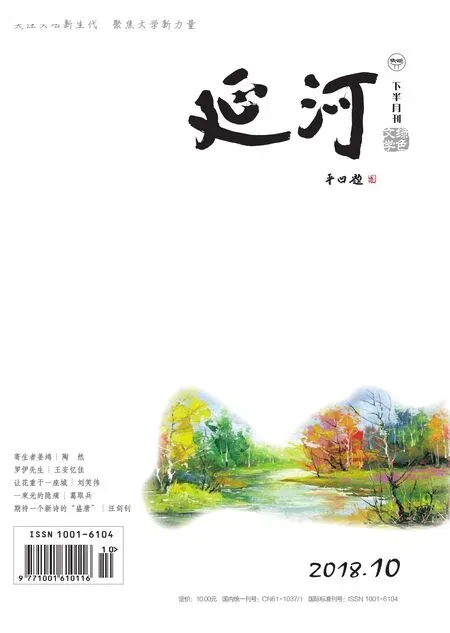丁家台旧事
丁国梅
(一)
很多很多年前,几十里外的汉江水在钟祥市旧口镇的大王庙处溃堤,洪水一泻千里,在丁家台的旁边冲出一条大漕,就是现在的丁家潭。我母亲便出生在那里。
我奶奶坐了十个月子,却独我母亲存活,所以我母亲是丁家台唯一进过学堂的女性。
父亲出生在一个叫向庙的村子,他从小就父母双亡,跟着唯一的哥哥过活,没想哥哥在新婚不到一年就过世了,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之后,嫂嫂抱着十二岁的我父亲痛哭一场后,就改嫁了,不知去了哪里。许多年后,我父亲寻找过她,但最终无果。
经人介绍,我父亲十三岁就来到了丁家做了童养(子)婿,改向姓为丁,名大元。都说买来的媳妇入赘的郎,父亲老实仁懦,在家很少说话,落个清闲不操任何心,家里家外都是我爷爷和母亲操持。奇怪的是我奶奶很待见他,可能是丈母娘看女婿,也可能是我父亲了了她没儿子的夙愿。
我母亲识文断字,能耕会耙,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所以母亲一直瞧不起一字不识的父亲,父亲好像也不喜欢母亲。后来破“四旧”,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乡里妇联给母亲做思想工作,鼓励她和父亲离婚,当晚,母亲抱着我流了半夜眼泪,早晨起来找到妇联主任说:“不离,死都不离。”妇女主任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
父亲是放马的,村里放牛的是一个半傻的女人叫望儿,她小时候倒还灵光,后来得了一场大病,家人就给她服用了朱砂,病好了人却傻了。再后来就嫁给了一个给生产队拾粪的哑巴。望儿每天屁颠屁颠赶着一群牛跟着我父亲,她很佩服我父亲,在她眼里,我父亲绝对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英雄,我父亲也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和傻望儿谈笑风生。
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房子又少,所以作为老幺的我一直跟母亲睡,我知道母亲其实很苦,她常在夜里偷偷地哭泣,我很怕,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就是怕她死了,便紧紧地抱住她。
多少次我被母亲嘤嘤的哭声惊醒,发现她没有睡,而是披着衣服坐在床上,我就爬起来抱住她大哭,她就用她的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夹袄把我裹起来,抱在怀里轻轻拍打。她也不再哭泣,只是不断地发出长长的叹息,喉咙还时不时发出口水艰难的吞咽声,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我脸上滚烫滚烫。
这时候父亲就坐在堂屋的门槛上,那门槛是一条整块的长形青石块,冰凉冰凉的,父亲坐在上面抽着自己卷的喇叭状旱烟,被巨大的黑夜叼着,把夜抽得一明一暗,不时传来一阵剧烈地咳嗽声和无奈地叹息声。
(二)
六十年代的丁家台,犯了男女作风问题是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过,鲜见有人敢越雷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内心疯长的野性便从嘴里无栅无栏地蔓延出来。但有个人例外,她就是李妈。她总是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笑,从不参与打闹说笑。
李妈和她男人是应城人,他男人姓田,好像叫反修,老人小孩都叫他老田,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多年前老田挑着一货郎担,李妈挑着被窝行李,顺着汉宜路半乞讨半卖些针头线脑来到了丁家台,在村头的避风处搭了个窝棚,队长见他俩可怜,便收留了他们,他们正式成为丁家台的一分子。
队长的老婆连喜婶是个热心的人,对他俩嘘寒问暖,不久就和李妈处得像亲姐妹。当时李妈可能二十多岁,剪着一个上海头,一丝不乱,一有空就用手沾水把头发抹的油光发亮,她的声音很好听,就像村头大杨树上广播里播音员的声音。大姑娘小媳妇也都爱围着她听她讲些应城的趣事,缠着她唱应城的民歌,李妈也不推诿,清清嗓子就开始唱:
难为我的爹,难为我的娘,
把我拉大没报恩,我是一个忤逆人。
莫看雀大各自飞,我离家门还要回。
儿是娘心以快肉,怎么舍得离一步。
……
李妈拖着长腔,字字句句幽怨悲怆,直唱得李妈眼圈红红的,大伙都说好听,我却觉得一点都不好听,像我母亲半夜里哭的调子。
有一天,李妈和连喜婶拉家常,说着说着她拉着连喜婶的手哭了起来:“我有件事在心里憋了好久,不说出来压在心里难受啊!我把你当亲姐姐告诉你,你千万别说出去。”
原来她和老田不是因为遭旱灾逃荒出来的,他俩是私奔出来的。她应城有个瘸子老公,还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儿子不到四岁叫大顺,小的是女儿刚刚一岁叫小秀。她实在想他们,特别是小女儿。
她清晰地记得她走的时候,大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平时吃不着的饭菜,小秀也睡在洗得干干净净的摇篮里。她告诉大顺:“顺儿,记住,你是哥哥,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妈妈去城里给你们买好东西。”
狠狠心就跟着老田走了,再也没回去。
就在去年年跟前,老田偷偷回了一趟应城,才知道李妈襁褓中的女儿小秀,在她出走的当年就死了,是饿死的。好在儿子大顺还健在,已经会帮瘸子爹拾柴禾打猪草了。
李妈还在抹着泪诉说,连喜婶愣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丢下手里的针线活反复地问:“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
第二天再去出工,就没人和李妈说话了,人人都对她避之不及深恶痛绝,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她也不再骄傲地走在人前,好看的上海头也不再用水抹得那么服帖,任它毛毛糙糙地随风飘散。
打此后李妈却同我母亲出奇地要好,一有空闲李妈便拎着一个装有针线杂什的细篾篮子来到我家,一五一十的、没完没了的纳着鞋底,一五一十的、没完没了的跟我母亲诉说她应城的大顺和小秀。
我母亲就安慰李妈:“女人苦啊,像哪样都苦,你当初若不跟老田跑出来,还不是苦,一样的。”说着还偷偷抹泪。
这时李妈把板凳往母亲身边挪挪,低声问:“姐,听说前些年管理区的贺书记为你打了脱离(离婚),你怎么没有离呢?”
“我和你不同,你是丢家当捡家当,哪儿都是家,我是吃老米的姑娘,爹妈是自个儿的,娃子是自个儿的,往哪跑呢?硬撑着吧,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
“听说那贺书记的老婆离婚,回来就跳河死了,是不是真的?傻女人呃!”
母亲低着头没有回答。
我奶奶见不得李妈来我家,躺在床上指桑骂槐:“真不怕遭雷打哟!没脸没皮。”不时从厢房里传出敲击床板声音和赶鸡鸭的吆喝声,“起起,喝喝……真不要脸。”
李妈走后,我母亲就去说我奶奶:“姆妈,都是女人,她苦着呢,您这是何必呢?”奶奶来气了:“我就知道你的心思,你是不是想学她?你滚啊!”母亲也是个烈脾气,和奶奶对着干:“我上对天下对地中间对良心,我没有做对不起谁的事。谁瞎说谁烂嘴。”奶奶就颤颤巍巍地指着我母亲说:“你个赔钱货败家女,我给你的祖传的银镯子呢?拿出来。”这句话是奶奶的杀手锏,此言一出,我母亲顿时就软下来,声音低低地说:“掉了,说了一百回了。”“掉哪儿了?放家里怎么就掉了呢?是不是掉姓贺的家里了。”奶奶还在嚷嚷,母亲默默地走开。
母亲拖着板车来到几里外的野鸭河,这野鸭河长满鸡头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鸡头苞的学名叫什么,但我知道它的果实的学名叫薏米。母亲把镰刀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由于近处的长得粗壮的都被别人钩走了,母亲就汲水到水中央去钩。每钩一摞上来,母亲就把腿上吸血吸得滚圆滚圆的蚂蟥揪下来,骂一声,然后扔得远远的。
晚上,我们一家人就在院子里削鸡头苞梗子皮。鸡头苞梗子浑身是刺,剥去刺就是白嫩嫩的藕带状的梗子,一尺长的样子就一掐断,够一大把了就用稻草扎起来,一把刺莲梗可以卖五分钱。这时候母亲就在扎扫帚,她麻利地把一种叫铁扫帚的植物扒拉扒拉,用麻绳细细缠绕,不一会儿一把精致的扫帚就扎好了。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挑着扫帚和刺莲梗子去集市上卖,有时候运气好,一天可以卖到几块钱。
李妈来丁家台的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望顺。紧接着又赶了个女儿,取名望秀。等到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老田夫妇就开始犯愁了,甚至名字也懒得起,在应城刚出生的小孩子都叫毛毛,我们那里的毛毛的发音是毛猫,他就一直毛猫到了七岁上学的年龄。报名的那天,老师说总得有个名字吧?老田就说您就随便画个啥是啥吧。那年正值罕见的干旱,老师挠了挠头,看看枯黄的庄稼说:“就叫望水吧!”
就这样那毛猫就成了望水,但大伙还是习惯叫他毛猫。他大我五岁,那时候是学校实行严格的升留级制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级,没有商量的余地,老师和村干部的孩子也一样。我读一年级的时候他读二年级,我读二年级他还读二年级,我后来读四年级了他仍然读二年级,最终以小学二年级告终。
(三)
小时候的夏夜,总是有着满天的星星,夜幕也清澈得像甘冽的泉水,这就是我们藏猫猫的好时候,十几个人分两组,藏好了就“啊”一声报警,我们就开始寻找,真找不到了就喊:“找不到了,我们投降,啊一声。”对方果然“啊”一声,我们便循着声音找到了。周而复始,不亦乐乎。
记得是插秧割麦的农忙时节,大人们吃罢晚饭早早地睡了。那天藏猫猫的时候,比我大两岁的学芝姐和我一组,她钻进禾场的小麦堆里,叫我往她身上盖了一层麦子杆,我随即钻进旁边菜园的番茄地。我是第一个被找出来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组被一一被找到了,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学芝,高兴死我们了,我们这一组齐声叫:“认输认输认输……”
他们认输了,我欢天喜地地跑去掀开麦子杆,傻眼了,学芝不在里面。我们大声喊:“学芝出来,学芝出来,他们认输了,‘啊’一声……”
但她终究没有出来,我们理所当然地回去睡了。第二天她也没有出来,她哥哥嫂嫂骂她说肯定是这阵子农忙,跑出去玩了。也许是太忙,谁也没有再在意这事。但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学芝出事了。但究竟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脑海里总觉得那天麦垛旁,曾经有个高大的黑影一闪而过。
农忙过去了,学芝没有回来,一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回来,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她也没有回来。她失踪的时候应该是十四岁左右,因为我清晰的记得她来过月经了。我觉得很神秘,问她流血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干重活就很累。
学芝从此消失在丁家台,没有人记起她,除了我。我还发现学芝不见的第二天,林场里就有一种鸟,很小很小,也是黑色的,没有姐姐裤裤鸟大。它不时地从树上飞下来,落在我家篱笆的木槿条上,嘴里发出如哨的尖尖的声音:“学叽,学叽,唧唧学叽,唧唧学叽……”发音清晰准确。我想仔细看它的时候,它总是迅速钻进林子深处,就像躲猫猫的学芝钻进麦垛里。

我把鸟的这个事情说给三姐听,三姐仔细听后说:“咦,还真像耶!那鸟真像在喊学芝,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
我说给妈妈听,妈妈说:“你再瞎嚼,小心我撕你的嘴。”
妈妈越这样说,我越相信那鸟就是学芝变的。
(四)
清晨的太阳金子一样撒满丁家台的旮旮旯旯,只有阳光是公平的,无论贫穷富贵,毫不吝啬地给予。
就像四季过后,望儿的女儿凤儿也一样长大了。十六岁的凤儿苗条白净,特苗条特白净。
这时候,来凤儿家的人多起来,都是来提亲的。凤儿生在穷家小户,父亲是个哑巴,母亲是个傻子,那些不好找媳妇的男孩子家纷纷打起了她的主意。望儿高兴得像过年,隔天拿两颗糖果乐呵呵地给我吃,我不想吃。
倒是哑巴天天来找我妈,脸憋得通红,吧吧吧地乱叫,手不停地比划,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我母亲一直能听懂他的“话”,哑巴说那些跟凤儿提亲的人不是斜眼歪眉,就是矮小丑陋,还有傻乎乎的像望儿的,再不就是穷的饭都弄不上嘴的,反正没有一个正气的。
我家跟凤儿家据说很亲,还没有出五服。我们两家上辈都不发人,我们这房只有我母亲,他们那房也只落下一个哑巴,所以我母亲对凤儿就特别疼。她比划着告诉哑巴这个事交她,让他放心。哑巴点点头,朝我母亲竖个大拇指,吧吧吧地挎着粪筐走了。
当晚我母亲就去供销社称了斤白糖,去了一个叫潘湾的村子,我一个远房表叔的家,专门为凤儿来物色对象。那潘湾在汉江边上,责任田大都是汉江边上的滩涂田,不交公粮水费。当时有一句老话说:喂母猪种滩田——发财无渊。只要人勤劳,潘湾人吃饭是没有问题的。
过了几天我们家就来了一个很高很帅的小伙子,一看就是特精明的人,是我远房表叔带来的。
一会儿凤儿就来了,她穿着一件红格子衣服,那是她去年挖了一年的半夏才买的,平时不兴穿。她梳着高高的马尾,扎着根红色的细丝带,两根丝带坠在马尾里煞是好看,那年很流行,这个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偷偷买的。
凤儿一进门跟我远房表叔打了个招呼,就坐在靠里边的板凳上,低着头不说话。倒是那帅小伙眼睛顿时放光,话多了起来,把板凳也往凤儿那边挪去。凤儿也时不时抬头看看那小伙,不停地抿嘴笑。我发现凤儿今天特别漂亮,本来她平时脸只是白,今天白里透红,粉嫩粉嫩的。
看那情形,我妈妈心里十有八九了。便在里屋喊:“凤儿,进来我有话要说。”
我母亲亲声问凤儿:“你觉得这个男娃子可不可以?”凤儿只是笑不说话,我妈妈急了:“你究竟同意不同意?一句话的事,再这样含含糊糊我可不管了。”凤儿连忙低声说:“看他,他同意,我就同意;他不同意,我就不同意。”
这桩好事就这样成了,那天那男的给了凤儿两百块钱见面礼,绝对是鲜有的巨款。因为那个时候相亲最多是给一百的。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凤儿变得爱笑爱说话,整天精神饱满激情四射的样子,我都羡慕嫉妒恨了。
年底凤儿就出嫁了,那天钱平很帅,凤儿很美,敲锣打鼓热热闹闹,都是我母亲一手操办的。
第二年夏天凤儿怀孕了,我们都替她高兴。有一天回家,凤儿在和我母亲说话,不停地流泪。原来医生说凤儿可能因为怀孕会眼睛失明,她现在看东西已经觉得模糊了。
母亲说:“这事太大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姆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事外人也不能做主。”凤儿说:“谁都不能做主,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我母亲叹了一口气,把凤儿的手搁到自己的膝盖上说:“你既然这么想呢,就生下来吧。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日子也不好过,说不定是胎气不好,孩子一生下来眼睛就好了呢。”
凤儿生了,是个女孩。满月那天,母亲叫上我说:“幺姑娘,你去把凤儿接回来住满月,去小卖部买点东西,带点茶事,免得她婆家人瞧不起她,说她娘家没人。”
这时候凤儿已经全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的女儿却收拾得很干净,那孩子白白净净的很秀气,像凤儿。孩子二月生的,叫春桃。我在堂屋里爱不释手抱着春桃,等着凤儿收拾东西。却听见房门嘭地一声关上了,里面有推推搡搡的动静,听见凤儿小声说:“不行,不能做那个,刚刚满月还没干净呢。”里面传来钱平压低的粗嗓门在吼:“你个瞎婆娘还想不想过了?”
半个钟头后,里面平静下来。
凤儿虽然眼睛瞎了,却很能干,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里的活儿她也可以干,就是比别人慢。所以免不了钱平骂她,钱平不再柔柔地喊凤儿凤儿,人前人后都叫她瞎婆娘。
每天早晨她洗完衣服,钱平就用自行车把她带到地里干活,我见过凤儿除草,她不用锄头,蹲在地上用手扯草。她先摸到棉花秧子,用一只手把棉花秧子的根部护着,用另一只手很快把周围的杂草扯干净,再往前……
最神奇的是凤儿还会穿针引线,她袖子上总是别着一张针,她一回来她的哑巴爹就拿出几件穿破的衣服让她补。只见她熟练的从袖子上取下针,从细篾篮子里抽出一根线,用嘴把线头咬细,再把针上的那根线尾巴也小心的咬细,拇指和食指沾点唾沫,把两根线头一捻,然后迅速一拉,线就穿过去了,用完就再留一段线在针上下次再用它带线。她补的衣服虽然颜色搭配极不协调,但针脚却端正整齐。
那年八月,桂花飘香。春桃已经会坐了,俗话说会忙的忙八月,不会忙的忙腊月。花生、黄豆、芝麻等等农作物都是在八月收获。钱平一家全家出动,翻过汉江堤抢收黄豆,小春桃也抱出来了,在田头放一个簸箕让她坐里面,放上一个小玩具,她就能玩上半天。凤儿会隔一段时间来喂一次奶。
中午太阳正毒的时候黄豆已经收割完毕,钱平说:“瞎婆娘,不用你帮忙上车了,你把春桃抱到阴凉的地方歇歇。”
凤儿欢喜地朝春桃的方向摸摸索索地走去,忽然一个踉跄,什么东西穿过布鞋底扎进脚板,生疼生疼。
汉江堤边有很多柳树,微风凉凉地抚在身上甚是惬意!凤儿摸着吃奶的春桃,满满的幸福写在嘴角。
这时候凤儿觉得脚不对劲,用手一摸粘粘的湿了一大片。便随手扯了一把草放在嘴里嚼烂,敷在疼处,这个方法是她哑巴父亲教她的,很灵,血果然止住了。
第二天早晨,钱平骂了半天,凤儿才磨磨蹭蹭地起床,吃了早饭把衣服洗后又去睡了,说不舒服,任钱平怎么骂都不动。大忙的季节怎么能有闲人呢,钱平去村卫生室买了两板感冒胶囊扔给凤儿说:“吃四颗吧,翻倍吃好得快。”
两板感冒胶囊吃玩了,不仅不见好,还发起烧来,钱平用自行车把凤儿带去卫生室输了一瓶液。
几天过去,凤儿还是不见好,饭也不想吃,身上还起了黑色的点点,脚肿得厉害,伤口总不愈合,还流着脓水。钱平也慌了,知道可能不是感冒,又把凤儿送到村卫生室。赤脚医生告诉钱平,凤儿可能是因为脚底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还说败血症是个大病,必须到大医院。钱平悻悻地甩了句:“什么叫败血症,分明就是败家症。”
大热的天,大忙的季节,家里躺一个病人,凤儿也没有了奶水。钱平的脾气越来越坏,他把平时纳凉用的竹床搬到后厢房,把凤儿搬到竹床上去睡,眼不见心不烦。
倒是凤儿的婆婆念凤儿平时的好,时不时地递口水喂口饭。凤儿一直发着低烧,人也迷迷糊糊,一清醒就喊春桃春桃。正吃晚饭,凤儿又开始喊了,钱平把碗一摔,进去就把凤儿抱到外面的板车上,拖着就走,他妈妈赶紧赶出来问:“钱平,你要干什么?”钱平说:“这败家婆娘我不要了,送她回娘家。”他妈妈慌忙说:“不行啊,嫁了的女泼了的水。哪有这样的,小心遭报应。”钱平大吼一声:“我已经遭报应了。还能怎么报应?这瞎婆娘就是一灾星。”
就这样,嫁出去了的凤儿又回来了,还是低烧不退,清醒了就喊春桃春桃。
没过几日,凤儿就死了。我去跟钱平送的信,我去田里找到的他,他正跪在地上摘花生,汗流浃背,旁边放着一副碗筷,应该刚刚在地里吃的午饭。听到噩耗,钱平顺势倒在地上仰天大喊:“凤,凤儿啊,我对不起你,我也没办法啊,我们都是苦命人啊……”
本来,在路上我就想好了,见到钱平就扇他几个耳光,还想好了该怎样左右开弓,该说哪些恶毒的话语,为死去凤儿出气。但我却没有,我看着痛哭不止的钱平,愣了许久后,竟抱着又是泥又是水的钱平痛哭了一场。
按当地的风俗,出了嫁的女儿死娘家了,是不能从大门抬出去的。我父亲把哑巴房子的山间(就是房子的侧面)打了个洞,用门板把凤儿的遗体抬上了钱平请来的一辆农用车里,走了。记得那年凤儿出嫁也是这辆车,只是当年这辆车挂着大红花,而今天挂着白花。
凤儿就像一盆无人看管的窗台上的花,上不及天露,下不接地气,用尽一生的养分,开了一次艳丽的花,就匆匆谢世。
凤儿走后哑巴就病倒了,不多久哑巴也死了。房子的山间打的洞也没有补上,黑黢黢的看着瘆得慌,后来我母亲搬了一些高粱杆子把那个洞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望儿成了五保户,村里照顾她,安排她去乡里的养老院。
走的那天,是我父亲送走的,父亲帮她收拾了一板车破破烂烂的家当。我父亲在前面拉,望儿在后面推,都佝偻着身子,像被风儿卷起的两片抱成一团的枯叶,朝着夕阳的方向艰难地移动着。
走着走着,望儿仰头问父亲:“元哥,我不想走,我几时回来呢?”
父亲用力地拉着车半晌没回答,直到把他自制的旱烟抽完了,才幽幽地说:“走吧,走了就不回来了,一辈子也不回来了,这鬼地方。”
(五)
汽路(当时我们把公路称汽路)通客车的时候,应城的大顺拿着一张发黄的半截信纸,按上面的地址找到了丁家台。
那大顺的长相颇似李妈,身材又瘦又高,腼腆的像个女孩子,穿着一件很大的不合体的衣服,但明显是新的,上面还有折痕。他斜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条白毛巾,几个馒头,还有几十个皮蛋。馒头是他路上吃的,皮蛋是带的礼物。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皮蛋,说叫松花皮蛋,用谷壳子裹着的那种。毛猫给我尝过一小小口,小到我没有尝出任何味道,只闻到一股浓浓的刺鼻的味道。
大顺说地址是瘸子爹给他的,瘸子爹病了,病得很厉害,他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怕自己死后大顺一个亲人也没有,就想着让大顺投奔他亲妈。其实瘸子很早很早就打听到了李妈的住址,当时就请人用信纸写下来放在枕头里。
过了几日,任李妈如何挽留,大顺还是走了,斜挎那个帆布包回应城了,说舍不得他的爹。我们这里没什么特产,李妈就烙了几个火烧粑装在大顺的帆布包里,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孝顺爹。
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已经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人们的内心开始随着春天的来临蠢蠢欲动,思想就像天生会攀越牵牛花,举着一只只空碗,不停地向上探头。
村长拿着一摞招工表,说广东裕元鞋厂招人,毛猫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四处奔走相告,一下子就有十几人报名。
毛猫拿着一张招工表鬼鬼祟祟把头探进我家篱笆院问:“梅子,你妈妈在不在家里?”
我说:“不在哩,你走吧,我妈说不让我去广东。”
毛猫一脸憧憬:“去吧,去了我们以后就是城里人了,你是不是没路费?我回去把一袋豌豆偷的卖了借你。”
这时,我母亲背着一捆柴火回来,见到毛猫就骂道:“你这个红脑壳砍头的,又想来把我的老幺叼出去吧?快滚。”
其实我也不想出去。母亲说十几岁的姑娘伢出去了就会没人要了,以后会嫁不出去的。
真正填表出去的有十五个人,三女十二男。我的好朋友书琴,金凤,勇梅跟他们走了。我忽然很羡慕她们,觉得她们是朝着希望朝着梦想去了。
送他们去乡里坐车的路上,人人都一脸的茫然的表情,但内心却急切的想逃离这里,都不说话,各自扛着自己的蛇皮袋默默地走。
这时毛猫走到我身边说:“梅子,我教你唱个歌吧,我刚刚学会,蛮好听。”
“……痛苦痛悲痛心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只有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毛猫唱得很投入,十几年了,第一次看见他流泪,听着听着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临上车,他走过来对我说:“梅子,你信不信我以后在城里会攒很多钱,开桑塔纳回来?你一定要等我。”
我肯定不信,从小到大我都不信他的话。
第二年,他们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说太累了,又熬夜,受不了。最后只有五个人留在广东,全部回来了。毛猫没有回来,勇梅告诉我:没有回来的都是因为没有路费。
后来毛猫真的混的很好,他是第一个开小车回来的人,还染了一头红色的头发,倒是应了我妈妈老骂他的一句话:红脑壳砍头的。
在我出嫁的第二年,毛猫带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黄色的卷发蓬蓬松松地高高盘起,眉毛很弯很细,嘴巴红红的,大大的眼睛,纯黑色的眼珠,不像我们乡下人的眼珠都带灰黄色的。
毛猫却说:“她是化了妆的,其实长得没有你好看。”
骗谁呢?我回去对着镜子颓废了半天。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得又土又丑。
那小白后来给他生了个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田白雪,一个叫田白静。
毛猫作为第一批打工仔,很快成为裕元鞋厂的车间主管,权力很大,老婆在广东石碣开了个花店,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温馨的小家。
至今为止都没有人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那天毛猫被一辆车送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下半身已经瘫痪,车上带着个轮椅,村里人猜想毛猫可能是跟别人打架打的,因为他从小就是打架斗殴的代王。
那夜小白在他床前跪了一个晚上,谁也拉不走,毛猫也不说话。早晨李妈端了一碗鸡蛋送进去,毛猫把碗砸向小白,大声骂道:“叫这个婊子滚出去,骚货。”
小白哭着走了,走的时侯给李妈留下了一笔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丁家台。
(六)
父亲嗜好抽卷烟,我家房前屋后旮旯里都种满烟叶。那烟叶肥厚硕大的叶子,上面一层白绒绒的毛,摸上去有点黏黏的感觉,粉红的喇叭状的花儿,微风吹来,满屋子软绵绵的香味。母亲说,父亲一辈子最拿手的活就是种烟叶,比谁都种得好。
那次我去看父亲,他明显瘦了,脖子上很多包块,他说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想喝豆腐花。他进屋拿出一个袋子给我看,说是二姐打工前跟他买的,味道很好。我看了,那是冰泉牌豆腐花,我说知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看父亲,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忽然想起他想喝的豆腐花,连忙骑自行车到村头的小卖部,店老板说豆腐花三块钱一袋,我摸遍全身也就两块多一点,只能下次跟他买了。
买点什么呢?我竟然不知道父亲喜欢吃什么,好像除了三餐粥饭,父亲也没有吃什么别的东西,我就按自己的喜好买了几根火腿肠。
父亲问:“这个东西怎么吃?生的都能吃?”
我说:“当然,可好吃了。”
父亲尝试着咬了一口,艰难地吞下去说:“不好吃,腥。”
我答应父亲下次买冰泉牌豆腐花,父亲笑了。
回来的第三天,娘家人来给信,说我父亲走了。
我去的时候父亲已经下榻了,躺在一木板上,头发跟生前一样,雪白雪白的一丝不乱。父亲一生爱干净,一些破旧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桌上还放着一根咬了一口的火腿肠,还有一个空的豆腐花袋子,冰泉牌的。
我紧紧地握着他冰凉的手,放声大哭。
奇怪的是母亲却不哭,她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流泪,过了许久许久,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的人啊!你划不来哟!跟着我没有过一天好哦……死了好,死了好哦!到那边弄点好吃的,用块正田多种点烟叶,不再受苦受穷了……”
望儿也从福利院回来了,她长年腋下夹着一件黑底红花的缎面袄子,那是凤儿出嫁前钱平和凤儿专门去沙洋扯的面料,我母亲手工做的。望儿傻乎乎地站在我父亲旁边,直着个大嗓门使劲地哭,呜呜……呜呜呜……像草原上孤狼的叫声,悲切而绝望。
第二天福利院来人说望儿没有回去,所有人都慌了,发动全村出去寻找。
有人说看见望儿夹着那件黑底红花的袄子走进林场了,几天后又有人说,看见一个腋下夹袄子的女人在汉江堤上。
福利院依着这些线索找了几天终究没有找到,也就不再寻找。最后我母亲去福利院拿了一些望儿的衣服回来,在哑巴的坟旁起了一个小堆,也算入土为安了。
(七)
我母亲晚年信上了基督教, 一天聚会散后,我发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白发老人,他骨子里透着儒雅简静,农村的老人不会这么纤尘不染,腰背挺直。他指着我问我母亲:“这是你家幺姑娘吧?真像你年轻的时候。”
“小贺呀,不对不对,是老贺了,你怎么就一走几十年不回来呢?”
“你说呢?”
“唉……”一阵静默后我母亲平静地说:“我是吃老米的姑娘,不是媳妇。算了算了不说了,年轻时太傻了,现在老了也想明白了,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用生命来换的。”
那白发老者明显眼睛潮湿,假装翻圣经,又是一声轻叹:“是啊!我们在时光面前太渺小了,好多事儿就像在昨天。方孝姑死的太不值当了,我跟她打脱离回来的当晚,就跳方家河死了。她无父无母,无亲无靠,十一岁就来我家做童养媳,任劳任怨。我最对不起她了。”
“唉!我也对不起方姐。”
“这么多年了,不说了,对了宝姑,后来我到县城后又找的一个老婆也姓丁。”
“哈哈哈,这么巧啊?”
“不巧,她不是姓丁我也不会要她。我本来不打算再结婚了的。”
白发老者从包里拿出一个蓝格子手帕,慢慢打开,取出一个什么东西递给我母亲,说:“宝姑,这手镯我保存了几十年,我想还是物归原主吧,毕竟这是你家传家之物。”
母亲没有接,甚至看都没看一眼那手镯,平淡地说:“就是一个银手镯而已,又不值钱,你拿回去吧,我不想再看到它。”
“我知道你的脾气,那我拿回去了。唉!我们都老了,这次可能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要保重身体,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好,你也一样,注意身体,多喝水少吃油腻。”
老者走后不久,母亲急急地唤我,她手里拿着两沓钱,吩咐我:“快去追你贺伯,他留这么多钱给我干什么。”
我追出去,哪里还有人影,丁家台门口那条白色的土路如巨蟒一样蜿蜒在绿油油的小麦地,空荡荡地伸向远方。
母亲把钱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怔怔地看着一张纸条,那上面字迹工整地写着:宝姑,不要想着怎样把钱还给我。我知道我的身体,在世的时日已不多了,留着也没有意义。你苦了一辈子,一定要把这钱用完,不然到那边我也不原谅你。
(八)
一轮巨大的夕阳挂在丁家台的西边,久久不肯坠落,红红的,像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