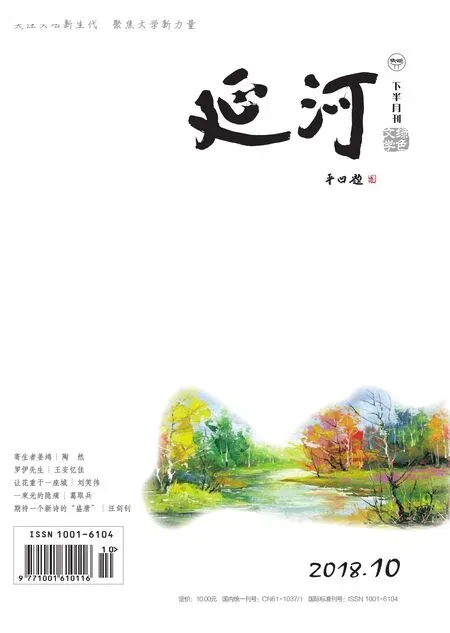一束光的隐痛
葛取兵
1
我是在一堆遗弃的垃圾中发现的。
一只残旧的煤油灯。
岳父岳母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已经七十高龄了,叶落归根,这是中国人内心无法泯灭的宿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一句看似简单的俗语,却隐含着乡下人厚重的生存哲理。再繁华再富裕的地方也不及自己老家好,虽然简朴,甚至是贫瘠,也挡不住归家的心。其实是担心终老异乡,让灵魂找不到回乡的路。回乡终究有个让灵魂安息的土堆,有麻雀、八哥、斑鸠的鸣叫,有野菊花、黄荆、映山红的花香,也有鸡鸣狗吠的热闹,再俗再庸的灵魂也不再落寞。在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数人年轻时总是摁不住驿动的心,义无反顾地走出村子,在那个叫城市的森林中四处闯荡,把光鲜的岁月一路抛洒,却找不到一片落脚的屋檐,老了还是心甘情愿抑或是心存不甘地回到自己的老窝。我的亲人亦是如此,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沿着这样的轨迹或远或近地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归家了。岳父的老家是湘北的一个普通村落,叫骆坪村。村名究竟有什么意思,无从探究。倒是村边有一条河,古称微水,学名叫游港的河,竟然在《水经注》中可觅到蛛丝马迹,但村人叫骆坪河。在村人的眼中,河流到哪里就得随乡就俗,他们不管读书人的称呼,到了他们的地盘就得服他们管辖。如娶回家的女人,进了门就没有她的原姓了。在村子里女老人家都用男人的姓氏称呼,比如我的岳母,本姓杜,岳父姓汪,村人都叫她汪娭姆。村子四围是大片大片的水田,所以这里被称之为畈,而山村则被叫之为冲。大抵畈里的人瞧不起冲里的人。
老家的那幢二层砖房还在,只是形同一个满脸沧桑的老人,在村口守望着漂泊在外的游子。岳父曾几次千里迢迢回乡,整葺老屋。无人居住的房屋格外容易衰败,没有温度,就如生命孱弱的老树,风一吹,雨一淋,似乎就有摇摇摇欲坠的感觉。有一年刮大风,屋顶上小小的瓦片吹烂了不少,岳父回来将老屋的木檩进行了更换。又一年,再次回乡把屋檐用水泥浇注了,老屋才显得有些结实。可是,不管怎么修葺,老屋还是愈发的老去了,正如正在老去的岳父岳母。
岳父三十多岁的时候,从村子里外出办厂,后来又去了远在湘西怀化的小儿子家,帮忙照顾孙子。去年春节,在怀化生活了十多年的岳母说,想回老家住。已在怀化扎根安家的舅哥舅弟没有附和母亲的话语,或许是舍不得老母,抑或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只是一时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八月,夏季正浓。身为小学教师的妻子放了暑假,我陪同她来到了怀化。舅弟曾与我商量过老屋装修一事,为父母亲要重归故里做些准备。舅弟的言语中,饱含了浓浓的不舍之情。男儿多为孝子,总是希望父母就在身边。平时父母待在身边久了不觉得,一旦离开,却是“咯吱”一下,恍若从白昼中陡然间掉进了黑暗中,找不到眼光停留之处,无所适从。当我曾经离开父母只身一人来到一座城市,夜深人静之时,看到满窗的灯火,我就想念起我的父母亲,眼泪总是奋不顾身地冲出来,从眼眶里直扑向脚下的土地。
想不到,岳父说回就回了,思乡心切,月底竟然回到了老家。
老屋已经很老了,所有的门窗基本上腐烂了,电线上满是蛛网,地板上堆砌着渣土,好像容不得人插脚,苔藓泰然自若地爬上了墙脚。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垃圾。一堆又一堆的垃圾,曾经是岳父岳母生活过的物品,时间久远了,原本有用的东西,也已变成了废物。
这只煤油灯也不例外地被扔进了垃圾中,等待运走。我无意的一眼,余光中有一股熟悉的感觉,定神,在尘埃中发现了它。
这是一只普通的玻璃灯盏。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沾满了尘泥。上面应该有一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灯头上还有一个高高的玻璃灯罩。而现在,灯头已经找不到了,抑或是锈蚀成粉尘了,毕竟已有二十多年光阴。曾经在老屋呱呱落地的舅侄,在这一段光阴中也长成了青皮小伙子。或许,曾经在这只煤油灯下吮过母亲的奶汁。如今这只铁皮制成的煤油灯头在这漫长的二十几年,一点点地锈成了粉尘,随着岁月一同淹入了历史,只是无人知晓或无人记录在案。
煤油灯,曾经是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照明工具。我到今记得小时候的梦想,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三十年光阴,这一个梦想已成为中国农村的现实。在岳父的老家,已耸立起一片三楼、四楼,甚至是五楼的房屋了。外墙是光洁的瓷砖,不锈钢的防盗网,农村到处可见城市的碎片。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煤油灯,势不可挡地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高楼里怎么也找不到它的身影。它成为乡亲嗤之以鼻的物具,他们早已毫不吝啬地将它扔进了垃圾堆中。如果不是岳父外出二十多年,我可以料想到这只煤油灯的命运,它怎么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这只煤油灯带回了城里的家,用清水反复洗净了它身上的污泥。它圆形的肚子里竟然闻不到星点煤油的味道。我细细地闻了又闻,是想找寻那种曾经熟稔的气味。岁月真的是一把刮骨钢刀,甚至连一点点气味都削得干干净净。
我至今非常奇怪,小时候,对煤油味有着一种偏爱。那种煤油的独特芳香,淡如空气。吮着它,感觉一股温暖存在,享受它静静抚摸我们周身,每一个细胞都含着它的体温。几十年了,从离开家乡,就再没有闻到过煤油味。这只煤油灯,让我自然地触摸到那些情节,那些温暖的夜晚。
洗净的煤油灯,被我把放在书房的书柜中。妻子说,灯与书格格不入。而我想,灯是黑暗中的光明,书更是照亮人生前行的灯。
怀念一盏乡村的煤油灯,照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照在一间间温暖的房屋内,在黑夜即将来临时,总给我们光明和镇定。
2
煤油灯曾经给我带来了温暖与光明,因为它温暖了我的每一个黑夜。
夕阳融尽在西边的山色中,黑暗铺天盖地涌入我的村庄。山峦在黑暗中隐去,绿树在黑暗中隐去,老牛也如一位隐士在黑暗中咀嚼寂寞。母亲在堂屋点燃煤油灯,一柱灯花在黑暗中燃起,恐惧在温暖中远远隐去。尽管灯光微弱,跳动,闪烁,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屋子里的一切,能够在熟悉的屋子里行动自如,并且找到自己灯光中的身影和位置。我弱小的内心终于在一柱灯花中得以安定。有时候,一阵微风吹来,甚至于我们穿过屋子的背影,让灯花晃动,摇摆,灯下所有事物的影子也跟着晃动,但它的温暖不会散去,不会被风将魂招去。在乡村,煤油灯是温暖和光明的代名词,因为有了它,我们才不至于被一个个固定轮回的黑夜像河水一样淹没,才不会在黑暗中丢失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直到天亮,睁开惺惺睡眼,在穿进窗棂的阳光下寻找自己。
那个年代,煤油灯的命运跟乡村的命运一样,贫瘠,清苦。一户人家一盏灯,做饭时灯在堂屋,一家人便都围在堂屋。做好饭后,把饭端到里屋,灯便也跟着到了桌上,但更多的是成了哥哥姐姐做功课的工具。在乡下,再重要的事,也没有读书的沉重,饱含着一代人的希望。在父母的心中,煤油灯就是我们兄弟的农具,春种秋收,走出田埂,在城市中找到霓虹灯的灿烂就是父母一生最大的收获。
这个场景至今温馨着我的梦想。我们兄弟几个围守在桌子周边,哥哥姐姐在桌子上做作业。我与妹妹站在哥哥的背后,盯着灯花在微风中忽明忽暗上下跳动。想象着天上的星星,田间的萤火虫,还有奶奶曾经絮说过的神话故事(那时叫讲古)——灯花姑娘。一个从灯花中跳出的仙女,美丽勤劳善良,爱上了同样和她一样勤劳善良的青年,于是天天帮助他侍弄家务,后来结为了夫妻。如此简单的故事,却让我们入迷。虽然简单,但充满了神奇与温馨,足以让我们幼小的心灵盈满希望。小小的煤油灯燃亮了整个童年的夜空,让我的童年在它摇曳的光中温暖前行。
母亲在灶旁忙着弄晚餐。烧茄子,煮南瓜、炒白菜,最美的煎鸡蛋,或紫苏,或辣椒,有时也会有一盘炸泥鳅。满屋子烟火气,却是最朴实的味道,至今都在盈实着我们的每一天。灶口的火光不时窜出来,寻找煤油灯的光亮,如同我们兄弟结伴嬉戏,跳动的欢乐照亮着母亲疲惫的脸庞。
父亲此时正走在回家的田埂上,荷着锄头,牵着老牛,不紧不慢。黑夜对父亲无所畏惧,熟稔的田地牵引着父亲在黑暗中归家。屋前的狗吠声,不紧不慢,俨然一种召唤,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父亲已进了庭院。最喜欢从田间归来的父亲,总会带来一些惊喜,春天的野草莓、饭泡里,夏天的杨梅、桑葚,秋天的猕猴桃、毛栗子。即使在冬天,父亲也会捎带些李子,抑或是松子。在煤油灯下,父亲带来的礼物让夜色多了光亮,我们快乐的咀嚼声让黑暗不再寂寞。此刻的父亲,静坐在门边,远离灯光的父亲似乎有些晦暗,但一闪一闪的纸烟照亮了父亲古铜色的脸庞。那是一张坚定的脸,在他的脸上我们找到了安稳和温馨。
晚饭后,我们洗了手脚上床睡觉,母亲却还在忙碌。煤油灯如豆般的火苗悠忽闪烁,可母亲就是在这盏灯下,做着我们兄弟几个的穿戴。每当夜深人静我醒来时,看见母亲还在这盏灯下缝缝补补……母亲坐在床头纳鞋底,灯光的着落处,如皮影般放映着母亲缝补与纺织的纤巧,穿针引线的娴熟,这些是构成我灵动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纳着鞋底的母亲很安静,也很安详,有时还会唱些小谣曲给我们听。我钻进被窝里,静静地听着母亲纳鞋底的声音,那根细细的线把我拉进了梦乡。
小小的煤油灯陪伴了我多少年的时光?我没有仔细点数过。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幸福又心酸的日子,一段温暖又温馨的日子,一段单纯又美丽的日子,忘不掉,擦不去,几十年来隐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时不时蹦出来,让我感动与怀想。正如岳母的这盏煤油灯。
3
然而岳母的煤油灯却是一盏有故事的灯。
那时村庄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一种模式,一样的泥砖屋,一样的棉布衣,甚至于脸色也是一样的,如煤油灯的光亮,浅黄浅黄。晚上村里一户人家一盏灯,全家人凑在灯下,各自做事,一起说话。此刻,静夜无边。而岳母是村里唯一有两盏灯的。岳母说她是村里最奢侈的人。
那时岳母是村庄里的妇女主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岳母是一名赤脚医生,更重要的是她还肩负着接生的重任,用村人的话说就是接生婆。岳母最识得村子的痛痒,在她的眼里,没有识不得的人,没有识不得的声,没有识不得的路。那时农村就医条件差,赤脚医生作为改善农村看病难的天使曾在全国各地蜂拥而至,成为新中国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岳母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所谓赤脚医生,其实就是公社卫生院组织村组一批没有受过专门培训,只是简单进行学习后,足以招架日常小病,便抽身返村,旗鼓开张,摸索上岗的那群医生。严格地说,赤脚医生就是半农半医,是半个庄稼人,一只脚带泥,一只脚穿鞋,时常还要捋起裤管打着赤脚下田忙农活,插秧、种菜、割谷子。赤脚医生时常是在地里把活干到一半的时候被人寻到田里来,急匆匆地去看病,一把谷子扔在田埂上,抑或是摘了半篓子的猪菜,等着家人寻去,甚至第二天又接着忙碌。

岳母是在二十几岁时开始行医,当时还是一个小媳妇。大队要配备一名赤脚医生。年轻又读了点书的岳母,便选送到离家五六里远的公社卫生院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半年学习,居然学得一招半式,比如量体温、测血压、听脉搏,比如包扎伤口,还有最重要的一招就是打针,打屁股针。不过那时不像现在的街头门诊,一点头痛发热,动不动就给你来两瓶吊针,只有在重病情况下,才能输液,俗称打吊针。乡人说,某某不得了,打吊针了。言下之意就是病危了。那个年代西药十分稀贵,抗生素几乎是救命药。在农村更多的是中草药当家,艾蒿、鱼腥草、蛤蟆叶、金银花等遍地生长的野草,是赤脚医生行医的硬通货。村子里谁有点感冒发烧,岳母到田间地头扯几把草药,洗净,要患者煎水喝,此时就会有浓郁的中药香遍及每个角落。事实上岳母更多的时间是荷锄采药。
初为赤脚医生的岳母,在她的眼中医生这个职业格外崇高神圣。她说,她渴望成为一名穿白大褂的行医者。但作为赤脚医生,她同样感到满足,有一股重担在肩的使命感。每一次接诊,她都是那么的细致认真,安静地听取患者的诉求,细细地了解病情的症状,为他们号脉听诊,慎重地开出处方,总希望早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想像那些日子,岳母常常背着一个有红漆画“十”字标志的白色药箱,里面摆置针管、针尖,葡萄糖、感冒药,酒精,棉团等物品,进东家,出西家,穿田过畈,为村民看病。打针最令人惧悚。打针时,医生将硬币大的小砂轮在注射液的瓶颈旋一圈,用铁夹将它敲脱。再用酒精或开水将针头简易消毒。之后让病人略微褪下裤头,医生左手捏着棉球,蘸了酒精,在屁股涂抹二圈,右手执着针管。只听得“噗”的一声闷响,患者本能的“咝哟”一声。医生往肉里推药水时,患者往往忍不住“咝咝”地倒抽凉气,眉头紧蹙。我最怕打针,小时生病感冒,宁肯吃小而苦的各色药丸,也不愿意打针。时到中年都不敢看医生给别人打针。
岳母不仅是一名赤脚医生,还是一名接生婆,远近都有名。方圆十里,凡是有人家要生孩子的,都请岳母去接生。特别是难产,非叫母亲不可。作为接生婆,同样是一名女人,对于生育充满血腥的痛苦,她感受尤其深切。岳母生育三胎,我的妻子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我曾经试探性地问过岳母,是否有过失误的经历,岳母没有直接地回答我。她停顿了一会儿,也就是分把钟的时光,但我明显感到岳母的情绪有一丝波动,像是一条直线,抖动了一下,旋即回到原状。岳母缓缓地给我讲述了一次经历,那是一个夏季的夜晚,电闪雷鸣,雨下得像有人用盆往外倒水,似的一盆盆往下倒,咬牙切齿的样子。已是夜半时分,突然大门敲得山响,有人在喊,撕扯着的嗓音里有一种近于绝望的呐喊。岳母没有睡,她隐隐闻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她随着绝望的呼喊声,披风破雨来到产妇身边。晚了,一切都晚了,胎儿也没有生的迹象了,产妇也命悬一线。当时也顾不了换衣,立马抢救产妇。黑暗中,煤油灯在风雨中飘摇,时间也在风雨中飘摇。当东方露出鱼肚白,雨停了,产妇的呼吸也平稳了,惨白的脸终于有了一丝血色。只是孩子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看一眼,就消失在无边的黑夜。他走得肯定一点也不心甘,他来不及啼哭,他把一切抱怨交给电闪雷鸣。孩子的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着旱烟,烟雾中的脸色隐藏着巨大的失子之痛。看不到眼泪,看到的只是黑夜中的平静。
岳母说,这天早上有点邪。当她提着煤油灯走在回家的路上,虽然下了暴雨,但田间的小路并不泥泞,岳母走得很稳当。刚走出村口,砰的一下,岳母恍然是谁绊了一下脚,抑或是有人在背上狠狠推了下,岳母甚至来不及喊一声,就跌入草丛。煤油灯从手中飞出,在空中飞翔了一个漂亮的弧线,然后奋不顾身的扑向地面,甚至有一丝抉择的味道,然后粉碎了,成了一摊玻璃渣。一股浓浓的煤油味,挣扎在清晨的空气中,难道是那个尚未来到人世的胎儿在发泄人间的不满?岳母满眼泪水,是愧疚,也是遗恨。岳母的讲述戛然而止。她站起来,走向屋外,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半截树桩上。这时正是黄昏。看着岳母的背影,我恍若看到那个早晨,田野里长满了庄稼,骨碌骨碌拔节的水稻,赛跑似的往上窜的玉米,到处洋溢着清脆的馨香。岳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我听见乡村在晨曦中渐渐热闹起来。岳母的回乡,我得以揣摩这方水土。有时在周末闲暇的时候,回乡,闲散地走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像岳母一样,来来去去,听野草与庄稼絮絮碎语,看狗与鸡们相亲相爱。
这次出诊后,更加改变了岳母行医的姿态。对于村子里的孕妇,她主动上门了解产期,随时给予关注。其实岳母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只要哪家产妇要生了,接到叫唤,不管白天黑夜,随喊随到,即使屋外凄风苦雨,岳母也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哪怕是刚刚端起饭碗,她也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冲进雨幕中。白天还好,最怕的是晚上,没有灯,岳母一手执着煤油灯,一手打着油纸伞,在黑夜中前行。那个年代,煤油灯的命运跟乡村的命运一样,贫瘠,清苦。每到夜晚,煤油灯就在桌子和窗台上幽暗晃荡地闪动着,露出它温暖的面容,照亮一个清贫相依的家庭,是平常而朴素的事。我常常想,那一柱煤油灯,就是一个光明的使者,每一次出行,都是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当哇哇的叫声划破夜空,村庄又多了一个新生命,他睁开来到人世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炷明亮温暖的煤油灯光,虽然简单,但充满了神奇与温馨,足以让幼小的心灵盈满希望。小小的煤油灯燃亮了整个童年的夜空,让童年在它摇曳的光中温暖前行。
在乡村,煤油灯是温暖和光明的代名词,因为有了它,才不至于被一个个固定轮回的黑夜像河水一样淹没,才不会在黑暗中丢失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直到天亮,睁开惺惺睡眼,在穿进窗棂的阳光下寻找自己。
岳母用了多少煤油灯,她已记不清。究竟自己把多少孩子带到了人世间,也不记得了,胖的,瘦的,美的,丑的,聪明的,愚蠢的,富贵的,苦命的都有。但她记得谁家的孩子身上的胎记。记得许多孩子出生时,是5斤、6斤,还是8斤。她像一个女神,提着接生的小箱子,行走在有风有雨,有鸡鸣狗吠,有月光和闪电的大地上,一次次迎接生命的诞生,为村庄平添一次又一次喜悦。现在有很多人儿女都过膝了,碰到母亲都是毕恭毕敬的,原因是母亲把他们接到了这个世界。
随着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赤脚医生渐行渐远,最终退出了时代的舞台,“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为历史。正如煤油灯,已经成为一个乡村的老皇历。煤油灯的退隐世界后,电的光芒闪亮而来。电灯刺破了黑夜的坚韧,煤油灯决然退去,把这个戏台留给新的物质。退去不代表空白,煤油灯的存在无法抹杀,因为它温暖了一个时代,温暖着一辈人的记忆。是的,灯下那份温暖、安静的氛围不会消失,它会永远点燃乡村回忆的空间。
4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岳父与人合伙从事茯砖茶生产经营,举家外出,到县城办起了一家像模像样的茶叶加工厂。岳母也追随照顾岳父,一出就是二十多年,曾经的中年,虽然不是少小离乡,回乡时却是两鬓斑白的老人。母亲说,刚离开家乡,每到晚上或是清晨,她总是举头遥望远方,眼窝里全是泪水。只是时间久了,渐渐习以为常了。再后来子女成家立业,她又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带孙子,竟然融入了城市的生活,会打麻将,会说普通话,也会跳广场舞。
如今岳母已老,曾经满头的青丝中闪耀着刺眼的白发,岁月沧桑张扬在脸上,浮华初现。对赤脚医生的日子,岳母却是念念不忘,又如何能忘,十七年的赤脚医生生涯,那股熟稔的苏打水味道,弥漫着厚厚的日子。第一个接生的孩子,都即将走向成人之旅。有一次岳母拿出一个证件给我,是当年赤脚医生的证书,正是一个时代的坐标。证书上有一张一寸的黑白照,记录着岳母的青春印记,那时岳母二十四岁,刚刚为人妻为人母,年轻的面庞注满对生活的期待。在微笑的背后,是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注解。
岳母说,要是赤脚医生也能办养老保险退休,就好了。说完是一声沉重的叹息砸下来,仿若能把日子砸出一圈火花四溢来。她的眼睛里分明隐忍着泪水,这不仅仅是心酸,更是一个时代特征被遗忘的泪。
返乡的岳母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有些拮据。农村老人的养老除了子女的救济,没有更为宽广的路径,虽然每个月可以领取55元的农村退休金,但在当下物价飞涨的社会,55元钱仅能买到一壶色拉油,而且只能是最差的调和油。尤其是乡下人情费用疯涨,结婚生子满岁做寿,一张张红色请柬,压抑着乡下的老人。岳母再一次开始乡下生活的模式,种菜喂猪养鸡,却难以改变生活的窘困,这让岳母心情有点烦躁,甚至埋怨岳父的无能。七十高龄的岳父竟然在村里一家私营企业当上了搬运工。这让我的妻子伤心不已,竟在夜深人静之际,痛哭流泪。我知道她是心痛年老体弱的父亲,何以承受如此重压。
我知道,岳母期盼着这一张证件能温暖她的晚年生涯,而我却无能为力。
母亲的期盼终于有了些许结果。在我行将结束这篇文章之时,岳母打来电话说,她刚刚接到通知,赤脚医生可以到政府领取每月120元的困难补助,她正忙着去乡政府办手续。突然间,我仿佛看到那盏煤油灯的光芒,在灯光暗淡之时,母亲从发髻取下别针捻高了灯芯,灯光抖然亮了许多,浅黄中闪出白光,在黑暗中洇开,水雾一般,涂抹在岳母的脸上,一闪一闪地无声跳跃。
煤油灯渐行渐远,但记忆却从不漫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