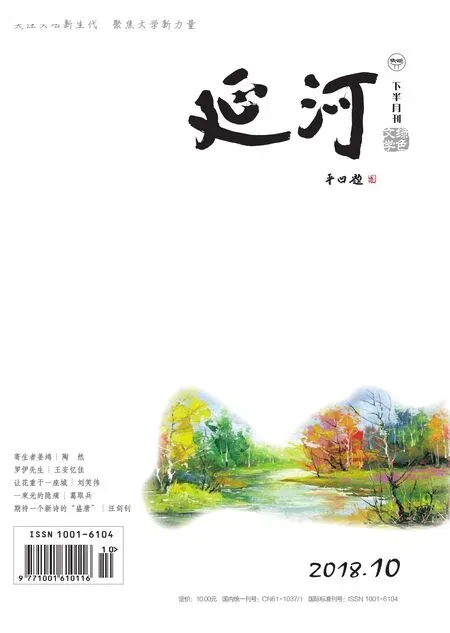树的守望及其他
刘中驰
石榴树
暮雨急,榴花湿,栅栏雾迷,榴枝婀娜。伸出手臂的榴枝,把榴花托出栅栏外,院里院外皆榴花。张扬肆意,满院红绿。
烟云蒙,青瓦青。沾了榴花的雨滴,变得浅红微醉,飘飘然。华清宫内,玉娘石榴树下轻舞,不知“贵妃花石榴”是否迷倒万千。在长安,“榴花遍近郊”的盛景,何等壮观,也只有爱到骨子里的武则天才会这般任性,爱石榴,她是第一等。
两千多年前,这株喜人婀娜的石榴,被张骞带回中原大陆,扎根两千多年,无限繁茂,视为吉祥的象征,中秋团圆都要吃石榴,多子多福,团团圆圆。痴爱,是骨子里对石榴的赞美。
喜庆的红,自古最爱,红花,红籽,让人欲罢不能,石榴天生讨喜。庭下石榴花乱吐,调皮的石榴花似娇蛮的青春女子,爱美,不羁,总是那么大放异彩,但又拿捏得恰到好处,落落大方,自然喜人。“一丛千朵压阑干,翦碎红绡却作团。”在白居易眼中,石榴花大气磅礴,如红绸剪扎,铺展荡漾,几近妖娆。
石榴花最爱农家,争及此花檐户下,任人采弄尽人看。姑奶家有一颗石榴树,极大,遮蔽着整条小巷,是小巷衬托了石榴树的魁梧,还是石榴树装扮了小巷的雅静,只有它们自己心知肚明。在一起,才会相得益彰,生动有趣。那时,我喜欢搬个凳子,踩着凳子去摘石榴花,姑奶不让,我就偷偷地摘,看着漂亮,就想拿在手里。坐在石榴树下把玩,满地猩红,披满小巷。
等石榴长大,摇曳的枝头,蹦跶着黄灿灿地石榴果,涨红了脸,咧开嘴欢笑的时候,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有石榴吃啦。能够到的就踩凳子摘,够不到的,有竹竿绑上网兜,网下来。姑奶是不准我们上树摘石榴的,她说石榴枝细,禁不住压,压伤了,来年就没有石榴吃了。我们言听计从,为了来年的石榴更大更多,之后都在树下仰头望。摘下的石榴,姑奶不独食,左邻右舍都分几个,一起尝尝。树梢上剩下的几个,她从来不摘下来,任石榴在树梢喜笑颜开,仰望蓝天。她说:“留几个在树梢,给鸟儿们解解馋。受了贿的鸟儿,来年不会糟蹋这棵石榴树的。”现在想来,一切豁然,世间所有的惊喜和美好,都是你积累的善良和人品。姑奶现在老了,但依旧健朗,大家依旧喜欢着她,像喜欢那棵茂盛的石榴树一般。
石榴,又被唤为丹若、天浆、沃丹,极仙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像仙女。不过,石榴总和美有脱不了的干系。“芙蓉为带石榴裙”。梁元帝在《乌栖曲》中,首次用石榴定义了一种服饰,女子的裙子,多用石榴花提取颜料,扎染,变成石榴红色的裙裾,美丽得体。石榴裙,应运而生,流传至今,“拜倒在石榴裙下”多来形容男子对女生的爱慕。
石榴子和青花瓷盘最配,一个素雅不争,一个晶莹剔透,它们像一幅画,令人垂涎,但又不忍下口。“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也只有杜牧,能把石榴的神韵写得如此生动了。石榴,不急不躁,有始有终,它的娇美,它的不羁,自顾自的欢喜,那是内心的愉悦,还是天生的痴呢?或许它在等待,等待中不想让自己悲伤,所以带着一颗饱满的心在仰望,如落入人间的仙子,等一份懂得的痴爱。
柿树
从记事起,院中的那颗柿树就安扎在了院内,树干清瘦,树叶葱茏。与红砖青瓦的房子,一起照应着家人的安生。柿树守时,春天,起死回生般地从枯枝上发芽,青嫩娇羞;夏天,枝叶茂盛,遮蔽整个院落;秋天,硕果累累,似灯盏,光艳迷人。家,被一片金红包裹着,温暖喜人。
听姐姐说,农忙时,只有她在家里陪我。姐姐一身粗布碎花衣,两束麻花辫,树叶筛落的阳光,扑在她有些土气的脸上,我扣着一个花兜兜,咿咿呀呀地不知所云,躺在摇床上,她一边无心地摇晃,一边数满树的柿子。虫鸣缠绕,鸡鸭欢叫。这样的场景像姐姐为我勾勒的一幅画,清冽,淡美。
枝头青涩的柿子,待秋风轻轻一点,叶落满院。柿子,娇羞地展露了出来,像串串冰糖葫芦,又像是盏盏灯笼,红艳,亮目。熟透的柿子,光滑剔透,宛如穿了件素纱禅衣,一眼能看穿肉核,吹弹可破的一层薄皮,轻轻一含,那汁液便被吸入口中,在舌尖上打转,碰撞味蕾,厮磨出秋日暖阳般的香柔,绽放,盛开,轻匀绛蜡裹团酥,不比人间甘露,芳香,馥郁。
霜降摘柿子,这是乡村的规矩,遵时令。早早地准备好网兜,用铁丝串口,撑开,绑在竹竿的一头,这样勾下来的柿子就不会落地,破裂。红红的柿子,软软的,哪经得起摔呀。爬上树,能够到的,直接用手摘,够不到的,就用得上网兜了。把柿子网进兜里,巧劲一勾,一颗完整的柿子就躺在了网兜里,连上几片绿叶,红绿相间煞是可人。那时,我和姐姐比赛网柿子,在母亲的指挥下,你追我赶,欢声笑语在树上回荡。
摘下的柿子,不能立马就吃,要在柿蒂上抹点白酒,放置几日,名曰“风柿”。院子里,窗台上,摆放的都是柿子。顿时,给寒秋肃杀的小院平添了丝丝暖意,一下子韵味鲜活起来。几日后,那色胜金衣美,甘逾玉液清的柿子可以品尝了,母亲总不会忘记亲戚、邻居,你家几个,他家几个,一院的柿子最后所剩无几。母亲总说,好东西吃不完的,年年有,我们不能吃独食。的确,年年的柿子,总是那么鲜美,甜到了心窝里。
神鼎十分火棘,龙盘三寸红珠。中国红,突然想起这三个字,再适合柿子不过了。柿子属于乡村,乡村又最有中国的文化神韵,中国红般的柿子,坚定,从容。在深秋,萧瑟的村庄,一抹柿子红,那就是故乡的色彩,是秋天,留给村庄的最后鲜亮。这红,由内而外,洗心革面的红,透彻,不留余地,是晨曦中的朝日,倾尽所能的浸染。柿子红,中国红,谦和,不漏声色,它不和春日百花争艳,不和初秋百果争熟,它淡定,无争,隐于乡村、山涧,凝结成别样的柿子红,中国红。
回家,一树的柿子,耀眼,沉淀。满树的喜鹊,麻雀叽叽喳喳,飞来赶去。这若在小时候,母亲早赶走了这些鸟雀,今日怎么任凭他们啄食?她说:“鸟儿们,也辛苦了一年,留点给他们,他们的叫声,不会让家里太空唠。庄子上也没几个人了,没人送了。就让柿子留在树上看树吧,树老了,太寂寞。”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我久久地看着树,它老了,奉献了一辈子,不该让它那么寂寥。一树寂寞红,独守乡村,些许伤感,像母亲,但又无法割舍那片故土。
银杏树
四都有古树,千年银杏立于村口,眺望太湖。
几百年前,太湖水直抵村口,与银杏树隔岸相望。出湖打鱼的渔民看到叶枝繁茂的银杏便知到家了。这棵树,于四都人,是灯塔,是方向,是温暖的臂弯。
沧海桑田,挺拔、旷达的银杏树牢牢地守住了脚下这块清宁、滋养的土地,已把触角深入土地的肌理之中,融为一体,扎根生长。
这颗仰慕已久的银杏,此时才得见容姿,树冠参天,遮天蔽日。主干支干纵横交错,枝丫树叶层层密密。玉骨冰肌未肯枯,树表肌理清晰,如果不是有四五人合抱的粗度,真不敢相信你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岁月。银杏树呀,仿佛你懂得“慢”的真谛,疯长一通不如扎实前行。你不像肆意妄为的柳树,也不像浅薄蛮生的梧桐。你是睿智的,铺满稳实的根,长出拨云的冠,长成一道景致,站成一种信仰。在四都村,你受到人们的礼拜与仰视,敬若神灵。

仰望树顶,鸟雀在枝头鸣唱、嬉闹,你追我赶,缠绵不休。树下,青草葱茏,围树争宠,有几颗小草还长到了你的身上,好生调皮。“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枝孙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乾隆皇帝的这首《银杏王》再适合不过眼前这颗银杏了,这颗孓遗植物定然也为路过四都的真可僧人庇荫遮阳呢吧,那是一种默契与相知。我不知你和真可僧人聊了什么?但那肯定是心与灵的交汇。
我喜欢你这颗孤独的老树,不奉承、不虚假,独自缓慢地生长着。我想,这也是你能够长寿的原因之一吧。千岁以后,依然开花结果。任凭世事如何嘈杂,人间如何繁复,你依旧仰天微笑,精神饱满,吹着湖风,听星月呢喃,孤独都孤独的独树一帜、风华绝代。在时光的长河里,你有一种孤清的美感,而在我的眼中,你有一种孤芳的文艺气息,这种气息与生俱来,是刻骨的深入。郭沫若说:“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熏风会妩媚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东方圣者,深得我心。我相信,不管是风、鸟还是神仙,他们都会依赖、信仰你的。今日来此与你相遇,借你一片荫凉,浮想联翩;做你的一片树叶,翩飞起舞,沾染些许的灵气。
亲近古银杏,仿佛在人生迷茫处,看到了绿意与希望。四都人是幸福的,无论遇到什么挫折,看看这颗古意绵绵的大树,那希望就充盈心中,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生在古树的苍绿中。
千年的阴晴圆缺,千年的草木枯荣,唯有银杏,千年不衰,灵气十足。因了这颗银杏,四都变得静谧而安详,村民的日子如银杏树一样踏实而美好,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棵树的命运就是村庄的命运,和千年银杏般顽强挺立,诠释对美好对希望的向往。
树的坚守
喜欢那些寒风中,脱光叶子的树,瘦而坚韧。
冬日的荒野里,寒风肃杀,一排排光着枝桠的树,与寒风对视,与苍茫大地对立,不过它们也拿大树没办法了,脱光了它的树叶,打折了它细小的枝条,留下的都是坚筋硬骨。冷彻天地的寒风,本想统一天下,没想到遇到了这样的“硬骨头”。不屈服的树,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保护开春后的枝繁叶茂,花果飘香嘛,为了延脉与坚守。
大树,守护着一方天地。在村庄,肃静的树木,俯瞰村庄,生怕在这个冬天会丢了什么。草屋,老宅,猪圈,烟囱,都在老树的视线内。冬日的村庄,显得萧条,但一眼看去,清爽通透,河水清,树木净,泥土黄。一场大雪,又把村庄包裹的像是童话世界。被雪花披盖的树,像是穿了棉衣臃肿的爷爷,直直地,向上,伸向天空,感受冬的温度。
在冬日,还郁郁葱葱满枝绿叶的树,是没有风骨的,只适合生活在城里,连鸟儿都不会选择这样的树做巢。这样的树被唤为“城市绿化”,少了树本该有的野性与傲骨。
凛冽风中,树梢上,黑黑的一团,毛刺林立,在空荡的树枝上独立,这是寒风中的鸟巢,这些鸟儿,不追逐温暖的南方,它们独立,不做温吞的懦夫。远看仿若漂浮在空中,疏离,突兀,仿佛整个冬天都是它们的,你说他寂寞,孤独,其实这才是它们的天下,自在,遨游。天空,大树,鸟巢,勾画出冬日田园的素描画,简约但又气势磅礴。像是冬日的老农,守护自己的田地。
走在冬日的田野里,不要害怕朔风的骚扰,也不要烦躁枯草的牵绊,让整个人走进这荒凉,你会瞬间发现,整个人都是精神的,空气中,土壤中,蕴涵的都是无穷的力量。那树一动不动,枯枝纵横,在辽阔天空的映衬下,孤立,寂静,像是死去般孤独,但这种决绝的孤独正准备爆发能量,扑面而来。像是陈忠实写的《白鹿原》,无限孤独之后,成就惊世大作。
站在风里,画面感十足,有种孤清的美感,这美感不是孤芳自赏,不是抠图,不是画作,这是大自然天然的杰作。晨雾中,干涸的河道,干枯的树,一村民牵牛路过,走在蜿蜒的田埂上,意境苍茫。这不是文艺,是刻骨的生活,是烟火的气息,一瞬间就能刺穿漂浮的灵魂。越苍凉,越寂寞,古意缠绵。
多像国画的留白,没有累赘,一目了然。你可以添加,你可以想象,但那都是虚幻的。黑黑的树皮,粗壮的树枝,团团的鸟巢,目不能及的田野,荒凉。是初始的样子,沉稳又带有气势。似中年男子,深沉,无人能懂,但又迷倒万人。人,做一棵独立于世的树多好,没有庞杂繁物,静对空凉。
冬天的树,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诗,不奉承,不言语,用心去读懂。把自己放在里面,独自去解读大地和天空的私语吧。月吹,日吹,寒风吹,他们吹不动的,树是天地的精灵,是使者,天空在,大地在,树就在,根就在。它不管你风花雪月、一世繁华,一棵树,见雨露不喜,睹霜雪不惊,独自站在冬天的最顶端,风华绝代地寂寞着。
冬日乡野里的树,魁梧,绰约。苍茫大地,有了树,才找到了主心骨。寒风中的树,铅华洗尽,卓然独立。冬日,择一棵老树,立在茫茫白雪之上,和粗犷的大树远眺,不说一句话。风停在树梢,天与地亲昵,沉默,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