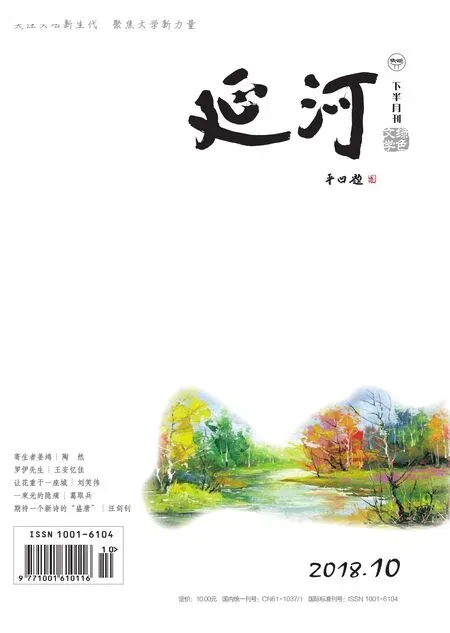右臂纹身说明书
维 摩
如你所知,夜晚的城市要比白天宽广。行人和故事被一栋栋大楼收纳折叠,覆盖以黑暗,太阳升起之前,其中的一部分将被永远遗忘。我陪几个客户在酒吧里喝二茬酒,出来时已是凌晨三点,除了街口执勤警车闪烁的灯光,整个世界没有一丝活气。
荒凉的夜风吹来,每个人的心脏都紧了一下。这时,他骑着嗡嗡作响的折叠电动车停在我们面前,问需不需要代驾。
客户们为这样的好运气爆发出小小的欢呼。我说要,当然要,然后掏出车钥匙递给他。他问清了我的车牌号,骑着车下进了地下停车场,不一会儿就把车开了上来。
送客户回酒店的路上,后座一直很热闹,话题围绕着酒吧里那位微胖的驻唱女歌手渐次展开,关于她的胸部有E还是F的讨论始终没有结果。其中一个很肯定地说她的黑色深V领下根本没有胸罩,否则以这个尺寸应该会更挺拔夺目才对,而不是左右摇荡的两坨。我用不太响的笑声来表示对这个意见的赞同,然后扭过头去看了代驾一眼。他脸上毫无表情,像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在我的印象里,代驾应该都很健谈,这是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从这个角度来看,眼前的这个人并不合格。
我注意到这个沉闷的家伙右臂上有纹身,这座城市里的小混混都喜欢这么玩儿。虽然他看上去早就过了雄性激素过剩的年龄,但假如他纹的是黑斧头或者关二哥之类的图案,我还真是得自求多福了。
我有些后悔,送完客户,车上就只剩下我们两个。按照常理,这个时间很难找到代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白天还有工作,睡觉时间同样宝贵。几乎可以断定,我的急切被空旷的街道放大后,做出了草率的决定。幸好我没有喝醉,我想起来手套箱里刚好有一把螺丝刀,而我正坐在副驾驶位上,随时可以取出来自卫。此外,后备箱里还有一把换轮胎用的扳手,这是威力惊人的武器,足以扭转任何战局。
想到这些我平静了很多。他驾驶速度均匀,过弯平稳,喜欢用换挡拨片而不是一D到底,不必要时双手从来不离开方向盘,这样细腻的男人不应该是个坏蛋。于是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晚还出单?”
他的声音和预料中的一样,有烟灰和粗沙的质地,如果仔细听,尾音里还有豫东平原村庄里微微上扬的习惯,他说:“我睡不着。”
我说:“好主意,我也想办个代驾,因为我也常常睡不着。”
他说:“其实没那么好,除了挣点辛苦钱,这个活儿没一点意思。想象一下,每天你都坐在路边,看昼夜分割路灯点亮。或者空荡荡的末班公交车从身边缓缓经过,夜行的路人倦鸟归巢,树叶在夜风里哗哗抖动,纸屑或者塑料袋横穿辽阔的马路,然后整个城市寂寞无声。如果运气好遇到下雨,可以有雨声为伴。但是你得躲进公交站,嚼着从24小时便利店买来的食物,上面的温度一点点流失,另一只手里的纯净水凉薄无情,灌进肚里会把肠子洗成透明。这时,有人从饭店或者酒吧出来,脸上笑容温暖,酒气萦身,也可能脏话满口,扶着矮小的女贞树呕吐。你想迎上去,有人就先于你搭上了话。你没必要跟他争,争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也许做完这一单就要回家睡觉,而你还有用不完的漫长时间。”
交谈使我的胆子逐渐大起来,我说:“能不能看看你胳膊上纹身。”
车厢里的空气像是被缓慢冻结,又被缓慢解冻,解冻前我甚至把右手放在了手套箱上。幸运的是我并没有把它打开,他在沉默中开出了大约一百多米。这一百多米过于漫长,我觉得经历了一百公里,等他把车停在一盏路灯下面时,我才再次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他拉高袖子,一幅带边框的画裸露出来,我立刻意识到那条手臂上应该有好几幅画,按顺序依次排列,绣在皮肤上。
他说:“这是一个故事,你如果愿意听,我讲给你。”
十几年前,葵市还没有膨胀,也没有这么拥挤。我一头闯进来,既没有学历也没有技术,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去爬管子。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在一个老乡那里蹭饭时学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点酒,他借着酒劲儿数落我,说我白活了二十郎当岁,一不能赡养父母,二不能成家立业,实在对不起“男人”这两个字。我低着头听,听着听着就放下了饭碗,那天我至少三次产生了想走的念头,又三次把这些念头扼杀在喉咙里。夜晚就在这样的反复中走向深处,这时他老婆走过来收拾碗筷,他站起来穿上外套,说走吧。我站起来时肚子又咕咕叫了两声,他说没吃饱就再扒拉两口,他老婆却已经把桌子收得干干净净。他说算了,走吧。我说我一个人回去,你别送。他说傻逼,跟着我。
那天晚上我跟着他,就学会了爬管子。学会以后他就让我单干,并且划定了严格的区域。他不到我的地方去上班,我也不准到他的地盘去工作。
我爬过刷黑漆的铸铁雨水管,也爬过刷黄漆的钢制煤气管,黄色的管子要比黑色的管子细,但更牢固更稳定,没多久铸铁管就被白色的塑料管取代了,塑料不承重,能爬的只剩下黄色的煤气管。这活儿对身手要求比较高,我小时候在塔沟练过武,虽然不成器,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荒废,干这些就像逛超市一样,毫无压力。这个工作干了五年,五年来我从没有失过手。我渐渐熟悉了这个城市,认识了不少朋友,攒了些钱,也动了安家的念头。总之,所有年轻人应该经历的事情,我都完全经历过;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正在日复一日地干着。我的酒量和腰围尺码渐渐大起来,生活开始向好的一面发展。不幸的是,新建的高层楼房都把煤气管道的位置预留到了大楼内部,电梯和楼梯间挂起了摄像头,我只好整夜在旧城区转悠,挑选合适的工作地点。

这份工作确实有着不错的收入,我年轻,花销大,收支平衡还能略有盈余,真是理想不过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那一天我运气很差,连续爬了两趟都没有什么收入,临近这个时间,饥肠辘辘,你知道的,凌晨要比白天饿得快些。好在夜里有风,家家都开着窗户,有些人开着空调,滴水声清晰单调。我顺着黄色的管子走上去,走进了七楼住户的厨房。月光很白,厨房里很安静,一碗白粥和半盘剩菜在餐桌上放着,空气里有微弱的花椒油气息。我从厨房里走出来,外面是客厅。那里陈设很简单,电视对面是一张沙发,沙发上坐着一个人,那个人正面对着我。
成吨的血液同时涌进了我的脑袋,有那么几秒钟,我丧失了听力和视觉,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房门就在不远处,我可以夺门而逃,也可以悄悄退回厨房,走原路离开,但我很快恢复了冷静。我看出来那是一个老人,我估算着距离。如果他喊叫,我可以在几步以内锁上他的喉咙,想好这些我就放心大胆地往前走,一直走到他的面前。月光穿窗而入,把他的瘦脸弄得半明半暗。
我问他,你看见我了?他说,是。我说,你怎么不喊?他说,我怕。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他说,我怕我等不到儿子回来那一天。
说完这话,他竟然捧着脸抽抽搭搭起来,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有一只表,应该不是什么名牌。我把它解下来戴在自己左手手腕上,然后推开窗户,把他扔了下去。
他的身子很轻,三两或者七两的样子,比一片树叶重不了多少,落地的声音可以忽略不计。
后来我就去考驾照,给人开出租车,车主跑白班,我跑夜班,自己挣的钱,需要再给车主分一份儿。比起爬管子,这个活儿更辛苦。我早就习惯了黑白颠倒的日子,这个工作让我兴奋。我乐意跟一身夜色的人打交道,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都和白天的自己迥然不同,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有一次我遇到教我爬管子的老乡,我没有收他的车费。他说生意现在不好做,一晚上需要跑很多地方。我说你也可以学学车,干点正经营生。他说傻逼,别逗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听人说,前阵子他从楼上掉下来,人还活着,身子却稀碎了。这条新闻上过当天的排行榜,下面的留言都是很简洁的粗话,带着刻薄的喜感,念出来不怎么好听。不出意外的是,他老婆孩子以及票子都归了别人。嫁人前他老婆曾经给我打过电话,问我能不能给他送回豫东老家。我想起来她收拾碗筷的狠劲儿,顺手就挂断了。
秋天,我在机场接到一个很瘦的女孩。那么荒凉的深夜,她只是穿着短裙和白色球鞋,手里的iPhone发出蓝汪汪的一团光。人流很快散尽,机场悄无声息,她应该是最后一班落地的。我被她细长的双腿晃得心慌,就迎着那团蓝色的微光开了过去。
她说:我没钱。
我说:没事,我送你。
有这样一双长腿的女孩子当然可以不付车费,但她完全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借口。换了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一个买得起机票的女孩子会没钱打车。在她摘掉耳机拉开车门的同时,清寒裹着很淡的柠檬味儿慢慢从后座升起,这样性冷淡的气息,竟然一下把我刺穿了。
免费乘车的代价是聊天,她很懂规矩。
我问:旅游,还是找人?
她说:找东西。
坐飞机来找东西?
一盆花。她说。
什么样的花?很值钱?
她没有回答我,后视镜里是一张单薄的脸。我拨了一下后视镜,角度下移,从那里可以看见她并拢的膝盖。灯光从侧面车窗外投射进来,每一次都在修饰那双细长的腿,有时暖黄,有时腻白,有时粉嫩,有时五色交缠,可惜的是光线太暗,不能延伸到裙子里面去。我说怎么称呼你,她说:董小姐。我说那不是一首歌吗,她笑了一声,说:大叔,你也知道啊。
萌系女忧的调调,清甜可人。
后来我才知道,萌并不代表简单。知道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已经给她做了好几次免费司机。每次搭车,她都去往不同的地方,大都是夜间,酒吧咖啡馆什么的。有几次她跟我借钱,不多,一两百块,我都爽快地掏了腰包。这件事很好理解,我这么一个单身大叔,总会做一些怪事。闻到那股淡柠檬味,我就会想起她单薄的嘴唇,嘴唇里总是连篇的谎话。我相信那些谎话的唯一动机,就是想闯进去尝尝舌头的味道。
在葵市,初秋和深秋的差别,就是一场雨的事儿。雨不大,下下停停跨了五天,满街的人都穿上了厚外套。凌晨三点,我在吴记吃刀削面,刚往碗里添上辣椒,电话就响了,董小姐说她在苏荷门口等我,快点到。我匆匆吃了几口面,喝了两口汤,跳进了车里。
酒吧散了场,除了灯光,附近空空荡荡。她和一个个子很高的姑娘站在路边等我,抱着肩跳着脚驱赶寒气。我迎着她们开过去,她俩拉开门挤上了后座。我打开暖风,问她们去哪儿。她没有答话,个子很高的姑娘说了一个快捷酒店的名字,说话声音并不清亮,却很好听,有点沙瓤西瓜的感觉。我注意到她胸部很大,长发,豹纹高跟鞋,放在人群里非常耀眼。
我说我知道一个距离这儿更近一点的酒店,环境不错。
我也困了,咱仨去开一间房,我付房费。
没人理我,我朝后视镜里看了一下。她俩正纠缠在一起,吮吸声浪涌过来。董小姐的右手侵入高个姑娘的黑色深V领,妄图包裹那枚硕乳,左臂环着她的脖子,想把她揽到怀里来,可她过于瘦小而对方过于高大,她无法完成自己想象的动作,只能像猴子一样挂在树上,发出粗重的喘息。
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吗?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点头,但我确实点了点头。他看了我一眼说,有那么一瞬间,我摘了空挡,右脚放在了刹车上,我想把她们撵下车,让他们冻死在深夜里。后来我说服了自己,我已经在葵市扎了根,生活走向正轨,黑夜里有很多事违背常理,我没必要再参与进去,只要做看客就好。
我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的角度,继续往前开,偶尔扫一眼镜子里的画面。
高个姑娘扭动着,高跟脱落,短裙翻卷,露出豹纹内裤的一角。董小姐翻身跨坐在她腿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我曾经幻想过她以同样的姿势对付我,或者更加充满侵略性,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我开始后悔借钱给她,虽然不多,但也够买很多碗刀削面的。
那晚之后,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见过董小姐,生活就渐渐平淡下来。有时我会突然想起她俩,就把车停在苏荷对面,关掉灯看着人流散场。她俩没有出现,倒是意外地接了几单生意,这让我渐渐忘掉了那几百块钱,心安理得地接受季节转换。
我还是习惯凌晨三点前到吴记吃刀削面,天气越冷客人就越少,价钱却涨了一块。我埋怨老板不厚道,老板很无奈说牛肉和煤气都在涨,他不涨就赔了。“走遍葵市,哪一家刀削面有我们家的碗大?”他说的是实话,我跟他开着玩笑,从前台取了一只卤蛋,转身往自己的座位上去。屋子里食客稀稀拉拉,所以老板关掉了一半电灯,靠墙的地方光线昏暗。就在墙角的暗影里,我发觉一个男人正在看我。
被看一眼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又一个夜晚来临之前,我去万达百货附近接车。白班司机迟到了一会儿,我站在路边吸烟,电话响了,你可以猜到是谁。
她问:最近怎么样?
我说:挺好,没人借钱,手头宽了不少。
她说:我请你喝酒。
我说我开车,不能喝酒。她说少跑一天车没什么大不了,我和茉莉都想你了。原来那个高个子姑娘叫茉莉,她俩竟然还在一起,我犹豫着想拒绝,她却在电话里起了高腔:
别给脸不要脸啊,我在长夜里。
长夜里是一家小酒吧,它太小,在葵市没有名气,爱玩的和会玩的都不往那里去。如果不是夜班司机,我也不会知道它在哪儿。我给车主打电话请了假,车主有点意外,他说你开车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请假,不是想跳槽了吧。我说我只会开车,也跳不到什么高枝上去。他哈哈笑了两声,说这车年头也差不多了,明年低价转给你。这回意外的是我,但我忘记了说谢谢,我挂掉电话,坐公交赶往南城区。
公交站距长夜里有四五百米,徒步走过去大约十一二分钟,就在这十一二分钟里,夜晚罩上了最华丽的袍子。城市的繁华不在白天的写字楼,而在夜晚的人流里。我推开长夜里的门,小小地吃了一惊。小屋里竟然满满的都是人,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酒保举着托盘在人群里穿行,有人举着手臂随音乐摇摆。吧台边的圆形小舞台上,一个黑色深V领的女人叠腿坐着,手里捧着麦克风。
那是茉莉。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唱《浮夸》,我只听了不到一半,就猜到这里人满为患的原因。她的沙瓤西瓜用来唱歌真是好听,我听了这么久的电台广播,竟然不知道这首歌的女声版更有味道。她看到了我,就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她招手的方向看过来,就像舞台聚光灯打在脸上,我的虚荣心一下子膨胀起来。
小舞台边的桌子应该是给我预留的,我坐下来,与茉莉的豹纹高跟鞋近在咫尺。她晃荡的时候,几乎踢在我的鼻尖上。她与出租车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她坐在高凳上俯视全场,就像长夜里的女王。在灯光里仰视她,我有一点透不过气来。这时候有人点了一首《董小姐》,她拿到歌单笑了一下,冲着身后点了点头。我这才发现后排的鼓手边坐着董小姐,她戴着毛茸茸的帽子,怀里抱着一把吉他。她在给茉莉伴奏的时候,从没抬头看过我一眼。我猜她知道我在看她,但她就是不愿意抬头。
唱完这一首,就到了场间休息,贝斯手接管了麦克风,唱黄家驹。茉莉拉着董小姐走下来,她坐在我的对面,董小姐坐在我旁边。这是张四人桌,茉莉身边空着一个位置,有个男人端着啤酒想要坐下来,茉莉说了声“滚”,他尬笑了一下离开了。
有烟么?
我掏出烟和打火机递给她,她抽出一根点燃,然后把烟和打火机都交给了董小姐。董小姐接过来,点燃一支,吸了两口,把剩下的半支递给了我。我能感觉出那支香烟上带着唇印,但我来不及细想,我接过来含在嘴里,淡蓝色的烟雾立刻笼罩了这张桌子。酒保端着酒走过来,凑到茉莉身边说,茉莉姐,咱这儿不让抽烟。
哦,她说,就一支,说完举起杯子朝我俩晃了晃。
我喝酒快,碰到第三次,面前的酒杯就见底了,茉莉面前还有小半杯,而董小姐的酒几乎没怎么动。一曲终了,茉莉朝台上比了个手势,贝斯手心领神会,把歌换成了《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发现这个小乐队很不简单,不知道长夜里给他们开出了什么价钱。只是董小姐看上去有点不在状态,茉莉朝她举了举杯子说,让他替你喝点呗。
我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董小姐的嘴唇就递了上来,我感觉到淡柠檬味柔软坚决,一股冰凉的液体撬动我的牙关,缓缓注入口腔。我从未想过以这种方式替女人喝酒,动作很是僵硬。茉莉托着腮笑了一下,说戏做过了,有点儿像摔跤。董小姐没笑,抽出纸巾擦着嘴说,走吧,我饿了。
茉莉说好,说这话时她垂着睫毛,长发和红唇在灯光下有些妖。我身边虽然坐着董小姐,还是忍不住向她半露的胸部望过去。她起身往外走,我俩就跟着。酒保在门口等她,把羽绒服和包交到她手上,说茉莉姐,要不要帮你叫车。她摇了摇手说,不用。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喝了很多酒,醒来的时候我躺在酒店的地板上,董小姐躺在大床上,茉莉不知去向。我洗漱完坐到床边,董小姐依然没有睁眼。空调暖风嗡嗡作响,我看见她睫毛在轻微抖动,不知是害怕还是期待。我把手伸进被子,摸到她温热光滑的乳房。那两枚乳房鸡蛋样大小,我一只手足以掌控她们。我的手捏住她们的时候,她的皮肤上起了层层叠叠的鸡皮疙瘩。我没有遭到抵抗,就抽回手去解自己的衣服。她裹着被子坐了起来,轻声说:
我不喜欢男人。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喜欢女人。
说完这话我就把她压在了身下,她踢我、抓我、拧我,咬得我肩膀生疼,我还是做完了想做的一切。事实上她只抵抗了一阵儿,剩下的时间都在哭,嗓子秃秃的,声音没有光泽。我穿上衣服那会儿,她已经蜷缩成一团棉絮。我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扔在床上,那里面是现金和一张机票。
我走出酒店,天幕微蓝,空气冰冷,有辆车停在马路对面。看到我走出来,它抖动了一下开走了。我看着它白雾迷蒙的背影,猜测茉莉会不会坐在车里面。如果董小姐离开葵市,从此在她的生活里消失,她会不会就此轻松下来。她的乐队里应该有个更棒的和弦,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听一听。
夜班时我心神不宁,就开车到了那家酒店,停在马路对面。我看见房间开着窗,一个瘦小的身影站在窗口,灯光从她背后奔涌出来,把她的身影推搡得摇摇晃晃。楼下的车辆和人流匆匆忙忙,没有谁注意到这条孤单的影子。我害怕她纵身一跃,所有的事情就不可挽回。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但是影子终于离开窗口了。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的车跟前,还是穿着那双白色球鞋,拖着来时的拉杆箱,只是背后多了一把吉他。
送我走,她说。
她错过了飞机,我只有送她去郊区的高铁站。一路上我喋喋不休地说着,我说茉莉有自己的生活,你不应该这样打扰她,你们这样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她问这番话是不是茉莉的意思,我没有回答,她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董小姐消失很久以后,茉莉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喝酒。只有我们两个人,话题也非常轻松。她有些醉了,我掏出烟给她点上,她吸了几口,眯着眼看我。
他是不是找过你?
谁?我说。
他给了你钱和机票,让你打发董小姐走。
我说,难道那不是你的意思?
你明知道我和董小姐找你,不过是演戏给他看,你却将计就计,让我们一败涂地。
你没有任何损失,我说,你那些不好的传闻烟消云散了,你还是葵市最好的夜场歌手,我还是你的忠实粉丝。你和你的乐队回到最好的酒吧演出,挣得比长夜里多得多。我夜班拉活儿,每天都会往你那里跑几趟,节假日什么的,还会有外地人专门跑来嗨。现在不仅男人们捧你的场,女人们也喜欢得不要不要的。
如果不是她的豹纹高跟鞋在桌子下面踢我,我还要继续说下去。
董小姐是有点太黏人,她说,但是我更讨厌他。
你想让我怎么办?
帮我摆脱他。
我为什么要帮你?
她把烟灰弹落,指甲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说话的语气也闪闪发亮,她说你手上的那只表我认识,我租的房子就在那个老头的对门。
我没得选择,他说,说完这话他就把袖子卷到最高处,我看见这些故事在他的右臂纹身里依次出现,最后剩下一个空白的画框。
现在,你知道了一切。我需要你和你的车,去做最后一件事。做完这事,我会补上这幅纹身。说完,他俯下身,从地垫下抽出一件东西,反射着路灯的冷光。
那正是我放在后背箱里的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