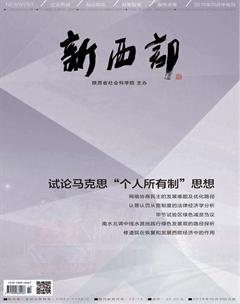严歌苓创作中“文革”叙事的独特视角探析
雷静 邓家鲜
【摘 要】 “文革”记忆是旅美作家严歌苓最擅长表现的文学内容之一。尤其是对“文革”背景下人性的复杂性有着独特的写作视角:从儿童与成人视角的交织,女性视角下的独特叙事,对文化视角的修复等角度展示出严歌苓对“文革”带来的苦难有着独特的理解,并致力于展示人的本真状态,呈现出严歌苓构建的独特的“文革”世界。
【关键词】 文革;严歌苓;叙事视角
随着严歌苓作品《天浴》《金陵十三钗》《归来》等的改编引发了一轮研究其作品的热潮。特别是2017年12月,随着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的上映,关于“人性”、“善良”的定义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一时间刷爆各大社交网络,这一部分正是得益于作为编剧的严歌苓以其独特的视角书写了那段荒谬的岁月、那段红色的记忆。严歌苓文学创作对“文革”带来的苦难有着独特的理解,并致力于展示人的本真状态,将笔触深入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性深处,将美与丑一并撕破,在儿童和成人的双重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和文化视角的修复中开辟出其个性化的文学天地。
一、儿童与成人视角的交织
描写“文革”的作品浩如烟海,严歌苓之所以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在于她不同于其他作家纯粹的成人视角叙事,她常能够以儿童的视角展示“文革”对孩子内心世界的影响,同时以孩子单纯的视角淡化事实的惨烈,尽可能以比较轻松的笔调去讲述。同时又能够保留成人视角的冷静与客观,以过来人的角度揭示儿童视角所无法达到的深度,使作品主旨得到升华。
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因为,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其一生的。严歌苓也不例外,其童年的经验就集中体现在其《波西米亚楼》和穗子系列中。《波西米亚楼》写失去了童趣、童心的童年,童年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其穗子系列以孩童的视角描绘成人的世界,在看似诙谐的语言下反映着特殊时代下的无奈,孩子本应是纯真的,却在时代的染缸下被人性中的恶所浸染。《穗子物语》(2005年)中描写最多的是关于自杀的故事。《角儿朱衣锦》中李叔叔跳楼自杀,穗子只能掩饰内心的悲痛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孩童内心的怜悯忧伤在这个时代不允许释放,穗子渐渐变得沉默,这实则是一个孩子的自我保护方式,更是一个孩子的自我封闭。朱阿姨自杀未遂,穗子默默地守在她身边,虽然弱小却想竭尽全力保护她,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1]穗子为之痛苦,却无力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这个时代竟被禁止,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阶级对立,人性中的美好与温暖消失殆尽,引发读者对整个时代的反思。
在叙事视角上,严歌苓站在童年穗子和成年穗子的双重角度对“文革”进行叙述,当看到童年穗子的无心之举犯下大错,“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2]成年后的穗子为之揪心,却不得不眼睁睁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一切。这些年幼的女孩却偏偏有一种毁灭一切的魄力,恰恰抓住人心中最脆弱的东西加以毁灭。两种视角的交织,是时代大悲剧下的无能为力,更是人性自律的沦丧。
二、女性视角下的独特叙事
严歌苓既拥有作家所必备的敏锐直觉,同时也具有女性所特有细腻多情,这使得她在进行“文革”叙事时有不少作品能够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创作,关注“文革”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生命体验。严歌苓所追求的女性主义,往往不是对男性扭曲、丑化后而进行的女性赞歌,她力图表现的是一种客观平等的两性关系,女性不再是爱情中被动的一方,她们对爱情有着绝对的主动权,能够把控自己的爱情和命运。这一表现形式在严歌苓的“文革”叙事中形成了一种模式:女性勇敢追爱,在“文革”的考验下实现价值、收获爱情。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年)便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作品中率真的文工团员田苏菲打破恋爱模式中女性处于被动的局面,而是熱烈地追求欧阳萸。虽然最终如愿嫁给他,却始终处于婚姻摇摆的边缘,直到“文革”的到来使丈夫曾经的爱慕者烟消云散,在苏菲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欧阳萸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终于回到了田苏菲的身边。作品将重心放在女性对爱情的执着与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斗争与革命成为陪衬,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个人价值的追求才是叙事的中心。
除此之外,严歌苓还极力表现“文革”对女性心灵的摧残、对女性的压抑、对女性发展权利的限制,揭示出一个时代的隐痛。《雌性的草地》中“雌性”是女性天性的自然释放,是人性使然。但在那个动乱年代,一群少女被放置到荒凉的大西北,她们有着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名字——“女子牧马班”,在这里她们不再拥有性别,自身的“雌性”被完全压抑。严歌苓用其细腻的感悟向我们展现时代对女性的迫害,让人为之心碎,这来自于严歌苓同样作为一名女性的自觉。
严歌苓对“文革”的叙事不局限于对政治的批判,她站在女性的视角描写“文革”,女性则在时代苦难中显示出坚韧、包容的品格,成为自我价值的追求者和实践者。自古以来,中国女性一直处于男权社会的弱势地位,严歌苓在其作品中所描述的“文革”中的坚韧的女性形象,不仅寄托了其对该时代女性的赞扬,更表现了女性主体意识从缺失到觉醒的过程。
三、对文化视角的修复
在对严歌苓“文革”叙事的研读中,还发现其有一些作品常从文化视角来探寻特殊时代社会,且其文化视角经历了一个探寻和修复的过程,这种变化与严歌苓个人的人生体验不无关系。严歌苓少年时期经历“文革”,父亲的遭遇、萌娘的不幸,年少时受到的伤害使得她在早期的作品中充满压抑、控诉的情绪,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对人性进行剖析,痛斥人性的扭曲。这在其早期作品《绿地》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中可见出,内心的压抑得以宣泄,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还不时地在作品中与笔下的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黑暗,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让它蔓延。它需要某种冲击力,使法律与理性出现缺口。”[3]十年“文革”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压抑被变本加厉的释放,道德价值观被当下的主流所引导,个人的判断丧失,道德处于失控边缘,这个时期严歌苓对“文革”带来的伤害是严厉控诉的,不仅反思政治所带来不幸,还控诉了“文革”对人性的压抑。
1990年严歌苓赴美留学,异国的经历使严歌苓与过去拉开了距离,“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4]此后的十年她跳出原先的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从人文的高度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对“文革”的苦难表述开始加入浓浓的人文关怀与伦理思考,从表层现象深入本质,从故事的经历者到回忆者最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严歌苓认为出国对于她而言可以说是一次新生“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的更宽泛些。”[5]严歌苓开始通过对“文革”中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来刻画人们所受到的精神的创伤、情感的扭曲、心理的异化、道德的沦丧,去反映整个时代的苦难,这正是她对文化视角进行修复后作出的改变。
“文革”作为中华民族无法忘却的记忆,无数作家拿起手中的笔去书写那段艰难的岁月,严歌苓作为“文革”的见证者,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能够跳脱出政治本身,给予笔下人物浓厚的人文关怀,深入探索人性的隐秘,以女性细腻的笔触描写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些独特的叙事视角使得她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表达。这也正是严歌苓作品多次被搬上银幕,引起强烈反响的奥秘所在。在对严歌苓的创作赏析中让人了解过去的那段岁月,领悟严歌苓对生命、对人性的感悟,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领略其文学魅力。
【注 释】
[1] 嚴歌苓.有个女孩叫穗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54.
[2] 严歌苓.穗子物语[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自序.
[3]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
[4] 严歌苓.在美国呆下来,活下去[DB/OL].http://www.360doc.com/2014-04-17/.
[5] 孙宁.严歌苓:我到河南种麦子[DB/OL].http://www.kanunu8.com/2003-11-28/.
【作者简介】
雷 静(1993-)女,大理大学2017级语文教育学科研究生.
邓家鲜,女,大理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