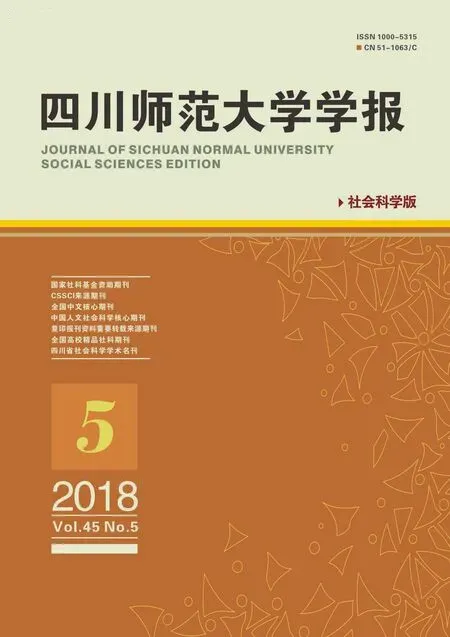栖居与游戏:对旅游体验问题的再认识
蔡寅春1,,谢辉基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610072;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一 引言:对旅游体验问题再认识的学术意义
旅游体验是旅游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这一问题通常又与旅游的本质、旅游真实性等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据董培海等的总结,旅游体验自产生之初即与现代性体验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2],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谈论现代性,则必然要涉及到人的异化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3]。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现代性反思,Turner等学者将旅游活动视为现代社会的宗教替代品,认为旅游体验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离开世俗世界的休憩”[4]20。在此思维框架下,“逃”与“寻”成为了解释旅游者出游行为的关键词[5],并在学术界内获得了广泛的支持。Dann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周期性的逃逸”(periodic escape)这一概念[6]。国内学者谢彦君在分析旅游体验的价值时也发现了相似的机制,他称之为“快乐—痛苦”两极情感模型[7]。就以上梳理可以看到,旅游体验对日常生活世界具有某种补偿效应[8]84,这是从对现代性的对抗中发展出的学术观点。对此,MacCannell的研究有着很好的解释,他将处于旅游欲望深处的动力因素同现代性所引起的断裂感进行了连接,认为:“只有那些力图摆脱日常生活的羁绊,开始懂得‘生活’的现代人才会有本真的经历和体验。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陷入越深,他就越会想起存在于他处的现实和本真。”[9]181MacCannell认为,现代社会带来的虚无感,个体需要返璞归真,旅游体验的目的地就是寻找真实。
由对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入手,Cohen在《旅游体验的现象学》一文中,根据旅游者“追求中心”程度的不同,发展出一种“旅游体验的现象学类型学”[10]。据张骁鸣等的总结,这是可考旅游学文献中较早使用现象学方法探讨游客体验的文章之一[11]。
在Cohen之后,大量与现象学相关的旅游体验研究成果开始涌现。如前文所述,谢彦君等提出的两极情感模型将旅游体验从对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中剥离出来,进而论证旅游体验作为旅游世界硬核的可靠性[12],实际上即受益于此。他将旅游体验的本质收束于对愉悦的追求,并以此为旅游的本质,而这正是杨振之等在分析中所批判的。通过对旅游真实性问题的反思,杨振之等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观中获得启示,认为旅游的本质应在于对诗意栖居的短暂获得[13],在《论旅游的本质》一文中,这部分讨论被进一步深化[14]。在其最新的反思中,甚至以“体验—世界”的关系为现象学的分析基础,提出了“游戏说”的尝试[15]。
通过对上述学术观点的对比可以看到,从谢彦君到杨振之,他们在讨论旅游体验与旅游本质的关系时,均使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或观点,但其所依据的现象学理论是有显著差异的。虽然二者都在尽量避开真实性问题对旅游体验分析的干扰,但是真实性问题的影响在其中仍旧可以看到。作为中介者或是桥梁作用的现代性,似乎为旅游体验的探讨垫定了一种潜在研究基调,即通过旅游体验可以同愉悦等感受建立起某种直接的联系。作为结论的一种,旅游体验通常被认为对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消弭作用[16],这是支撑旅游体验能够与旅游的本质建立起直接联系的重要环节。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被治愈了的旅游者”在通过旅游活动获得暂时性的“回归”之后,为何还会出现重复的出游?在已有的学术分析中,研究者们极少对此产生质疑。然而,就基本定义来看,作为词根“tour”一词,本即包含着往复的意思[17]7,这是一种动力机制。如果仅从“诗意栖居”和“愉悦性”来理解旅游体验,显然并不足以解释推动重复旅游背后的深层因素。
旅游者需要反复出游,这是从“周期性的逃逸”中剥解出的学术现象。在传统分析中,除“过渡仪式”对此有过特殊的关注外,对旅游体验问题的探讨极少涉及这一方面。然而,就杨振之等所提出的“对诗意栖居的短暂获得”来看,出游活动的重复性必然要与旅游的本质发生关联,在此基础上对旅游体验的深入分析才存在可能。已有的分析虽然关注到了现代性的挤压与重复出游之间的关系,但是深入的探讨仍然缺乏。作为主流研究范式的“逃逸—回归”模型,虽然对旅游活动的社会性和需求性进行了反思,但在解释旅游体验的内涵及其层次的分型上仍有推进的余地。考虑到“重返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提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经逐渐引起重视,且这一议题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说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5]。本文立足于对旅游体验内涵的发掘,将对旅游现象的理解在“与世界打交道”这一特征词的引导下进行继续推进,在补全前人所遗的基础上,希望对旅游研究新视域的打开能有所启迪。
二 体验、现代性及旅游的本质
体验是否是旅游的本质?这个争执由来已久。命题的提出最早可以溯源至20世纪60年代大众旅游的兴起。在对“伪事件”(Pseudo-events)的批判中,美籍社会学家Boorstin将“体验-真实性”的话题引入了旅游研究。他认为,“真实性”的提法实际上只是流行的群体性消费文化的一种噱头。大众化的游客需求是狭隘的,一则大众化的游客体验根本无力辨别真假,二则扁平化的游客预期一定程度上亦助长了地方伪事件的出现[18]78-90。甚至就动机来看,多数旅游者的出行目的也未必是要去追求目的地社会的本真现实。恰如Bruner所说,“西方游客消费旅游,并不是去看埃塞俄比亚饿死的孩于,而是去寻找‘高尚的野蛮人’,一种他们想象中的人物形象。”[19]也即是说,“体验-真实性”的话题实际上是一个双向度的问题,它的一端联系着游客体验,另一端则联系着主客世界的客体现实。从逻辑上看,二者应当是可以重合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完全覆盖。于是,这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旅游体验与客体世界的具体关系问题。
自Boorstin后的四十余年间,经MacCannell、Cohen等学者的持续努力,“体验-真实性”话题在旅游研究者内部发生了关注点的转向。以国内中山大学王宁教授的《对旅游体验之真实性的再思考》[20]一文为显著界限,学界对体验或真实性的讨论已同“体验是否是旅游的本质”等建基性问题产生了直接联系。
同期的研究中,Berman曾以Jean-Jacques Rousseau文中出现的“现代性”一词为契机,对现代性与现代性体验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他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体验,“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21]15MacCannell深受这类观点的影响。他指出,大众旅游的产生同现代性背景间有着紧密的联系,Boorstin眼里“看似荒诞的旅游行为”,其实质是那部分的旅游者试图在他者的世界中寻找自己失落的“真实”——“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陷入越深,他就越会想起存在于他处的现实和本真”[9]181。
Morris和他的研究同伴在讨论中将这种寻找“自我本真”的行为倾向称之为“怀旧”[22]。心理学的分析显示,怀旧与其说是一种行为的倾向,不如说是某种记忆的被唤醒[23]。Goulding指出,怀旧中孕育着一种暂时性的记忆的重现,或是逃离现有社会的一种解脱,对个体来说“它即是一种消费偏好,也是一种消费体验”[24]。词源上,怀旧有“因思慕家乡而引起的焦虑或痛苦”之意,由希腊文中“Nostos”(返乡)与“Algos”(痛苦)两部分构成,通常与乡愁一词相联系,至20世纪时被现代心理学定义为一种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疾病[25]。换言之,就真实性一词来看,MacCannell等提出的“体验-真实性”的看法实际上是与现代性背景下的“返乡”一词相联系的。在此,与其说是现代性滋生了旅游者对“真实性”问题的思考,不如说是旅游者在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游戏,在旅游行为中建立起完整世界中的永久性的家居生活”[26]178。
Rojek的看法与MacCannell等相似,他视旅游与休闲为现代性条件下的一种“解脱方式”,其效用是弥补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失落感[27]78-80。这类说法目前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依Gruburn此前在《人类学与旅游时代》中的看法是:体验、旅游、真实性及现代性关系的揭示,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的出现总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有关”的学术困惑[28]115-123。这样的提法虽不能完全地涵盖所有的游客动机,但至少相对合理地解释了游客体验在诉求与感知上的分异。如Cohen等即认为,虽然现代性与游客体验间存在显著关系,但并非所有现代人同周围环境都是同等疏离的,从中心到边缘的游客体验呈现出由神圣到世俗似的阶梯式分布[29]。
在Jafari的“跳板”隐喻[30]与Graburn的“人生仪式”论[31]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谢彦君[32]与张凌云[33]分别从“体验场”与“非惯常环境”的角度对旅游体验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了区分。在《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中,谢彦君继“体验世界是旅游世界的硬核”[34]41-84的表述后,进一步指出:旅游的本质应当归属于一种非惯常环境下的异地体验,其目的是追求“愉悦”,余暇与异地将旅游体验与一般体验区分开来[35]36-41。王玉海批驳了谢彦君“追求愉悦”的观点,指出虽然张凌云提出的“非惯常环境”的说法不周延,但是旅游追求异地短暂生活方式的说法却是可以肯定的[36]。在对“旅游-真实性”问题的批判中,杨振之教授指出,旅游研究对真实性问题的讨论至王宁教授的“体验-真实性”一说,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讨论范畴,进入到对旅游本质的探索层面[13]。这一观点在其续作《论旅游的本质》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通过旅游属性的现象学考察,杨振之等得出结论:作为众多存在方式的一种,旅游的本质乃是人在地上实现“短暂的诗意栖居”[14]。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同是出于对现代性与体验真实性的思考,当谢彦君等学者还阈于“旅游的本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37]及旅游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具体关系[38]的讨论时,以MacCannell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学者已试图在“体验的效用”中为旅游的本质或存在的意义寻求某种解释的可能[39],虽然这样的尝试在“体验-真实性”的话题下总是因“现代性”观念的介入,在内容与效用间反复地“兜圈子”。只就个体体验的真实性一事来看,以上研究至少指明了这样一个方向,即:体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性是揭示体验内涵与旅游本质的必经路径。
从“旅游的本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一提问来看,“体验是否是旅游的本质”这一问题在问题产生之初即出现了提问上的偏差。若缘此道路继续追问下去,得到的仅会是“旅游体验={x|x∈审美、愉悦、非惯常环境下的休闲体验……}”或是体验的层级性问题。可以看到,这些揭示至最末非但不能有效解释旅游的本质问题,而且其本身即已内在地包含于某种存在方式当中。换言之,如果我们就旅游体验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点来谈论旅游,那么旅游经历本身并不是某种体验,甚至不是某种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某种生活经验的切换,而是“终有一死之人”同内外世界进行交遇的一种基本方式。由此入手,对旅游体验及其内涵的理解也就进入了一种新的层面。在先前的分析中,Jafari等提出的“跳板”理论虽然接触到了这一点,但讨论并不深入,有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推进的可能。在此,Heidegger在分析人的存在状态时所提出的栖居与游戏观念,或可提供出一种很好的分析视角。
三 旅游、栖居与游戏
(一)游戏:终有一死之人与世界的交遇
“交遇”一说出自Heidegger,即人与世界打交道,“交遇”有沟通、通道之义。物与物的照面谈不上“交遇”,惟有在主观与客观世界遭遇,才称得上“交遇”。《存在与时间》一书中Heidegger将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称为“此在”,所谓“此在之存在”就是此在“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40]67-91。在此,之所以“复兴”这一观念,是因为此前对体验与真实性话题的讨论已将研究的要点从“体验是否是旅游的本质”这一命题导向了对旅游本质或其存在方式与意义的思考。作为以上问题的延伸,我们并不打算从“体验-真实性”的角度对游客体验与现代性的关系重做一番申述,或是对旅游体验的对象或其价值进行一番“游憩式”的考量。既然旅游体验被界定为异地经历的一种[41],那么在对旅游本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即只有一个,即:“体验”如何在异地的经验中取得“栖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向我们阐明:根据栖居的本质来看,旅游是什么。
“场”的概念来自于格式塔心理学,由谢彦君在《旅游体验的情境模型:旅游场》中提出[42],其性质相当于MacCannell的“旅游情境中的舞台设置”一词。所谓“场”或“设置”,是指体验赖以存在的方式,即空间。如果说是非惯常环境的存在为旅游体验的实现提供了某种边界,那么毋宁说是旅游世界的出现为栖居世界的出现让渡出了某个位置,通过这个特殊的位置时间与空间被聚集起来。例如一座桥,它“轻松而有力地”飞架于河流之上,在使河岸相互贯通的同时,也使得河岸得以作为河岸而出现;因为“桥”的存在,河岸与陆地被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河岸不再是作为坚固陆地无关紧要的边界线沿着河流伸展,而是与“桥”一道把后方河岸广阔的风景带向河流[43]147-150,152-153;此刻往来于两岸的“终有一死者”通过“桥”对诗意空间的让渡,以“诗性”为尺度,栖居于天、地、神、人的聚集当中。这类聚集,因为天(Himmel)、地(Erde)、神(Götter)、人(Mensch)四方的到场而形成一个自然封闭的阈限空间[44]18-19。虽然“游戏空间”一词在先前的研究中很少使用,但是从许多有关于旅游业的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45]。恰如龙江智等所说,“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的提法虽尚存争议,但较之一般世界“旅游空间”存在某些时空上的特异性,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46]。从根本上说,所谓旅游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对旅游体验及旅游本质问题的讨论在“体验场”或“现代性”的背景下其实具备了某种存在论上的意义。

图1.诗意栖居与四方游戏
《宅经》有语云:“……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当居住成为人的一项基本任务的时候,对“诗意”的追求就成为了“人”在地上赖以存在的方式[43]147-150。说到“居住”,我们通常以为是一种行为,是人类在其他许多行为方式之外也在做的一种行为——我们在这里工作,然后在那里居住。然而,我们并不只是简单的居住着——这近乎无所事事;我们还从事各种活动——我们经商、我们旅行,在途中居住,一会在此地,一会儿在彼地。“此在”一词原始地即意味着“栖居”。所谓之“栖居”,他本源地隐藏着一种“游戏”的味道。
“游戏”(Spiel)一词在古希腊时期既已经有所体现,Plato甚至认为“生活应当像游戏一样过”[47]795。为休息故,人需要游戏[48]5-26。游戏,既是个体休息与消遣的方式,也是终有一死之人与世界交遇的方式。Kant讲,人的活动惟有两种:不是劳作(有目的的活动),就是游戏(无目的的活动)[49]144,游戏是生命的无目的[50]89。我们视生命的理想状态为游戏,除了它内在的自由外,至为重要的是,游戏的存在客观地要求有一种闭合式边界的存在,也就是先前分析所谈到的那个概念——“场”。“场”的存在为游戏的发生提供了某种客观环境,同时对游戏的发生提出了特定要求,它要求游戏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谁无视规则的存在,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一旦这些规则遭到破坏,由规则建构起的游戏世界的“场”就会崩溃[51]14-15。这意味着,游戏本身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对游戏的参与者们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那就是要严格的遵守游戏自身的规则。在此,严肃与自由,这对看似难以化开的矛盾,一同构成了游戏的一个特有属性。
以戏剧为例,演员手拿一个空酒杯,煞有介事地做饮酒动作,表示已经将酒喝了下去。这一程式化的动作表现得如此的真实,京剧票友没有谁会怀疑他的真实性,在观看中甚至觉得自己和演员一道感觉到烈酒穿肠。但是,不懂京剧的观众就会猜想,那杯中是否真的有烈酒。两种态度是如此不同,一个是以超然的真理来理解喝酒的事件,另一个是以对生活的认识来观看和思考喝酒的动作。后者也许会得到一种科学认知的快感,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入戏,没有进入到戏剧所呈现出的那个世界当中。相反,假如游戏者知道以“游戏”的态度去对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么艺术与实在间看似天成的界限就会消失。
艺术与生活间界限与距离的消失,这是否意味着游戏本身是以追求“愉悦”为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游戏的存在方式来说,一切游戏的存在或展开,都向游戏的参与者“强硬”地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在游戏中被游戏(Spielt ein Spiel)。谈及“游戏”,我们很少将它与严肃等词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这应归咎于游戏本身所呈现出的自由性。从游戏的生成条件来看,这样的自由却必须以一个事实为前提,即惟有游戏者全身心地投入游戏时,他才在进行真正的游戏。这样一来,游戏的目的也就消融在了游戏自身之中,游戏本身也因此获得了某种“玩的严肃性”。
游戏,似乎是人类生活的一项基本职能[52]24。Taine认为,一切严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游戏来表现,例如希腊人“他们以人生为游戏、以宗教与神明为游戏、以政治与国家为游戏、以哲学与真理为游戏……在与一切严肃事情的游戏中他们尽情的展现自己(Selbstdarstellung)”[53]270。Schiller甚至将Kant“游戏是内在目的的自由”的说法提升到了美育高度,他指出,游戏是一切美的表现形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54]89。至Heidegger那里,“游戏”甚至已经成为了“终有一死之人”追求本真存在的一种方式,他将天、地、神、人的四元游戏视同于诗意生活的理想范式,并借助Hölderlin的经典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的栖居”表现出来,认为有了诗人,才有真正的栖居;在重新去寻找诗意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栖居[55]160。也就是说,倘使我们要尝试对旅游事实及体验问题进行思考,那么对“游戏”精神的分析事实上已经将我们导向了对“场域”与“栖居”问题的思考。
Huizinga在《游戏的人 》一书中系统探讨了游戏的作用以及独特的游戏观,指出了游戏是第一位的,它是文化的摇篮,认为:“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出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须和物质的功利。”[56]11-12进而总结出游戏所具有的自由性、虚拟性、封闭性、权威性、审美性以及非功利性,而这和旅游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如果“游戏”是“终有一死之人”与世界交遇的一种终极方式,那么作为其实现形式之一旅游的行为,在发生基础上就注定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与其他体验相并列的体验形式。例如,戏剧。一出完整的戏剧总要求有多种情感的介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象Parthenon神庙迄今仍耸立于希腊这一事实便可以知晓。一旦卷入其中,Parthenon神庙就不只是一个在希腊存在的历史遗迹,而是作为一个神秘的宗教世界向“游戏者”敞开。游戏的特质在于向观赏者敞开一个世界,对此,Cohen无不犀利地指出,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旅游就是一场游戏[57]。当我们以游戏的方式来对待人生、对待生活时,一个广阔的栖居世界便向我们打开。
法国诗人Baudelaire曾给“现代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他说现代性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58]458。虽然,现代性一词在许多地方都在饱受争议,但就“旅游”这一事实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其价值。因为惟有在诡僪多变的现实压迫下,“栖居”的效力才会显现出来。人须要“游戏”,这一“此在”需求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的在世方式所决定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被抛的在世者”,人须要不断地与“世界”打交道,须要不断地在与天、地、神、人的游戏中唤回自己的本真存在。
旅游是什么?从人与存在的角度,我们或许正可以用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定义它:旅游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出来的,它为天、地、神、人四元的相互映射与游戏让渡出空间;同时对游戏的参与者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必须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游戏,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所具有的目的。
(二)游戏的层次与旅游的本质
如果说,旅游的介入只是将Heidegger“思诗同源”的高远引向了更为平实的日用生活的话,那么对游戏层次的旅游学区分在此就显得极为重要。
关于体验的内容或是层次,许多学者都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在理论上虽有所建树,但是解释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除个体差异的干扰外,很大程度上同旅游活动中游客体验的复杂性有极大关系。如Ryan等即将旅游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游憩活动,认为其中包含了学习、娱乐等多个成分[59]48-73。虽然在具体建构上还存在差异,但是旅游体验存在复杂性的说法却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至于“体验是否是旅游的本质”的问题,就旅游体验的复杂性一事来说,说游客在“消费”某项体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虽然某次经验中可能带有某个主观色调,但是真正织构出一次完整旅行经历的,却是多个体验类型的复合[60]。先前许多研究在分析中提出了“剧场隐喻”[61]这一说法,在此我们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旅游行为以“内在的自由”为目的的同时,还伴有愉悦、紧张等情感以及一些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虽然“体验”与“场域”是旅游研究的硬核,但是简单从体验的角度去反思或是探寻旅游的本质是没有结果的,我们需要去追问它的存在方式,并由此来反思旅游体验的层次。
在先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居住成为人的一项基本任务时,对诗意生活的追求内在地要求人必须游戏。“游戏”是“终有一死之人”在地上据以存在的方式;作为“诗意栖居”的一种特殊形式,旅游是在游戏中产生并作为游戏而生产出来的。游戏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作为栖居方式的游戏(spiel),由Heidegger的诗意栖居观发展而来,它的时间界限面向于人的存在以及整个生命历程;另一种“游戏”(play),主要是指闲暇时光,时间相对短暂,偏向于玩乐性。前者我们称之为大游戏,后者为小游戏。从这一视点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将“游戏”划分出如下层次(见图2),这些层次相应地也是我们理解旅游及体验层次的一种方式。

图2.大小游戏与旅游体验的获得
(1)习得(Study)。Plato指出,游戏最基本职能就是学习,一切幼子对生活能力的跳跃都是在游戏中实现的……在游戏中学习乃是人之天性[62]496-540。目前许多研究成果也已经证实,旅游活动带有极强的学习与教育成分[63]。将旅游视作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就体验的内容与效用来讲,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2)游戏(Play)。正如Cohen所说,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讲,旅游就是一场游戏[57]。Aristotle说,“闲暇”是德性发展的必需品,一个井然有序的城邦,公民必须学会如何正确使用它的闲暇时光[48]224。作为休憩方式的一种,游戏与愉悦在旅游事实中实际上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64]179。我们说到“游戏”,其实总带有一种戏谑性。产生戏谑的原因是,在意识深处,旅游者已经下意识地将旅游现实看作是一出布景[65],仪式下的布景是可以“掩盖真实”的,从舞台与真实性的视角出发,Play(游戏/戏剧)介于艺术与实际之间[66]38,无怪乎Boorstin等人要对大众旅游者的出行目的提出质疑了。进一步讲,作为栖居方式的“游戏”,如果被浅化为闲暇的“游戏”,那么旅游情境的持续舞台化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与在现世“诗意栖居”的本意是背离的。由此可以推想,在以追求愉悦等为目的的体验行为之上,想必还有更高的境界。
(3)对话(Communication)。这是由习得与游戏(Play)进一步的上行,“游戏”(Spiel)的结果所进入的第一重境界是对话。真实性问题的研究表明,一切形式的游戏,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同内外世界的交流中与“自己”取得联系[67]。这里暗示了一种条件,那就是“我”与“你”的区分。所谓“边界”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对“我”与“你”的叙事中产生的。所谓存在(Sind),不过是“你是”、“我是”的一个叙述方式。这种方式内在地要求“人”必须对话。在对话中,人存在。对话需要的存在合理地揭示了“位于游戏前台的游客为何总是试图向后台渗透”[68]的行为倾向。
(4)焦虑(Anxiety)。对现实的焦虑,是旅游者选择出行的一个重要原因[69]。这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中已经得到证实。在哲学分析中,Heidegger讲,焦虑乃是人最本真的存在[40]181-230。因为会焦虑,所以人存在。作为游戏(Spiel)方式之一的旅游,看似已经将这份焦虑给消弭了,然而实际上他只是被隐藏了起来。或者说,那种对自我存在的焦虑被推向一种更为精深的层面。这里包藏有两种境况。一是游戏(Play)对于焦虑的遮蔽。当游戏以愉悦为目的时,由游戏而敞开的游戏空间被闭锁为某个布景。这种闭锁,一方面诱致了游戏空间的异化,一方面则是迫使游戏空间与现实世界出现断裂,焦虑被这个断裂的空间暂时性的掩盖起来,但其实并未消失。为消弭焦虑与掩蔽之间的矛盾,他们因此需要不断地去游戏。二是对话的存在将对自我存在的焦虑推向了一种更为精深的表达。因为布景的存在,体验者对前台产生了怀疑。这份怀疑,一方面驱使着他们不断地尝试深入后台,一方面又将这份担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对“我”与“你”的存在差异将被消弭的担忧。虽然对话的目的是意图对存在的焦虑给予彻底的解决,但是游戏的结果却将对诗意生活的追求推向了表达的对立面。
综上所述,如果说对话前的游戏是试图将最普遍意义上的焦虑掩盖的话,那么游戏之后的对话则是试图在放大这种焦虑。这份在焦虑与现实间的遮蔽与放大,看似一组不可化开矛盾,却恰好构成旅游现象的一个特异属性。由焦虑而起,又归于焦虑,在这种循环往复中,无论是游戏还是对话,其实都在朝着Heidegger所提出的“在劳绩中诗意栖居”的目标迈进。而这恰是旅游活动存在的意义所在。所谓之旅游体验,它在本质上是以游戏(Spiel)的方式呈现的[15],但其结果却并不止步于对于愉悦的追求。研究者们需要看到,来自于存在的焦虑,虽然可以被单次的旅游活动所掩抑,但它并未因此而消失。隐藏在体验深处的焦虑,促使人们需要通过反复的出游以缓解存在的焦虑带来的压力。焦虑的缓解,带来焦虑的累积,这是旅游体验与旅游本质之间潜藏的一种内在逻辑。在已有的分析中,研究者对体验问题的探讨却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四 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现代性体验的反思,研究者们在异地经验中发现了旅游体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补偿效用,同时也从“周期性的逃逸”中剥解出旅游者需要反复出游这一学术现象。然而局限于旅游体验与愉悦等感受建立起直接联系的前在设定,虽然揭示了通过旅游体验可能产生的直接效果,但却对“被治愈后的旅游者为何仍会出现重复的出游”这一议题缺乏解释的深度。就文本上看,旅游体验对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消弭作用,这是支撑旅游体验得以论证的关键环节。旅游产生愉悦,在已有讨论中,研究者们极少对此产生质疑。然而,从Heidegger栖居观的角度来看,将旅游体验等同于对愉悦的追求这一提法,其实并不恰当。解析旅游体验与旅游本质之间的关系,需从人的存在方式入手。本文以杨振之等在2017年提出的“游戏说”为核心,对旅游体验的层次等进行了反思。主要结论包括如下三点。
1.旅游体验与旅游本质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体验是否是旅游的本质”这一提问在开始就出现了些许的偏差。若缘此路径追问下去,得到的结论是对“旅游的本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回答。这是一个二元问题,由对旅游体验的阐释及对旅游本质问题的追索两部分构成。研究者们若纠结于此,对旅游现象的认识将始终处在争执当中。
2.通过对“场”这一概念的解析,引入了Heidegger的栖居思想,并从习得(Study)、游戏(Play)、对话(Communication)、焦虑(Anxiety)等4个层次对旅游体验的层次性进行了描述。分析指出,旅游体验是以游戏(Spiel)的方式呈现的,但其结果并不止步于对愉悦的追求。研究者们需要看到,对焦虑的对抗是旅游体验产生的一个动力因素。作为游戏(Spiel)方式的一种,旅游体验看似已经将这份焦虑给消弭了,但实际上仅是将之隐藏。闭锁的旅游情景将游戏空间外化为某种布景,这种天成体验结构使得被暂时遮蔽的焦虑在“游戏”之后被再次放大,迫使旅游者需要通过重复的出游以缓解此种焦虑。掩蔽与放大,这组看似争执的矛盾不断循环和往复,看似冲突,实则构成了旅游活动作为游戏(Spiel)的一种可靠性,旅游的本质也由此产生。
3.此外研究者们需要看到,作为存在方式的游戏(Spiel)实际上是游戏性(playfulness)与严肃性(seriousense)的综合体[15]。谁不认真的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51]。这一特征决定了旅游体验的空间约束性,同龙江智等谈到的“心境的跨越”[46]有着相通性。就外延上看,旅游情境的存在对所有游戏的参与者都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要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一切,方才能够进入游戏的世界。结合前人对旅游体验与愉悦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游戏性与严肃性之间的互属与交融,恰好形成了旅游体验世界的一个殊异性。在此属性的支配下,旅游情境呈现出一种向外封闭而又向内展开的游戏结构,该结构导致了焦虑的遮蔽与放大。研究者们对旅游体验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对此议题的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将对焦虑的分析进一步纳入到对旅游体验的研讨中,或将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积累。
(二)启示与展望
1.本文将对焦虑的思考引入到对旅游体验的分析中,这是对既有研究在解释旅游者的“周期性逃逸”时未能提供有效的分析证据的一种补充。已有讨论虽然注意到了旅游体验对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消弭作用,但未深究产生焦虑的社会源流,因此在解释旅游需求的重复性上仍缺乏一定的逻辑证据。本文从存在论的角度引入Heidegger对于焦虑的观察,用以解释旅游需求的重复性。这部分分析是基于哲学观念的,此处所谈及的焦虑,与心理学上所讲述的焦虑感,是有一定差异的。虽然二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但哲学分析中所阐释的焦虑是来自于哲学存在论的,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与心理学上所讲述的焦虑感并不能完全等同。研究者们如果寄望在此方向上有所推进,需要将情绪体验与现象学中的涉身性(embodiment)结合起来,从情绪变化的角度去深入理解旅游体验给人生经历带来的改变。研究者们需要看到,对旅游本质问题的理解不能仅从旅游体验质量的角度去做片面分析,需要将旅游体验产生的效果放置到旅游活动的发生背景中去理解旅游的本质。在此过程中,不应忽视“周期性的逃逸”这一潜在指标对理解旅游体验和旅游本质问题的先天约束。本文虽然从对焦虑的观察中发现了“遮蔽—放大”对旅游本质的支配性,但对相关概念的阐释仍缺乏一定的技术性定义。如何将哲学问题化解为实际的旅游学问题,这是研究们需要继续去探索的。虽然哲学上的焦虑与痛苦等负面情绪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不能因此而片面地认为旅游活动就发生在“痛苦—快乐”的线性转换间。如前文所述,旅游现象具有“暂时性”的内在约束,这一约束是否是推动“周期性逃逸”的内在原因?这一点需要结合旅游的本质及对旅游体验内涵的阐释进行综合解释。在此问题上,情绪体验与现象学中的涉身性应该能提供很好的解释路径。作为方法辅助,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70]11-15和随行纪实法(go-along)[71]表现出了很好的应用潜力。
2.本文在分析中引入了哲学概念上的游戏(Spiel)理念。并在对栖居概念的理解中,将旅游体验理解为习得、游戏、对话、焦虑等4个层次。除概念的指向带有显著的哲学性外,这些讨论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具有显著的衔接性。本文的分析打破了旧有传统讨论将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放置在“真实性”与“现代性”下的写作思路,创新性地提出了“游戏—焦虑”的对抗观念。讨论虽然揭示了游戏与焦虑在推动旅游者重复出游上的动力学机制,但对旅游体验本身的深入分析仍显匮乏。如何将旅游者带入游戏?这是未来研究将持续推进的地方。这里潜藏着三个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其一,旅游者是如何进入游戏的?其二,为什么特定的游戏需求总是出现在特定的游客群?其三,既然焦虑无可避免,那么如何打通现实世界与旅游世界之间的隔阂,从而使得现实中的每个场地都具有游戏的意义?传统分析虽然注意到旅游活动对旅游者人生的增益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增益并非持久性的,它在旅游活动结束之后会不断地接受耗损,耗损的结果是使先前被遮蔽的来自于存在论的焦虑再次凸显出来,本文称之为掩蔽之后的放大。结论虽不完全可靠,但研究者们在此需要看到,旅游体验对人生的增益作用并非是一劳永逸的。这是观测旅游本质的另一视角,在传统分析中该观念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作为研究的展望,研究者们或许需要进一步思考:除增益外,出去旅游究竟给旅游者的人生带来了哪些负面的影响?这些正负向的影响如何对旅游者的人生以及对旅游意向本身等产生影响?以上分析或将成为未来旅游体验研究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