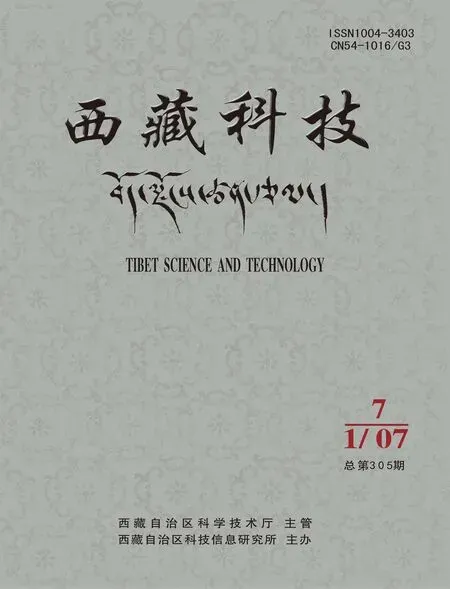民族地区公共品供给与减贫成效研究*
张建伟 杨阿维
(1.西藏大学科研处;2.西藏大学财经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民族地区是指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3个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顶层设计、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方面的倾斜力度,使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成效显著。2016年,中央财政投入民族八省区的专项资金达279.6亿元,占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量的41.9%,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总数从2015年底的1813万下降到2016年的1411万,下降了22.17%,402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虽然民族八省区在脱贫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民族八省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依然滞后。因此,关注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率,让贫困农民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对贫困农民增收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民族八省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监测数据,对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品进行描述性分析,试图为精准扶贫中公共品供给政策的完善积累实践证据。[2]
1 民族地区公共品供给分析
1.1 民族地区生活性公共品供给分析
生活性公共品是指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的公共品,如住房、饮水、炊用能源、照明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品。
从表1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生活性公共品供给有较大差异。①在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方面,内蒙古、宁夏、新疆三省份占比较高,超过了12%,分别为19.4%、13.4%、16.3%;其次是云南和青海,在3-6%之间,分别为5.5%和4.3%;占比最小的是广西、贵州、西藏,在0.5-3%之间,分别为1.2%、0.9%、2.5%;说明内蒙古、宁夏、新疆贫困地区住房条件较差,仍然有超过12%的农户存在住房贫困,没有得到较好的住房安置。②使用照明电的农户比重方面,各个民族地区相差不大,最高为99.9%,分别是内蒙古、广西,最低是西藏自治区,为93.8%,表明西藏仍有6.2%的农户没有使用照明电。③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方面,各民族地区差异较大,超过80%的有三个省区,分别是广西、青海、新疆,为82.3%、80.1%、84.7%;而内蒙古最低,只有39.2%,其次是西藏50.0%,表明内蒙和西藏管道供水能力较弱。④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方面,各省区占比都不太高,最高的是新疆,也只有79.4%;西藏和云南不足30%,分别为28.3%、25.5%;表明西藏和云南农户大部分直接饮用天然水,没有经过净化和处理。⑤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方面,内蒙古、宁夏、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相对较高,分别为91.6%、89.5%、87.3%、81.4%、84.9%、83.1%;云南和西藏较低,分别为75.1%和65.8%,表明云南和西藏农户饮水仍然严峻。⑥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方面除了云南和西藏占比较低,分别为81.0%和71.5%,其余地区占比较高,在90.0%以上,表明云南和西藏地区农户厕所普及率低,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使用露天排便。⑦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方面,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新疆仍有超过50.0%的农户使用柴草,宁夏、贵州、青海地区使用柴草农户比重较小,在30.0%左右,表明农户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较低,应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表1 2015年民族地区生活性公共品供给状况 单位:%
1.2 民族地区生产性公共品供给分析
生产性公共品是指与居民从事生产需要的道路、出行、通电、信息等公共品。
从表2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生产性公共品供给状况各地区呈现出较大差异,通电的自然村比重和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两个方面比重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
从具体各个方面来看,①通电的自然村比重方面,整体比重都较小,不足20%,占比在10.0-20.0%之间的有3个,分别为内蒙古(19.4%)、宁夏(13.4%)和新疆(16.3%);其余5个省区不足6.0%,分别为广西(1.2%)、贵州(0.9%)、云南(5.5%)、青海(4.3%)、西藏(2.5%)。②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方面,占比很高,均在90.0%以上,最高的与最低的省区相差只有6.1%。③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方面,除内蒙古(39.2%)和西藏外(50.0%),其余省区网络普及率相对较高,占比在60.0%以上,有的省份达到80.0%以上。④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方面,各省区差异较大,只有新疆达到79.4%,其余地区都在50.0%左右,有的省区不到30.0%,分别为内蒙古(32.5%)、宁夏(50.7%)、广西(37.7%)、贵州(34.5%)、云南(28.3)、青海(54.7%)、西藏(25.5%)。⑤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方面,占比在90.0%以上的有1个,为内蒙古(91.6%);80.0-90.0%之间的有5个,分别为宁夏(89.5%)、广西(87.3%)、贵州(81.4%)、青海(84.9%)、新疆(83.1%);60.0-80.0%之间的有2个,分别为云南(75.1%)和西藏(65.8%)。

表2 2015年民族地区生产性公共品供给状况 单位:%
1.3 民族地区服务性公共品供给分析
服务性公共品是指与居民社会发展服务需要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
从表3可以看出,民族地区服务性公共品供给除有合法行医证医生、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较高外,其余有卫生室的行政村比重、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方面供给较低,且区域性差异较大。
从具体各个方面来看,①有卫生室的行政村比重方面,各省区均不足20.0%;②有合法行医证医生、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方面,各省区比重较高,达到90.0%以上;③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方面,各省区差异较大,占比在50.0%以下的有两个,分别为内蒙古(39.2%)和西藏(5.0%)。占比在60.0-80.0%之间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宁夏(66.9%)、贵州(73.7%)和云南(72.3%);占比在80.0%以上的有3个,分别为广西(82.3%)、青海(80.1%)和新疆(84.7%);④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方面,整体呈现低水平状况,且各省区差异不是很大,最高的为新疆(79.4%),最低的为西藏(25.5%)。

表3 2015年民族地区服务性公共品供给状况 单位:%
2 民族地区减贫成效分析
2.1 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规模
从表4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和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总体呈现减少趋势,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2011年3917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1813万人,减少了2104万人,减贫率为53.17%,年均减少526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29%;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2011年的12238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了6663万人,减贫率为54.45%,年均减少1665.7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61%.
从时间维度来看,2011-2015年各省区农村贫困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内蒙古从2011年的160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76万人,减少了84万人,减贫率为52.5%,年均减少了21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13%.宁夏从2011年的77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37万人,减少了40万人,减贫率为51.95%,年均减少了10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2.99%.广西从2011年的950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52万人,减少了498万人,减贫率为52.42%,年均减少了124.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11%.贵州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507万人,减少了642万人,减贫率为55.87%,年均减少了160.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97%.云南从2011年的1014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71万人,减少了543万人,减贫率为53.55%,年均减少了135.7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39%.青海从2011年的108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2万人,减少了66万人,减贫率为61.11%,年均减少了16.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5.28%.西藏从2011年的106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8万人,减少了58万人,减贫率为54.72%,年均减少了14.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3.68%.新疆从2011年的353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180万人,减少了173万人,减贫率为49.01%,年均减少了53.25万人,年均减贫率为12.25%.
从空间维度来看,2015年各民族省区贫困人口规模差异较大,各民族省区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分别为内蒙古76万人、宁夏37万人、广西452万人、贵州507万人、云南471万人、青海42万人、西藏48万人、新疆180万人,分别占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规模的4.19%、2.04%、24.93%、27.96%、25.98%、2.32%、2.65%和9.93%.

表4 2011-2015年全国及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规模 单位:万人,%
2.2 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
从表5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26.5%下降到2015年的12.1%,下降了14.4%;全国农村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12.7%下降到2015年的5.7%,下降了7.0%,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
从时间维度来看,2011-2015年各省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内蒙古从2011年的12.2%下降到2015年的5.6%,下降了6.6%.宁夏从2011年的18.3%下降到2015年的8.9%,下降了9.4%.广西从2011年的22.6%下降到2015年的10.5%,下降了12.1%.贵州从2011年的33.4%下降到2015年的14.7%,下降了18.7%.云南从2011年的27.3%下降到2015年的12.7%,下降了14.6%.青海从2011年的28.5%下降到2015年的10.9%,下降了17.6%.西藏从2011年的43.9%下降到2015年的18.6%,下降了25.3%.新疆从2011年的32.9%下降到2015年的15.8%,下降了17.1%.
从空间维度来看,从空间维度来看,2015年各民族省区贫困人口发生率差异较大,内蒙古、宁夏、广西、青海贫困发生率低于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分别为5.6%、8.9%、10.5%、10.9%.贵州、云南、西藏、新疆贫困发生率高于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4.7%、12.7%、18.6%、15.8%.除内蒙古低于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外,其余七省份贫困发生率都高于全国。

表5 2011-2015年全国及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 单位:%
2.3 民族地区贫困人均收入
从时间维度来看,从2011-2015年民族地区各省区人均收入总体呈现增长趋势,高于全国贫困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内蒙古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6642元增长到2015年的8201元,增长了1559元,增长率23.47%.宁夏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5410元增长到2015年的7255元,增长了1845元,增长率34.10%.广西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5231元增长到2015年的7927元,增长了2696元,增长率为51.54%.贵州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4145元增长到2015年的7171元,增长了3026元,增长率为73.00%.云南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4722元增长到2015年的7070元,增长了2348元,增长率为49.72%.青海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4608元增长到2015年的7933元,增长了3325元,增长率为72.16%.西藏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4904元增长到2015年的8244元,增长了3340元,增长率为68.11%.新疆从农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5442元增长到2015年的7341元,增长了1899元,增长率为34.90%.增长幅度较大的是贵州和西藏,“十二五”期间,贵州加大扶贫力度,西藏在中央和全国对口支援的大力支持下,脱贫成效显著。
从空间维度来看,从空间维度来看,2015年民族各省区农村收入差异不大,超过8000元的省份有两个,分别为内蒙古(8201元)和西藏(8244元)。7000-8000元有六个省份,分别为宁夏(7255元)、广西(7927元)、贵州(7171元)、云南(7070元)、青海(7933元)和新疆(7341元),民族各省区农村人均收入都高于全国(6948元)。

表6 2011-2015年全国及民族地区农村人均收入 单位:%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利用民族八省区的公共品监测数据,对民族八省区公共品及精准扶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①民族八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性差异较大,总体呈现供给不足的状况。②民族八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结构性差异。生活性公共品供给大于生产性和服务性公共品供给,政府公共品供给偏向于生活性和基本生产性方面,导致民族八省区贫困农村公共品供给扶贫效率低下。③民族八省区公共品供给内部结构性差异较大。生活性公共品供给方面,使用照明电的农户比重、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等方面供给大于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炊用非柴草的农户比重。生产性公共品供给方面,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较高,通电的自然村比重、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等方面较低。服务性公共品供给方面,有合法行医医生、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和有幼儿园或学前班的行政村比重较高,有卫生室的行政村比重和有小学且就学便利的行政村比重较低。
3.2 政策建议
当前受行政区域分割、政府部门本位主义、农村治理结构失衡、村民原子化和阶层分化等因素影响,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呈现碎片化困境,既偏离了公共品供给的政策目标,也制约了扶贫的精准性和实效性。[3]
3.2.1 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力度。无论是发达省份的农村,还是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都存在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不平衡的状况,也存在公共品内部结构性差异问题。因此,改善贫困人民的物质生活,就要加大对生活性公共品供给力度,提高贫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就要加大服务性和生产性公共品供给力度。[4]
3.2.2 优化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当前中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体系,由于贫困农民缺乏与政府有效沟通,在利益表达方面处于失语状态,导致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在落地中出现供需错位、贫困农民积极性不高、利益博弈等问题,不仅无法精准瞄准而且村庄之间甚至村庄内部也不能受益,不能有效实现精准惠民。[5]因此,建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完善贫困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实现政府与群众双方的有效沟通,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和公众参与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从而提高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和效率。[6]
3.2.3 加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区域协同公共品治理体系。民族地区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受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民族贫困地区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各自为政,对资源进行激励博弈,从而致使公共品呈现低效供给、重复供给和碎片化供给,没有充分发挥区域效应。因此,精准扶贫要求民族各省区加强跨区域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区域公共品协同供给,优化整合各民族地区区域资源,协同发展产业布局,构建民族地区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有效缓解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错位与不足、“碎片化”倾向和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7]
3.2.4 完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监督评价体系。由于民族贫困地区整体贫困治理体系不健全、贫困农民信息闭塞、缺乏群众参与的监督机制,以至于一些项目出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精英工程”,既浪费了贫困资源,不能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不能真正发挥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8]因此,完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等方面的监督评价体系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