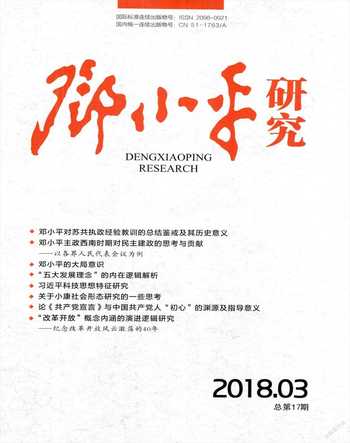万里与凤阳大包干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凤阳县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凤阳大包干”的成功实行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的启迪、应允、支持分不开。时任中共凤阳县委办公室秘书的陈怀仁同志对万里五次来凤阳调研现场记录进行整理,于1980年5月撰写此文。2018年是纪念中国农村改革40周年、万里同志诞辰102周年,陈怀仁同志特对此文稍做修改。本刊一并刊登,以飨读者。
[关键词]万里;凤阳大包干;农村改革
[中图分类号]A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117-18
万里同志对风阳人民十分关心,他在安徽工作期间,曾五次来凤阳视察,特别是从1978年至1980年的四次来风阳,正值凤阳县遭受百年不遇大旱和艰难推行农业“大包干”时期。他每一次来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解决最关键性的问题。“凤阳大包干”的由来与发展,大致历经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与万里同志的启迪、应允、支持分不开。
一、“大包干”的启蒙与前奏
这一阶段,万里同志两次来凤阳。
1978年7月19日下午,万里同志来凤阳时,凤阳正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全县塘坝干涸,小河断流,山区和高岗地区大部分井底干枯,人无水吃,畜无水饮,大片庄稼被干死。万里同志听县委书记陈庭元,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吉诏宏汇报这些情况后,亲自到农村检查灾情,重点检查了霸王城、门台子电灌站和临淮关轮渡码头。他发现电机太老,耗能大,效率低,指示县委抓紧时间更新。之后,万里亲自过问拨给凤阳县无偿抗旱经费110多万元,从北京市平谷县调来70多人的打井队,帮助凤阳县打机井123眼、砖井500多眼;还从部队调集100多辆汽车拉水供应灾区,共解决10000多户农民吃水和22000多头牲畜饮水问题,并解决一部分地区抗旱救苗用水,大大地缓解了凤阳县受旱灾情。从此,凤阳最穷的印象已在万里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从而也萌生了他对改变风阳贫穷落后面貌的思考。
同年9月11日,万里同志再一次来凤阳视察灾情,在凤阳召开定远、凤阳、嘉山三县负责人会议,他再三叮嘱大家,要千方百计解决灾区农民饮水、吃粮和烧柴问题,以保证他们在那里安心居住下去。会上,根据陈庭元、吉诏宏的汇报,供应凤阳县农村救灾粮8000万斤(实际用掉6953万斤),救灾款391.7万元,救灾煤600吨,还指示县委给重灾区社员从集体耕地中增划一部分菜地,借一些小粮地、饲料地(每人半亩、每头老母猪半亩),让农民自由种植度荒。这些都为凤阳县人畜安全过冬,及时投入1979年春耕生产提供了物质保证。
1978年初春,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安徽“省委六条”启示下,马湖公社书记詹绍舟顺应社员的强烈要求,在他蹲点的大队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费用包干,统一分配。每一百斤产量的打分标准是:鲜山芋10分,小麦60分,水稻60分,黄豆70分,杂豆80分,高粱50分,玉米50分,花生50分,油菜籽150分,芝麻200分,烤烟(每斤均价伍角)300分。规定全队统一做场,分组收打,粮食统一过称人仓,各组抽人保管。生产队以各组实交产量多少、孬好给计工分。分红时,各组凭工分从队里分回实物,再按工分分给社员。
他们这种做法虽然条条框框还很多,但是,有了“联产计酬”这一条就大大地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大旱之年,全县农业大幅度减产,唯有他们实行“联产计酬”的8个生产队没有减产。县委对他们这一做法采取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三不”态度,密切观察,多次去了解情况,帮助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与此同时,梨园、江山、总铺、黄泥铺、官沟、宋集等公社的部分生产队,也都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分组作业责任制。
万里同志的“借地种菜”和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为凤阳县农民敢于撼动20多年来土地公有制的神圣化模式、实行“大包干”开启了思路,鸣起了前奏。
二、“大包干”的诞生与稳定
这一阶段,万里同志多次接见凤阳县负责人,并于1979年6月5日亲自到凤阳了解“大包干”的情况,支持“大包干”的做法。
由于1978年马湖公社突破了不准“联产计酬”的禁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秋种时,这种办法已向全县“扩散”,有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还提出包产到组,为此,县委常委多次开会讨论,并向省、地委请示汇报。
1979年元月3日,在省委扩大会议期间,万里同志召开定(定远)、凤(凤阳)、嘉(嘉山)、宣(宣城)、郎(郎溪)、广(广德)等穷县负责人座谈会,陈庭元、吉诏宏二同志汇报了凤阳县马湖公社“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及群众要求包产到组的意见。万里同志说:“‘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可以搞,鼓励你们搞。”在元月21日的縣委常委会上,陈庭元、吉诏宏传达了万里同志的指示,经讨论决议:(1)抓紧时间推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2)包产到组是民意,人心所向,肯定能增产,积极向上级要求干。县委在元月22日的区、社书记会议上宣布这个决定以后,春节期间全县各地都在忙于分组、量地、定措施,有的队已在暗暗地包产到组。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正确引导搞好生产责任制,县委于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召开了7天的(区、社、大队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会上,认真传达贯彻省委元月份的扩大会议精神,请有关社队介绍经验,发动大家讨论凤阳县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责任制。发言介绍的有: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宋集公社的“三组(长年组、临时组、专业组)”、“四定(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责任制;城南公社齐涧大队的“分组作业,定额包工(长年包工、季节包工、小段包工、按件包工,比照同等劳力包工)”责任制;总铺公社小石塘生产队的“分组劳动,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责任制。还有的讨论了1962年的“责任田”和“五统一”办法。在分组讨论时,大家把各种做法加以比较,有的说:“一组四定”定不住;“定额包工”包不好;“全奖全赔”奖不着,赔不起;“五统一”统不起来;马湖公社“联产计酬”效果好是好,就是太繁琐,不容易搞。梨园公社石马大队书记金文昌说,他们这些经验只是在大会上介绍得好听,实践中不好干,都不如我们大队小贾生产队实行小组包干简单。有的同志说,政府不就是想多要一点粮食么?干脆来个“大包干”,该给国家的我们交齐,该给集体的你提留去,剩下的你不要管,由社员自己分配。在讨论情况汇报会上,多数区委书记都反映下面要求搞“大包干”。县委认为,分组包干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是关系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问题,不敢擅自决定。正准备向省、地委请示汇报时,恰巧,地委书记王郁昭于2月15日下午赴合肥开会路过凤阳。晚上,陈庭元、吉诏宏在招待所向他汇报群众要求“大包干”的意见,王郁昭同志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到省里向万里书记汇报。
王郁昭2月17日上午回到滁县,下午和18日上午召开县委书记和农办主任会议,传达省里会议精神。凤阳县陈庭元、周文德参加会议回来后,在19日的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王郁昭传达的省委16日会议精神。陈庭元传达说,王郁昭同志说,昨天他向万里书记汇报了凤阳要求搞“大包干”的意见,万里书记说可以搞。散会时,我又问:王书记,万里书记讲“大包干”可以搞,我们回去就在四干会上宣布叫干了?王郁昭说,你们就干吧,万里书记说:“‘大包干可以先搞实验,个别包到户也可以实验。”这个精神传达后,凤阳县委常委讨论决议:“当前全县采取三种形式生产责任制:一、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好一组四定;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三、‘大包干。单干问题不在大会上讲。”2月20日上午,陈庭元在县委农村工作会议总结大会上说:“万里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我们,一切办法都是为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为了多收粮食。能多收粮食,把群众的生活搞好,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好的政治,否则就是坏政治。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和县委常委讨论的意见,我县在群众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可采取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好一组四定、‘分组作业,联产计酬、‘大包干三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诞生的。“凤阳大包干”生日就是1979年2月20日。
1979年2月20日以后,在20多天时间内,全县有2500多个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的70. 8%。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具体政策跟不上,各地分组包干的办法不统一。为了总结经验,指导全县,3月上旬,县委农村政研室派吴庭美、刘洪学到农村调查研究。他们重点帮助岳林、甄岗、卫前、岗集等4个大队和岳北生产队讨论制定“大包干”的具体办法,形成《城南公社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调查》,在县委1979年3月13日的《情况反映》上印发全县各社队。同时,县委又于3月15日召开区、社书记会议,进一步分析形势,讨论制定“大包干”的具体政策。然而,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大标题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文章内容与改革开放精神相悖,不利于实行大包干。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的分量,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在这关键时刻,万里同志于3月16日来到滁县地区,他当天晚上叫随行人员张万舒给凤阳县委打电话。电话里传达了万里书记的指示:“让实践来检验,‘大包干只要能增产,不仅今年干,明年还要干。”3月17日上午,县委召开常委会义,传达万里同志的指示,又进行了人人表态式的讨论,一致通过决议:“继续稳定、发展‘大包干,如果今后有问题,由县委集体承担。”下午,陈庭元在区、社书记会议上宣布这个决议,从此人心才稳定下来。
由于风阳实行“大包干”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万里同志的表态支持,他对“大包干”这个新生事物高度重视,所以这次来,对“大包干”的做法询问得非常仔细。当陈庭元汇报到干部群众反映“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时,万里同志高兴地站起来、笑起来,说:“那好啊!能吃陈粮烧陈草,我就批准他们干三五年。这样干,功效提高了,剩余的劳力只要不是赌博、不是干坏事,他们去搞家庭副业,搞自留地,搞生财之道的,我都赞成。对家庭副业不要干涉,哪怕他干一万元也可以。”陈庭元又汇报说:“目前干部怕错、社员怕变的思想还很严重。”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搞好生产,社员能不能富起来。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多一级核算照样是社会主义。”“你们要搞三年‘大包干,我就同意你们搞三年。不过现在不推广,搞三年看,能搞好,我再推广你们的经验。”“……三年能不能把凤阳花鼓(讨饭碗)丢掉?要甩到太平洋里去。”“要往致富上想,中国就是富慢了,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富得越快越好。”万里同志这些重要指示,对我们既是支持和鼓励,又是鞭策和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都为我们的“大包干”得到万里同志当面表态支持而欢欣鼓舞。
6月25日,万里同志派省农委主任周日礼等三人来凤阳调查研究,帮助总结指导工作。他们在盛夏季节,冒着酷暑高温与县委负责同志及田广顺、周义贵、陈怀仁、吴庭美、刘洪学、丁永鑫一道,深入到马湖、东方红、总铺、黄泥铺、江山等十几个公社,了解干部,走访群众,研究实行“大包干”的具体政策,探讨“大包干”的理论依据,寻求“大包干”的发展前途。在此期间,滁县地委政研室陆子修和陈修义也来帮助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省、地委有关同志的帮助下,凤阳县实行“大包干”的政策逐步走上条理化和理论化。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周日礼的署名文章《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从此,“凤阳大包干”名声大震。霎时间,新闻界、文艺界、理论界的记者、作家、学者云集凤阳,中外参观、访问人士络绎不绝。通过他们的宣传,“大包干”兴然时髦,凤阳大地呈现在一派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之中,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心潮澎湃,欢欣雀跃,陶醉在幸福之中。时任江山公社书记陈本田说:“以前看江山一片荒凉,来江山恼闷愁肠,年年都吃回销粮,公社书记干不长;今年实行大包干,粮食产量成倍翻,干部满意,群众喜欢。”城北公社姚湾大队一位70多岁的姚老先生对“大包干”赞叹不已,比古论今地说:“大清朝顺治皇帝不理政事,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康熙皇帝施行裕民政策,当时出现了麦秀双穗,马过双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十人九歌,龙颜大喜的盛世。我们今年像康熙年间一样,也是麦秀双穗,马过双驹,十人九歌,皆大欢喜。”考城公社社员姚登祥、姚登凤两家用大条石雕刻“鸟枪换炮,今非昔比”、“黄金时代,幸福之最”的大字镶砌在新盖瓦房大门额上,以此表示对“大包干”的颂扬,祝愿“大包干”永存。
三、“大包干”的完善与推广
1979年,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组成效显著,粮食总产最达44000万斤,比1978年的29500万斤增长49%,人均收入150元,比1978年的81元增长85%,一年甩掉了逃荒要饭的帽子。但是,“大包干”到组还是小集体生产,新矛盾还不断出现,实践证明,它不如“大包干”到户更简单。
在全县推行“大包干”到组的同时,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已经暗暗地包干到户了。经过是这样的:小岗队起初分成4个组,干不多久,组里产生新矛盾,每组又“发叉”,全队分成8个小组。没干几天,又有吵嘴打架的,还是干不好。一天晚上,生产队开社员大会解决矛盾,到深夜也没解决好。有的社员说,这样干不好了,干脆分到户里干。生产队长说,如果大家能答应两个条件,我们就同意分到户干。第一,午秋二季(当地方言,指夏秋两季)每户收打的头场粮食,就要把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准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不准对上级和外队人讲,谁讲谁不是人。有位老农说,还要再加个第三条,今后,如果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队长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养到18岁。大家异口同音地答应,诅咒发誓按这三条办。于是,连夜抓阉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全部分好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之后公社知道了,叫他们还并到组里干,不并就不给种子、化肥、耕牛贷款。
1979年4月10日,县委书记陈庭元去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公社书记张明楼最后唯唯诺诺地汇报了小岗队群众自发分田包干到户的事,陈庭元吃惊地问:“怎么能让他分到户呢,你们公社没过问么?”张明楼说:“我们也是才知道的,已经派人去制止了。”陈庭元离开公社一里多路后,叫车子开回头,亲自到小岗队了解情况,并于4月15日又去梨园公社。张明楼汇报说:“陈书记,遵照您的指示,公社派几位得力干部去小岗队做工作,动员他们并到组里干;并采取措施,把全队的种子、化肥、耕牛贷款都扣在公社,等他们并组后再发。”陈庭元和张明楼一道到小岗队挨门挨户地走访社员后,用商量的口气说:“老张啦,他们的庄稼已经分到户里安种了,投入有多有少,再并起来分红时不好算账,就让他们干到秋再说吧。”陈庭元的话让张明楼感到突然,说:“陈书记,您上次的意思是不准分到户干,这几天,外公社也有人知道了,说我们梨园公社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2000多个队,就算他这一个队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最多多收一点粮食吃。”张明楼很犯难地说:“陈书记,我也知道社员这样干能干好,但是以后要犯错误怎么办?”陈庭元沉思着说:“要有错误我们县里承担,不要你公社负责。”张明楼手一伸说:“那行,那您写个条给我。”陈庭元板着脸说:“这样的事只能干,哪能写条子呢。”张明楼说:“我的书记,如果将来出问题,您调走了,我到哪去找您?”陈庭元无奈,坐上吉普车一路上一语没吭回到县里。次日上午,陈庭元又到梨园公社,他带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田广顺、县委农村政研室主任周义贵、板桥区委(辖梨园公社)书记林兴甫一同前往,请他们共同作证,如果小岗队包干到户犯错误由县里承担。就这样,小岗队的包干到户幸存下来了。由于包干到户利益更直接,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优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这个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人均收入400多元,是1978年的7倍。他们在1978年前的23年合作化中,从未向国家贡献过一斤粮食,1979年包干到户第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万斤、油料2万多斤。这个队的群众说:大呼隆干了20多年,什么“绝招”都用过了,就是治不好我们队的“穷病”,还是包干到户灵验,一剂“药”就治好了。
一举成名众人知。1979年,小岗队包干到户一年取得的显著成果,对周围群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秋种时,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都在悄悄地学小岗,往包干到户上“滑”。然而,当时“不许分田单干”的“紧箍咒”还未取消,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又多次去劝说小岗队社员拢到组里干。群众已经尝到了包干到户的甜头,说什么也不愿再拢起来,多次找县领导说情。
12月中旬,县委农村政研室派吴庭美去小岗队作调查,写了题为《-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小岗队包干到户一年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旗帜鲜明地支持小岗队群众要求继续包干到户的意见。陈庭元把调查报告送给万里看,万里看后赞赏说,这个材料好,我就像看小说一样,一口气把它看完了。他指示小岗队包干到户不要变。
1980年元月24日,万里同志为了眼见为实,在到中央任职之前来到小岗队视察。他挨门挨户地访谈后,看到每家每户大屯满小屯尖的粮食,高兴地说:“这下好了,社员可以随便吃饺子吃面条了,抗战时期群众家里要有这么多粮食,我们也不得挨饿了。”他坚定地指示说:“只要能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社员能够改善生活,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一级领导再也不要给群众上‘紧箍咒了,他们还没住瓦房,还没盖高楼么,有什么可怕的。”他对群众说:“我批准你们干三年。”万里同志的指示,再一次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不仅小岗队的包干到户保住了,也能推广了。这时,“大包干”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完善和推广阶段。1980年下半年,凤阳县全面推行了包干到户的办法,由原来的“大包干”到组发展为“大包干”到户,统称“凤阳大包干”。从此结束了20多年吃“大锅饭”的历史,为全国农村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农村改革問题时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童大林在全国第二届人才研究学术讨论会上说:“‘大包干这项改革给凤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万里说:“‘大包干不仅解决了中国农民吃饭问题,也拯救了社会主义。”
“风阳大包干”是凤阳农民谱写出来的一曲壮丽的凯歌;是万里同志心系人民,与凤阳广大父老乡亲心心相印、尊重实践、勇于探索的结晶;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凤阳大包干”的形成,凝聚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就是“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尊重实践、勇于探索的求实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首创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它必将永远激励着凤阳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