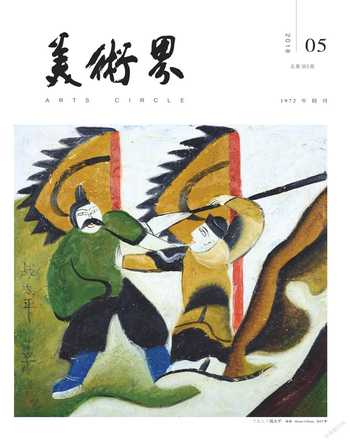城的门
羌人六
一
人生在世,就是过日子,把日子过好。日子背负着人间冷暖,片刻不停,黎明与末日,灿烂与黯然,都隐藏在生命之树的枝叶之中。一串串日子朝开阔处延伸,漫漫人生路的必经走廊,如同《西游记》中的取经之路,不乏风景、奇遇和鬼怪神灵。
德国作家赫塔·米勒说:“人生是一个长长的经过句。”我深以为然,很多时候,人这一生,就是麻烦和折腾。
在四季分明、群山环抱的断裂带老家,美满幸福的人生,不但意味着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同时也意味着拥有好的名声。
在断裂带,即便是像收废品的杨叔那样普通的人,也都是有名声的,名声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钥匙,也是一个人的交际指南,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也能在人和人之间产生裂隙,一个人名声不好,即便家财万贯,也只会让人退避三舍,躲瘟神一般。一个人的名声可以比风、博尔特和闪电跑得更快。
名声,即是一个人的面子,一个人的另一张脸。没人可以靠自己的面子活着,但活着的人,需要面子。面子并非虚荣,却也经常充当虚荣的替身。含蓄、朴素的家乡人眼底,如果他人谋事欠妥,或给人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当事人的脊梁骨,当事人的后脑勺,准会扣上“过场多”的名声。名声不好,人的面子也跟着变薄。
童年的时候,我就明白面子是争不来的,只能自己挣。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当过军人的父亲尤其爱面子,堪称典型。“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就是当年母亲对父亲的评价,为了面子,他给我们的贫寒之家制造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灾难”。
父亲“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例,经常被母亲当作反面教材,用来教育我和弟弟。母亲不知道的是,她的苦口婆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岁月的皮肤上为我勾勒出一点可爱的父亲形象来。如果没有这些形象,我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记忆中的父亲,我怀念着的父亲,总是和“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话挨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有回父亲的一个战友到我家来玩,见父亲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羡慕不已,不止羡慕,还主动喊父亲脱下来让他穿了会儿,战友临走的时候,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父亲毫不犹豫地把夹克脱下来送给了人家,大方的样子,好像人家穿在身上确实比自己更好看似的。父亲的战友如获至宝,高高兴兴穿着父亲的夹克走了。物质拮据的年代,勤俭的母亲哪里看得惯父亲如此败家,责备似拧开的水龙头,源源不断,毕竟,那件皮夹克花了家里不少钱。如同塞万提斯的光辉巨著《堂吉诃德》中古罗马政治家卡顿所言:“顺利之时朋友多,危难之时门冷落。”又过了好些年,父亲的那位战友已在县里当了不小的官,境况不佳的父亲同样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从未去找过他的战友,帮自己渡过难关。
贫苦的岁月并没有扭曲父亲的灵魂。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话的后面,隐藏着父亲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我的言谈举止以及做人原则。
岁月冲走了太多,却冲不走记忆中的父亲。时隔多年,当我回忆早年的父亲,我总是想起这句话;当我听到这句话,我也总是会想起我的父亲。冥冥之中,父亲依旧活在这句话中间,活在我身上,我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是他在人世间流淌着的血液。
空气的皮肤上脱落的现实会落到眼睛里,落入我的生命之中,然后,蜕变成一截截长短不一,也没有肋骨的记忆,柔软、恍惚。这些年,我一直带着它,带着它们,四处奔波辗转,为的是,像父亲一样,活出自己的本色。
二
2016年春节过后,我决心在绵阳园艺山上一个楼盘买套房子安家落户。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我和我的这个想法,如同犯下了弥天大罪,很快就变得孤立无援。母亲和亲友们都觉得我“没有必要充面子”“异想天开”。苦惯了的母亲尤其不高兴,要我:“別跟你爸一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亲人们善意的基础和理由,无非是城里房价太高,还有就是,地震过后,家里的房子从青瓦房变成了两楼一底,压根不缺房子,家里房间多的是,就算我的脑袋,我的肚脐眼,我的双手、双脚分别住个单间,也没问题。与此同时,我知道众人担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丝恐惧,生怕我“过场多”,给他们添麻烦,找他们借钱。
被泼了凉水的我并未死心,凭着工资和稿费收入,又东拼西凑些钱,终于交了首付。也算幸运,六月份拿到房子开始装修,已经一穷二白的我,熬更守夜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断发表、获奖,稿费和各种奖金维系和延续着装修的各种开支。
年底,房子顺利装修好了。不但还清了借来的钱,竟也没欠谁一分一毫。在绵阳熬了四五年的我,从此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窝。
眼下,在绵阳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避风港,但是,我时常感到自己仍然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浑身上下携带着断裂带痕迹和气味的乡下人。大多数时间,我都在一种无根的状态下游离,真正的快乐并不多,压抑和孤独如同空气,环绕着我的心跳和呼吸。
曾经,那个断裂带上孤独的少年总是会听见远方的召唤;如今,他经常听到的则是故乡的呢喃。只是生活和不断生长的岁月,早已为我们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生活茂密芜杂的枝叶在岁月的摇篮里继续生长,让我领教了更多,也使得我陷入了巨大的茫然和焦虑。
日子一天天溜走,又一天天返回,我平时很少出门,大多数时间都木偶一样静静待在这座城市一个小小角落里面,在自己狭窄的书房,读书、写作、思考、冥想。
在绵阳,于我而言,最神秘的,并非大街上那些窈窕性感的年轻女子,而是那一扇扇或敞开或紧闭的门——城的门。城的门如此陌生,又仿佛似曾相识,浓缩的现实一般,暗暗指向我的生活,秘密翻动我内心的千言万语。
我试图让自己厘清自己的处境。
毫无疑问的是,我对人世的冷暖与复杂体验,是从离开断裂带,步入城市生活开始的。
三
绵阳,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个样,巨大的蜂巢,喧闹的摇篮,人类活体标本的展示基地,当然,也不乏五颜六色的生活。
纵横交错的马路和遍地林立的高楼大厦时常令我晕头转向。
我的记性不好,总是记不得路,每次开车在城里晃荡,都要像个患了健忘症的老人一样不断问路。当然,这不是最麻烦的,要是媳妇刚好一起,我们准会吵得不可开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媳妇却对我的这一软肋从无悲悯之心,这,也是我们发生争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绵阳这么长时间,除了去沈家坝跟诗人雨田喝酒打牌的路线比较熟悉不会迷路之外,大多数去过多次的街道,我都干脆利落、效率奇高,总有办法很快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前些天偶然在某杂志读到一个外国作家的发言,这个作家讲到一个令我激动不已的观点,他说:好作家一般记性都很差。我至少开心了小半个晚上。
出门时我总会感到惴惴不安,不开车的话我总是尽量带够零钱,因为出租车司机还是值得信赖的,见惯了城里人的狡猾世故,我时常在想,与其相信这些人,不如信赖出租车司机。也许,世界上再没有比打车更为公平和诚实的交易了。
我默数过许多遍,从绵阳园艺山所在小区门口回到自家客厅,至少要刷两次门卡,穿过六七扇门,铁门、玻璃门、电梯门、防盗门……在保持了一段时间新鲜感,以及对社区安保措施的满怀信心之后,我开始对此莫名厌倦。仿佛所有的热情,都被这些形形色色的门,吸掉了似的。
在城里,进门出门的人,都显得格外渺小,仿佛整个儿地小了一截。
“菜籽落了海!”
这句话,同样出自我那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父亲之口,在我穿过一扇扇门往家里走的过程中,它时不时爬出我的脑袋,与空气对接。菜籽落了海,覆水难收。穿过一扇扇门回家,意味着我正慢慢消失在人群之中,成为一颗掉进城里的菜籽。
在城市,每个人都是一粒菜籽。地震过后,断裂带很多人都在江油或者绵阳买了房子,绵阳的房价,也是地震过后一路飙升的。在绵阳经常会遇见老家的人。几年前圣水寺公交车站的一幕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内心五味杂陈,那天,我刚从老家开车回到绵阳,过了圣水寺门前,大老远就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空气的皮肤上晃动,以前一个在断裂带做生意的个体户,算是有钱人了,经常到镇上二娘家的批发店进货,我认识他。早就听说他处理掉断裂带的家业,来绵阳城里定居了。他的车正停靠在路边,一个拖着行李箱的青年走了过去,略显疲惫的他满脸堆笑地下了车,帮着人家把行李箱放进了后备厢。几乎一刹那,我意识到,他的角色是一名野的司机。并非瞧不起人瞧不起他的职业,只是,偶遇让我怎么也无法将现在的他和过去的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张故作迎合的笑脸!
我踩了一脚油门,飞快地路过,生怕他的目光撞见我的想法。
四
岁末的绵阳城一天天热闹起来,醒目的灯笼和旗帜在路灯上摇晃、飞扬。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年关,是旧时的说法,年前这段时间是穷人们还债的时候,过年就像过关一样,所以叫“年关”。所以,大多时候,说“年关将至”,很不恰当。然而,最近大半年时间,每一个日子,对我而言都是“年关”,度日如年。
不用待在单位,不用朝九晚五上班,依然感觉自己比任何人都忙碌。媳妇怀上了孩子。断裂带的母亲很忙——弟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媳妇的娘家人也很忙——老人需要照顾,照顾媳妇和肚里孩子的重任一下子砸在了我头上。生活的螺丝在拧紧,既要照顾媳妇孩子,又要读书写作,很多时候,我深感力不从心,却又无可奈何,漫漫人生路,原来真不是那么好走的!美国诗人庞德晚年诗集《比萨诗章》的一句话可以用来总结我目前的生活:与生活搏斗,我失去了中心。
媳妇预产期在年前几天,春节,要回断裂带老家过年是不可能的了。小时候,老是幻想自己能在城里过年,如今,当我终于有条件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心里反而没有一丝激动,最惦记的,是老家的年,最想過的,还是故乡的年。
故乡的年,从家家户户杀年猪开始。记得小时候,杀年猪,一般是五六点钟,黎明还没有到来,星辰漫天,大地仍然一片漆黑。父亲母亲提前就请好了刀儿匠(老家对杀猪匠的叫法)和帮忙的人,他们早早地来了,站在院子里抽烟、寒暄,然后便开始杀猪。杀了猪,吃过刨汤肉,母亲会取些剁好的新鲜肉交给前来帮忙的人,算是感谢。
现在,杀年猪依然是断裂带的重要风俗。只是没有我小时候那么有人情味,杀年猪变成了一种生意,断裂带有了专门的杀猪点,家家户户无需请人无须亲自动手,杀猪店的帮工开着火红色的三轮车将猪拉过去,杀好,装进干净口袋或者箩筐,就算完事了。用老家人的说法:“现在杀年猪更方便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方便里是不是也少了些什么?
在城里,许多原始步骤被省略,生活似乎就更方便了。一切都是现成的。应有尽有。唯一缺的,我想,就是记忆中老家人过年的那种形式或者仪式感。
无论城的门之内,还是城的门之外,一切的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五
来绵阳几年,入了城的门,自然知道城里的一些“过场”。看过一则新闻,说某地大凡小事请客成风,很多原本宽裕的家庭生活变得举步维艰,有的实在撑不住了,甚至举家出门打工谋生。请客的名义背后,当然是收礼了。孩子满月要请满月酒,满一百天要办百日宴,还有周岁宴,红白喜事自然不在话下,后来竟然变本加厉,有的人家里换了扇门、买了辆车也要请客。人情社会,出这样的新闻,一点也不感觉荒诞。
除了因我开车经常找不到方向发生一些摩擦之外,我跟媳妇还算融洽,很多处事原则也一致。我们都是怕麻烦的人,懒散的人,不想欠人情的人,结婚就不说了,我们早就商量好,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尽量不兴师动众,贺新房就算了,孩子没有出生,我们已经决定,满月酒到时也免了,不请客,不收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没必要给亲朋好友添麻烦。
年初,搬进新家过后,母亲还有一些主要亲戚到绵阳家里来玩过一次。母亲来了,弟弟两口子来了,二娘和姑父来了,三娘也来了。
我已经事先声明,来家里热闹热闹就行了,别太客气,红包,是坚决不会要的。
母亲带了些腊肉,还有菜园里的新鲜蔬菜。
从买房到装修完房子,母亲不是没有出力,给我们拿过两千块钱。这连半平米房子都买不起的两千块钱,一直让媳妇耿耿于怀,觉得母亲太抠门了。我只好打圆场,说家里供我读了这么多年书花了不少钱,地震后修房子又欠了一屁股债,家里也拿不出什么钱。
婆媳关系历来是千古难题,母亲这些年似乎一直耿耿于怀,不满意我媳妇,我是知道的,以前媳妇有工作的时候母亲嫌她懒惰,现在勤快了又说人家没工作。开始我还很以为是,经常不给媳妇好脸色,后来就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媳妇呢,不是没有毛病,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说母亲对我们太抠门。我经常为此发火,媳妇就不说了。
那天,母亲在新房子里转了一圈,偷偷跟我竖了个大拇指。这是她表达“深意”的一种方式,然而,唤醒的却是我心中的苦涩和委屈。走到这一步,我品尝了多少辛酸,付出了多少汗水!
在家里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亲戚们已经下楼准备开车回断裂带老家了,本来打算再住两天的母亲,突然一字一顿地跟我说,她这就下楼跟亲戚们一起回去。
我没搭理,没问为什么。
母亲脾气倔,不再说什么,一阵风似的跟着出了门。
母亲出门去了,我的心却莫名其妙地疼了起来。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从来不曾理解她。外婆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母亲的个性最为突出,脾气最怪。这些,都是母亲的几个姊妹总结出来的,我当然理解母亲,父亲去世多年,母亲从未有过改嫁的打算,身边就有男人死了没多久就找到归宿开始新生活的例子。有好几年时间,家里只有母亲独自一人支撑包揽着大大小小的事情。不容易。
想到这些“不容易”,我这才醒悟过来,赶忙下楼去追母亲。母亲下楼十多分钟了。
出了电梯,就看见母亲正一脸无助地站在那儿。
我很快明白过来,母亲不知道怎么出去,一扇门将她拦住了。她或许也没有看见,墙壁上那个白色的开关。
母亲的遭遇让我既生气又辛酸,我一边心里抱怨她不该耍性子,一边嘴上说:“上楼去吧!”
“快点开门,我要回去!”母亲气呼呼地说。
我一头雾水,不明所以,母亲,这是唱哪出?我哪里得罪了她?扪心自问,我算是有孝心的人了,不是白眼狼。我怎么了?母亲怎么了?生活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了?一连串问号。完全没办法理解,生命中,怎会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最终,母亲还是跟着亲戚回老家去了。
我始终没搞明白,母亲那天为什么会生气,母亲为什么会突然决定离开。
六
一天,媳妇正在盐亭老家读高中即将参加高考的妹妹突然打来电话,说不想读书了,说想来绵阳打工,说想住我们家里。
我听到这么幼稚的想法,坚决表示反对,不但坚决反对,还很生气。
每次跟媳妇回她的老家,我都跟她的妹妹说,在学校里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读书虽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也肯定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了。不然,做什么?打工,当服务员。前年媳妇的妹妹就在我们面前表达过这个想法,我们没有明确反对,只带着她一起去杨肥腸吃了顿火锅。吃完火锅,我让媳妇妹妹去问问这里的服务员,一个月多少工资?
反对的另一个原因则纯粹是出于我的私心,并不是吝啬家里多了一副碗筷,而是我要读书写作,我希望家里清清静静,没有任何干扰。但是,不会有人理解这一点。
我确实过于迂了,好话说尽,却没人愿听。后来我才发现,就连岳父岳母,也认准了这个老二不是块读书的料。
一切都无济于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拦得住?媳妇的妹妹很快就来绵阳了,住进了空荡荡的次卧,好像是我们专门留给她似的。即便是普通的农村亲戚,我和媳妇也不会拒人门外,媳妇的妹妹,更不消说。我们生怕怠慢,更怕家里人今后对我们指指点点。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告诉媳妇,等着吧,不管你妹妹在家里住多久,最终,她准会带着恨离我们而去。我有这样的预感和判断,一个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心里怎会涌出感激?
在家里被岳父岳母宠上了天的媳妇妹妹,用母亲的话来形容,简直就是懒得烧蛇吃。在家里天天除了睡大觉,就是打游戏,别的什么也不做。摆在门口的鞋子臭气熏天,让她洗了,倒是勤快,直接把鞋子扔进洗衣机。我跟媳妇还是平生头一回见用洗衣机洗鞋的人。园艺山上冬天风特别大,加上又住在高层,风声就像一列呼啸的火车,绵延不绝。一天夜晚,媳妇妹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条微信:“满屋子鬼哭狼嚎,吓得本姑娘睡不着觉……”
“满屋子鬼哭狼嚎”,当我看到这句话,气得都要炸掉了,一夜没睡好,这可是家啊,不是乱坟冈!可是,除了在媳妇面前抱怨几句,我又能如何?
一切麻烦,都是自找的,除了怪自己不该在绵阳买房子,还能怪什么?
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媳妇妹妹就回老家去了。
有一回媳妇回老家办事,回来后垂头丧气地跟我说,她妹妹跟家里和周围的亲朋说:“以后,打死我也不去姐姐家住了。”
我松了口气,家里清静了太平了,我才能安心读书写作啊。
然而,世事无常,没过多长时间,媳妇妹妹又来绵阳找工作了,媳妇问她要不要在外面租房子住,人家却面无表情,坚决如铁,只说了一个字:“不。”
七
搬入新家之后,我以为换了新的住所,能更加安心读书写作,现在回头去看,这种想法太过天真幼稚。
前几年在三里村三舍租房写作那种心无旁骛的韧劲,被现实的搅拌机一点点地磨碎了。
在绵阳,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思就像城里的马路,一天也静不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小区内整天都有装修的刺耳轰鸣,对面的建筑工地也一刻不停,更有家长里短。面对喧嚣,面对陈芝麻烂谷子,面对剪刀、石头和布,我分身乏术,筋疲力尽,有限的精力经常被不相干的事情绊倒。
城的门如同一道栅栏,并没有切断我与现实的纠葛和纷纷扰扰,无法静心写作,我陷入了莫名的恐慌和焦虑。
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而期盼的俗世温暖像穿过指缝的时间一样,慢慢散佚在潮湿和透着霉味儿的空气中。无形的苦闷,则像是断裂带的流水,流过我的生命,冲刷着我的灵魂,令我倍感煎熬和窒息,无处宣泄。
一切的一切,又恍如幻觉。
我来到世上的第三十个年头。
我的身后跟着长长的日子。
日子背负着人间冷暖,片刻不停,黎明与末日,灿烂与黯然,都隐藏在生命之树的枝叶之中。
深夜,一个人在园艺山静悄悄的马路上游荡,回忆过往,我忍不住默诵起荷尔德林激动人心的诗篇,为自己加油鼓劲:
“英雄在铁铸的摇篮里生长,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
但愿吧,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
责任编辑 韦 露
——以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