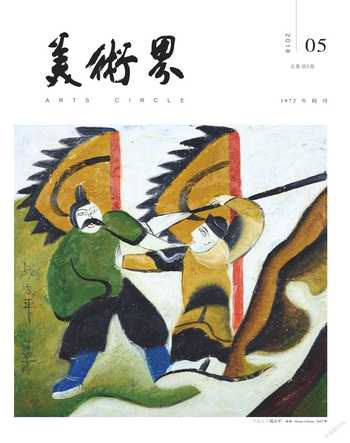来福
宁经榕
来福看见了那白色带了潮气的香味从窗外飘进来,如早晨松林上空穿流的白色云雾,还像烟囱里腾出的丝丝缕缕白烟,缓缓向屋里四周散开来。这气味时淡时浓,时有时无,有时如一片蓝天上的云,没了像是散在半空的风。
来福从床上支起身子,最近有些反常,醒得愈来愈迟。按说以前都是天麻麻亮就醒了,今天太阳都升起来了,要不是闻到窗外飘进来的松香味,兴许现在还在睡着哩。
来福太爱这松香气味了,那香气似乎已经融进他血液里了。三十六年或者四十年前,记不起来了,他就来到这片林子了,一边守林一边割松脂。妻前几年去世了,葬在松林边上,来福每天早上干活前,总是要先清理干净妻墓上的杂草。那些杂草长得飞快,像他额头的皱褶般,一夜间呼啦啦爬上了额头。以前有传说,额头上再也容不下一根皱褶时,一个人生命也就到头了。来福现在额头还有些空余,也不能说明什么,指不定哪天早上起来,额头就长着满满当当的皱褶了,谁说得准呢?女儿早嫁了,嫁到两千多公里外的城市里。外孙出生时来福去过,要搭上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时腿肿得都拢不起来了。儿子在镇上粮所上班,节日才回来一趟。倒是侄子旺新常来看他,一来就拿几包烟几瓶米酒。那烟都是盒装的,来福不爱,他喜欢自己卷的,放在水烟筒里咕噜咕噜吸得痛快。酒倒是不错。
旺新在大村里管事,边管事边种着几亩田,吃不完的米就用来酿酒,酿酒剩的渣就用来养猪。几头猪肥肥大大,杀一头够全村人吃一天,当然是要用钱买的。
来福割掉的松脂就是给旺新拿去卖的,以前是他爹,他爹死后就由他接手了。松脂论斤卖,一斤三块钱,来福每天能割二十斤左右,能卖六十多块钱。由于松林属于集体林,村里要占大头,七三分,算起来来福每天能得到二十块钱上下。
每个月六百块钱,对来福来说,是够得不能再够了。儿子回来过节会塞几百块钱给他,他也要,放到那口褪了红漆的木箱里。现在他已经攒了一小笔钱了。儿子和儿媳妇都是在单位上班,也在镇上买了房子和车子,他们不缺来福这点钱。他最近才清楚了,他要这笔钱来做一件事。
来福把松香刀和勾刀插进皮带里,拎着蛇皮袋和水烟筒,沿着山沟往松林走去。是深秋,沟边的树叶、路上的泥巴都裹了层细细的霜,沟里的水似乎冻住了,没有半点声响。过了几个坎,松香味愈来愈浓,水也发出了咕咕嘟嘟的流动声。来福就看到了松林,在一个平缓的坡上。
每天他走到这里,看到这片松林,闻到这阵浓郁的白色松香味时,就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心田悠悠蕩开来。
妻的墓也裹着层白霜,像昨夜下过了一场小雪。来福用勾刀把新冒出来的杂草割掉,勾刀是妻生前用的,刀背生着黑锈,刀锋依然锐利飞快。每一刀他都足够耐心,和以前给妻梳理头发一般,妻舒心地看着镜子。镜子里,两人面容安详平和。
清理好墓地,来福开始收松脂了。松香刀在松树上刮出一道道伤痕后,松脂从伤口渗出来,在下边用钉子钉上一条白袋子,松脂就流到袋子里。过两三天就凝结成块了,这时就可以收了。
来福来到一棵粗大的松树旁,它身上的白袋子已经结满散发着白色香气的松脂。它身上有两块平行四边形的疤,前面一块,后面一块。来福拍拍松树的躯干,像拍一位老朋友的肩膀,说旺牛呀你悠着点啊,你还要活几百年呢,留点本钱以后吃,别老一刀下去你就把松脂给流完啦。来福把塑料袋里的松脂倒进蛇皮袋里。
旺牛旁边是一棵细长的松树,直愣愣挺着像根电线杆,袋子里的松脂只有肥皂大小。来福摸摸树皮,说瘦狗啊,你怎么还是光长个不长肉啊?怪不得你这么小气,我也不怪你,多少就多少了,你先把肉给长了。
瘦狗旁边是一棵弯曲的松树,像一个调皮的小女孩走路,总爱绕弯。它身上的袋子里什么都没有。来福说,小花驴,就数你最娇气,高兴就满满当当,不高兴一个子儿都不给。
走了一圈,蛇皮袋有点沉了。来福坐在一个树墩上,秋风从松林子上吹过,发出了蚕吃桑叶的声音,日头还没睡醒,懒懒散散扔下几块光斑。他有点累了,喘着气,吸了口烟就呛住了,咳得整个松林都在震动。可他心里安详得很哩,这里像个温馨的大家庭。咳嗽了没人会怪你吵,它们会安静地等你咳嗽停下来,看你咕咕噜噜吹着水烟,听你讲些过去的事情呵。
来福想起去年到儿子那住的那段日子,他夜里咳个不停。儿子叫他去看看医生,他愣是不肯,说咳几下算什么大事。一天晚上,他咳得厉害,喉咙干干烈烈像着了火,他住的房间和儿子儿媳就隔一堵墙。半夜儿子开门进来,叫他去趟医院吧,来福说什么也不肯去。下半夜火从喉咙烧到了肚子、口腔、鼻子,咳得整个房子嗡嗡震动。儿媳终于爆发了,说你咳我不说你,让你去医院你又不去,你受得了我们受不了我们明天还要上班呢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呢!
呵,多大的事呀,嫌吵我就走嘛。来福早想回来了。那里的水有股怪怪的味道,空气黏黏稠稠的,厕所干净得拉不出东西来,连水烟筒咕噜咕噜的声音也响得不痛快。
儿子说,爸,你别理妇人家,说话没个大小,你回去了谁来打理你?
来福说,不是这事,是我自己想回去。
他就回来了。
旺牛、瘦狗、小花驴,你们说是吗?我要不回来,你们恐怕要无聊哩。来福吐了口烟,风一吹就钻进松叶里了,自从回来以后,咳得少多了。他已经决定要攒钱把这片松林子买下来,死后就埋在松林子边上,妻的隔壁,和妻一起看松林长大。
他算了下,一个月能攒下三百块,一年就是三千六百块。松林地大约有十亩,按照之前五百块一亩的价格来算,总数五千块左右,一年多就能攒够。可买松树还要一笔钱,这笔钱可不小,他问过木厂的人,要两三万。不过也没关系,他现在木箱子里已经有两万多了,就等冬天一过,他就找旺新说去。
可他还是担心,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额头皱褶就长满了,也许明年,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天。近段时间睡眠不太正常,一天比一天醒得迟,是不是某些事情来临的征兆呢?
最多在这个冬天了,一定把钱攒到三万块,这样一来,旺牛、瘦狗、小花驴你们要多受点苦了。来福这样想着。
来福站起来,他要在每棵松树上多割几道口子,让松香出来更多些。秋雨来了,无声无息,像柳絮样从天空飘落,飘过苍翠的松叶,落在来福的头上、脸上、手上,透凉透凉的。好个细细的柳絮呵,要是再大点,就是雪花啦。来福没见过雪,女儿说一到冬天,她那里的雪花纷纷扬扬,人站在天空下,头发一会全白了。有时晚上睡觉前世界还安安静静,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听见窗外下雪的声音,那声音像柳絮飘落到屋顶、地上和池塘的声音,微微的,却能听得到,也能看得到,甚至还能摸得到。打开窗子,世界洁白的一片,很多小孩在外面滚雪球、堆雪人,相互追逐打闹,外孙女也吵着要出去玩呢。
来福是被这突来的秋雨迷住了,似乎看到了孙女在松林里蹦来跳去,追逐那些飘浮在空中的柳絮。孙子小时候来过这里,可被蚊子咬了几下就不敢来了,等到长大些更不来了,嫌弃这里到处是裸露的牛粪羊粪,牛粪羊粪上面还有嗡嗡的苍蝇。
可秋天哪里有蚊子呵?牛粪羊粪也被人们铲起来了。来年春天时,就是很好的肥料了。牛粪打的土,稻子长得特别快,呼呼啦啦就蹿起来了,稻叶和谷子还有一股幽幽的香气的,闻起来让人心情舒畅哩。
来福的松香刀举起又落下,落下又举起,他的架势很好看,扎着马步,挺直腰,手有节奏地舞动着,像一位功力深厚的拳师在打拳,又如京剧老生扯着亮嗓在比画动作。松树在松香刀的挥舞下发出沉闷的声响,像爸爸在给孩子拔掉乳牙一样,每棵树都在咬着嘴唇忍着这一下。疼了一下,不久就长出白白亮亮的牙齿了。
秋雨在他头发上凝成了细细的水珠,他脸上湿漉漉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等到割完最后一道口子,来福的长衫已经湿润了,背上的皮肤冰凉凉的。他打了个喷嚏,眼前的雨呼啦一下就窜开了,一会又重新飘卷过来。来福用食指在松树那道口子上刮了一下,温热黏稠,嘴上掛了笑,喃喃地说,孩子们,天凉啦,出门要添衣服,晚上别踢被子啊。就在雨中转身往回走了。
来时地上裹着霜,回来天上落了雨。来福看着这条他不知走了多少遍的小路,在这里他度过了多少个春天,就度过了多少个夏天;度过了多少个秋天,就度过了多少个冬天。有个春天,他和旺新两人喝醉了,旺新送他回来,他又送旺新回去,旺新又送他回来……来回送了三四次,都是走这条小路。最后旺新送他的半路上,他走不动了,趴在路边的草丛上睡去了,旺新背了他回来。
后来咳得厉害了,旺新就不爱和他喝了,烟酒倒也拿来。一边拿着烟酒给他,一边劝着他少抽烟少喝酒。来福说,旺侄儿,来喝点。旺新总是摆摆手,说来福叔,少喝点,少点,我还想看你多割几年松脂呢。
多几年少几年有多大差别哩?来福还是喝。旺新不陪他就自己喝,烟也抽,抽完自己的抽旺新送的。不抽不喝白天不精神,晚上睡不着。
雨一直下到了冬天,秋雨变成了冬雨。小路上,松林下到处是牛羊的蹄印子,整齐齐的,乱糟糟的,把人的脚印都踩没了。
再过半个月,犁完了地,牛就进棚了,休息一个冬天,来年好有力气拉犁。来福也想窝在屋子里,生上一堆火,烤几只红薯芋头,暖洋洋地度过一个冬季。可钱还差点哩,他依旧每天早晨披着雨衣,带上两把刀、一个蛇皮袋、一个水烟筒到松林里。松树还是像夏天般苍翠,它们的世界没有冬天。
等到天放晴时,来福打开红箱子,清点了几次,够三万了。于是买上两瓶二锅头上旺新家去了。旺新在老屋子换椽子,连绵的冬雨把椽子浸透,软塌塌地垂下来。旺新看到来福,从屋上下来说,来福叔你别拿酒来呀,我酿酒的不缺酒。来福说,今天不一样,喝这个。说着掂掂手里的二锅头。
坐到台上,喝了几口,旺新说来福叔,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换完椽子去找你呢。来福端起酒瓶说好,谁来谁去都好。旺新说来福叔,以后不用到松林里割松脂了,村里把松林卖掉了。来福听了后,手里的酒瓶猛地跌到地上,他突然觉得全身都冷了,冷得打哆嗦,他颤着嘴唇,问旺新说你把松林卖哪了?旺新说卖给隔壁村矿老板了。说隔壁村原来不是有个堆矿的料场嘛,现在堆不下了,要建一个规模更大的。说来福叔,到时我给老板说说,让你帮看料场,钱一定比割松脂多。
来福呆愣愣地看着地上破碎的酒瓶洒出的酒,还透着一股芳香,这股香气似乎是从窗外面飘进来的。窗外是片辽阔的田野,田野不远处的一个坡上是松林。
松林里,松树白色的伤口正在结着黑色的疤。
责任编辑 李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