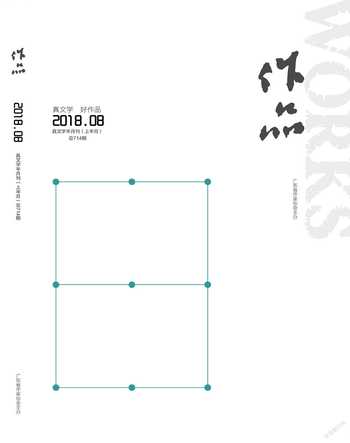罗威纳,一个圣诞故事(短篇小说)
达安·赫尔马·范·沃斯(荷兰)
令他吃惊的是,她身上的味道既不像普通的牛奶,也不像低脂的法式奶油干酪或希腊酸奶,而是像脱脂乳。他手摩挲于窗帘之间,然后握成个小孔,窥探那个在解自行车锁的女人。在她一米之外,两只肥硕的海鸥为了一小块圣诞蛋糕争夺得不可开交。昨晚在酒吧,他问了她很多问题,希望她只是把自己的主动当作一种好奇,结果也如他所愿。他还记得她的三个回答:1.加冰的伏尔加。2.戏剧研究。3.这个文身?是只燕子,你真能看出来吗?我妈说:“我就像只燕子,时飞时停,时飞时停。”他没有问她是属于天空还是属于大地,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她极不雅观地大腿一甩跨过车座,然后踩动自行车摇摇摆摆地离开了街道。他继续看着,看着那堆呕吐物、那只鸟儿、那扛着棵圣诞树的邻居。
最后,他看向对面那套久无人居的公寓,那套除他以外无人关心的公寓。他和那套公寓一样在衰老,无人记录其中点点滴滴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最终会带来可怕的转变,而那时已无对象可以指摘。他开始觉得生活百无聊赖,只有望向那套公寓时,这种想法才会暂时消失。
但也没那么糟吧,不是吗?他刚过四十岁,还拥有一头浓密的头发,每天清晨醒来还有生理反应。但这就是他所定义的年轻吗?
他转身背对着窗户。对面的公寓让他如芒在背。他知道接下来一天会发生什么。他会泡茶,尽管最后并不记得。他会清洗炉灶,尽管它并不脏。他会在街上来回踱步,坚信这也是种运动。然后在上床前,他会向自己保证不要忘记她身上的味道。
十三年前,那是最后一次有人住在那套公寓里。之后一段时间,大楼前面挂起了“租赁”的牌子。有一天,牌子不见了,但他并没有看到谁把它取下来。
搬来的那个男人总是夜间活动。他极少露面,总把窗帘合得紧紧的,让人无法窥探。即使在没有半点人影活动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视还一直闪着蓝光。他总在奇怪的时间去取邮件。还有在半夜里发出的声响,那介于捶打声和咆哮声之间的声音是什么?
当他自己的生活没意思时,他便越来越被那扇窗户吸引。他盯着窗框,陷入幻想。有一天,对面的那个怪邻居不见了,“租赁”的牌子却没有重新挂起。公寓像是被抛弃了。不过他没有放弃。
十五年前,在寻找那些通常能成为出版小说的写作素材时,他慶幸自己总能从他人的生活中得到灵感。二十三岁那年,他发表处女作。当时,一些青年作家越来越受到杂志、电视节目和一次性出版物的青睐和追捧,而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位列这些青年作家的排行榜之中。当时他觉得,这种对榜单的疯狂已近乎歇斯底里。但现在他感叹:至少当时还有榜单呀。
今天情况变得更糟。他没有变,他的语言也变化不大,但情况却已不能同日而语。尽管没人能够描述出他下滑的趋势,但文学界已达成共识,他的出版作品变得越来越贫乏无味。不管怎样,媒体对他在事业倒退领域起的“模范带头作用”置若罔闻。
他的名字逐渐在榜单里消失,他写不出好的小说(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除了厚以外),他输给了其他人,他年纪增长、变得更加叛逆(在他自己的眼里: 更有原则)。他前三部作品创作之快让同行既羡慕又怀疑,这些作品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版权费让他一时生活无忧。现在,他为一两家尚未觉察其市场价值下滑的杂志特约供稿。尽管背地里他因此非常鄙视它们,但至少他还有这个精力啊。
平安夜。街道对面,那些空间狭小、屋顶低矮、挤满工人的房子里,圣诞灯饰已挂起,光彩夺目。他听到远处有轨电车电缆的绷紧声和自行车链条的嘎嗒声。午夜时分他开始行动了:就像在梦里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就像在梦里无所谓何种理由。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离开家时,他一手拿着一根中间系着个大圈的绳子,另一手握着一个铁撬,尽管他可能并不会用上,但此刻街道出奇地安静。一切准备就绪。
要到那套公寓的门口,必须先爬一段隐蔽的台阶。他心跳加速、呼吸紊乱。当然他没有看到名牌,如果房子没有主人,这应该不能称为入室偷窃吧。他把手和手腕穿过信箱,朝门把手的方向扔绳圈。经过十分钟的不断投掷和咒骂,就在他考虑用铁撬的时候,他听到咔嗒的一声。
公寓里有一些家具,上面覆盖着一层手指无法拭去的灰尘。他闻了闻自己的指尖:所以这就是那个夜间活动的男人生活的味道,污浊、变质、腐臭。电源并没有被切断,煤气灶仍然可以点着。他打开一扇窗,直视街道对面自己的公寓。
他打开客厅的灯,这时他才发觉墙上的照片。这些照片数目众多且被精确有序地挂在墙上。在这约百张的照片里,他看到四个人的生活缩影。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一些地图和日程安排表,但其中联系并不清楚。他感觉自己在看一个代码的不同序列,无法找到破解的方法。
令他失望的是,房子里没有那个男人的任何痕迹。他是做什么的,他去哪了,谁还在继续支付煤气费、水费和电费呢——没有任何答案。他手指拂过那些照片,就好像在解剖它们一样。屋子一角,放着一个陈旧的担架;床垫上面可见片片湿渍但没有任何破洞。他转向窗户,盯着街对面自己的房子。他继续呆在那。最后,他躺下睡着了。
*
第二天,他正在过马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直奔而来,停在他面前。后门唰的一下被推开,两名男子冒出来,把他扔进车厢。他艰难地站起身,吃惊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长得像罗威纳犬的男人说道:“很高兴你回来了。”
他没有回答。
“你消失有一阵子了。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失望,但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因为你回来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工作。你应该很清楚,你离开后,有项任务一直等着你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是永远不会过期的。”
“一项任务?”他说,“我应该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他从来没有这样确定过。
“你当然是,”罗威纳说,“你屋里的灯亮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很奇怪你竟过了那么久才给我们发暗号。”
他想要挣脱他们,但没有成功。
“听着,蠢货,”罗威纳说,“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应该无须告诉你如果反抗的话会发生什么吧?”
确实,没有必要反抗:在狗的眼里,这个世界不存在慈悲或怜悯。他的心跳在加速,但他保持住了冷静。他听到自己的嘴里有序地组织起音节、单词和句子。他的声音非常理性,甚至冷漠:“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
“你之前本该完成的任务。”第二个男人说道,“干掉一个人,一个怪挞,没啥道理可讲的。”
那一刻,他所有的恐惧和幻想都变得如同实物,有棱有角有分量,卡在他的喉咙里。
“还有,不要谈什么报酬,”罗威纳说,“你要有点良心,我们已经为你支付了近十三年的账单。还有,我差点忘了,你必须在年底前干掉他。”
“为什么那么急?”为什么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关心这个荒诞事情背后的安排?他搞不清楚,但他的声音似乎知道它在做什么。也许他应该听从这个声音。
“这不是你的问题,”第二个男人说,“但从交税的角度来看,最好在年底之前行动。”
罗威纳点了点头。
“我要除掉谁?”他冷漠地问道。
“谁?”罗威纳十分惊讶,“就是十三年前那个目标。”第二个男人递给了他一份档案。
他打开档案,顿时面色惨白,在第一张照片中,他看到了自己。
晚上,他走到附近唯一营业的打印店。他上网搜寻目标人物的图片,打印出五页纸,上面满是照片。在曾经对面邻居的浴室里,他用一块胶布将照片贴在镜上。所以那个夜间活动的家伙是名杀手。回家是不可能了,他肯定一直被盯着。他也不能报警,因为他甚至不知道要对警察说些什么。他试图像今天早些时候那样让声音引导自己,但只有沉默。
或许这段时间里,他最好听他们的。他要盯着自己曾经的家,这并不困难吧。但他们说这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到底在准备什么?他没问,他们也没说。他看着照片,发现自己变老了。他现在更瘦,皮肤也有点褪色。但即便如此,面包车里的人认不出他吗?难道他们没有仔细地读档案吗?或者他们很清楚他是谁,而这一切身份互换只是某玩笑的一部分?
不,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不是在开玩笑。这种肯定让他脊背发凉。他们肯定知道得比他多。他只能顺从。
他坐在窗边,盯着自己的公寓。客厅里亮着一盏灯,卧室里的晾衣架上挂着袜子和内裤,但在这里,他闻不到那洗净后特有的、令人舒心的味道。但或许那味道已经消失了吧。
他看着前门。三个小时过去了,无人来访,甚至连邮递员都没有。后天,他必须结束所有准备工作。或者至少也要让人觉得,自己不是在游手好闲。他拿来记事本,制订了一个计划,但没有写下任何东西。那两个男人告诉他,他会在后天拿到步枪,然后用它完成任务。曾经,在得克萨斯的靶场上,他也练习过射击,并且颇有天赋。
他们不是那种你可以拒绝的人。为了回归正常生活,他必须执行这次任务,别无他法。但是在他能想到的所有人当中,为什么偏偏是他,必须消失呢?
*
第二天早上依然没人敲门。他做了一些腹部练习和拳击训练,他知道自己要尽可能保持好身材。这么多年后,他终于再次找到健身的动力。
*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们光明正大地接他上了车,就像他是他们中的一员。面包车缓慢行驶在运河上,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交谈。圣诞节结束了,商店重新开业,人行道上的针叶树旁立着一些垃圾袋。
罗威纳问道:“你发现了什么吗?”
“我不想骗你,”他说,“目标人物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
“是的,他就是个悲剧,”第二个男人打断道,“一个怪挞。”
“悲剧,我不确定,”他说道,“但什么是怪……”
“就是悲惨的,”罗威纳说道,“可悲的。”
“也许吧,”他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必须消失。难道我不应该知道原因吗?”
罗威纳惊讶地看着第二个男人,就好像他从未听到过如此怪异的话。
第二个男人说道:“应该是你给我们一个关于目标人物的详细分析,而不是我们给你分析。快说说让我们听听!”他转向罗威纳:“我跟他说:‘你应该给我们一个对目标人物详细的分析。我们听听看!”
一阵沉默随之而来。“好吧,”他说道,语气里带着疑惑,“目标人物一直很孤独,无人探访,两天都没看到他出家门。”他结巴了片刻,内心惊恐,原来连自己都觉得上述是事实。然后他继续贬低自己:“他是一个失败者。他的生活毫无闪光之处。他用厨房的剪刀修剪自己的脚趾甲。他观看《鼹鼠》。他的指骨间长有湿疹,睡觉时总要在上面敷膏药。有时他会放一张唱片,这样至少能听到别人的声音。他上一个约会的女孩身上有脱脂乳的味道。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他说完了,筋疲力尽,一种莫名的悲伤涌上心头。也许这就是一个怪挞通常的感受。
罗威纳转向第二个男人:“终于有令人放心的消息了。开始我还以为他完全失去了线索。但听到这些,我相信他比目标人物还要了解他自己。我的朋友,这才是做事的正确方式。”
第二个男人说道:“记住,最晚在新年前夜要干掉他。你还剩下两天的时间。”
“我明白,和有利税率有关。”
他们俩一起点了点头。
羅威纳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杀了他。”
“是的,”他回答道,“他永远也不会。”就好像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静静地等在那,等着人瞄准他。
只剩两天。后天,就必须完成任务。步枪的手感很好,重量也适合他,上面还刻着:Blaser Germany DE。德国人,他心想,还会有谁?口径:0.243。瞄准器已经拧紧,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在交给他枪时,罗威纳十分得意又故作随意地说道,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方法。
他的方法包括哪些,他不敢问。现阶段最好闭嘴,相信直觉,祈求最好的结果。
一旦任务顺利完成,他必须想办法处理掉武器。但首先他必须能够迅速地拆卸掉它。在那天剩余的时间里,他都在勤加练习,让自己变得更加精通熟练。他轻而易举地关掉瞄准器,迅速地打开和关闭消音器,高效地折叠好枪支并放在随身携带的盒子里。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那个盒子对杀手而言有些女气。
此刻,在这套曾令他神往的公寓里,他坐在一角,枪托搁在肩上。他拉伸脖子放松肌肉。顺着枪管,他的视线从灰泥上的裂缝转移到湿渍的斑块,再到参差不齐的斑点,想象这是一只动物留下的痕迹。他食指放在扳机上,輕轻一按,听到咔嗒一声。
晚上,为了犒劳自己,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当地货摊上他买了个炸苹果饼,毕竟这正是一年中吃这个的时间。在回大本营的路上,对于那个曾经属于他、现在却成为射击目标的公寓,他看都没看一眼。
夜里,他突然惊醒。他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苛刻地评价自己的生活。罗威纳只是向他提了个简单的问题,并没有进一步地鼓动他。就好像一个持续十三年的咒语突然被打破了一样。或许他真的做错了什么,或许他生活得太过随便,或许他太过相信人生的自然过程,那个他曾有过辉煌的过程。
几英尺外放着步枪盒。他呼吸急促。要杀他的人搬到街对面的公寓里,这真是太奇怪了。等等,那个人搬到这里当然是为了杀他。他躺在发霉的床垫上。但是,为什么那个杀手未完成任务就离开了呢?
或许杀手发现他是无辜的,有这种可能吗?他感到一丝微弱的希望,如鲠在喉。
但或许正好相反。或许他的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只能自己解决自己。但是无论前任杀手失踪的原因是什么,明天他都会站在那个杀手的位置上。
十二月三十日,在杀手的衣柜里,他发现了一套运动服。中午,他决定出去跑一圈。屋外寒风凛冽,每呼吸一次,肺部就一阵刺痛。他路过目标人物常去的超市,决定走进去。他买了两打鸡蛋,然后回到大本营。在那里,他准备了一顿中餐:两个巨大的煎蛋。他想象自己的肌肉在增长,相信自己在变得越来越健壮。十三年来,他第一次觉得提升自己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他把浴室里的档案图片带到客厅,并把它们挂在其他照片旁。他看着眼前五个毫无价值的生命,还剩一个需要了结。他走向窗户,拿起步枪,瞄准目标人物的公寓。他拉近距离,对准书架上的相框。他扣动扳机,轻轻地咔嗒一声。明天他会用上实弹。
如果对一个生命的定义是由拜访他的人数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目标人物几乎可以被认为不存在。这样的话,人们还会说这是谋杀吗?
年末最后一天,就是今天了。但他首先必须再见那两个男人。在扣动扳机前,他需要知道目标人物为何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同时,他也对“怪挞”的含义十分好奇。但他知道那两个人不会轻易地满足他的要求,特别是没涉及税收利益的情况下。他需要主动出击。他抓起一条红毛巾,走到外面,把它绑在门柱上。然后他等着,知道他们会主动来找他。
*
他明白自己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感觉到了。他们需要他来完成任务。他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掌控局势的人。
“好吧,”罗威纳说,“事情不太对劲。我们需要关心这个吗?”
“是的,”他说,“在我看来,目标人物的生活一直很平静。我是名职业杀手,我需要知道他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在处理什么问题。”
“就这样?”罗威纳问道。
他点了点头。
“好吧,”罗威纳说道。沉默在他们之间的空气中振颤。“他虚伪。”
“就这个?”
“虚伪就该死。”第二个男人马上应和道。
“我不明白,”他说,“虚伪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骗人。”
“他骗人?”
“虚伪是最严重的犯罪,”罗威纳不情愿地解释道,“很多人疲于生计。但就有像他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有权享受舒适的小生活,他们一面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一面又带着某种不尊重甚至嘲讽的表情。嘲讽破坏了我们试图构建的一切。人们曾经相信他。他们都是真心实意的。但他什么也没做,这让他们失望透顶。他必须消失。”
他想表示异议,但做不到,因为那个男人说的都是真的。
“对了,”他说道,“能告诉我什么是怪挞吗?”
罗威纳翻了翻白眼:“这简单,就是卑鄙小人、蠢货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没什么其他需要问的了。
*
黄昏来临,鞭炮声起。他反复地拆卸和组装步枪,一次又一次,熟练到无须再看着枪支。他盯着墙上的照片,特别是其中一张。罗威纳是对的,目标人物是虚伪的。他的作品充斥着那种令人厌恶的讽刺和风趣,他用这些来保护自己。现实中,他总是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当他触碰到物或人时,他也毫无感觉。他唯一关心的是那些他看得到的东西:乳房、书籍和逗号。
目标人物本应在十三年前就被解决掉。在他逃过一劫、被额外赠与的日子中,他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依靠别人,需要不断的赞美和不断的爱。
但他却从未觉得需要赠与他人什么,他就是一个怪挞,一个卑鄙小人,一个蠢货。他需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装载好步枪,时间到了。
*
十一点五十分。步枪扛在肩上,瞄准器作为窥视孔,他紧盯着对面的公寓。到了午夜,目标人物会出来看烟火。他专注于呼吸,试图保持镇静。目标人物的邻居提早出来,点亮了夜间的第一道火光,但他没有抬头看。最后,一个人走到门口。不是目标人物,是一名访客,一个女孩。在她的右手上有一个燕子图案的文身。
他的眼睛在燃烧。只须拉动扳机,她的头就会像西瓜一样爆炸。他应该这样做吗?他想要这样做吗?女孩拿着手机,玩世不恭地抬头看向目标人物的窗户。也许她可以证明,目标人物不是虚伪的。她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再次打电话给他。然后她耸了耸肩,取走了自行车。就这样,她忘记了关于他的一切。她不会表态,不会为他的生命恳求。没有最后的抵抗,没有最后的辩论。她并不在乎。那一刻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正义的。也许只有体味如脱脂乳的女孩做出裁决才恰如其分。
那个声音又重新回来了,它说道:“我要杀了那个混蛋。”
女孩一走,他就走向目标人物的公寓。他进了屋。屋内有一股熟悉的气息,但他却感觉不自在。他来到卧室,看着街对面,发现自己在射击的范围内。目标已经及时被锁定了。
他跑回大本营拿起步枪。但令他惊讶的是,目标消失了。他跑回目标的公寓,然后又回到大本营。他就这样跑来跑去,他的脑袋里充斥着烟火的爆炸声和新年的许愿声。他来回地跑呀跑呀,跑向自己应得的结局。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