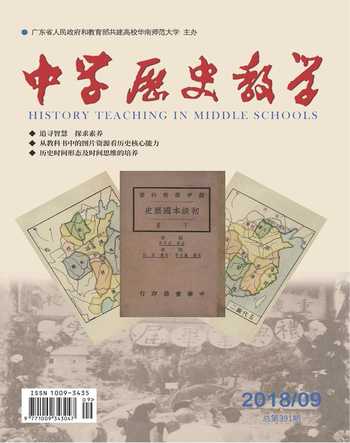大胆质疑,还须小心求证
李敏 孔军 常文强
笔者曾拜读叶朝华老师的《大胆质疑,小心考证》[1](以下简称叶文)。被他“用教材教”的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所折服,深受启发。他敢于质疑教材,共指出四处不当,其中两处已被新版统编教材采纳并修订。一为秦朝“统一货币”的图示,原只展示五国货币,现添加了韩国的铲币,改为六国货币图示,更符合史实;二为北京人化石的表述,原为“它的发现”,现改为“这一发现”,消除了指代不明的嫌疑。
叶文建议将统编教材七年级上第9课《秦统一中国》中量器图的标注由“铜量”改为“铜升”。他认为“从时间来看,商鞅在公元前344年统一使用了‘铜升。秦朝统一度量衡时加以推广,这在情理之中,建议图片下面标注‘铜升。”[2]依据是“商鞅采取行动统一度量衡,目前已经发掘出他那个时代的几种量器,其中包括一个铸有商鞅之名的著名的铜升。其日期相当于公元前344年;其容量等于0.2006公升。”[3]笔者认为仅凭此文献,无法说明商鞅统一使用“铜升”,也无法断定秦朝在统一度量衡时,沿用了铜升之名,叶老师认为的“情理之中”有待商榷。笔者在此略表拙见,敬请指正。
一、引文不够严谨
叶文依据的文献源自国学网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笔者认为参考纸质中译本或据纸质版制作的正规电子书更符合学术规范。笔者核对国学网[4]和纸质中译本[5]相关内容“商鞅采取行动统一度量衡。已经发掘出他那个时代的几种量具,其中包括一个铸有商鞅之名的著名的铜升,其日期相当于公元前344年;其容量等于0.2006公升。”两处表述一致。叶文的引文不仅多了“目前”二字,而且将“量具”误引为“量器”,可见其引用文献不够严谨仔细。
二、曲解引文文意
引文的文意是已经发现了商鞅统一度量衡的几个实物证据,其中有一个约公元前344年铸造,刻有商鞅之名的铜升。从引文描述可知,此升应为商鞅方升,又名商鞅铜方升或商鞅量。“‘商鞅量也叫‘商鞅方升。战国时秦国量器。青铜制。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时所造标准量器,是商鞅统一量制的重要证物。……现藏上海博物馆。”[6]铜量是铜质量器的统称。“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如战国齐国的子禾子釜、陈纯釜,秦国的商鞅方升、始皇方升、始皇斗,新莽的嘉量等,都是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7]商鞅方升可称为铜量。因此,商鞅统一使用“铜升”或统一将铜质量器称为“铜升”是对文意的曲解;秦朝统一度量衡时,将量器称为铜升,乃是曲解文意所得。
三、论证逻辑缺陷
“商鞅在公元前344年统一使用了‘铜升。秦朝统一度量衡时加以推广,这在情理之中,建议图片下面标注‘铜升。”[8]叶文仅凭商鞅统一使用“铜升”或统一将铜质量器称为“铜升”,就断定秦朝统一度量衡时,推广使用了“铜升”或统一采用铜升来称呼铜质量器,有些欠妥。
首先,叶文论证的前提是商鞅统一使用“铜升”或统一将铜质量器称为“铜升”,所引文献并无此意,是其曲解文献所得。“只有证实了史料的可靠性和有用性之后,方能作为证据。”[9]因此,所引文献无法作为“将量器图标由铜量改为铜升”的有力证据。
其次,叶文推理论证,有违“孤证不立”和“孤证难凭”的史学研究原则。梁启超指出“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10]杜维运认为,“维孤证必不可得结论,凭孤证得结论,与凭臆度,相去几希。”[11]叶文忽略了同本著作中与其结论相矛盾的证据,且没有以内证之法发现其推理论证存在的问题。
《剑桥中国秦汉史》叙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再次提及铸有商鞅之名的铜升:“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策。”[12]叶文立论依据文献中的铜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有‘临字。”[13]由此可推知,两则材料提及的铜升应该是“商鞅方升”。叶文因忽视其他相关史料,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前面提到过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只要是有关的,都应该找来,然后加以对比分析。……但至少可以发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14]因此,叶文历史解释的合理性略显不足。史料教学和史学研究“要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的史料,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15]唯此才能得出較为客观的结论,真正落实史料实证教学。
再次,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继承和推广的是商鞅统一度量衡的制度和标准。“下令统一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16]秦朝将商鞅时代量器加印诏书,重新颁行,更多是按商鞅的标准重铸了各种质地和形式的量器。秦朝虽统一度量衡,但铜升并非唯一的量器。“目前,像这种在秦统一中国后,器身凿刻或铸有统一法度量政令的量器,可见的仅有20件,其中大多为传世品。若去掉其中的陶量、方升和独诏量,两诏铜量仅4、5件,去掉椭圆形铜量,东海馆藏圆形铜量竟成孤品。”[17]秦朝统一度量衡,在量器方面除了铜升,还存在其他材质和形状的量器,如陶量、方升、独诏量,两诏椭圆形铜量,两诏圆形铜量等。因此,将“铜量”改为“铜升”违背了客观史实。
最后,依据考古器物命名一般原则,标注为铜量,虽不准确,也无问题。“一件器物的定名,一般的来说,是按照该器物的铸造年代,使用该器物的主人(简称为物主),收藏保管使用的单位,以及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及用途等特点作为依据的。务求得出能比较准确反映器物特征的名称。在衡量器具定名时,还必须考虑其重量、容量制度单位大小的级别。”[18]从铭文和用途角度,命名有商鞅量;从铭文、形制、材质和用途角度,命名有武城铜椭量,始皇诏铜椭量、始皇诏陶量,从铭文、形制、材质和单位角度命名有商鞅方升(商鞅铜方升)、始皇诏铜方升,依据时间、铭文、保管和使用单位和材质命名的有战国时期北私府铜量,简称“北私府铜量”和郢大府铜量;若特征较少,就直接以材质和用途命名为陶量或铜量。笔者查阅了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命名一般遵循这些原则。以铜升命名的量器多为方升,是秦制一升的标准量器(200毫升左右)。其余多为椭圆形铜量、圆形陶量或铜量。
据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和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秦始皇时代的一升标准铜量有两件传世,均为方形,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始皇诏铜方升。统编教材图片为椭圆形,因此,称铜量更准确。为方便一线教师利用文物进行史料教学,培养学生证据意识,建议教材标注量器现藏处或出土地。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培养学生史料实证核心素养。“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19]这给一线历史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哲学、史学研究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学习,力所能及的从事研究,以服务历史教学,不断提高教师的史学和教学素养,才能在日常教学中更好的坚持史料实证,接近真实的历史,给予学生态度熏陶和方法引领。“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实。”[20]这要求教师在教学和研究中,具备批判之能力,敢于质疑和提出假设;更要多方面收集史料,辨析史料的可信度;科学合理分析和逻辑推理;极力构建接近客观和真实历史。简而言之,大胆质疑,必须小心、科学求证,才能使“史料实证”核心素养在课堂落地生根,内化于学生之心,外显于学生之行。
【注释】
[1][2][3][8] 叶朝华:《大胆质疑,小心考证》,《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
[4]国学网:http://www.guoxue123.com/other/jq/han/008.htm,浏览日期2018年4月23日。
[5](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5-36页。
[6]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 1461页。
[7]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名家点金·文物知识系列(青铜器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0页。
[9]李稚勇、周仕德、陈新民著:《中外历史教育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1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12](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56頁。
[13]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馆等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14]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8页。
[15]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6]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7]朱磊:《东海县博物馆藏秦两诏铜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6期。
[18]朱捷元:《关于“两诏秦椭量”的定名及其它》,《文博》1988年第4期。
[19][2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