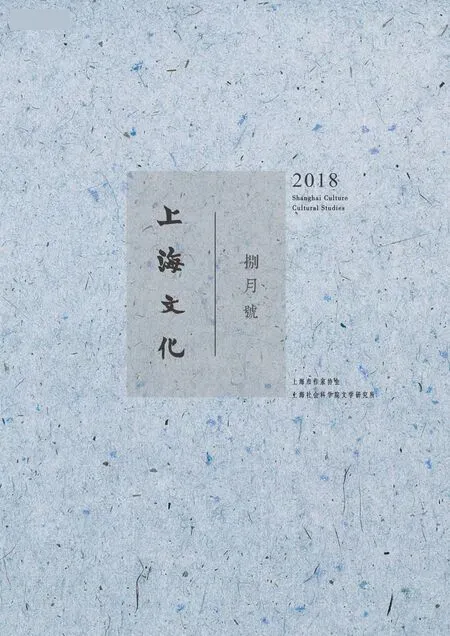从徐家汇善牧院看“罗马问题”的上海折射
——兼谈徐家汇天主教女性机构
莫 为 李 平
自1847年开始,上海的徐家汇地区便是新耶稣会重返中国后建起的天主教教务中心,也是天主教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教务基地①第一代来华耶稣会士受葡萄牙“王室保教权”的庇护。当时的天主教远东教务中心在葡属殖民地印度的海港城市果阿。随着远东传教事务的进一步细化,以利玛窦为先驱的耶稣会士以中国澳门为枢纽,试图进入中国内地开教,因此天主教中国的教务中心渐渐在澳门形成。18世纪,由于果阿爆发瘟疫,其远东天主教教务中心的地位瓦解,澳门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远东教务中心。和宗教慈善集合地。依托宗教服务所设立的医疗、慈善、教育等各种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徐家汇成为耶稣会历经解散重建后在东方世界全新呈现的象征。随着20世纪50年代肇嘉浜被填没,以及后来的社会运动和市政规划改造,尽管我们尚可在今天的格局中窥见其历史旧容之一二,但天主教耶稣会徐家汇社区的整体性样貌已基本消失。②今日的徐家汇是上海重要的城市副中心之一,其所处的徐汇区更是以此得名。而在20世纪初叶,徐家汇还只是上海边上的郊县。生活在徐家汇地区的居民,经常以“到上海去”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前往上海市区的活动。
图1这幅1948年的徐家汇地图清晰地显示:以贯穿南北的河流肇嘉浜为主要分割线,整个徐家汇被分成了西岸与东岸两大块。肇嘉浜的西岸集中着神学院、徐家汇藏书楼、耶稣会总院、圣依纳爵大教堂、徐汇中学、光启社、博物馆、汇师中小学、大修院、小修院、天文台、土山湾孤儿院等属于男性教徒的机构;而肇嘉浜的东岸,则主要是圣母院机构建筑群及圣衣院等女性机构。新耶稣会在徐家汇的布局与规划,是精细而缜密的。对于不同性别空间既分割又勾连(慈云桥)的设置,是新耶稣会传教策略的体现。然而,只要仔细察看这幅地图的顶端就会发现,善牧院这个机构所处的位置(今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所在地)十分尴尬:比较接近女性的东岸,却又被与肇嘉浜相连的李泾(又名法华泾)隔离开,似乎并不在新耶稣会徐家汇社区的地域内。而这样一个比较奇特的三角地带,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对象。善牧院的建立及其历史,是世界背景下教俗博弈过程在上海地区的折射,我们可以从中窥见20世纪世界动荡起伏的格局,并更真切、具体地解读徐家汇的宗教历史。

图1 1948年的徐家汇地图①此1948年徐家汇地图,载马爱德编:《徐家汇今昔》,美国Tripod杂志1992年7-8月刊,第4页。
一、徐家汇女性宗教事业与空间
耶稣会来华的过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篇章。历史上前后3个世纪,共计有1500多位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第一代来华耶稣会士约有500人,罗马教廷授予的、葡萄牙政府承担的“王室保教权”②葡萄牙“王室保教权”: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罗马天主教试图利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海洋实力,来实现海外传教的事业,故罗马教廷特别赋予西、葡两国国王以“保教权”(英语为“Royal Patronage”,由罗马教廷授予的、世俗政权承担,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教宗授予葡萄牙的保教权为“Padroado”,授予西班牙的为“Patronato”,英语统一译为“Patronage”)。葡萄牙获得在东方(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特别是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的发现,地理概念发生重要变化,自此好望角以东成为“东方”)的“保教权”,而西班牙则获得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区域)的“保教权”。时期的利玛窦,为初创时期的代表;其后,以处在教廷同葡国夹缝中的“法国传教团”为重要承接转折。而第二代来华耶稣会士约有1000余人,他们属于经历重建并处于近代中国弛禁时期,在法国“保教权”庇护下的新耶稣会。他们是继承人,也是开拓者。尽管两代人的国别属性差异巨大、使命侧重也有所不同,但是一贯不变的“适应政策”,③耶稣会适应政策: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策,是由利玛窦开创,并由随后几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参见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是耶稣会成为天主教最具生命力修会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的第二代耶稣会,是教宗庇护七世(Pius VII,1800—1823年在位)于1814年宣布重新恢复耶稣会建制后成立的,也被称为“新耶稣会”。面对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新耶稣会置身于新教差会及天主教其他修会的竞争之中,已不再是一枝独秀。承担信仰使命的强烈压力,促使他们调整了做法。突破性地将女性事业纳入活动版图,成为新耶稣会工作的重要亮点。
新耶稣会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1773年耶稣会被迫解散时,旧耶稣会滞留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团”成员通过10年抗争,终将其在华事业转托给同为法国血脉且早期就关系较为紧密的法国遣使会。需要注意的是,法国遣使会(以下简称为“遣使会”)是一支极具特色的天主教修会。学界对于遣使会的评价,多侧重于他们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对于天主教本地化的积极落实。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将遣使会入华传教士们的活动归结为以下特征:遣使会士在学术上不如入华耶稣会士们那样丰硕,更多地则是侧重于教务工作;遣使会士注重于到中国的一些偏远和贫穷地区布教和设立慈善机构,在基督宗教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参见耿昇:《从基督宗教第三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当年遣使会接续在华宗教事业时,不仅继承了第一代耶稣会士的传统,也在运作中加入了自身的理念。在遣使会看来,耶稣会一贯提倡的“适应政策”,应当落实在更为客观实际的运作活动中(第一代耶稣会士主要致力于思想层面的调和与开拓)。比如,应切实通过慈善的方式来改善穷困群体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辩白和礼仪上的正名;应像其中文名字“遣使会”②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Priest of the Mission),由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ncent de Paul,也译为圣文森特)于1625年创建于巴黎。1773年,耶稣会解散,1783年谴使会受到教廷和法王的特别委托,接替耶稣会在华的一切传教事务,并于1785年首次抵达北京。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遣使会”是汉语语境中的意译,由于其创始人为Vincent,在北美常被译为Vincentian(文森会士)。一样,派遣修士去民间真正地传播福音,并使受助者得到实在的帮助。因为对于当时诸多需要得到传教士解救的苦难群众来说,生存需求才是最直接、最紧迫的。法国遣使会的“务实”传教策略是有传统的,其创始人和总会长味增爵③味增爵生于法国达克斯(Dax)附近的普伊(Pouy),1600年升任神父。1605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在海上旅行时被海盗所掳,并被卖往突尼斯为奴,整整两年之后才获救回国。1607年,回到法国的味增爵开始反思并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工作。1625年,他创办了遣使会,并在巴黎及附近地区创办仁爱社团。在此基础上,他与罗伊斯(Louise de Marillac,1591—1660年)一起创办了仁爱修女会(Daughters of Charity)。在建立修会的同时,就已经着手展开女性辅助传教的事业,并且最终建立了附属于遣使会的“仁爱修女会”④仁爱修女会是遣使会的下属修会,最高领导为遣使会总会长。该会活跃于世界各地,为远方传教区提供女性修会的社会服务,如培养修女,或被派往医院、育婴堂、孤儿院、老人院等机构工作,开创了修女工作走向社会的先河。(以下简称“仁爱会”)。仁爱会最初一直在法国境内活动,但发展颇快。1660年(味增爵去世)的时候仅有60多个零散组织,1718年已经在欧洲设立了20个会省。19世纪开始,附属于谴使会的仁爱会女修士开始奔赴远方传教,并于1847年来到了中国。而新耶稣会士恰好也大致在这个时候抵华,法国遣使会将其江南(江苏、⑤当时的江苏包含上海县。安徽)及直隶东南的教务地区划归新耶稣会。受到遣使会在华事业从女性角度拓展的启发,新耶稣会在重新接过江南等地区教务的同时,也已经充分意识到女性事业的重要性。
1855年(清咸丰五年),新耶稣会法国神父薛孔昭(Luigi Maria Sica,1814—1895年)在青浦横塘发起建立最初的本地修女会“献堂会”。加入者是一批原来在家附近协助传教的贞女。之所以被称作“献堂会”,是因为希望这些贞女能够组成“奉献自己于天堂”的修会。根据西文资料的记载和金鲁贤主教的回忆:“1855年薛孔昭神父建立‘圣母贞女会’”(Marinanische Jungfrauen kongregatson,即献堂会——引者注)。当时“她们在圣教艰难时,在家守贞修道,全心热爱教会,保护教堂、团结教友。但是她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来领导,没有一个团体来照顾她们物质上和灵修上的需要,她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培养。薛孔昭神父的圣母贞女会使得她们有了组织,得到照顾,但是教会认为这些修女只是初级阶段。在经过初学之后,发给她们一块圣牌,让她们在堂口协助神父服务”。①参见VerbumSVD,Vol.16,1975,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S.62;《金鲁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天主教修会概况》明确了献堂会的首创性,称其为“中国第一个国籍女修会”。②倪化东:《天主教修会概况》,香港:香港真理出版社,1950年。这些修女在横塘地区的服务得到了新耶稣会的肯定,并且成为来华新耶稣会开拓女性宗教事业的缘起和契机。
1864年(清同治三年),献堂会迁往徐家汇王家堂地区。王家堂恰处在肇嘉浜东岸腹地。1867年,耶稣会士郎怀仁主教(Adrianus Languillat,1808—1878年)邀请法国拯亡会(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修女来到上海徐家汇,为献堂会修女提供指导和管理。其实,拯亡会于1856年才在法国巴黎创立,历史并不长。但是拯亡会和耶稣会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勾连。拯亡会的创建者安珍妮·司麦特(Eugenia Smet,1825—1871年)自立会之时就宣誓,永远跟从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拯亡会修女始终是耶稣会的左右手,而且历任拯亡会会长也都是经由耶稣会任命的。
1869年,耶稣会创办的徐家汇圣母院历经多年发展而正式落成,拯亡会和献堂会均迁入其中。徐家汇圣母院是一个功能齐全、管理有序的教会建筑群落,具有浓郁的宗教气氛。在新耶稣会的扶持和助力下,拯亡会与献堂会修女在其中相互学习。她们的使命日益明确,成绩蒸蒸日上。19世纪中晚期,上海新耶稣会女性事业的局面逐渐开阔。除了徐家汇圣母院总部,在新耶稣会上海开教的所有区域③新耶稣会在上海的产业主要在徐家汇、董家渡、洋泾浜、陆家浜等地区。都建有圣母院的分部(如洋泾浜圣母院、圣家院、上智母院、若瑟院)。它们为更大范围的中国民众提供了医疗、慈善、教育等服务。圣母院设有育婴堂、聋哑学校、诊疗所、工场、天主教圣诞女校(培养献堂会修女),以及为女性求学开辟新途径的徐汇女中、启明女中、明德女中、若瑟孤儿院(供外侨)、善导学堂等。
拯亡会之于新耶稣会,犹如仁爱会之于遣使会。拯亡会的法国血统及与耶稣会的历史联系,决定了它是新耶稣会拓展女性事业最理想的帮手。它是后起之秀,但是它带来的专业女修会的管理模式,使得已有上海当地服务经验的献堂会在运作方式上更为规范,取得的成效也更为显著。拯亡会和献堂会有所分工、各有侧重的活动,共同开拓了上海女性宗教慈善事业,可谓新耶稣会在江南地区的一大成就。对于拯亡会在上海的贡献,学界的认识尚不充分。事实上,她们并不是脱离新耶稣会的另一支宗教队伍,而是新耶稣会女性事业的最大承担者和主持者。
除了拯亡会,当年郎怀仁主教从法国请来上海徐家汇的,还有一支叫做“圣衣会”的修女群体。“圣衣会”是别称,它正式的名称是“加尔默罗会”(Carmelite Sisters,罗马天主教著名的四大托钵修会之一)。从天主教隐院修会时代起,加尔默罗会士就必须遵守“听命”“神贫”“贞洁”“静默”“斋戒”等会规。相传其会长西蒙·斯道克(Simon Stock,1165—1265年)曾亲见圣母“显现”并被授以“圣衣”,故得“圣衣会”之名。后来,圣衣会专门为女修道者设立了圣衣会的“第二会”,西班牙修女特雷莎(Teresa of Avila,1515—1591年)就是其中的代表。郎怀仁邀请的这支圣衣会,来自法国拉瓦尔圣衣院。拉瓦尔在巴黎西南300公里处,属新耶稣会法国巴黎省的势力范围。①法国拉瓦尔圣衣院:14世纪后,欧洲各国国王为加强王权,开展了反对罗马教宗权力的斗争。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1285—1314年在位)因捐税问题同罗马教廷发生严重的冲突。教宗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1294—1303年在位)去世后,在法国国王的干预下,选举波尔多大主教为罗马教宗,史称克莱芒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1308年,克莱芒五世将教廷从罗马迁往阿维农(当时属于教宗国,今天属于法国),之后的七任教宗都是法国人,并受到法王的控制,史称“阿维农之囚”(Avignon Popes)。拉瓦尔圣衣院便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历史上的法国拉瓦尔圣衣院,建立于“阿维农教宗”时期,其法国属性十分明显。②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农,标志着罗马教廷教宗权势的逐步衰弱。圣衣院修女的重要特点,即避世苦修。来自法国拉瓦尔圣衣院的修女们初到徐家汇时,被安置于王家堂。尽管水土不服带来极大不便,但她们依旧坚持到底,为当地奉教者作出了苦修的示范。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圣衣会正式迁入肇嘉浜东边的圣衣院(今日上海电影博物馆所在地),修女们从此更加厉行斋戒、克己苦身、严守缄默,在徐家汇圣衣院的高墙里,为这片江南的天主教圣地,树立了宗教灵修的榜样。
肇嘉浜东岸的徐家汇圣母院建筑群及圣衣院,是名副其实的新耶稣会融合拯亡会、献堂会及圣衣会而营造的女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与女性相关的宗教礼仪与务实贴切的宗教社会服务一刻也未停歇。圣母院建立后的近百年,正逢近代中国连续遭遇灾乱的世纪,修女们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在这个特殊年代里,显得更加珍贵。
二、“罗马问题”的欧洲发酵与中国途径
新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宗教事业的起始时间是1847年。③以徐家汇耶稣会住院1847年营建落成为标志。而19世纪中叶欧洲风云变幻,特别是罗马教廷的沉降起浮、欧洲政教角力的白热化,都对作为远东天主教教务中心的徐家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此时,向来以教宗为元首、实行政教合一的教宗国(Papal States),①教宗国:756—1870年,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以教宗为元首的政教合一的国家。4世纪,罗马主教向罗马皇帝要求赠予罗马城周围的财产,后通称“圣彼得财产”(Patrimonio di San Pietro)。321年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拉兰特宫赠给罗马教会,这是罗马教会合法拥有财产的开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宗在罗马操纵实际权力,并通过与法兰克王国密切的政治关系,扩大了教宗的影响力和权势。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Pepin,714—768年在位)为酬答教宗支持其篡位,将意大利半岛拉文纳至罗马的大批领土赠予教宗,史称“丕平赠土”,这是教宗国的开始。随后丕平之子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68—800年在位)又将贝内文托和威尼斯等城市赠送给教宗,教宗国版图逐渐扩大。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意大利实现统一,教宗国覆灭。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315页。经历了自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危机。1859—1860年的意奥战争之后,教宗国的2/3领土和3/4的臣民已经划入撒丁王国。这一时期的罗马教廷,只是在法国的强力保护下,才勉强保持了罗马及其周围地区,并得以维持对其核心地带的控制权。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被迫撤出罗马,意大利王国获得了统一。经当地居民投票表决,罗马被认定为意大利的国家首都。这样一来,教宗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历史性分离,产生了以争夺罗马城的归属为目标的“罗马问题”。罗马的争夺战,不仅体现于欧洲大陆上的对峙,而且在天主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此时的近代中国,清代康雍乾“百年教禁”发展至嘉庆一朝,已经同罗马教廷彻底断绝了往来。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恢复了在华的部分活动,但是罗马教廷同中国的交通依旧尚未恢复。尽管罗马方面跃跃欲试,②1859年,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曾训令天主教湖北代牧进京,同清政府接洽通使事宜,后代牧病故作罢。1881年,河南主教上书罗马教廷传信部,建议同中国通使,这两件事都只存在天主教会内部,并没有同清政府产生关系,因而视作罗马教廷内部的动作。参见杨大春:《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但是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多年间,清政府同罗马教廷仍然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法国在华的“保教权”成为在华天主教群体唯一的保护伞。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③天津教案:1870年(清同治九年)天津市民同法国传教士冲突而酿成的案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天津占用望海楼皇宫旧址为领事馆,法国天主教士也在庙宇兴建教堂,并邀中国官员参加开堂意识,引起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不满。1870年,传天津发生教堂虐死婴儿等事件。在天津官员检查过程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1840—1870年)以“保教权”名义出面阻挠。冲突中双方开火。民众怒不可遏,将法国领事及随从打死。后民情激愤,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等毁坏。后清政府派李鸿章、曾国藩出面求和,英美也在其中调停,以清政府赔款50万两白银以及处罚有关当事人告结束。震动中外,李鸿章试图与罗马教廷联络,希望通过“联系罗马”来稀释法国的在华“保教权”。自1881年起,清政府方面开始积极谋求与罗马建交,④1881年,李鸿章会晤英国时任香港总督时谈及教案之严峻,以及法国在华“保教权”的诸多流弊,并请其转达李鸿章希望同罗马建交的意向。但一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原来,这时的罗马教廷被自身的难题牵绊住了——罗马成为新统一意大利的首都后,欧洲各国在意大利的问题上,都竭力争取自己的权益,“罗马问题”已经不再是内政问题,而跃升为国际问题。教宗国客观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根本无法参与中国的天主教事务。
在这段罗马天主教式微的时间里,欧洲的教俗势力互相抗争、交替起伏。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蓬勃而起,整个欧洲世俗化的进程骤然加快。在欧洲范围内天主教氛围最浓重的法国,教俗之间的博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并直接影响到整个欧洲。1901年7月2日,法国议会通过《反教权法案》,政教关系逐渐恶化。1902年6月,法国激进民主主义上台执政,组成了孔勃内阁。①孔勃内阁:1902 年, 以激进派为核心的左翼集团获得议会大选的胜利。6 月, 激进派埃米尔·孔勃(E.Combes)上台组阁。在竞选纲领中, 激进派就曾宣称:“镇压教团, 将宗教财产世俗化,取消用公共资金向教士支付津贴, 我们要将这重要的自由主义信条付诸实践—— 一个自由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国家中的自由的教会。”激进派的执政预示着政教关系的走向。孔勃在其施政纲领中,秉承了激进派的精神, 声称要继续执行由他的上任制定的针对教团的结社法及教团学校的世俗化政策,以捍卫共和国。新政府很快宣布,禁止天主教会擅自在法国国内设立学校,并陆续关闭大批教会学校;还以法令形式,关闭一切未获得政府准许擅自办学的修道院。②在孔勃眼里,宗教教育是决不能容忍的“害人事业”。在对教团结束审批之后,政府派出的警察和宪兵迅速关闭了未经批准的教团的会所,它们的学校也在学期结束后被关闭。到1903年10月,约有1万所教团学校被关闭。1904年7月7日, 在孔勃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所有教团成员从事任何性质的教育活动(为殖民地和外国培养教师,受教育者为成年人的教会学校除外),他们的学校在10年内被逐步关闭。在孔勃政府的冲击下,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利益损失惨重。1904年7月,法国政府同罗马教廷断绝了外交关系。1906年,法国宣布实行政教分离政策。③David Thomson, France: Empire and Republic, 1850—1940,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8, p.261.
1906年,法国驻华公使通知清政府,此后只负责保护本国教徒,放弃对其他国家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教”权力。1907年法国政府又连续颁布法案,针对天主教会的财产作出处置。由于法国孔勃政府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改革措施,罗马教廷宣布与法国彻底决裂。此时为清政府末年,正值“庚子事变”④庚子事变:也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清朝末期。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由黄河北岸山东、直隶两省农民首先发起的武装暴动。1900年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农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中国基督宗教信徒与西方人士,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同年6月,清政府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且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八国组建远征军引发“八国联军”之役。之后,中国当时正处在另一个时代关口,故未对欧洲的教俗纷争、政权更迭作出反响。1912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新旧制度交替。1914年,萨拉热窝刺杀(Sarajevo Assassination)⑤萨拉热窝刺杀:1914年6月28日发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当天为塞尔维亚之国庆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一名隶属塞尔维亚“黑手社”的波斯尼亚青年学生)枪杀。这次事件导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遂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与同盟国交战4年,直到1918年终止。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后利益分配及奠定战后的世界格局,召开了“巴黎和会”。作为协约国胜利一方的意大利坚决阻止在这次世界会议上提出“罗马问题”,以避免其他国家通过这个问题向本国施压。同时,“巴黎和会”对于中国利益的巨大损害,激起了国内民众的义愤,导致五四运动爆发。
这时,罗马教廷在意大利政府的掣肘下,无力在欧洲取得发声机会,于是转变策略:一方面,将原本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之下的东方教会部(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Oriental Churches)⑥东方教会部,1862年由教宗庇护九世创立,附属于教廷传信部。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教廷圣部(Roman Congregations)。①教廷圣部:罗马天主教廷机构,负责罗马教廷中央的行政事务,是罗马教廷的执行机构。1588年,由教宗西斯笃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在位)创立。教廷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试图将解决“罗马问题”的途径与渠道转换到东方来;另一方面,1919年起,罗马教廷还展开了一系列动作。这年11月,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位)发布《夫至大》牧函,②牧函(Pasroral Letter)是罗马天主教主教写给其他教区内神职人员或教徒的公开函件,具有教令性质。以作为对于在华部分教案的回应。③比利时籍遣使会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1940年)于1917年上万言信于罗马教廷,希望“中国教友能够享有应当的权利和义务”,而“国籍”成为中国天主教的最大阻碍。他认为法国在华“保教权”对中国和罗马教廷双方都有大害。该信由汤作霖神父带往罗马,但迟迟未得回复。直到1919年《夫至大》牧函发布。虽然《夫至大》牧函针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的天主教会,但是其中提到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天主教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见赵雅博编:《雷鸣远神父传》,台中:天主教小兄弟会,1990年,第327页。《夫至大》牧函的首句便言明:“夫至大至圣之任务”(牧函也因此得名——引者注)即是“宣扬福音于万民”。教宗本笃十五世指出:首要的传教目标是拯救灵魂。他斥责传教士划分畛域的行为,是“将‘天主的葡萄园’视作‘私有财产’”;④《夫至大》牧函中文版见《铎声月刊·“夫至大”通牒专号》第3卷第12期,1944年12月。提倡将信仰置于传教的中心,而打破国籍、修会和等级的藩篱,就是牧函中的首要问题⑤刘贤:《夫至大牧函及其中国命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9期。——“诚以天主圣教既属至公,公则无一国民,无一邦族,可据为私有而令他族”“圣教会是天主的,是普世共有的,不属于欧美,亦不属于东亚,这正是公教以所以为公”。⑥成保禄:《过夫至大通牒二十五年的几句话》,《铎声月刊·“夫至大”通牒专号》第3卷第12期,1944年12月,第244页。在“巴黎和会”后国内掀起的五四运动伴随下,中国民族觉醒的意识提高了。罗马教廷为契合中国实际情况,并为自身利益服务,在大范围采取行动,以提倡培养天主教“中国化”为口号,试图发出能够影响欧洲的“罗马声音”。
1922年实质性的进展出现了。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年)⑦刚恒毅,意大利人,1876年生于乌地纳,有艺术天赋,16岁进入修道院。1897年进入罗马大学。1899年晋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战地医院任服务司铎,建立弃婴医院,收容孤儿。担任署理主教时,刚恒毅积极参与儿童保护及慈善事业,要求意大利政府接济儿童,不要轰击慈善机关。1921年,正式升任主教,并且祝圣。接教廷传信部部长王老松(Willem van Rossum,1854—1932年)通传,以天主教罗马教廷宗座代表(Delegatus Apotolicus)的身份抵达中国。其来华的使命,正是贯彻和执行《夫至大》牧函的精神。刚恒毅将自己的使命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作为宗座大使,其使命应当是纯宗教性质,而不带世俗政治色彩;第二,尊重中国政府,绝不为外国利益服务,宗座大使只代表教宗;第三,罗马教廷不干涉政治;第四,罗马教廷在中国不谋求帝国主义式的利益,中国应当属于中国人民;第五,天主教是普世的宗教,主教应该在当地的中国人中选出,外籍教士应该在结束开辟教区、完成培训神职的任务以后去到别的地方,筹备建立新的本地教会。⑧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主徒会出版社,1980年,第56-57页。

图2 1926年,6位中国神父受到教宗邀请前往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们举行祝圣仪式
紧接着的1924年,刚恒毅在上海徐家汇主持召开“第一届中国教务会”,①该会议的名称由罗马教廷决定,是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作出了极具突破性的重大决定:针对许多教堂为寻求法国庇护,经常悬挂法国国旗的事实,会议明确“教堂内不得悬挂国家国旗和国徽”;针对外国利益集团在华分割势力的乱象,会议明确教省的划分必须依照中国国内行政区划而定,并以主教公署所在城市命名;“传教士是由其所属修会由宗座直接或间接派遣的司铎,为非教友宣讲基督信仰,并为此在传教区的代牧领导下,建立起奉教者的信德”,这完全是为了告诫传教士只有教会而非其母国是真正的长上。②参见顾卫民:《刚恒毅与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五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在刚恒毅看来,“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是为了恢复“使徒式传统”——传教事业不能以强权为后盾,然而事实上19世纪以来的传教路线,同这个“爱和德行”的传统相悖。显而易见的是,自“巴黎和会”后的一系列来自罗马教廷的动作,都是对法国在华“保教权”的解构。通过削弱“法国声音”,来唤醒人们的“教廷意识”,从而为“罗马问题”的天平向教廷方向倾斜作出铺垫。罗马教廷借助东方,来激发对于宗教历史传统的回顾和敬仰,输出“罗马声音”,唤起“罗马意识”,从而帮助解决其迫在眉睫的“罗马问题”。
1929年,“罗马问题”的解决出现了重大进展。教宗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签署了《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教宗承认意大利王国,承认罗马为其首都,意大利各主教就职时必须宣誓尊重国王和《拉特兰条约》;同时,意大利王国正式承认,教宗拥有独立的梵蒂冈城国(Vatican City),教宗为政教合一的、合法的国中国之君主,有派遣和接受使节的权力,并在罗马城享受治外法权。梵蒂冈四周由高墙与罗马城隔开。历经60年,“罗马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刚恒毅提倡本地化策略,中国国籍神父的数量有了明显上升。但此时徐家汇的法国耶稣会事业,既无法得到教廷的支持,又经历了母国宗教势力的极大削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正在此时,又有一支法国天主教的女性修会来到了徐家汇的一隅,这就是“善牧会”。
三、善牧院的历史贡献
上海徐家汇善牧院(Hospice of Sisters of Good Shepherd), 1933年10月由法国善牧会修女创建于贝当路910号(今衡山路910号)。善牧会(Sisters of Good Shepherd)③参见“善牧会”辞条,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516页。于1825年创立于法国巴黎,是罗马天主教的女性修会,旨在教养和保护误入歧途、无家可归的青年妇女。徐家汇善牧院的建立颇有意思,它虽属于罗马天主教在华的慈善机构,也处在徐家汇肇嘉浜流域,可是从地图上看,却在两河汇流的另一个三角洲上,而并不在新耶稣会徐家汇社区的建制内。实际上,徐家汇善牧院的确切地理位置的确不在徐家汇,而是在法租界。
20世纪初,上海法租界已经完成了其3次扩张。1914年(民国3年),法租界获得越界筑路权,租界实际范围扩至北自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南自斜桥,东自麋鹿路(今方浜西路)、肇周路、斜桥,西至徐家汇畔。法租界从黄浦江自东向西,共设4个区——霞飞区、中央区、福熙区和贝当区。而贝当路正是法租界贝当区的尽头。一旦过了贝当路,便是河渠纵横的徐家汇地区。那么,上海法租界计有1.5万余亩地之大,为何要选在贝当路创建徐家汇善牧院呢?
如前所述,从空间格局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来自法国巴黎的新耶稣会在徐家汇的地理规划——肇嘉浜东西两岸的男女社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均认真承担起相应的宗教功能和社会服务。善牧会,作为罗马天主教的女性修会,若安置于耶稣会徐家汇社区的空间,是再合适不过的。而作为一支法国血统的女修会,其最佳的安置地点,自然是肇嘉浜东岸。因为东岸的徐家汇圣母院已经建成且具有相当规模,如果善牧会加入其中,一定能更加完善其指导修女和服务女性的职能。但是,必须要加以强调的是此时的时间坐标。1933年,徐家汇宗教社区的“天主教性”被高调申明,特别是1922年刚恒毅作为罗马教廷宗座大师来华并于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天主教教务会议,明确了所有修会的“教廷属性”,要求不再强调天主教各修会的国别性。从这次会议就在徐家汇召开来看,其意味十分明显:迫于当时“罗马问题”的世界背景,罗马教廷为了输出“罗马声音”而以恢复“使徒传统”为口号,通过强调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地化策略,淡化徐家汇新耶稣会所作事业的法国属性。

图3 1933年的徐家汇善牧院
失去徐家汇主导权的法国天主教势力,只能选择在距离已经建成的徐家汇社区仅仅一河之隔的贝当路建起善牧院。其位置的选定,明显是依旧为了遵守新耶稣会徐家汇社区的男女空间设置(接近女性空间的一侧,而事实上又被河道隔开,处在法租界一端)。
徐家汇善牧院创立时,已经是新耶稣会徐家汇社区的中晚期,法国势力逐渐式微并退居租界地带。徐家汇天主教社区因为其恢弘周全的宗教建筑、设施和服务,而被称作富有浓厚罗马教廷色彩的“远东梵蒂冈”。对于罗马教廷而言,他们的“罗马声音”终于成功地传播到远东,并在中国上海的徐家汇得到了回响。但是对于徐家汇而言,整个法国新耶稣会历时数十年缜密规划精心营造的社区,其典型的法国特性成为了一种累赘、一种多余,又不免让人唏嘘。可贵的是,法国天主教修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往上海的使命,他们选择法租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以宗教慈善和社会服务为重要窗口,为处在战乱苦难中的中国送来福音和希望。徐家汇善牧院与新耶稣会徐家汇社区之间的若即若离,正是罗马教廷与法国天主教修会之间关系的写照。
善牧院建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法租界宣布为中立,租界因而免于战火纷扰。然而整个上海,特别是非租界区,则战乱迭起。建立之时旨在教化妇女归正的善牧院,加入了救济难民的队伍,为战乱中的百姓提供衣食,更重要的是设法帮助他们进入法租界,兑现对他们“生”的承诺。由于善牧院救助上海难民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们获得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资助。善牧院于1947年扩大规模,增加收容人数,且不再设有对女性孩童的年龄限制,收留了许多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童。善牧院内设有小教堂与修女院,有中外修女十几人,她们平时向妇女儿童进行宗教与识字教育,同时传授缝纫机、刺绣、音乐、美术等手艺。由此可见,虽然徐家汇善牧院在法租界单处一隅,属于罗马天主教修会,但她们长达60年的慈善事业实际上与徐家汇圣母院是一致的,都在女性救助、女性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实在而可贵的贡献。
1949年后,徐家汇善牧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于1955年停办。1956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国妇幼”)迁入其址。今天,当年善牧院的部分事业已经通过“国妇幼”而发扬光大了,但历史依旧令人感慨。从世界史的视角看,徐家汇善牧院,是“罗马声音”在上海的体现;从上海历史的视角看,它是迄今为止,徐家汇地区仍保持原先基本功能的仅有的几个宗教场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