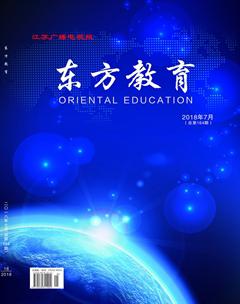儒家祭祀内涵与时代价值
摘要:《论语》先进篇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体现儒家的鬼神观和祭祀精神。随着儒家三祭之对象由鬼神变为了人,也使得鬼神和祭祀有了人文之意。今日我们寻常百姓和国家举行祭祀英烈活动不得不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祭祀精神的时代继承和发展。祭祀对于孝道的传承和整个民族英雄情怀的形成以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今日仍要重视祭祀之优良传统文化,崇德报恩,缅怀先烈祭忠魂。
关键词:鬼神祭祀祖先英烈英雄情怀
一、鬼神之内涵
在周朝,“鬼神分为四种,天神;地川;人死曰鬼,即祖;百物曰魁(即魅,俗称妖怪)。”[1]34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鬼神之指代有天地人怪,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四方百物,祖先等[2]450。鬼神之事,涉及祭祀之礼节。所以鬼神的内涵包括了古代祭祀的对象,基本是天、地、人。后来儒家三祭之礼: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3]95也因而鬼神具有了人文之意,这当然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把对鬼的恐惧和神的崇拜,转向了对已经故亲人祖先和圣贤的敬重和敬仰。天地是万物之本,祖先是类之本,圣贤是文化之本[4]23,所以都需要后世的祭祀以表达感恩之情。
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两种解释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问怎样去事奉鬼神。孔子说:“没能事奉好人,怎么能事奉鬼呢?”关于孔子对季路的问鬼神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解释是何晏认为的“鬼神问题难以言明,语之无益。”[5]137,一种以朱熹的注疏中所理解的“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这两者解释对季路有无获得结论的理解不尽相同,何宴认为孔子没有告之季路,而朱熹认为孔子实深告之季路侍生的道理。
1.“鬼神问题难以言明,语之无益。”
何宴所注认为,鬼神之事情本身难以述说清楚,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季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直接主题在他看来说来是没有益处的。那么为何没有益处?首先,这需要从鬼神之事所涉及的政治实践来思考。在春秋时期鬼神祭祀之礼不仅是自身对祖先和神明的祭祀如此简单。皇帝是通过祭祀之大礼去感恩天地之神,祈祷风调雨顺,百姓安康。“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所以,事鬼神的祭礼对于维护现实有序的规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孔子应该不会太多涉及判定鬼神祭祀之事。其次,维护社会伦理的功能。如孔子所言“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6]474-475可以看出,如果他对鬼神之事做判断,对社会现实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百姓之间的伦理孝悌,尊卑有序的传统道德的现实影响。若人死后有意识,子孙则生前不好好侍奉把这份孝以十分隆重的祭的礼节来代替,或人死后无意识,子孙们就不举行祭祀之礼,那么显然这两者都不利于社会风俗和礼节的传承。所以孔子对于这个事不敢妄下结论。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7]178既然科学无法去证实,运用理性也难以辨别,有何必盲从或者否定呢?所以孔子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2.告之“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之道理
“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8]126朱熹认为,孔子实际上告诉季路道理:如果不能诚信孝敬现世之人,那么这个人也不会在亲人已故后能尽祭祀之礼。首先,朱熹从生死之顺序而出发,推敲孔子告诉季路的道理,要先学会生的道理,学会事情人的道理,才到事神之礼节。学礼节也必然是遵循顺序,现世之人都不对他尽孝心,何会懂得死后的祭祀之礼节。如范氏所说“事人者,为臣则忠,为子则孝,则忠孝可以事鬼神。”[9]其次,从儒家的孝的道理出发,告诉季路,尽了事人之道,也就相当于尽了事鬼之道。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孝文化,孝文化事仁爱的起始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离不开以血缘之亲凝结的孝。孝的表现在生死上,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0]2462在这个意义上,祭祀可以说是孝的延伸——由生延伸到死。
三、儒家祭祀精神之时代价值
随着儒家三祭的演变为天地、祖先和圣贤,儒家的鬼神观有了人文意义。对今天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儒家重视祭祀,往往祭祀的是人,而不是神。冯友兰先生认为,祭祀崇德报功,祭祀的对象是各种人如木匠供鲁班,都是对各手艺开拓者的报恩。[11]即使把人当神敬是理性的而不是迷信的。今天的祭祀传统节日如中元节、清明节等以及祭祀之礼的继承,并不代表我们相信鬼神的存在。我们更愿意相信科学,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祭祀就是一种反科学的迷信之行为。我们应该学习孔子對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不亵渎,并传承今日祭祀之优良传统。
(一)人民重视祭祀传统节日,缅怀祖先报恩情
首先,追思念。今天我们百姓之家的祭祀主要是对亲人祖先的礼节如清明节和中元节。特别是清明节落雨纷纷似乎都在表达着我们的思念之情。这些祭祀节日的存在不代表我们相信人故之后变成鬼和神,而是一种孝心的延续。“葬祭之礼......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乃更见其情意之真。”[12]17我们通过祭祖来表达思念。因怀念所以有礼。因为祖先是我们生命之本,所以怀念过往。当祭祖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一代人对上一辈人的思念,这是人类情感的最原始最真诚的表达。这也是抒发出爱的重要表达方式,祭祖中每个人心中的画面也许不一,所求也不一,心中情感的表露形式也许也不一,有人流泪,有人心中感慨万千,有人忙前忙后,但是最普遍的情感就是一种怀念,念亲人,念亲情。
其次,报恩情。祭祀祖先可以让有血缘之亲的亲族之间感受亲情,懂得感恩。除祖宗之外,人之所以祭祀诸神祗,亦皆报本反始之义。[13]201祭祀中我们清理树枝,打扫杂草,鞠躬跪拜,是一种崇敬之情,这会在家族中青少年的心里留下懂报恩情的道德感受,启示子孙后代懂的去孝顺现世的亲人。报恩孝顺是传统美德,当青少年接受到这些润物无声的道德情怀的时候很大程度可以激励他们在生活中外化为对父母亲人的孝敬之情,这也算是对祖先的报恩之又一表现。在祭祀中对天地、祖先的敬仰和报恩之情,是一种孝道的润物细无声的传承之道,这样的情感与道德的传承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领悟生活之道。在祭祀中,面对死与生,可以激励自己在世之人好好生活。当我们生活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时常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着。当我们面对故去的祖先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懂得他们给予了我们生命,我们应该在现世好好生活,不求建功立业,但求平凡中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不求见载史册,但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有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轻生,不浮躁,为生活而活,这就是一种孝,这就是对祖先恩情的最大回报。
(二)国家重视对英烈的纪念活动,缅怀英烈祭忠魂
儒家祭祀的对象曾有天地,祖先和圣贤,因由他们有着对国家和人民之本的原始意义,所以以祭祀崇德述恩。今日的我们祭祀对象拓展到英烈,同样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因而英烈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脊梁,新中国站起来了得于他们的流血付出,他们的恩情亦如古之天地对于万物之生灵,祖先之对人之本,圣贤之文化之用。所以儒家祭祀的时代价值应该拓展到英烈的缅怀活动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烈们是脊梁,是支柱,是魂。国家的和平,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也因为这个使命他们奉献生命,他们身上彰显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英烈的缅怀纪念活动,如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等。他出席各种活动通过讲话希望倡导整个社会形成崇尚英雄的风气。
首先,缅怀英烈。回顾历史,多少先烈站在敌人最前线,用肉体之躯抵挡敌人的子弹,不惧牺牲,宁死不从,保卫祖国。这是“精忠报国”精神的最好体现。今日我们重视举行公祭日、到烈士墓前祭祀典礼,缅怀英烈。我们抱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感恩英烈的付出带来了我们国家的和平,给予发展的条件。饮水思源,所以我们国家不会忘记英雄。崇尚英雄的氛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之柱。国家对英烈的关怀和缅怀可以讓人民群众心中更加崇敬英雄,学习他们无私奉献,胸怀祖国的英雄情怀。
其次,捍卫英雄,珍惜和平,复兴祖国。缅怀英烈,可以让我们回顾历史,铭记历史,珍惜今日的和平,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英雄,不能让英烈们既流血又流泪,不能抹黑虚无英雄。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英雄,那这个民族将没有希望。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英雄是一个代名词,他们不畏险,不畏难,心中以国家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为中心。在抗战年代的英雄为了祖国的和平而流血,今日的英雄为着祖国的复兴而奋斗。许许多多的人民公仆倒在了一线,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为着祖国科技的创新坚持到最后一刻,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日日夜夜奋战在工作岗位上。这些在和平年代平凡的英雄们同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重。
四、结语
曾几何时,我们在中元节,清明节等祭祀节日的时候去思考,人死后是否有意识,他们是否会化为鬼在地下还是上天为仙。如果不存在,为何我们如此重视在节日里一个家族的祭祀之礼,拔草除树,鞠躬跪拜?我们进行这些活动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把祭祀对象赋予了人文意义。我们是因为不忘本,祖先对家族生命之本,英雄对国家安宁之本;知晓生活之不容易,和平之不容易;知道感恩对于维系一个亲情和国家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性。所以通过祭祀,祭祀祖先,祭祀英雄,给予后世的我们带来孝与报恩之传统道德的道理。中华民族的任何传统节日都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拓展其内涵,丰富其形式,不忘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
[2](唐)贾公彦疏,彭林著,[清] 郑玄注《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蔡德贵著.五大家说儒[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4]蔡仁厚著.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5](魏)何晏集解. 四库家藏论语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刘向著.向宗鲁校正.说苑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刘宝楠: 论语正义[M](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G]十三经注疏: 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论语新解[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简介:罗培玲(1993-),女,广西梧州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