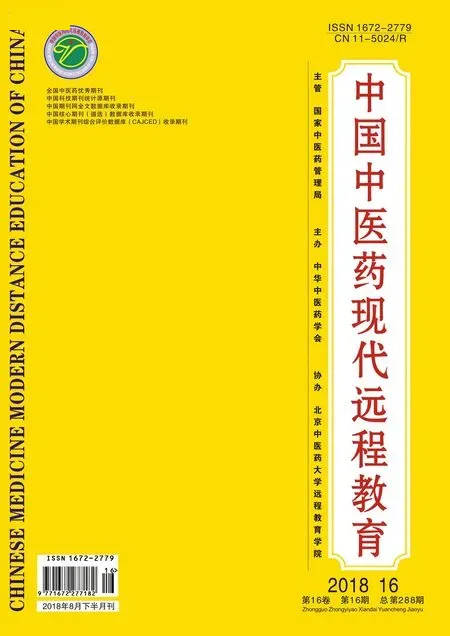我国动物药本草考证研究进展※
肖洪贺 杨 洋 高 佳 许 燕 段双蕊 谢 明
(辽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动物药是中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血肉有情之品”“行走通窜之物”之说,动物药备受历代医家所青睐,其功效常常是植物药、矿物药所不能替代的。清代医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有云:“动物之功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而且具有攻性”。温病医家叶天士言:“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可见动物药确有一般植物药不可比拟的功效[1]。
但由于古代文字、刻板、绘图、印刷等条件限制,一些传世的本草著作成为孤本,随着朝代更替,时代变迁,各个医家在相互印证、抄录、翻刻的过程中,真伪相杂或篡改原著时有发生,加之动物药原动物基原复杂,古代分类学不够完善,致使本草所载的动物药名实不符,或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或一名数物,或一物数名,严重影响动物药的科学研究及临床应用。为此,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医药学者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本草考证和资源普查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查阅CNKI中近50年关于动物药本草研究的文献,并结合现代和古代本草学著作,将动物药本草学研究情况加以综述,旨在总结前人宝贵经验,为动物药的本草考证及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动物药本草论著
1.1 古代主流本草中动物药收载情况 动物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远在战国时期《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中便有关于麝、鹿、犀、熊、牛等药用动物的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动物药67种(18.4%)。公元6世纪初,梁代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名医别录》的365种药物,编撰成《本草经集注》,共记载药物730种,其中动物药113种(15.5%)。公元657年(唐显庆二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共载药物850种,其中动物药128种(15.1%)。公元973年(宋开宝六年),由刘翰、马志等编撰的《开宝本草》,共载药983种,其中动物药达149种(15.2%)。公元1108年(宋大观二年),由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共载药物1746种,其中动物药达326种(18.7%)。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61种。清代赵学敏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共增药物706种,其中动物药122种[2-4]。从以上的主流本草中不难发现,动物药种类随着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从最初汉代的67种,增加到清代的近600种,足见对各代医家对动物药的重视。我国历代本草著作动物药收录情况见表1。

表1 我国历代本草著作动物药收录情况
1.2 现代本草中动物药收载情况 动物药的资源考察、文献整理工作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半个世纪的实地调研和系统的考察,采集了大量药用动物和动物药材资料,并编撰了一系列动物药专著。主要的专著有《中国药用动物志》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 《中国海洋药物辞典》 《中国动物药志》 《中华本草》 《动物本草》 《中国动物药资源》,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保护药用动物资源、扩大新药源,开发中药新药,丰富现代药用动物学内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5-6]。我国现代本草著作动物药收录情况见表2

表2 我国现代本草著作动物药收录情况
1.3 药典中动物药收载情况 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编撰的《中药大辞典》 (2006年第3版),收载药物6008种,其中动物药740味,占12.3%[7]。2005年版《中国药典》[8]共收载药材553种,其中动物药52种,占9.4%,收载中成药制剂570种,含动物药的制剂达165种,占28.9%。2010年版《中国药典》[9-10]共收载药材641种,其中动物药52种,占8.1%,收载中成药制剂1071种,含动物药的制剂376种,占35.1%。2015版《中国药典》[11]共收载药材618种,其中动物药51种(紫河车未被收录),占8.3%,收载中成药制剂1491种,含动物药的制剂达461种,占30.9%。近3版《中国药典》收载动物药的数量基本不变,但含有动物药的成方制剂数量呈现大幅度增加。中药配伍是中医用药的特色和优势,被药典收录的动物药成方制不断增加,能够说明动物药越来越受到临床大夫的重视和青睐。2015版《中国药典》收载动物药见表3。

表3 2015版《中国药典》收载动物药
2 动物药本草考证研究
本草考证一词,最早由本草学家谢宗万先生于1963年提出。他指出,本草考证就是历代本草所收载的药物从品种方面加以考证,找出古人药用的正品。谢宗万先生在《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12]中,对本草考证做了定义:中药品种的本草考证,是通过历代本草文献研究,结合当今药材市场调查鉴定,核实古今用药品种的延续与变迁,考订出传统药用正品和法定正品,使古为今用,达到正本清源,辨明是非,澄清混乱,保证用药安全有效的目的。谢宗万先生认为:“考证并从而确定历代本草所收中药材的原植(动)物品种,不但对如实反映用药的历史事实,研究不同历史时期药物品种的变迁情况有所帮助,而且特别对正确地继承古人药物生产和临床用药经验有现实意义”。
关于动物药本草学考证研究,参考的古籍文献除了前文提及的《神农本草经》 《本草经集注》 《新修本草》 《开宝本草》 《证类本草》,还有《名医别录》《本草图经》 《药性论》 《雷公炮炙论》 《本草蒙筌》《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备要》 《本草便读》等专题类本草。纵观本草考证专家学者的论著,主要从药用动物的名称历史沿革、原动物基原、功效主治、性味归经、采收炮制、配伍、用法用量等方面,对历代本草中动物药进行深入考证研究,或分析动物药品种混乱产生的历史原因,或梳理道地药材地域变迁历史,或归纳整理动物药药用特点,最终确定动物药的正统基原,为其现代研究提供文献依据。
2.1 环节动物门 张卫[13]、刘晓帆[14]通过系统的本草文献梳理,对水蛭的基原进行了详实考证,指出传统中医使用的水蛭具有生于水中、个头较小且能吸食人及牛马血的水蛭的特点,结合《中国植物志·环节动物门·蛭纲》中关于水生吸血类水蛭的记载,确定具有以上3个特性的水蛭的品种有2个属8个种,考虑我国古代医疗活动的地域因素,最终锁定古代沿用的正品水蛭为日本医蛭Hirudo nipponia Whitman、丽医蛭H.pulchra Song、南京牛蛭Poecilobdella nanjingensis sp.Nov.、菲牛蛭P.manillensis(Lesson)以及湖北牛蛭P.hubeiensis Yang 5个品种,而《中国药典》收载的水蛭为水蛭科动物蚂蟥W.pigra Whitman、水蛭H.nipponica Whitman或柳叶蚂蟥W.acranulata Whitman的干燥体,经与《中国动物志》对比,发现药典所载的水蛭科动物蚂蟥W.pigra Whitman和柳叶蚂蟥W.acranulata Whitman应分别为黄蛭科 (Haemopidae Sawyer)宽体金线蛭W.pigra Whitman和尖细金线蛭W.acranulata Whitman,水蛭H.nipponica Whitman为《中国动物志》中的日本医蛭Hirudo nipponia Whitman。尽管与古代药用品种有所不同,但药典所载的水蛭科动物蚂蟥W.pigra Whitman和柳叶蚂蟥W.acranulata Whitman均含有水蛭素,故张卫等建议《中国药典》保留原有日本医蛭H.nipponica Whitman,增补菲牛蛭P.manillensis(Lesson)。
2.2 软体动物门 我国动物学家邓明鲁教授在本草考证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其带领团队对《本草图经》中的动物药进行了梳理、考证。邓明鲁等[15]对《本草图经》中牡蛎、海蛤、蛞蝓、石决明、真珠、乌贼鱼、紫贝、马刀、贝子、甲香等20中软体药用动物的原动物基原进行了考证。章明珠[16]、江波等[17]对虻虫的原动物基原进行了考证,确定虻虫的原动物基原为复带虻Tabanus bivittatus Mats,药典记载与本草考证结果相符。蔺爽等[18]对海螵蛸的使用方法、功用主治、临床应用和配伍规律等进行了考证。
2.3 节肢动物门 刘向东等[19]对《本草图经》中蝼蛄、蜣螂、雀瓮、蚕、衣鱼、蜂蜜等21味药用昆虫的原动物基原进行了本草学考证。秦燕等[20]对蚱蝉、蝉蜕及蝉花名称的沿革、本草记载及基原考证等进行了考证,明确了蚱蝉和蝉蜕的原动物为蝉科昆虫黑蚱Cryptotympana pustulata Fabr.,蝉花的原昆虫为蝉科昆虫山蝉Cicada flammata Dist.。律光明等[21]对五倍子的考证指出,五倍子性酸涩寒,具有较强收敛之功,本草中的功效记载有解毒消肿、生肌敛疮、乌发、养血调经等,炮制方法以炒、焙为主。蔺爽等[22]对蜈蚣的功效主治、炮制配伍、用法用量等进行了考证,赵荣国等[23]对桑螵蛸的名称沿革、原动物基原及其着生植物进行了考证,李娜等[24]对全蝎的功用主治、临证应用、配伍规律、炮制方法等进行了考证。陈璐等[25]通过查阅古今中医药文献,对冬虫夏草的品种、产地和药性论述中存在的争议等进行了本草学考证。闻崇炜等[26]对僵蚕的考证,指出僵蚕基原最初为“食桑者,四月头番蚕,病风自死”,目前也可用白僵菌感染家蚕4~5龄幼虫制得。河南颖川和山东棣州是僵蚕的重要历史产区,而当前主产区为江浙、安徽、四川、广东等地,规格等级最初要求为“色白、条直、质硬”,后又增加了“断面光亮”及其它显微特征分析。谭承佳等[27]对蜣螂的考证发现,蜣螂在处方中常以蜣螂、推屎虫心、黑牛儿、大乌壳硬虫名称出现,结合《名医别录》中的“鼻头扁者为真”和《本草纲目》中的“鼻高目深、背负黑甲、身黑光、昼伏夜出、见灯光则来(趋光性)”以及推粪球的特性,确定其基原为金龟子科昆虫蜣螂Catharsius molossus(Linnaeus),与现药典记载相符。
2.4 两栖纲 肖井雷等[28-29]结合史书记载、形态学、遗传学、银带及同工酶电泳对哈蟆油原动物基原进行了考证,指出我国东北地区的林蛙有黑龙江林蛙(Rana amurensis Boulenger)、桓仁林蛙 (Rana huanrenensis Liu,Zhang and Lliu) 和东北林蛙(Rana dybowskii Guenther),哈蟆油的动物基原为东北林蛙(Rana dybowskii Guenther)。
2.5爬行纲 高士贤等[30]结合现代分类学观点,对《本草图经》中爬行动物爪婿、石龙子、鳌、蛤蚧、蚺蛇胆、金蛇、乌蛇、白花蛇等药物的原动物基原进行了考证。包华音等[31]对壁虎进行了名称、品种、产地生境、药用部位、采收与炮制、性味归经与功能主治等方面的本草考证。吴丹勇等[32]对《本草图经》中龟甲及秦龟动物基原做了详细考证,明确《本草图经》所载龟甲、秦龟二者实为一物。其龟甲的动物来源应该是乌龟属Chinemys和水龟属Clemmys多种龟类。林喆等[33]对乌梢蛇的考证发现,乌梢蛇的炮制方法主要有酒浸、焙、生用、粉碎、炒等。
2.5 哺乳纲 邓鸿等[34-35]对《本草经集注》中鹿及其药用部位进行了本草学考证,明确了鹿茸、鹿角并鹿角胶、鹿髓、鹿血、鹿肉和鹿脑的古籍出处以及性味功效,并确认“鹿鞭”与“鹿肾”并非同物异名,前者指鹿的阴茎,后者指鹿的肾脏。鹿的阴茎首载《备急千金要方》,称鹿茎筋;鹿鞭一词首见《医林幕要探源》,鹿的肾脏首载《名医别录》,称鹿肾。熊付良等[36]对《本草图经》中牛及涉及到牛的动物药如牛黄、牛乳等进行了考证。邓鸿等[37]对驴鞭进行考证,确认为驴的阴茎。林贺等[38]对鹿茸的功效主治、配伍、用量等做了本草考证,李娜、李冬、于淼、胡丽娜等对鹿角胶[39]、羚羊角[40]、刺猬皮[41]、穿山甲[42]、虎骨[43]的功效主治、配伍、用量等进行了考证。
3 结语
虫类药既有“虫蚁飕络”“行走通窜之物”之说,性喜攻逐走窜,通经达络,搜剔疏利,无处不至;又有“血肉有情之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特点,且资源丰富,而备受各代医家青睐[44-47]。国医大师朱良春善用虫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顽痹病症,收效显著,并有成方制剂益肾蠲痹丸传世[48-50]。此外,中医认为动物药具有蠕动走窜,搜剔络脉,松动病根之功,正对肿瘤病根深藏、药难透达的特点,在恶性肿瘤的治疗方面也有不错的疗效[1,51-53]。由于时代久远,动物药品种和药性理论方面均存在不统一甚至混乱的现象,加之动物药原基原动物种类繁杂,用药品种混乱现象相当普遍,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动物药的发展和广大患者的医疗体验。在今后的科研中,应加大力度继续做好动物药的本草考证研究,归纳、分析历代药性学说及其演变历史脉络,分析药材品种混乱产生的历史原因,结合现代分类学观点做到药用动物基原明确,名称统一,并运用现代技术鉴定其基原和品质,保障动物药市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