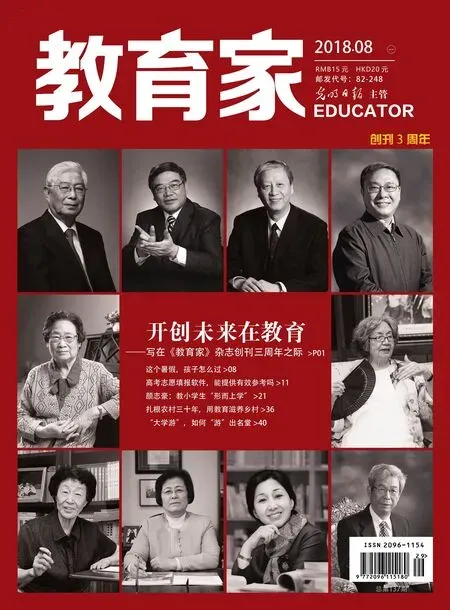自觉而快乐的阅读时光
文 |
我从1963年7岁入小学算起,到1998年取得博士学位止,跨度达35年,这个“学生时代”真不知从何说起。我愿跟大家说一说学生时代阅读的故事!
我于1963年在长沙新湖南报子弟小学入学,后转入衡阳中南路小学。到1966年三年级快结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套。我本来对学习是很上心的,老师也经常表扬。“文革”期间无课可上,我不愿意在学校浪费时间,开始逃学,常和一帮小孩捣蛋,如把黄蜂窝装进墨水盒放到局长案头。后来,母亲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你这小孩不教育将来不得了呀!”不久,我又在暗处用弹弓击中一个司机——他在批斗会上正摁着一位我所爱戴的长辈的脑袋。父亲在地委上班,朝不保夕,这事让母亲心惊肉跳,便把我送到长沙祖母处,这正中我下怀。
我从小生活在祖母身边,大家都批评祖母溺爱我,祖母很不服气:“他们哪里懂得教育!”后来我才知道,祖母清末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第一班读过书,以第一名考入,1912年元月以第一名毕业,她的毕业证书由校长朱剑凡亲手书写,是第一号。而管她这个班的,是徐特立。后来,她又当上了徐特立办的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的主事,当时也就20来岁。
她却并未“教育”我。吃完早饭,我就到附近的小人书铺租书回家,天天如此。这时,我家所在的学宫街已改名“学工街”,紧邻的蔡锷路也成了“大寨路”。干部们自顾不暇,许多小人书摊便冒了出来。
要说迷上看书,早可追溯到我1964年在新湖南报子弟小学时,有次看见教室隔壁一间房里好几个架子上全是彩色大幅连环画,字不多,还有拼音,情节生动活泼,后来便常去那。可惜1965年转学衡阳,就没这条件了。
后来字认得多了,看连环画不成问题。和祖母各拿一本读,真是其乐融融。除了租的,也有家藏的,如民国出版的《米老鼠开报馆》,有趣极了。还有许多书讲的是历史故事,如《夏完淳》《李定国》《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有讲外国故事的,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神秘岛》《海底两万里》《雪莱的故事》《托尔斯泰的故事》。一两年时间,大约读了几千册小人书。我最基本的中外文学历史知识,就是从小人书得来的。
渐渐地,小人书被当成“封资修”一扫而光,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每天除了读书取乐,还能干什么呢?没老师教,错别字自然不少。幸亏我读了便爱说,把“得宠”讲成“得龙”,把“捧出”讲成“棒出”,虽然总是笑声一片,却因之得以及时纠正。这时候来看没图画的“字书”,火候自然到了。
那时读书是要担风险的。老保姆总是说:“你莫净看些鬼舞尸起的书,危险咧!”鬼舞尸起,是长沙话乱七八糟的意思。当时我看的,却是一本红色儿童读物《微山湖上》。至于《莫里哀戏剧集》,只能关在屋里读。不能不说,我家躲过了抄家,是一大幸事。(见拙文《丹书铁券》)
就这样,当我把所能得到的白话文中外名著读完后,开始了文言作品的阅读。一开始,是读表哥表姐的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这种课本原文注释都在一面,无需翻页,十分方便。将中学六年的文言读完,再去读《镜花缘》《聊斋志异》什么的,就没啥障碍了。我现在的一点文言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我也爱读诗。一天,祖母拿了本七伯杨德豫译的《朗费罗诗选》给我,读到《人生颂》时,真是热血沸腾。外国人的诗,我只能背几首和一些零散的句子;唐诗宋诗清诗等,却能背下几百首。其实除了《长恨歌》《琵琶行》,我确实没“背”过唐诗,都是因为读书多,经常见面记住的。
这时候已经开始看学术论著了。由于到手的书有限,便反复读。如周有光的《字母的故事》,有趣极了,但印数仅300册。
有一天,我发现了祖父所著布面精装《积微居小学述林》,一问,才知道是专门给苏联人印的。这是一部文言写作的训诂学专著,我试着阅读,发现也能读懂,而且趣味盎然。我至今没弄明白怎么会对这本书感兴趣。而这,大约就是我研究古汉语的开端。
我还养成了厕所读书和边走边读的习惯。记得有次在大寨路上买了个葱油粑粑,店家竟然用线装书页来包它。我边吃边读,边上的娭毑(对老年妇女的尊称)说:“咯只伢子硬是只书憨子咧!”
中小学因为改为春季招生,延长了半年,1970年春,我小学毕业了。几年没到学校,中南路小学管事的说不能直接毕业,还要读个六年级。见到同班同学办离校手续,而自己“留级”,真是羞愧难当。
几年没学算术,上课有些跟不上。受祖母长期熏陶,如果功课不名列前茅,就无地自容。于是课后看教材再做习题,一周之内就赶了上来。再过一周,就考了九十多分。这使我认识到阅读对于学好数理化的好处。今后若干年,这一招屡试不爽。
1971年春,在我14岁半的时候,分到了郊外湘江边风景优美、藏书丰富的衡阳市第九中学。由于交通不便,这里成了“走资派”和“黑五类”子女比较集中的学校,老师也多是“政治上不过关”的。但这未必是坏事,在这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这中学总共四年(初中高中各两年)。这时候,武斗已经结束,上课也逐渐走向正轨(虽然经常学工学农学军,还挖防空洞)。那时升大学靠推荐,跟成绩好不好没什么关系。有熟人被推荐,考官问他:X=2,2X等于几?他瞠目结舌,答不上来却依然被录取。所以前两年,我还经常往长沙跑。几乎每学期都去,有的期中考试都被耽误了,但期末考试从没耽误过。每当这时,我便故技重施,看书,做习题,总能全班第一。开始,班主任彭老师还说两句,后来甚至让我给他姐姐捎东西。

1988年在武汉大学,杨逢彬(左)与同学合影
长沙的长辈为了我遇到问题时能有所请益,相继给我介绍了几位祖父的学生,他们要么住得不远,如易祖洛、易仁荄(他们是远房兄弟)、何申甫;要么常来,如廖海廷。跟他们,我又学到了不少东西(见拙文《我的四位家庭教师》)。
能找到的书有限,就开始买书了。七十年代初,上面发了一个极薄的16开解禁书小册子,有我祖父的《词诠》;近处的长沙古旧书店也恢复营业了。我买了竺可桢的《物候学》,读得烂熟。有次姑妈拿钱让我买肉,我花四块多“巨款”买了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
班主任让交班费用来订报纸,组织大家读报。这样,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在此之前,在家中床底下找出几十斤《参考消息》,仔细读了一遍。这份报纸是内部读物,每日精选世界各地的文章。这对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该有多震撼啊!九中图书馆新到了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书中讲杜甫家有“三重茅”,因而是“地主”。中华书局版的《史记》也到了,管图书馆的老师见我读得起劲,就一册册借给我。
也看数理化的书,还迷上了装矿石收音机,居然能收听十几个台。还用铁丝做捕鼠笼和能够连发的弹弓枪,劈竹子做弓箭,都很成功。
后两年,和同学感情日深,去长沙的次数减少了;参加了校田径队,短跑在全市取得了名次。这时,正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各种竞赛如火如荼。我得了作文比赛、俄文比赛第一名,绘画比赛也得了名次。只是后来作文比赛第一名作废,因为我的作文中引了柳宗元的《江雪》。老师同学都安慰我,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两年,除了和同学互相交换小说外,内部出版的国外小说也读过不少。一次,同学借来《白居易诗选》,转借给我,没想到它后来不翼而飞,为这事我差点挨了书主人的揍。这时候,我长沙的大姑去了街道图书馆做事,还办了市图书馆借书证,借书方便了不少,我也因此读了《太平广记》《山海经》等书。
我把我的学生时代,写成了一部自觉而快乐的阅读史。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我希望当今的父母们要给孩子玩的时间,不要带着他们在各种课外班中间穿梭。若想让孩子成才,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动手的兴趣是首要的。一旦这种兴趣养成,无论学文史哲,还是数理化,都不成问题。腹中空空,纵然会弹钢琴,能“高雅”得起来吗?胸无点墨,字写得漂亮,又有什么用呢?从前课业负担重,孩子想阅读没时间;如今下午3点就放学了,而家长还在上班。建议各校建阅读室,由一两位老师辅导学生读各种新奇有趣的课外读物。最初可讲故事(如《神秘岛》),紧要处戛然而止,同学们自然会到书中寻找答案。还可建手工室,培养孩子做各种东西,如装矿石收音机、望远镜、潜望镜,等等。在玩中学的东西,是记得最牢的。
——给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