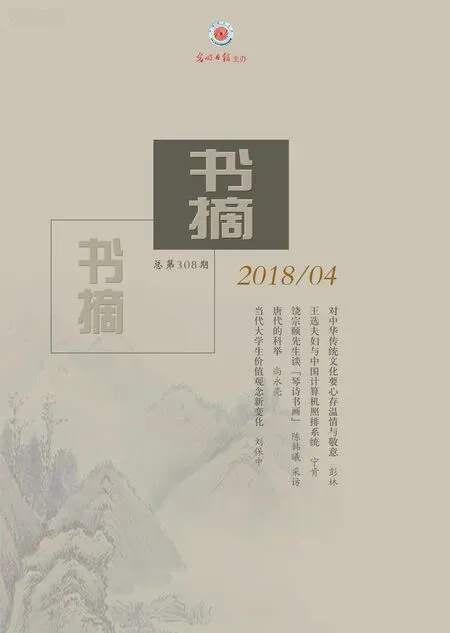唐代的科举
☉尚永亮
考试与竞争
在历时三百年的唐代历史进程中,科举考试也存在一个从高官士族逐渐向下层平民转移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从初、盛唐到中、晚唐宰相中进士人数所占比例即可以看出来。
据吴宗国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唐太宗时候的宰相,只有许敬宗一个人是秀才,房玄龄、侯君集两人是隋朝进士,其余的26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从高宗时候开始,宰相中科举及第者就逐渐上升,比例加大。高宗朝宰相是41个人,其中2人是隋朝的秀才,唐初进士及第者有9人,明经擢第者2人,总计科举出身者13人,已达1/4。到了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一下激增到20人,占了这个时期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科举出身的宰相中,有一些是平民子弟。这样一些平民子弟、下层士子考上了进士,而且当上了宰相,无疑对一般的士人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由此可以看出,科举正日益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而这样一些高级官吏又有很多是来源于下层民众的。到了中唐时代,这种情况就更突出了。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宰相等高官中科举出身者日益增多,科举也就受到人们格外的重视,一般的士子竞趋科举之路就势所必然了。
与前代的察举辟召制度比起来,科举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它对士子个人才能的判断,相对有了客观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由考察者带来的主观随意性。换句话说,就是在试卷面前人人平等。你有没有才能,通过你的考试就可以得到展现了。但是科举也有它不公平的一面,这就使貌似公正的科举留下了不公正的可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的是不糊名的办法,每个考生的名字考官都可以看到。那么考官对这个考生的个人喜好、亲疏远近等等,都会影响考生的成绩。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算考试完全是客观公正的,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但由于参加考试的人太多,而录取的名额太少,在士子的高期望值与考试的高淘汰率之间也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从初唐一直到晚唐都始终存在。
那么,唐代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呢?最起码是以千为单位的。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曾经对《唐摭言》的一段话作过一个分析和统计:学校与各地所送的生员,每年明经是1390人,进士是663人,两者总和已经超过2000了。每年2000的举子有多少能成为幸运儿呢?据《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进行统计,整个唐代进士考试共260次,其中登第的人数,在35人以上的仅26次,30人以上的共53次。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亨四年,录取了79人,录取最少的是永徽五年(654)、调露二年和永隆二年(681),各录取了1人。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登第人数最多和最少的都在初唐,这恐怕是科举处于草创阶段的情况。到了中唐,登第人数大抵被规定在20人左右。比如唐德宗在贞元十八年就下诏书说:“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之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据这个诏令,每年考试所收的人,明经不超过100,进士不超过20,那么举子被录取的机会就只有百分之一二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比起我们现在的高考,恐怕还要严格许多。

清状元及第“独占鳌头”玉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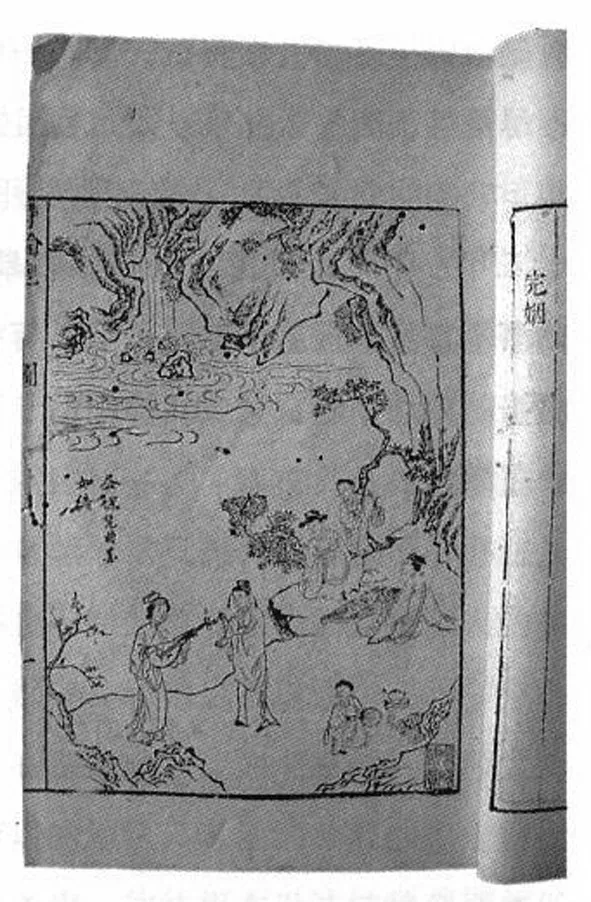
《古本戏曲丛刊》明末刊本《郁轮袍传奇》书影
由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者多,录者少,便注定了绝大部分人在过桥的时候,都是落水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士考试的竞争程度就大大加剧了。这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从举子们最初参加的县级的考试就已经开始了,此后还要经过州、府等等一系列考试,要经过京城礼部试和吏部的关试。每一场考试都对举子们的智力和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量。随着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摘得桂冠者充满了得意的笑,而落第失意者则充满了痛苦的悲。
同时,面对同样的科举考试,不同地域的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唐代的文化教育因地域不同,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状态。盛唐以后,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但南方地区在文化上却相对落后,许多南方士子要获得知识,参加科举考试,往往需依赖北方士大夫的传授和支持。这些士大夫,主要是被朝廷发落的流人、贬官。作为远离京城的蛮荒之地,南方诸地是这些贬官的天然流放处所。而这些贬官到了南方之后,最常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兴办教育,传播文化,奖拔当地优秀的后进之士。比如,张说被贬岭南,对韶州士子张九龄就颇为赏识,后来张九龄考中进士,一直做到了宰相。柳宗元被贬永州、韩愈被贬潮州时,不少士子向他们求学,经其指点,有些后来就登第了。
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特别是作为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就显示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此地文化发达,考生的水平自然就高,所以往朝廷举荐的名额就要多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粥多僧更多,僧多粥少的局面还是得不到真正的改观。在关中地区,又以京兆府和同、华两州表现最为突出。京兆府就是京城所在,同州是现在陕西的大荔,华州是现在陕西的华阴。这两个地方因为靠长安比较近,文化水平高,每年推送的举子也就非常多。举子多,优秀者多,竞争力自然就大。所以,每年这几个地区都要发生一场选送人才的激战。
更为激烈的竞争是争当“解头”。所谓“解头”,又称“解元”,是乡试中的第一名。凡是被州府作为“解头”选送入京的举子,几乎是未来必然的进士。这就像今天各地所谓的高考状元一样,因名列本地区之首,自然被各高校的招生者所看重,进入名校也就易如反掌了。正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在争当“解头”的过程中,竞争就非常激烈。《集异记》里记载了王维的一件逸事,说王维早有文名,又“性闲音律,妙能琵琶”,年轻时来到长安,游从于达官显贵之间,深受岐王的看重。当时有一个进士叫张九皋,声名也很大,而且受到了公主的举荐,人家都认为张九皋当年必能作为京兆府的头名被送到朝廷参加考试。王维也受应举,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岐王,请求歧王关照自己。岐王就对他说,公主的势力太强,不能跟她力争,我给你谋划一下:你把你以前写得比较好的诗誊录十篇,把你所拿手的较哀怨动人的琵琶新声准备一曲,后五日到我这里来。王维就依照他的吩咐这么做了。届时岐王又说,你如果直接拿诗文去谒见公主,公主是不会见的;如果你能按照我的说法,装扮成伶人,就大有希望。于是,王维就穿上岐王为他准备的锦绣衣服,带着琵琶,来到公主府第,混在一群伶人的前列。当时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年龄很轻,皮肤白净,非常帅气。公主一看,就被他吸引了,问这是什么人呢?岐王回答说:这是懂得音律的人。于是就让他“独奏新曲”,结果“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就有点儿惊讶了。一问曲调的名字,说叫《郁轮袍》,公主就更为奇异了。这时岐王就向她介绍了王维,说这个年轻人不仅懂得音律,而且会写诗,写的诗没有人比得上。等王维把他准备好的诗卷递上去,公主只读了几行,就惊诧地说:这些诗都是我以前所诵读的,原以为是古人所作,难道就是你写的吗?于是就让王维赶紧更换服饰,把他从伶人堆中请入客座。王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使得一座尽欢。岐王一看时机成熟了,便开口说道:如果今年京兆府能得此生为解头,那就给国家添彩了。公主就问:干嘛不让他去应举呢?岐王答道:如不作为第一名推荐,此生是义不就试的。听说你已经答应让张九皋做解头了,所以他不参加。公主就笑了,说那只是受人所托而已,现在王维这么优秀,如果要考进士,我当为你尽力。王维赶紧站起来道谢。于是,公主很快把考试官召到她的宅第,直接吩咐他予以关照。这样一来,王维就做了解头,而且一举登第。
这件事情很具戏剧性,从中可以发现京兆府在送人参加进士试的时候,内里还是有很多机关的。当然,据傅璇琮先生考证,王维之事不尽可信。因为张九皋是开元名相张九龄的弟弟,他是在中宗景龙三年(709)明经登第,王维则是在开元九年进士登第的,两者相差了十二年,不可能发生王维与张九皋争解头这样的事情。不过,尽管此事不真实,但这段文字仍然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它展示了文士争解头的活动,以及贵戚对科举的干涉。而在本质上,则反映了科举竞争之激烈。
进士的荣耀
前面说了,明经科主要考的是背诵,制举科主要是关乎政治,进士科与二者有所不同,要考时务策、帖经,还要考诗赋。而且这些内容也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唐朝初年,规定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这项规定自唐初至唐末没有什么改变。所谓时务策,固然着眼于现实问题,但有时也常从儒家经典或“三史”中命题。由于涉及的书籍多,难度不小,所以到中唐时就有人建议,让礼部事先告示天下,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以便考生有个准备,以此达到劝学的目的。说白了,这一建议其实是在替考生着想,帮他们缩小复习的范围,减轻学业上的负担。
时务策之外,还要试诗赋、帖经。据《唐语林》记载,早在高宗调露二年(680),吏部员外郎刘思立就认为进士只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这里说的“杂文两道”,是指一诗一赋,“帖小经”,是指《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诸经。刘思立的建议当时是否已被采纳?如果采纳了,持续了多久?这些我们还不大清楚。但到了盛唐时期,这二者都得到了落实。自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开始,朝廷对增考诗赋作了进一步规定,而到了天宝年间,试诗赋已成了定局。与此大致同时,开元年间,一方面增加了明经试“时务策三道”的内容,另一方面规定“进士改帖大经,加《论语》”。所谓“大经”,指的是篇幅较大的《礼记》《春秋左氏传》。
从上面说的这些情况看,进士与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又有相互渗透的特点。唐初的时候,明经只考经书,进士只考时务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经加试时务策,而进士加试帖经。这种情况说明,唐王朝在延揽人才时,也在强调他们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以避免单打一。换句话说,考明经的既要熟悉儒家经典,也要关注社会现实;而考进士的既要通晓时务,也要明于经术。
不过,进士与明经科最大的不同,在于考诗赋。能诗能赋,既需要丰厚的文学修养,也是一种综合的创作能力,某种意义上,它对考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以业文为主的考生们提供了一方可以驰骋才情的天地。由于进士科不大需要记诵之功,更偏重对现实的观察和解决方略,同时又能使考生在自己最擅长的诗赋方面一展才华,所以颇受考生和各方面的重视。终唐一代,进士科的地位节节上升,整个社会形成了对进士一科趋之若鹜的风气。
据王定保《唐摭言》的记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年间,而到了唐太宗、高宗时期,就已经很盛行了。当时社会上把进士推重为“白衣公卿”,或者称为“一品白衫”。进士科被如此看重,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参加考试的人就多;而人一多,无疑增加了考中的难度。难到什么程度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考中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会落第。以至于落了考,考了落,这样反反复复,有的人考了几十年,直至两鬓如霜,还奔走在往返长安的科举路途上。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当时人们总结出的一句话,这句话把进士地位的荣宠和艰难说得非常透彻。
普通的文人向往进士,是想借此谋得一个进身的阶梯。一些达官虽已位极人臣,如果不是进士出身,也会感到一种难于弥补的缺憾。比如高宗时候的薛元超曾经因为军功做到了中书令,但并不满足,曾对人说:自己这一生富贵过人,但确有三大遗憾,第一个遗憾就是“不以进士擢第”,没有进士的名号。由此可知,进士吸引人的,除了它能给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外,还在于它的名声,这个名声是任何官位都换不来的一种荣耀。从理论上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人的价值高低几乎是由他所任官职的高低来衡量的。但是在唐代,一个人,特别是文人价值的高低,至少有一部分是要由学位文凭来衡量,这个学位文凭就是进士这个头衔。这种情况恐怕在中国此前的历史中绝无仅有,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整个社会对文化和文化人的高度重视。
盛唐以后,进士科更是一枝独盛,如日中天,而明经科则逐渐衰落。士子们看重进士科自不必说,连士子的家长们也对进士科格外地重视。据《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唐德宗的时候,有一个身任给事中的苗粲,当时儿子要参加进士考试,他却突然中风,中风以后,说话都不清晰了,卧病在床,不能动,但是对儿子应举之事却非常关切。临试的时候,他的病又加重了。儿子就问,你病得这么厉害,我是不是要去参加考试呢?这个苗粲口不能言,但是手还能动,就示意拿来纸笔,颤抖着手,连写了两个最能表达他心意而且是笔画最少的字。什么字呢?“入”,两个“入”字,意思是一定要去考。因为重病,写出来的字也歪歪扭扭,但是在这歪歪扭扭的字里,却深含着苗粲对儿子参加进士考试的热切希望。当然了,苗粲也十分清楚,来年还有科举,儿子到时候还有机会去考,而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这一次有个三长两短,父子恐怕就再无相见之日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在苗粲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考试关系到儿子的前程,他希望儿子能够先中进士,再中制举,最后官至宰相。这是他的一个衷心的冀望。
对于进士一科,不仅举子的家长重视,帝王也非常重视。据《唐语林》记载,唐宣宗特别喜好进士及第者,有一种很浓重的进士情节。因为他是皇帝,不能去参加进士考试,怎么办呢?于是就在禁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身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却为此生不能金榜题名而感到遗憾。
进士考试对那些富家子弟来说,相对要便利一些,因为这些人家里藏书丰富,学习条件优越。但是对那些贫穷家庭的子弟来讲,就要艰难很多。而贫寒子弟立志于科举,实际上就是立志改变微贱的境况。比如,袁州宜春人卢肇少年的时候,家境非常贫寒,这种贫寒也成为他刻苦努力读书的一种动力。当年韩愈从潮州转官到袁州,这个年轻的卢肇就去向韩愈请教。到了文宗的时候,宰相李德裕被贬为袁州刺史,卢肇一看,机会来了,他有了一位投诗献文的非常好的对象,于是就把自己誊写的诗文送给李德裕。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他是通过门荫入仕的,也就是靠他父亲做过宰相而步入官场的,但对于贫寒士子急着通过进士科的考试来改变自身地位的心情,却非常地理解、支持。李德裕看着这个年轻好学的后生,感觉不错,就直接把他推荐给主持进士试的礼部侍郎王起。结果卢肇进京赶考,第二年就及第了,而且名位很高,是状元及第。李德裕这类奖拔贫寒士子的事例不少,以至于后来他被贬到海南崖州的时候,许多寒士禁不住留下了热泪。所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说的就是这些贫寒士人对他的感戴之情。
对于下层士人来说,科举除了是使自己跃入龙门的必经之路外,还是能为家庭带来实际利益的一个工具,因为一旦金榜题名,士子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去赋役等等一般人家所应承担的义务。在中晚唐穆宗、敬宗颁布的诏文中就有这样的话:“名登科第,即免征役。”登科之后,你不用去纳赋税,不用去服兵役。晚唐诗人李频在《长安感怀》诗里,带着一种茫然的口吻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不知道这一第什么时候我才能拿到,因为全家都在等着我进士及第啊!所以从表面看,士子是一个人去进行进士考试,但实际上,在他身上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
一般来说,人们都想和高门结亲,可是高门往往会有名登科第的亲戚,亲戚之间又少不了走动,没有科名的文人在那种场合所受到的冷遇和奚落就非常严重了。《唐摭言》记载了一位家在宜春名叫彭伉的进士,说他进士及第以后,亲戚和当地的官员都来祝贺,彭伉就坐在首席。彭伉的连襟叫湛贲,这时在县衙里当差,亲戚就不允许他上桌。作为连襟,连桌子都不让上,湛贲的妻子非常生气,就对她男人说:“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贲听了妻子的话之后,也感觉到很郁闷,于是开始发奋努力,进行科考前的准备,并且最后成了正果,在贞元十二年,他一举登第。他中第的消息传到家乡的时候,正在骑驴郊游的彭伉惊讶地竟然失神从驴背上掉了下来。当地人就开玩笑,说:“湛郎及第,彭伉坠驴。”由此可见,在科举考试的时候,举子不仅要努力苦读,还要承担来自家乡父老、当地官员或冷或热的目光。于是通过苦读登第,以求步入仕途,提高家庭地位,就成了士子们的共同愿望,也成为他们走向科举场地的一种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