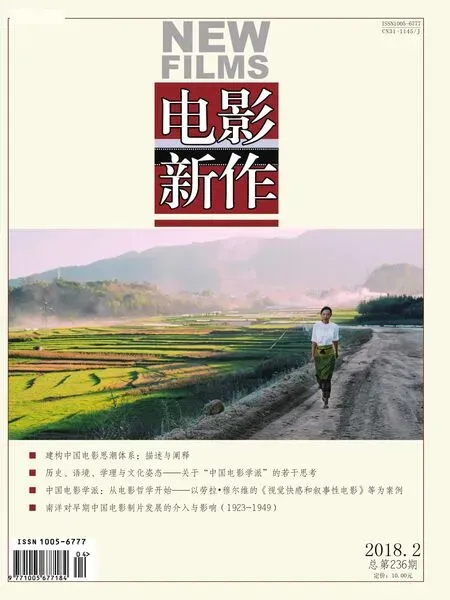荒诞现实下的生存追问
——《大世界》与城市边缘群像书写
王春晓
国内首部金马奖动画长片《大世界》(Have a Nice Day)是刘建的第二部动画长片。这部聚焦底层小人物的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一经亮相就获得了多方好评。《银幕杂志》称它“既能让观众感到发自肺腑的惊奇,也是充满活力、妙趣横生的后现代波普艺术之作”;在台湾金马影展上,评委们给予的颁奖词是:《大世界》反映了当代生活及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纵横交织的欲望,展现了极为犀利的批判视野。”英国《卫报》称它是“令人惊喜的发现、一种耳目一新的表达”“给中国动画电影带来巨大的信心和鼓励,为国产动画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和风格——成人黑色类型片”。
尽管如此,《大世界》也依然逃脱不了国际高口碑与国内高票房不可兼得的命运,首日排片率仅为2.3%,此后平均排片率在1%以下,累计票房不过262万。置身于习惯了低幼价值取向的国内动画电影市场,导演选择成人式的现实主义题材,意味着影片将
不可避免地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用这种形式是否能将粗粝的现实过滤得更加尖锐,更具有“现实”指向性;另一方面,形式反过来也在拷问内容,对现实题材的“纪实化”处理是否达到了“电影化”的要求,是否保有动画的假定性高度。因此,现实指向性极强的动画电影通常选择站在观众一边,在从现实到超现实的运用中极力调动观众情感,从而模糊观众对双重考验的追问。然而刘建的《大世界》却特立独行,不仅选择了以戏谑、讽刺的方式来表现底层众生相,甚至还造成一种追问。因此,解读《大世界》是怎样用荒诞写实的手法呈现城市边缘的真实生存现状以及引发的追问是需要思考的重点。
一、荒诞的个体:失意者的不妥协
《大世界》的背景设置在一个南方小城。司机小张为了挽救爱情,给整容失败的女友找钱继续做手术,冒险从工地老板那里抢劫了100万现金。然而,这包现金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效应。当这起抢劫案的消息传播开来时,老板雇的杀手、底层各股势力都在找小张以及这笔钱。原本没有关系的他们,产生了命运的交集。在一番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交手之后,他们最终错失了这笔钱。这是刘健导演的第一部院线电影,但并不是他的首部动画长片。早在2010年,他的处女作《刺痛我》就入围了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虽然两部电影在表现方式上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刘健都将重点放在表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无论是《大世界》工地司机小张,还是《刺痛我》失业大学生张小军,他们都是一无所有,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的小镇青年。到了《大世界》底层人物觉醒,他们开始试图寻求改变:小张的未婚妻想去韩国整容,是要通过改变自己容貌来改变命运;参与抢钱的一对杀马特男女,他们决定远离小镇,抢钱去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幻想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命运;被工地老板雇佣的杀手瘦皮也要这笔钱,他计划送女儿出国留学,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们不遗余力甚至冒着牺牲身家性命的风险穷尽各种方式寻求突破。工地老板、幕后大佬、杀手、饭店老板、女服务员、工地小夫妻,人物轮番登场,如同西西弗斯、坦塔罗斯、普罗米修斯在无尽的荒诞自由中,用渺小抵抗着未知的命运。
《大世界》中表现的人物像极了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那些街头巷尾擦肩而过的市井中人。“这种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中延续着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大故事,即中国观众能够集体分享的故事。这些电影尽管以小人物为核心,但讲述的都是整个社会在特定历史中共同承担的大故事。在今天,各种不同类型的小故事开始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而这些小故事也不再必须服从宏大历史或集体伦理的压力。在这个时代里,许多小故事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局部最大化地被接受,而不是同一个宏大完美的故事被所有人接受。小故事时代的到来是二次元写实主义出现的重要背景。”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大世界》将二次元的动画融合现实的题材,制造出一种游戏化的写实效果。与大叙事正好相反,二维人物特有的简单感,更好地表现出荒诞气氛。同时,二次元的方式也能更好地诠释天马行空、脑洞大开的表达。在影片中,杀马特男女在电梯幻想劫钱成功后逃离城市,去心中的净土香格里拉时,其呈现方式使用了大跃进的视觉符号,准确恰当地诠释了70年代底层小人物的理想主义、他们的时代属性和阶级色彩,以及现今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同时,坎普风格的画面本身也更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代底层人为主流所代表的当下的社会审美趋向。
在二次元的建构下,《大世界》让电影更“小”。没有一个大人物,有的只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缩影,车站里聊天的陌生乘客,网吧中痴迷于游戏和聊天工具的小镇青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追打,《大世界》中人物的语调虽总是干涩缓慢,却妙趣横生地刻画了市井图景,并将其尽可能地日常化、平凡化。片子里寥寥数十人,其实代表了身边所有的人。人们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机遇,通过物、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我拯救。同样国产电影的视角也聚焦着小人物越挫越勇的草根精神,顽强的生命力。《疯狂的石头》中山城的草根们疯狂地追逐一块石头,以期获得财富;《钢的琴》中废弃工厂的下岗职工自制钢琴,争夺抚养权;《我不是潘金莲》中村妇无止境地逐层上访,求说法还清白。《上车,走吧》中乡下年轻人北漂,为的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电影如同生活的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其中安置自己,想象自己,寻找着映照自己生活的影子。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展现出来的生活图景中,观众都希望能从整个时代或者社会中找到属于个人的位置,希望从中获得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关照与认同。
然而现实主义题材的核心在于质疑与批判,而非消解和抚慰。相较于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世界》呈现出更多的是批判态度。既然在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中,一袋钱可以改变女人的容颜,一个艺术家可以和黑道成为挚友,一个人可以为钱杀陌生人,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尤内斯库说,荒诞的另一层涵义,是要揭示世界和人生的无意义。而对于刘健所构建的荒诞电影而言,荒诞的反面是人物的命运,荒诞要揭示的正是草根们屈辱而又拼命改变命运的过程。当底层草根们的悲剧宿命只能得到黑色幽默般的展示,如同《大世界》片末的那场“车祸”,所有的“戏仿”“巧合”和“荒诞”的意义蕴涵成这样一句话 :“通过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一首语无伦次的和荒诞的诗,每一个人便能够对世界的残暴和愚蠢表示其轻蔑”,这种荒诞自然也就具有一种“批判现实”的意味。
二、失焦的群体:信仰的集体缺席
《大世界》中,信仰的缺失几乎已经成为所有人物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常态,无论是一般小市民还是老板,均深陷于这种信仰的缺失所带来的困惑、迷茫之中,借此导致的急功近利、道德滑坡、诚信丧失、人心叵测等一系列的问题,共同型构出城市边缘群像“集体浮躁”的意象。当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社会的进程空前加快,同时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影响之下,西方的价值文化理念涌入我国。在这种信仰缺失的背景之下,人们就很容易从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务实精神转向另一极端,即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严重侵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世界》中保安们在地摊吃饭聊天谈论的自由信仰:“菜市场”“超市”“网购”三种层面的“自由”,难道不正是消费主义侵吞自主意识的最鲜活诠释?这种“信仰”在当下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散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生活之中,人们沉浸于物欲的享受之中而日益消泯了理想,在信仰与价值上也日益为消费主义所主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信仰的缺席构成了刘建电影中人物“集体浮躁”的深层社会文化根源。
在《大世界》中所有人物将金钱视为终极信仰且执迷,以至于陷入毁灭。金钱在社会底层还尚能充当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然而在《大世界》中,金钱成了万恶之源,充当了人与人之间联结的阻碍。金钱无法成为人与人的联结,那信仰呢?刘健在影片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信仰符号:上帝和佛的探讨、自由的三重境界、象征美好的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这样的呈现,反映了当前的大众精神信仰处于真空状态,人与这个世界仅存的链接断裂了,并非信仰另一个世界,而是爱或生命的缺失。导演罗西尼西曾说:“世界因人而变,人越缺失人性,就越吸引那些或使人相信人与世界仍存在关联的艺术家们。而事实是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甚至不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像爱、死亡等,好像他们仅仅片面相关。人们失落的反应只有信仰可以拯救,唯有对世界的信仰可以将人们重新拯救。”
信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悄无声息的存在,比宗教带给人们更大的安全感,因为信仰是与一个时代大众最密切的联结,有时候足以弥合岁月的巨大裂痕。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信仰正处于一种逐渐淡化缺失的现状。而消费主义带来的物质享受让更多的人以“金钱”“权利”等因素来界定“成功”和“幸福”。随着这种影响的加深,中国社会逐渐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贫富差距使得底层大众处于一种在夹缝中摇摆的状态,他们一方面没有机会从精神领域得到真实的收获,另一方面也没有彻底从物质领域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大世界》中城市边缘人物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闹剧,反映出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需要重寻人与世界的联结,重新建立新的信仰,信仰这个时代的温暖,从这个意义而言,《大世界》批判现实的角度显然就是刘健手上的一根针,既用自己的方式,又持续为城市边缘群体发声,持续戳刺、回应人们身处的这个过度膨胀、虚妄至极的大世界同时给予观众新的希望,即使在如此虚妄的世界下,草根百姓的生命依然有光。
三、异化的城市:金钱至上的原则
刘健在《大世界》的结尾用红色的人民币结束了电影,也终结了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当手提包被打开的一瞬,人民币依然规列整齐,重见光明的瞬间,它们似乎幻化成为某种图腾,威严而具体,世俗却又至高无上。可以说,这是导演酣畅淋漓地对金钱社会下人性的扭曲投以冷嘲热讽。金钱成为躲在背后促发一切的行为纲领,就像司机小张的整容失败的女朋友一样,成为裹挟某种假设的前提,在消费主义的半推半就下反而愈发高举。就像刘健在柏林电影节接受采访时说的:“《大世界》描绘的是一幅群像图,没有绝对的人物主角,那包钱才是电影中真正的主角。”金钱是万恶之源虽被认为是片面的,但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精炼地指出了金钱的本质属性是工具,他说:“如果人们在生活中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毫无用处且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但人们是无法生活在桥上的,就是说金钱能够成为人类追寻终极价值的工具。”而将金钱至上视为最高原则就会产生金钱是罪恶之源。这就是城市为何会犯罪丛生的原因,也是城市的罪恶和堕落为何会成为电影中反复呈现的母题的原因。
在中国的城市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金钱对人的生存逐渐起了决定性作用,进而影响大众的精神世界。电影中所呈现的社会问题、犯罪丛生皆源自于金钱导致的贫富差距与人们日渐增长的欲望。有资产者和城市贫民的生存状态存在天壤之别,富人居住干净整洁的高档小区追求更高层次的奢侈享受,去昂贵的商业中心购物,草根大众则栖身破旧、脏乱差的住宅楼或出租屋寻找基本生活的温饱,为衣食住行斤斤计较。生活品质以及生存状态的差别导致的结果是社会阶层的分散,由此催生了城市边缘草根们漂浮的无根心理、不均衡的心理感受以及异化的生存体验。金钱与人的关系和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历经了从排斥到正视再到异化等阶段。金钱由此成为电影控诉城市金钱至上扭曲个人的主要手段。刘健从《刺痛我》到《大世界》,均表现了金钱在对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人性间隔作用,并生动细致地描述了生活于这些阶层中人的生存状态。金钱将曾经尚存脉脉温情的人情味异化为当下都市中漠然的人际关系。刘健用电影的方式通过人物对金钱的态度和人物的命运验证了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一个世纪前的预言:人无法在金钱的桥梁上温情地生活。
吉尔·德勒兹说:“电影应该呈现的并非是全世界,而是对世界的追问。”《大世界》用现实与超现实的手法刻画着底层大众的生存现状,其中所有的探讨、批判、追问都不断地冲击着观众,令他们为之深思。没有钱去好的美容院,没有钱去制作发明,没有钱支付留学费用,没有钱去香格里拉,这些贫乏更多的是温饱过后的企望。导演刘健在《大世界》所呈现或再现的不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一个尚待解读的现实。正如巴赞说的: “真实不再是再现,而是被对准的真实,不是再现一个已然被解读的真实,而是对准一个模糊且尚待解读的真实。”城市边缘的贫乏,是物质的贫乏,但更是精神的畸形,这应当是刘健在电影中所呈现并要表达的。
【注释】
①人民网.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大世界》:动画也能刺痛人心[EB/OL].http://game.people.com.cn/n1/2018/0110/c40130-29756806.html.2018.01.10.
②台北金马影展[EB/OL].http://www.goldenhorse.org.tw/film/about/highlights/.2018.11.22.
③人民日报(海外版)[EB/OL].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3/26/node_865.htm.2018.03.26.
④数据来源:中国票房.数据截止时间2018年1月21日[EB/OL].http://www.cbooo.cn/m/666459.
⑤李洋.中国电影的硬核现实主义及其三种变形[J].文艺研究,2017(10):14.
⑥[英]阿诺德·欣奇立夫.荒诞说——从存在主义到荒诞派[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65.
⑦[法]吉尔·德勒兹.电影2: 时间——影像[M], 黄建宏译.台湾:远流出版社,2003:603.
⑧新片场.法国艺术电影发行机构Memento films专访《大世界》导演刘健[EB/OL].http://www.xinpianchang.com/e7327.20180112.
⑨[德]格奥尔格·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
⑩[法]吉尔·德勒兹.电影1: 运动——影像 [M],黄建译.台湾:远流出版社,200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