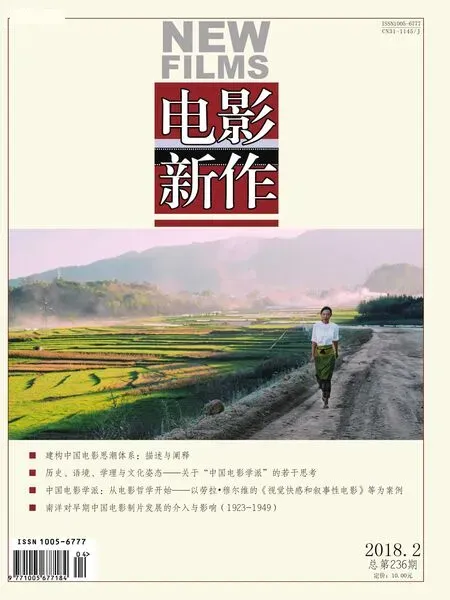顾长卫的影像变奏:从新启蒙美学到关系美学
李 飞
一、顾长卫:导演谱系中的褶皱
顾长卫在中国导演的谱系之中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如果从电影行业的从业经历来看,他在1984年就为“第四代”导演滕文骥掌镜《海滩》,次年则是《大明星》(1985),此后更以“第五代”代表作《孩子王》(1987)、《红高粱》(1987)、《霸王别姬》(1993),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的摄影师身份闻名遐迩。但如果从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的时间来看,顾长卫的第一部作品《孔雀》完成于2005年,晚于第六代绝大多数导演的处女作诞生时间,因此有的研究者则干脆根据第一部执导作品的时间将顾长卫归入所谓“第六代”导演群体之中。事实上,这种处理方式,将导演视为影视作品唯一作者的观点,基本上套用的是文学中作者的模式,忽视了电影生产的工业性质与集体性质,也忽略了作为电影内容与风格特色形成过程中摄影师扮演的重要作用。
本文无意介入到顾长卫到底是第五代导演还是第六代导演的争论之中,因为在这个标签的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方也很容易陷入到意气之争,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谱系中的特点按图索骥地在他的电影中寻找一一的对应且可以佐证的实例。同时,顾长卫的作品少,使得各方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这位自2005年执导《孔雀》的导演当下也仅有五部作品,其他四部是《立春》(2008)、《最爱》(2011)、《微爱之渐入佳境》(2014)、《遇见你真好》(2018)。但问题在于,在这种意气之争中,作为电影工作者的顾长卫真正的影像风格脉络可能被隐藏。从摄影师到导演,这本身意味着一种电影工业内部人才部门之间的流动与跨越的职业可能性。同时,从导演成长所要承受的“独特的行业内在法则和共享的社会外在因素”来看,作为导演的顾长卫是一个晚发者,他的作品成名路径同“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相同,通过国外的大奖增加业内认可,然而他已经享受不到当年张艺谋《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后带来的全国狂欢,只能如“第六代”导演那样惨淡经营。尽管捧回来银熊奖与良好的口碑让《孔雀》当年拿到千万元的票房——这样票房对于文艺片而言已经极为难得,但是相对于成本而言,该片依然是亏损的。另外,同“第五代”成长外部环境不同的是,他第一部作品诞生之际是在中国电影工业“冰海沉船”之后以好莱坞大片为样本,以市场化为导向,“重生”了新的商业电影的业态,电影人同样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压力与困境。在美学品位上,尽管在顾长卫的电影《孔雀》《立春》《最爱》之中对纪实与长镜头的偏好同“第六代”接近,但是他电影的风格与精神比当年同班同学更多传承了“第四代”导演的特色。
因此,顾长卫的这种复杂性与电影经历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导演谱系中某种德勒兹意义上的“褶皱”:他是“第五代”电影人美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不是掌握全局的导演;等他成为掌握全局的导演的时候,中国电影实践已经不是导演的谱系能涵盖的了——他失去了“第五代”陈凯歌、张艺谋等人那种“为电影而电影”的探索的实践环境,不得不在商业环境中纵横捭阖。相对于陈凯歌、张艺谋纠结的市场化转型,顾长卫的转型则是从他一直关注的青春/青年入手,进行类型化操作。如果说《孔雀》是已经中年的高卫强回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青春的他家三姐弟在家乡安阳发生的故事,那么《立春》中展现的是王彩玲和有着类似遭遇的文艺青年的故事,《最爱》则选择表达的是卖血被传染艾滋病的青年男女的故事,《微爱之渐入佳境》再现的是北漂的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遇见你真好》则是顾氏版本的青春校园喜剧片。尽管这些影片褒贬不一,然而顾长卫的影像风格已然融入了这种“青春表达”之中。
二、新启蒙美学
如果一定要按照作品的风格特色进行分期的话,那么顾长卫的作品中,从《孔雀》到《最爱》属于他的艺术电影阶段,占主导的是新启蒙美学,走的是文艺片的路线;而从《微爱之渐入佳境》到近期《遇见你真好》则积极面向市场,属于商业电影创作阶段的作品。在《孔雀》《立春》《最爱》等早期作品中,顾长卫采取的是一种诗意的纪实表达,秉持着一种新启蒙美学的传统。
这种新启蒙美学将电影语言表达方式变革同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联系在一起,而“启蒙精神所推崇的理念是抽象的个人主义和主体主义,乐于不断进取的功利主义以及无限制的乐观主义”。这种耦合,使得美学上的个人主义遭遇了思想文化上的个体主义以及与经济上的市场化意识、市场启蒙紧密相关的个人主义。审美的价值与思想文化上的价值以及经济中运行的个人主义价值呈现高度耦合之后,新的电影运动以一种新的狂欢的方式散发出其独特的魅惑力。受这种新启蒙精神指引的《一个和八个》(1983)、《黄土地》(1984)等以反思之名开启了对革命年代的反思与个人化书写。在《一个和八个》之中故事情节设置的是让被怀疑是奸细/被冤枉的王金来教育感化土匪逃兵,改造成为对抗战的有益之人,组织化的改造被个体化教化替代;《黄土地》的故事中代表公家人来到农村采风的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最后还是没能将翠巧从包办婚姻中解救出来,尽管片中留下光明而充满活力的尾巴,但掩盖不住的是作为组织之中个体的无力与失落——抽象的集体主义与规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启蒙用个人主义完成了对革命历史中集体主义的置换。张艺谋导演,顾长卫掌镜的《红高粱》的横空出世则将中国革命尚未完成组织化的农民的状态以“原初的激情”的方式呈现出来。血红的高粱酒同夕阳下农民抗战不对称的牺牲的惨淡现实交融在一起,形成独特的美学风貌。
相对于当时“第五代”之中的陈凯歌、张艺谋、张军钊等人,顾长卫在2005年之际上映的《孔雀》已经是处在电影中个人主义叙事泛滥的情形下对80年代的神话再祛魅。然而,这种祛魅本身的合法性却是站在当下——电影之中的画外音正是已经中年、操着安阳口音的高卫强发出的。《孔雀》的三段结构,正是围绕着高卫强的“意识流结构”以复式的方式展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酱醋茶等都纳入到电影的叙事之中。原作者兼编剧李樯赋予片中姐姐、哥哥、弟弟分别以审美、伦理、宗教的象征内涵,而顾长卫将这些以青春残酷物语的影像方式展现出来。如果从审美维度来审视姐姐高卫红,她苦苦追求着当伞兵的梦想,为了参军,她同招兵的军人打乒乓球,并请求人家帮忙,但被人家以公事公办拒绝。而另外一个为了胖乎乎的妹妹当兵更会讨好人、走关系的姐姐,更是把招兵的军人伺候得妥妥帖帖,为她的妹妹争取到了名额。高卫红失去了参军机会之后,回家茶饭不思,最后被家人按住塞食物,摄影机记录下的是背对摄影机的家人的动作。当家人让开后,我们看见摄影机记录下的是她咀嚼着塞进嘴巴的东西。此处长镜头的记录性表达,表现的是一个理想已死的高卫红的形象。而片中被人津津乐道的诗意化的高卫红骑车放飞自制的蔚蓝色的降落伞穿过大街的段落,实际上在构图、色彩、表情与动作等方面继承的是“第四代”导演诗意表达的影像风格。在这场景叙事中,表达出高卫红心中依然试图拯救已经泡汤的伞兵梦,最后也只能用替代性的方式来安慰已死的理想。当高卫红讨要降落伞之际,宁愿付出贞操的代价:这本身透露出理想实现路径受堵后心哀莫过如此的状况。而如愿以偿当上伞兵的胖女孩为实现梦想付出的代价,正如近片尾所示,高卫红多年后看到的,那个胖女孩的姐姐成了伞兵的老婆。这也正是新启蒙所处时代的时代症候。
如果同时考虑李樯的身份及剧中画外音主体——一度离开故乡的高卫强,那么《孔雀》再现的是“逃离安阳”(或片中“逃离鹤阳”)的人群们反观自己过去在故乡的生存状态。“反观者”高卫强的角色,用片中台词来形容是“沉默得像个影子”。然而,“沉默得像个影子”的高卫强在片中虽然所占篇幅并不大,但却显示出某种同现代都市生活的勾连——片中他和姐姐均自认为不受父母喜欢,处于游荡乃至被放逐的状态之中,最后甚至扒火车离开了这个他成长的城市,这构成了某种中国中小城市现代性游荡者的形象素描。即便当他多年后带回来一个当歌女的老婆和她的儿子,他依然保持着某种玩世不恭的浪荡态度——被老婆养着,在街头游手好闲,混迹在老人之中。当他父亲载着啤酒去别人家家里送礼,被突然窜出来的狗吓跌倒并绊倒车使得啤酒碎掉之际,高卫强以旁观者的姿态,笑了。这种态度,也正是某种逃离中小城市,拥抱大城市现代性的游荡者的心态写照:“游荡者在市内都市风景中进行‘研究’直至疲惫不堪,在陶醉中频频侵入遥远的空间和时间,被琐事触发继而追忆‘可能发生过’的潜在的琐事,捕捉不同的表情。”相对于80年代平移过来的浪漫的现代性想象,片中展现的是某种青春残酷物语——李樯赋予理想化象征的姐姐,却在片中处处碰壁。她的伞兵梦没有实现,最后草草把自己嫁给了民政局大院的司机小王。而高卫强感觉到智商不高的大哥使自己蒙羞,是阻止他获得爱(父母喜爱,女同学爱情)的障碍,因此买了老鼠药想要毒死大哥。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母亲将残存的药放入杯中,让鹅试毒,最后鹅死了,由此,将一场谋杀亲大哥未遂的阴谋给暴露了。而最后父亲以小儿子书中藏裸女画向邻里宣布儿子是流氓,同时也带来小儿子的离家出走与自我放逐。在这种青春残酷物语的表达中,曾以摄影师身份参加过“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在80年代中国先锋电影语言探索过程的导演,顾长卫的首部作品《孔雀》在向新时期中国的先锋电影致敬,尤其是“第四代”导演。毕竟,“第四代导演把纪实作为武器,将虚假当作敌手,以现实的渐进线立命,名义追求语言革命,而真正的激情却在记录社会变动”。
这种新启蒙精神正是将这种内容纳入到记录与日常审美之中。曾两度为“第四代”导演滕文骥掌镜的顾长卫将诗意表达与中小城市中破碎的理想,各种阴谋与人性黑暗,社会变迁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以及中小城市现代性等均融入他对社会变迁的关注与思考中。《立春》的叙事年代与人物均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延续了《孔雀》的这一关系,因为《立春》之中王彩玲的遭遇事实上是高卫红理想遭到现实挤压的命运翻版。这部“开创性地塑造了中国内地小城市怀抱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形象”的影片,不同于《孔雀》之处在于,“献身于艺术,献身于爱情”的王彩玲在现实受挫之后会以另外的方式站起来,片子近结尾,王彩玲收养了小女孩,一度贩羊卖羊肉。如果说《孔雀》之中高卫红具有某种“不被承认者”的意味的话,那么在《立春》之中,其则恰如其分地向我们展现了文艺青年在中小县城如何被视为“不正常者”而存在——王彩玲本人也被文艺青年内部视为某种不正常。这本身意味着电影在美学上作为一种社会感知的工具作用:“在被感知者的被感知状态中,原本的环节在于:在感知中,被感知的存在者以具体有形的方式当场在此……就其被感知状态而言,所有具体的物体感知的另一个环节还在于:我们所意指的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被感知者。”在片末,导演在想象界为王彩玲安排了一场在神圣的艺术殿堂——中央歌剧院之中引吭高歌她最终爱的《献身艺术,献身爱情》:“这首歌是她人生的主题,在剧中多次重复出现保证了电影情绪的完整统一,起到贯串情节发展的纽带作用”。
《最爱》作为顾长卫直面中国农村中出现的卖血传染造成的艾滋病村的现象,再次将“第四代”导演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传统彰显了出来。最为显而易见的是,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顾长卫套拍了一部同题材的纪录片《在一起》。对于电影和纪录片能够带来人们对艾滋病的理解与改变,在访谈之中顾长卫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⑫片中,顾长卫以一个12岁赵晓鑫的亡灵视角来讲述他叔叔得意与同样染上“脏病”(片中对艾滋病的称呼)的商琴琴之间跨越礼俗,跨越生死之恋。有论者将之视为某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只看钱的原罪。这种社会化的读解,忽略掉的是顾长卫对那些失语者生命尊严的呵护。亡灵叙事的方式使得顾长卫能够以某种近乎上帝视角来讲述他的故事。村中的废弃的学校,成了福柯意义上隔离病人的“异托邦”:“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片中,这种异托邦的出现首先是以一种病人所携带的物资集中管理分配的乌托邦蓝图出现的。然而,乌托邦很快在私欲与掌勺者面前变成了异托邦:管账的账本能丢,负责做饭的偷米。当赵得意的父亲赵连柱试图守护乌托邦的底线,公然将学校之中桌椅、电视机等搬走时,直接被质疑了合法性:他大儿子组织卖血,把热病传给大家;二儿子有老婆,还和人家媳妇胡搞。当这种近似于黑色电影之中大义凛然的控诉消解掉了赵连柱的合法性后,乌托邦彻底完成了向异托邦的转变:自私的异托邦的门打开了,同时乌托邦的门关上了。当赵得意与商琴琴最后领到了结婚证,沿路散发喜糖却没人接,镜头聚焦在商琴琴反复读结婚证上的内容的时候,其带给人一种跳出异托邦的生命的尊严感与温馨。
从《孔雀》到《最爱》,顾长卫表现了诸如高卫红、王彩玲、赵得意与商琴琴等“不被承认者”。在这种表达之中,他的新启蒙美学类似于朗西埃所言的“歧感”美学——这种美学通过对不承认者“与既存的感知、思想和行动结构之遭遇,来抵制司法裁断,在可感性秩序中制造裂缝”。对这些所谓正常社会之中“不正常的人”的生命经验的表达,顾长卫以80年代人道主义与启蒙的方式表现了他对社会变迁的关注以及对生命的思考。这也是他早期的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三、走向“关系美学”
当顾长卫完成了文艺片向商业电影的转身,同时也意味着他实现了带有歧感意味的新启蒙美学转向了关系美学。所谓“关系美学”,最早由法国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渗透到艺术实践的背景下提出的,意指“基于艺术所表征、生产和推动的人际关系来评判艺术品的美学理论”。这种“关系美学”强调的是艺术创造的新的社会连接方式、社交性等内容。在这个跨媒介叙事的时代,互联网与各种新媒体技术形态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与艺术实践的广度与深度远超过“关系美学”提出的年代,不同媒体形态之间那种媒介质材的规定性带来的隔阂也逐步被打破。“关系美学”对于电影表达、生产以及评判标准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其同传统的电影美学评判标准的区别在于其不仅仅从文本,同时也从电影本身的社会性、观众(用户)等角度对电影价值进行重估。在这种“关系美学”的影响之下,粉丝电影、网络大电影等概念一度流行并影响电影的生产创作。
近年来上映的《微爱之渐入佳境》以及近期上映的《遇见你真好》则反映顾长卫这种走向“关系美学”的趋势。《微爱之渐入佳境》直接就将杨颖、陈赫饰演的男女主角所在的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青年的情感生活与工作状态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喜剧性的呈现与轻言生死的表达,正是微时代人的“微”状态的写照: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退隐,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越来越成为审美关注的内容。在片中,顾长卫用文艺青年与微信的符号将电影圈中的喜剧段子以串葫芦的结构方式组织起来。“微男”“微女”的人设,人物之间的微信表达,电影短而碎的镜头组接等给影片带来浓郁的网络交流感。该片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以爱之名。片中,顾长卫的影像试图提炼的陈赫与所谓“微爱”,正是在微博、微信、微商等各种以“微”之名进行重新整合与聚合的微时代的“生活方式中充满巧合与零碎的爱情。这种社交网络中的情感,正是当下社会中急剧变迁的、流动的现代性”的体现。或许正是这种对“关系美学”与社交性的追求,使得电影更加关注的是“流动的现代性”之中北漂的文艺青年的卑微与大都市现代性的游荡者的虚无。尽管片中顾长卫自己本人亲自出马,饰演了懒人烤鸭的大厨师傅,然而,在“微”之中支撑人的尊严的价值依然缺场。这导致了故事停留在庸常的北漂文艺青年男女情感之上,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内爆后的尊严。如果说《孔雀》《立春》里中小城市构成某种生活方式上的压抑,那么《微爱之渐入佳境》试图以喜剧方式表现都市之中为了钱而导致的青年男女的异化与尊严价值的丢失。这也为该片带来近3亿元的票房。
《遇见你真好》本身迎合的是近年从网络到银幕中的青春怀旧潮流。这种顾氏版本的《致青春》,可以说是某种“子一代”成为父母之后给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看的想象的青春,同时也有某种致敬《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意味。不同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有鲜明的叙事者,叙事的年代与故事发生的年代,而《遇见你真好》尽管有明确的叙事年代,但是年代已经没有荷尔蒙飞扬重要,同时电影的表达侧重点在三对情侣关系上。片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着交流沟通的可能性。最为典型的是教导处主任、宿管阿姨王彩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这部电影采取了“关系美学”的取向,发挥的是艺术的缝合作用,通过回忆将曾经青春形塑成社群的经验。同时,在这部电影之中,顾长卫也在缓解上一部电影中对其他电影文本开涮的关系,而将该片弄成向经典电影与自我致敬的集锦:青龙被警察带走的时候的对白是致敬《无间道》,近结尾段教导主任打开纸条“在生命的旅程中,遇见你真好”后的尽头运用方式与情感表达则是在致敬《最爱》,宿管王彩玲的人设则延续了之前的《立春》。在这种电影与电影,电影与网络文化等的互动中,“关系美学”被强化了。
结语
顾长卫以青春、青年为电影关注点,完成了从摄影师向导演的转身。在十多年的导演实践中,他完成了影像风格的变奏,实现了从新启蒙美学向“关系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电影与社会、电影与观众、电影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等的改变。尽管顾长卫的影像风格发生了变奏,然而从《孔雀》开始到近期的《遇见你真好》,片中一以贯之的是内容上对中国现代性感知最为敏感的青年群体的关注。在这种青春为影像表达内容的影片中,贯穿着顾长卫的影像风格变奏,变的是风格,是观察的方式与视角,不变的是对青年、青春的关注。对于这位浸淫在电影行业多年的导演而言,无论是新启蒙美学中对歧见的发掘,还是新近的“关系美学”中对青年社群经验的挖掘,在变与不变之中,他依然试图继续触碰时代脉搏。
【注释】
①这种处理,在诸多研究中可见。如袁庆丰.第六代导演:忠实于时代记录和叙事功能的恢复——以顾长卫的《孔雀》为例[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19(6):50-55.
②杨远婴.百年六代 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J].当代电影,2001(6):99-105.
③《孔雀》票房一千万 打破“高艺术低票房”怪圈[EB/OL].http://ent.sina.com.cn/x/2005-03-30/0901689533.html.2005.3.30.
④戴锦华.冰海沉船:中国电影1998年[J].花城.1998(3):188-196.
⑤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76.
⑥该片编剧兼原小说的作者李樯认为:“姐姐、哥哥、弟弟分别代表了这样的三个部分。姐姐代表了审美,她总是在追求着理想,在不断遭受失望和拒绝后选择孤注一掷的毁灭。哥哥像个中年人,过得很世俗。弟弟代表宗教,代表出世,他似乎是在最后看透了某种东西……《孔雀》写的就是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写了普通人的成长历程。它有关命运,有关生活的本质。”参见杜斐然.安阳孔雀[N].南方周末,2003.7.31.
⑦三岛宪一.破坏、记忆、收集[M].贾惊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51.
⑧杨远婴.导演的谱系[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96.
⑨张民.《立春》:理想主义者的墓志铭[J].电影艺术,2008,319(2):23-26.
⑩海德格尔.欧东明译,时间概念史导论[M].商务印书馆,201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