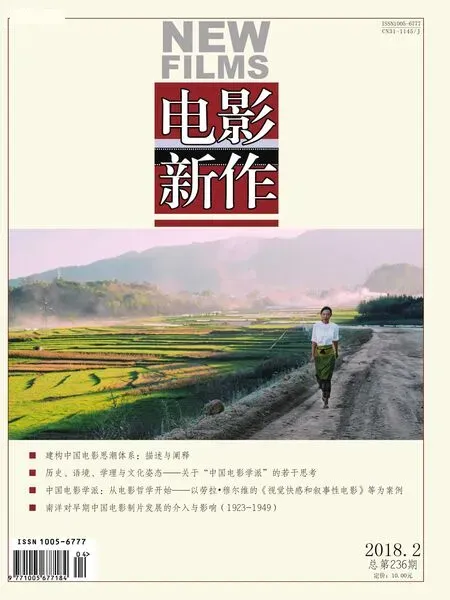贾樟柯电影中的纪实风格及其非现实元素
——以《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为例
徐春萍
一、贾樟柯电影的现实语境
关注现实,是贾樟柯的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贾樟柯就意识到电影具有记录中国真实状态的天然使命。在他导演的电影中,始终用最朴素的电影语言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事,并采用大量业余演员的方式,传达出最质朴的情感。而且,在《三峡好人》和《山河故人》中,他对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进行了创新式的表达,并通过分章节叙事与大时空、多画幅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其电影的现实性。
1.影像、主题与音乐的现实感
影像方面,长镜头是贾樟柯电影的突出表达手段之一。“主张采用长镜头(或称镜头段落)和景深镜头结构影片的‘长镜头美学’,是实现巴赞现实主义电影理想的实践原则,‘首先是一种本体论立场,而后才是一种美学立场’。”巴赞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可以无限地逼近现实,电影有权还原真实,其再现现实的独特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与好莱坞式快速、多变的蒙太奇相对立,长镜头追求记录感,编导渴望留住当时当刻的生活原态,借此保留易失的情感。长镜头尊重事件发展的过程和全貌,善于保持事件的透明感和真实性。贾樟柯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接受了大量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影像风格。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用大量长镜头展现三峡库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开篇三分钟的长镜头描绘出三峡人民即将搬迁的众生相,他们抽烟、打牌、扎行李,他们感叹、发呆、望故乡,他们个个都不一样,但在驶离故乡的船只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流浪儿。导演用长镜头营造的浮世绘将每一个在离乡愁绪下的个体串联,此时此刻,他们以最自然的状态谱绘出三峡移民的原貌。长镜头中的他们已然成了“移民共同体”。这一静默、冷静的长镜头记录着每一位打工者,镜头滑过他们、捕捉他们,一切都如同画卷在缓缓展开。不紧不慢的镜头摇过无比生动的人们,主人公不经意地出现,不被刻意突出,他被人群淹没,于是观众也不经意地感受到这才是生活的面目——没有动人心魄的变故,一切都在不经意中改变着。长镜头带领观众走进人物,读解人物心理。沈红与前夫的摊牌、韩三明与前妻的重逢与和解,在长镜头的注视下,时间近乎凝固,我们也在一分一秒地看着他们的表情,听着他们的呼吸。在这段冗长的时间里,凝固了人物几十年的光阴,岁月变迁,在生活改天动地之际,长镜头中的他们依旧平静,平静得如此乏味,一切都要变了,但什么也都没变。长镜头总是默默注视着众生,它以极端深刻和冷静的眼光提醒你,生活就是如此,并且将最原始的情感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观众。这种纪实手法所形成的质朴美感让我们在无限接近人物情感的同时,更带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审视。
人物的雕塑感是长镜头的附属产物。所谓雕塑感是人物在镜头中不产生位移,没有走位,以固定的姿态“凝视”镜头,看向观众。这更相当于戏曲中人物的亮相,即在某一段落结束之际,演员做规定动作并保持数秒来总结情绪、强化气势。在《三峡好人》中,几位少妇从破旧的楼层里现身,定格数秒,她们注视着韩三明,注视着观众,在人人举家搬迁的时代下,她们像极了吟唱《后庭花》的风尘商女。雕塑感的人物群像延续着其心理状态,也承接着观众的情感认同。对于大部分工地上的打工者,与其说他们是东奔西走的劳工,不如说是静止于据点的劳动者。在工地的工人大部分时间虽是在干活,但鲜有走位和位移,他们以定点的姿态将劳动者的身躯投射在银幕中,他们奋力捣毁断壁残垣,也在破碎的工地上眺望远方,这或许暗示着在银幕之下,他们将永生无法走出如此劳动的命运。在发现小马哥失踪前,贾樟柯赋予工人群像以诗人气质,此刻的工人停工,但无人嬉笑打趣,相反,他们与自身极度不匹配的诗人气质相映成趣,站在废墟上眺望远方,工人往常的力量与当刻的气质在定格处合一,这样的人物雕塑感打破观众对工人的刻板印象,重塑在破碎现实下、时代变迁语境下的新形象。
在悠长的镜头表意中,贾樟柯电影的主题饱含深沉与质朴。这些作品始终无法跳脱出对于老百姓,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关注。贾樟柯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每个生命个体都应该被平等尊重,贾樟柯对普通人、弱小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为他的电影染上了深重的人文色彩。《三峡好人》中,叙述主体则是百万移民与拆迁工人。在宏伟的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中,在闪着金光的三峡改造过程中,牵动着数百万的贫民的生计。他们是迁移大军,也是三峡工程的主体。在他们之中,家徒四壁者不在少数。也正是他们,才构成了百态的中国社会。阳光下赤裸上身的工人挥汗如雨,展示着最雄健的身体;贫贱夫妻百事哀,韩三明与前妻想要重圆婚姻依然步履维艰;风尘少妇如蝼蚁般躲藏在残砖断瓦中……在建设梦想的同时,这些人依然在顽强生活着,无论做何工作、如何生存。在每一个光荣实现之前,总会有一批人为此梦想负重前行。“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贾樟柯践行着自己的原则,将电影的纪实本性发挥到极致。在行将巨变的中国,在充满离别与毁灭的三峡故土,无数人生在这里变化,导演用镜头注视人间,读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贾樟柯对社会底层人民注入了极大的深情,他成长于山西的落后小镇,自小浸泡在乡镇,他对身边人的言行无比熟悉,而一旦当摄影机——这一强大的表达工具和具有强大宣泄功能的武器赋予他时,他便本能且快速地找到目标,如鱼得水,俯身贴近现实的土地。尽管《山河故人》横跨多时代多地域,但依然会从县城里的老百姓开始整个故事,同样关注着煤矿工人。小人物依旧有血有肉,他们的人生际遇背负着更多的不可能性和时代变动中的不确定性,对他们的关注,就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体认。
影片的情感不仅溶解在主题中,更会通过形式手段表现出来,比如电影音乐。音乐是电影综合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情感与命运的重要方式。同时作为电影表现实体空间之外的补充,音乐也为观众搭建了听觉画外空间。贾樟柯导演善用流行歌曲作为电影音乐,不仅是影片营造真实感的需要,更是自身对过去年代的内心缅怀与深刻总结。以下分别就《三峡好人》与《山河故人》的流行音乐运用作简要分析。
《好人一生平安》与《上海滩》是一组音乐对比。作为韩三明和小马哥各自的电话铃声,我们似乎可以从这音乐线索中预知到二人的命运走向,这是他们二人的自我定位,也是两人在新时代变迁中的角色暗示。作为外来者,憨态老实的韩三明,人生地不熟不说,还因为方言的差异存在着巨大的疏离感,致使眼前所见皆是破败与创伤。而作为当地的“老油条”,小马哥延续着上海滩式的生活方式,打架、混日子、敲诈勒索,过着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可以说,《上海滩》是属于小马哥的。音乐交代人物,也预示了他的结局。
“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两只蝴蝶》里的爱情不会成真,沈红千里寻夫,两人破镜无法重圆。沈红在画面深处,从人群中走来,她站在桥上,在这一蝴蝶视野下的制高点上回望三峡,却无法跟蝴蝶一样飞越眼前这破碎山河。当夜幕降临,破败的建筑工地被极富浪漫狂想的舞场取代,在幻迷的灯光下,人们跳起华尔兹,耳边响起“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过去的情感已然消逝,沈红在魔幻的舞场中怎么也寻不到过往的情感,就像消失的村庄,不留下一丝的痕迹。不过,毁灭与新生是可以永恒转化的。三峡故乡的湮灭是三峡资源的重生。《酒干倘卖无》似乎饱含了导演对于三峡开发的反思和对自然、劳工、百姓的感悟,“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旋律映照着台下工人淳朴的笑脸,没有这些工人和这些生活普通、艰辛的老百姓的牺牲,一切的丰功伟绩只能是空中楼阁。
《珍重》和《Go West》贯穿于《山河故人》中。这两首歌是时代的印痕,同时也是沈涛言无可言的内心写照,“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切关心你……”《珍重》诉说沈涛与两个互为情敌的男人有始无终的感情,再见与回望,沈涛的爱情坎坷却不得善终。送子离乡,《珍重》再次响起,自带经典属性的粤语歌曲又一次对沈涛做出审判预言——“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沈涛真的听到了到乐的呼唤?并没有,相隔海洋,母子始终未曾再相见。而到乐与中文老师,尽管身处一地,但巨大的年龄差异,早已将对方拒斥于万里外。每个人都“盼望世事有转机”,但所有人在大时代面前只能缴械投降,道一句:“珍重,再见!”如果说《珍重》是强调时代面前人的无力虚弱感,那么《Go West》则是在既定命运前的自我挣脱与逃避。在《Go West》的节奏下,沈涛翩翩起舞,她已心向自由。
纵观《三峡好人》与《山河故人》,流行歌曲的普遍运用营造了强烈的真实感。流行文化是具有标志性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文化认同,用音乐开拓心理空间,不仅为角色构造合理叙事的基础,也为观众打造情感体认。声音是有体积的,它存在于电影画面中,在不知不觉中引领观众走进90年代。那些飘散在街巷中的歌曲,电视机里、舞厅场上,收音机广播的音乐都在构建着真实社会下的文化序列。
除此之外,时事政治的插入也使影片具有高度现实性。大量新闻广播的引用增强了电影的记录性和文献性。贾樟柯借助新闻将三峡迁移等重大历史事件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新闻与流行音乐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影片题材的要求,也是在视觉与听觉上,多维度实现现实性的要求。
2.画幅、空间与叙事结构的新运用
贾樟柯的电影首先建立在县城这一现实感极强的地理空间内。在《三峡好人》中,随着外乡人进入三峡库区,故事就此开始,而建设中那破败不堪的工地则是故事发展的场域。小城镇是贾樟柯的生活环境,也是电影中一直以来特定的空间表达。小城镇里充斥着混乱与无序,人声鼎沸与破败荒凉。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妩媚,没有首都的庄严大气,但它凝聚着大部分的中国人,包容着这个国家所有的弱势群体。堆砌的土山、飞扬的烟尘,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小镇,而我们只能本能地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去审视出现在这里的一张张面孔。尽管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设计了未来感十足的2035年,但这时的故事依然以90年代的小镇为情感依托。特别是,当老人跨入到未来,小镇气息复现时,我们始终无法在未来面前,对过去避而不谈。这一层的地理空间在《三峡好人》中则表现为一种强大破坏力的入侵。三峡土地上演着空前的空间悖论:破坏也是新生,毁灭也是重建。在现代化的中国,强大的机械捣毁着一切应该让位的历史,考古
队对文物的抢救凸显在急速前进中的中国,对于历史远去的必然性和不可挽回感。另一层空间,是《三峡好人》中烟、酒、茶、糖的社会空间和《山河故人》的时空空间。这两部电影有明显的段落结构,烟酒茶糖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礼仪习惯,是人情社会的粘合剂,它们维系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但在电影中,它们却没有起到作用。《山河故人》表现的是时代更替,新旧冲突、中西冲突、老少冲突、父子冲突,暗示着导演对于过去的、失去的追忆与遗憾。过去时空中的沈涛与两个男人的情感抉择,现在时空中的母子无法彼此依存的情感空缺,未来时空的老少恋的无法结果,都是破碎的“山河与故人”的表达。总的来说,无论是用极端主观的意象分割的叙事段落,还是客观分切时空,导演都在片段式的、板块化的结构里渗透着不经意的现实关联,并在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叙事片段中蕴藏着一条一脉相承的感情线索,传递出现实的深层内涵。
二、贾樟柯将荒诞融于现实
贾樟柯运用以上传统构建现实性的手法和不同以往的表达方式,将残酷且平凡的普通生活神圣化、尊重化。在观影体验中,生活与审美的界限逐渐模糊,在贾樟柯的魔术下,电影已成为生活。但在如此高度现实化的叙事空间里,贾樟柯设计了几处极端想象性的非现实意象。这些看似与影片基调极不协调的视觉奇观,与现实语境交叠,却为影片营造出一丝荒诞感。从完全虚拟的荒诞意象——如飞碟、起飞的大楼——到贯穿影片、连接情感的“说书人”角色等,并在现实之上的想象与游离于非现实之外的夸张,共同构成贾樟柯导演电影的荒诞表达。
1.充满荒诞感的非现实意象
在《三峡好人》和《山河故人》中,有许多现实中不可见的符号,如出现在三峡改造工地上的飞碟和建筑物式的宇宙飞船。两个外乡人来到三峡寻亲,一个是寻找多年未见的前妻,另一个是寻找两年没有音讯的丈夫。在这一个以寻找为线索的神话寓言式主题里,飞碟将两人联系起来。三峡历经变革,打造人类史上的奇观景象的同时,也成了世界最大移民事件之一。在电影中,飞碟暗示着这一神秘的宏伟蓝图即将实现,但是韩三明与沈红在面对着眼前残破的三峡时,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未来世界时,是束手无策的。镜头随着飞碟移动,从韩三明转向沈红,这是面对几千年历史即将消逝的共同情感体验与缅怀。出现在土坡上的未完成建筑,令人惶恐的造型又阻止了观众的情感认同,显得极其陌生且怪异。这栋大楼脱离其现实功用而存在,当它变成火箭起飞的瞬间,它也完成了在地球上存在的使命,三峡库区也结束了存在上千年的自然景观的样貌,而对于沈红来讲,她也失去了寻夫的希望。
飞机坠毁是《三峡好人》中造成视觉冲突的元素。沈涛在路边目击一架飞机朝她飞来并坠毁,也预示着梁子此后的生活如同坠落的飞机一样,变无可变。沈涛是机毁人亡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梁子悲惨一生的旁观者。时代的变迁不无残酷,每个人的变化、每个人的失去,时代带走了生命中的一个个陪伴者,无法挽回。毕竟,“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在梁子走后,贾樟柯用了一段充满意识流的画面,而这段画面无实焦、不清晰,模糊的两人在森林中放火,无焦点、晃动的画面仿佛一个人在自焚。这样极具形式感的画面是梁子自身无法扭转命运的隐喻。
纵观两部电影,这些非真实的意象都拥有极端的视觉吸引力,作为已被现实环境浸透的观众,会在这些突兀的幻想景观面前被怔住,超现实的意象让观众感受到过分的真实。
2.“说书人”的预言家角色
两部电影中都设置了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他们跳脱出剧情,向观众阐述剧意。在《三峡好人》中,站在即将拆毁的屋子里的小男孩向着窗户唱《老鼠爱大米》,他瘦弱佝偻着的身体看起来显得有些扭曲和不正常,但他依然用尽全力喊出这首歌,“我会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而这首歌,仿佛成了不可实现的诺言,暗示着任何文明和生态都抵挡不住机械的倾轧和时代的摧残。“我爱你,爱着你”,让他转身回到了现实,或许也只有这句话才是最真的情感表达,可以看作是三峡人民面对眼前破败之景的怀念之情,更是韩三明想和妻子说的心里话。当沈红坐船寻夫,唱歌的小男孩再次出现,他如同先知,在制高点上总结着沈红对于未归丈夫最后的希冀,尽管它无法实现。
《山河故人》中扛刀的少年从过去到现在,时光流转,却始终以流浪关公形象示人。梁子家里供奉关公,但却无法逃脱悲剧命运。流浪的“关公”不回头地渐行渐远,这是对既定的时代变换的隐喻,也是沈涛与梁子、晋生感情的流浪暗示。
无疑,这两个人物贯穿影片,在叙事过程中提示着时光变迁、物是人非。他们不直接参与剧情,但却跳脱剧情为观众预言。
三、非现实元素的间离效果
无论是上述的非现实的意象,还是预言角色的出现,抑或将日常景观安插于不匹配场景而造成不搭调的荒诞与奇观,都在打破着贾樟柯一直以来的纪实手段,但是,这种打破又在间离中重组。在充分表现现实的基础上,贾樟柯又在深层次上将观众带入更深入的思辨层面,面对奇幻与现实的对抗,阻隔了观众对现实的无条件体认,从而进入到现实表达的最高要求:审视与批判。
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所创立的‘叙事体戏剧’(史诗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不使观众同舞台上所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产生共鸣”。在电影中,编导运用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穿插字幕、增加场幕等其他元素将观众与剧情拉开距离,从而使观众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剧情之外,而不过分沉溺。《三峡好人》中,贾樟柯使用诸多幻想元素,如飞碟、火箭等,这些非现实成分使一个原本高度现实的环境变得与大众生活格格不入。三峡库区是一个飘散着浓重烟火气的地方,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在这里发生着故事,这些卑微到尘埃里的民工、房东、贫民无一不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人群与弱势阶层的投射,这样的环境已经足够将大部分观众代入到纪录式的场景中,但人物头顶的飞碟、转身后的火箭升空等镜头,都在打破这部伪“纪录片”的真实感,也在挑战着观众的心理认同。但这些荒诞感的意象在把观众从剧情中抽离出来的同时,也将观众带到更高的层面进而对身处的现实进行审视和批判。
怪诞是“在电影剧作中描绘人、事、物、景时运用的一种古怪离奇、悖于情理、异常变形、极度夸张的表现手法”,“它便于揭示人物及其心理活动,反映和揭露社会生活,表现或深化主题,并能给人以新奇、强烈、刺激性的感受,以引起兴趣,加深印象。怪诞手法虽不符合生活的表面现象,但从实质看,却符合生活底蕴和艺术真实,因而是可信的”。在贾樟柯的电影中,现实与怪诞穿插相见,在相互抵牾中完成对影片、对生活的现实意义的表达与升华。而在《山河故人》中穿插的几段视觉风格与迥异的DV画面以及拉煤车的片段,也同样在给观众怪诞的间离感外,造成某种意义上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为揭示影像与现实内在的矛盾性和关联性,也是物化人物命运、内心的方式。贾樟柯在影片中运用大量符号化、隐喻式的荒诞怪诞意象,将人与人、剧情与观众的现实意义融聚在现实外的间离关系中。
结语
贾樟柯的电影与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位成长于山西汾阳的导演也始终将影片重心交给普罗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在《三峡好人》《山河故人》等影片中,贾樟柯不遗余力地诉说着平民百姓的动人故事。现实性是贾樟柯电影的特性,而揭露普通人的生活也是贾樟柯电影的母题。变迁、失去、冷静、悲剧,这些也都是人物必经的过程和结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影片携带着天然的记录现实之属性,但却利用非现实意象来营造荒诞性、怪诞感,借以疏离观众与剧情,从而将观众拉出现实,上升到思辨和冷静观察的制高点,增强反思现实的批判力。
【注释】
①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35.
②贾樟柯.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J].新一代,2011(7):36-37.
③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01.
④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