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应最大化股东福利
[美]奥利佛·哈特
(哈佛大学,美国)
一、 问题的缘起:弗里德曼或许是错的
在此我要讲的是我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教授合作完成的近期工作。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问题,即什么才是对于企业而言合适的目标函数,企业应该实现怎么样的目标,特别是针对上市大企业。虽然我主要讨论美国和英国市场,但我相信相关的情景也适用于中国。
这一讨论的基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上的著名论断。当时盛行的说法是企业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盈利并非唯一追求目标。弗里德曼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这一观点太过社会主义,企业要做的是符合股东利益地行事,即在遵循社会规范(包括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赚钱即可。
对此,我们的建议是:一方面我们肯定弗里德曼的观点,即企业应该代表股东行事,其中股东指对于企业有投票权的投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不同之处是:我们认为企业的持股人也是普通消费者,他们除了关心利润外,还有社会性和道德性的考量。比如虽然电动汽车比燃油汽车更昂贵,一些消费者出于对能源的考虑仍会购买电动汽车;又比如人们会关心用了多少水或电;还有的例子是人们更偏好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咖啡,即使其更加昂贵。所以,如果股东们在实际生活中有这些考虑,为什么代表他们的企业不能像他们一样根据这些社会伦理行事,如保护环境等?
弗里德曼曾特别提及慈善组织。他认为相比于企业直接捐钱给慈善组织,由企业将利润分配给股东,再由股东自行决定捐赠给其偏好的慈善组织会更好。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企业的盈利活动和其社会影响(破坏活动,如环境污染等)可以完全区分开来。但现实情况是:这两者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发生过很多起校园枪击案。在沃尔玛,特别是美国南部的沃尔玛,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只要销售枪支是盈利的,沃尔玛就应该售卖,然后将利润分配给股东。如果有股东关心销售枪支带来的恶性社会影响,那么他们可以将分红收益捐给控枪组织。这个例子听起来有些不合常理,因为先让沃尔玛售卖武器再让其他组织消除其不良影响是与一开始沃尔玛就不售枪支相比更加低效的做法,且后者可能更符合股东的意愿。
另一个常提到的例子是污染河流。对于企业而言,污染河流可能有利可图,然后企业再将所获收益转交给持股人,由他们单独去为保护环境捐款。这个方案也很讽刺,因为先污染再治理的花费很可能远大于最开始就不污染的花费。这些是我们想到的反驳弗里德曼观点的例子。
还有观点认为,我们可以诉求于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观点是上述提到的这些社会影响如售枪带来的犯罪或环境污染等是企业行为的外部效应,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收税来规范其行为,如对环境污染的罚款等。如果我们总能制定出针对这些问题的有效税率,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企业做最大化收益决策时会自动将要交付的税费考虑在内,从而规范其行为。
二、 “干净的”(clean)或“脏的”(dirty)策略
我们要讨论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不能依赖于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我认为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总统就不相信环境问题,又比如美国政府不愿去处理枪支售卖问题。
我们这篇论文的中心想法非常简单且有力。接下来,我会简述我们的模型,再用例子进一步阐述观点。
我们的模型设定是考虑一个由创始人F全持股的企业,在第0期,创始人准备让公司上市以将其股份出售给公众。假设创始人将出售其全部股份,所以企业会由一群新股东所持有,也会有新的经理人。整个模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两期模型,第0期企业被出售,第1期企业被新股东收购并进行经营决策,简单来说企业只有两个选择,即“干净的”(clean)或是“脏的”(dirty)策略。“脏的”策略情形下,利润率更高,但会污染环境 。企业的选择是:选择策略后产生利润,再将利润直接分红给股东,模型就结束了,不再考虑更长远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选择“脏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破坏,如持枪的不良影响或者环境污染。这些破坏不会直接针对股东,比如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环境污染,但是股东们知晓企业行为会造成这些不良影响。我们将这些破坏以金钱d来衡量。另一方面,“干净的”行为不会有任何不良影响,这让我们的模型更简洁。

表1 策略模型
从表1可以看到,“脏的”行为的社会净收益等于公司利润减去造成的破坏,即110-30等于80。所以从社会总体收益来说,“干净的”策略更有益。
我们考虑持股人都是普通消费者,并不非常富有,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持有一小部分股份,即股权结构是高度分散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持股人作为普通市民都会或多或少地关心社会事务,或者用社会学中的名词——“倾社会性”(prosocial,即以社会目标为先)——来表示。如何将这种“倾社会性”特征放入模型中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这里我们采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我们定义:如果一个人在考虑某行为时,不仅关注自身收益,同时也会考虑这一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效应,即给社会影响一定的权重,注意这里并不要求100%的权重,而且这一情形只会发生在你觉得你对于该行为的发生负有责任时,我们称这样的人具有“倾社会性”。所以我们定义的是一种特殊类型(要求较低)的“倾社会性”行为。
比如说,想象一个烟草公司上市,我们定义的“倾社会性”消费者仍会持有其股份(即使他们本人并不赞成吸烟),这是因为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需要对烟草公司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但是,如果现在企业内部需要投票决定是否向儿童出售香烟,这些持股人就会开始考虑该行为对社会的破坏,即他们的“倾社会性”属性开始起作用。特别地,当票数处于50∶50的关键点时,将要投票的股东会觉得自己的选择至关重要,即需要对最终投票结果负责。如果他认为不应该售卖香烟给儿童,那么就会投票反对它。
此时,最终投票结果就取决于投票者放置在社会影响上的权重。比如我们假设,持股人在利润上放置100%的权重,不售卖香烟给儿童的利润损失是10,但同时售卖会造成的社会破坏是12,如果这位持股人放置50%的权重在社会影响上,那么现在他开始比较售卖的损失和收益,因为10大于6(等于12乘以权重50%),所以他会选择投票支持售卖。而随着持股人在社会影响上放置更大权重,他就更有可能投票反对售卖香烟给儿童。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投票结束后的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倾社会性”的人并投票反对售卖香烟给儿童,但最终投票结果是大部分股东同意售卖。我可能会有一个晚上睡不好,但第二天我仍会是这家公司的持股人,因为我不认为我应该为这个结果负责,我仍然愿意在这家公司投资。这就是我们的模型中抽象出来的“倾社会性”人格。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个人走在路上并不小心丢下一张纸,如果他是我们模型中“倾社会性”人格,那么他会走上前捡起这张纸,因为他感到自己需要对这张丢下的纸责任;现在是另一人丢下了一张纸,这位“倾社会性”人并不会上前捡起这张纸,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他的错。当然,现实中有些人总会捡起地上的纸,而有些人甚至不会捡起自己扔的纸。我们考虑的是位于中间的人格,即一种典型人物特征。
当然,人类道德的哲学并非我的专长。如果你是结果主义者,你可能会说,路面上有纸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去捡起它会花费一定的成本,那么是否捡纸只需考虑成本和收益即可,而与是谁扔的纸无关。所以我们通过引入“责任感”这个概念与结果主义论区分开来。
引入“责任感”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篇论文中有更详细的例子进行说明,但核心观点是:当每个消费者考虑策略选择时,其选择“干净的”策略的收益为100,而选择“脏的”策略的收益为110-30λi。这里,消费者不会减去全部危害30,但他们会给予λ的权重,其中λ就是我们所说的“倾社会性”系数,且这一系数因人而异。所以消费者i就会比较100和110-30λi的大小,其中0<λi<1,表征人们“倾社会性”程度。λi越接近于1,表示该消费者越“倾社会性”;如果等于0,则是“完全自私”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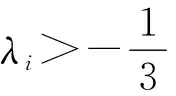
三、 企业应最大化股东福利
当然,我们也应该询问公司创始者:他的偏好是什么。当他出售这家企业时,他可能预见到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即企业要在“干净的”或者”脏的”策略中选择。那么创始者就可以在公司上市之前就将会影响策略选择的相关条例放在公司章程中,如这家企业必须选择“干净的”或者“脏的”策略。这就像是一种“完全合同”。当创始人出售股份时,这些股份就附带了相关合同,如制订特定的公司章程以规范企业行为。在实际中,企业甚至可以规定更多的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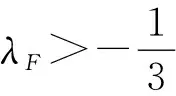

创始者如何防止这样的现象发生?如果创始人希望让公司保持“干净”,他有什么可选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
第一种方法是将相关选择写入公司章程,这种“完全合同”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因为人们难以预期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第二种方法是双层股权制(dual class stock)。这一方法更加常见。很多企业如谷歌、脸谱网上市时,除了有向大众出售的股份外,创始人还会持有更高等级的股份,从而对企业仍持有决定权。据我所知,中国的阿里巴巴也是类似的结构,马云仍会在较长时间里持有对企业的决策权。所以,此时创始人就可以控制企业的发展策略。但这种方法也有缺陷,比如随着时间推移,创始者后代中可能会出现对企业所有权的争夺,企业高层出现混乱,或是找不到合适的企业继承人。
第三种方法是采用“不完全合同”,阐明企业的发展宗旨,即把企业应该关心的其他目标如环境等写入章程中,这在美国的公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中比较常见,但也有操作性不强的顾虑。
第四种就是我们提倡的方法——投票。当企业被出售后,创始者不再干涉企业未来的发展策略,但是策略的决定应该由股东们投票决定,即公司经理人应该听取股东们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很多人听到这个建议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方法缺乏可操作性。当然,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经理人不可能每天咨询股东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我们想说的是:这主要针对那些会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决策,例如是否向儿童售卖香烟或沃尔玛是否售卖枪支等。现在的情况是:企业经理人做这些决策时并不咨询股东的意见,而股东们有时会通过建议书的形式在年会上给经理施压来表达意见。经理人并不喜欢建议书这种形式,而且即使建议书得到支持并通过,它对于经理人的实际行为也没有制约力。这与经理人应当听取股东建议这一原则相反。所以我们支持的是另一种形式,即经理人应该鼓励股东们进行意见反馈,特别当涉及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决定时。
让我们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为例。在这些国家中人们投票选举政治家,这就像是企业选择运营企业的经理人。但政治家并不要求民众对于每项具体政策进行投票,但是在某些重大决定时,政治家确实会让民众投票以咨询其建议。例如,在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这种现象很普遍。英国的脱欧投票也是一个著名例子,民众们投票决定是否脱欧。虽然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一投票的结果——脱欧,但是民众的意见在这种时刻应该受到重视。另一个例子是在澳大利亚,人们投票是否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法律。所以,在重要事项上通过民众投票来决定是一个相对好的方法,即使我们不能左右最终的结果。这样相似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在公司治理领域中。
一个重要区别是:市场中有很多公司,消费者可能因为购买指数型基金而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而且很多公司持股人以机构形式存在,这些机构如养老基金公司等又有他们自身的股东,所以当这些机构投票时,他们又应该咨询自己股东们的意见。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投票会非常多,难以在现实中实施。
但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仍然可以通过成立共同基金公司(mutual fund company)来解决。这些专业化的共同基金公司可以公开其对于某项公共事务持有的λi系数,那么持有相似λi系数的普通消费者就可以直接投资于这些基金公司,而不用再关心具体的投票。
当然,公开宣称λ系数并不实际,但是我们可以试想其他方法,如更具可行性的方法是成立“抑制攻击型武器”的指数型基金,即当有机会投票决定公司是否出售攻击型武器时,其会反对;而其他方面则和一般基金公司一样,在市场中进行广泛的投资,包括枪支公司。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市场中盛行着一种说法,即虽然消费者愿意持有多样化的股票,但这并不包括那些与他们意愿相悖的企业,如枪支企业、烟草企业或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但我们提倡的是另一种方法,即消费者仍会参与到这些企业中,并以此为契机改变企业发展策略。这一想法就可以通过成立有特定立场的共同基金公司来实现。
最后我想说的是,美国或英国,一个重要观点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即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那你就有信托责任,即你应该代表股东而非根据自身利益行事。相似地,如果你是机构,如养老金基金公司就应该对其投资人负责。
在美国,人们通常认为投资的信托责任就是对于货币收益率或利润率负责。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美国或英国公司是否应该从非洲撤资的讨论。一些股东希望企业退出非洲市场,因为这会支持当地某些政权变动,而这并非他们所希望的。比如,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就此事进行投票,它会宣称因为公司能由此盈利,所以秉持企业对收益率负责的态度,即“信托责任”,公司就应该留在非洲,继续投资。这些企业利用“信托责任”这样一个缘由认定它们只需要对企业收益率负责,而不用考虑社会影响。
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信托责任”指的是企业应该按照股东的意愿行事,而股东的意愿并非总是最大化企业利润。我认为企业经理人应该做的是咨询股东的建议,真正去问股东们的想法是什么。如果经理人这么做,他们会发现股东实际上会愿意牺牲一部分利润以带来更积极的社会影响。如果大部分股东都这么认为,那么忠实义务的做法就是从非洲市场撤资。所以,信托责任并非指最大化企业利润或市值,而是代表股东行事。最好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真实地去了解股东意愿,其中投票就是一种了解股东意愿的好方法。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过于武断,他宣称社会责任可以留给个人或政府去实现,而企业只需要关注盈利即可。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区分在现实中很难存在,特别是当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环境污染程度相关、不可区分时。在这种无法清楚区分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仅仅依赖政府或个人去解决这一问题。若企业此时仍然只关心利润,其必然造成企业的行为和使股东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间产生矛盾。因此,企业要做的是最大化股东效用,而非最大化利润。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询问股东们自身如何权衡货币收益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虽然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结合我们文中的模型,我们相信这一做法是完全可行的。
[唐雨璐 石烁 王永钦 译]
附:哈特教授主题讲演结束后,现场进行了互动环节问答,精彩纷呈。兹撷取一二,以飨读者。
问题1:您的模型将公司行为分为“干净的”(clean)和“脏的”(dirty)。请问凭什么标准来界定“干净的”还是“脏的”?谁有权力来做这种界定?另外,市场价值容易测度,但股东福利难以测度。因此,股东福利最大化并不可行。请问您如何看?
哈特:构建模型就是要对事实做简化并抽象,以方便研究。之所以区分为“干净的”和“脏的”也是这个道理。“干净的”没有社会影响,“脏的”有影响,仅此而已。但是,模型从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则是另外一码事。尽管不同地方的人们的价值观可能在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存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价值标准。你的问题虽然有道理,但是在我所讨论的范围内,我不认为人们在主流价值观上是有根本分歧的。
关于测度,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将更广泛的社会指标纳入到公司绩效考核中来。(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公司致力于测量其他公司对环境的影响。所以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测度方法以及更多的可被测度的指标。
我也需要指出,虽然我的研究谈到了最大化问题,给人的感觉是“必须先要测量出一个值,才能最大化”,但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投票人的感受。投票人心理会对公司的议案有一个价值判断。
另外,不能因为“错事的价值容易测量,好事的价值不易测量”,我们就去最大化错事的价值。我还是要强调,“信托责任”不只有管理层最大化股东价值这一层含义,狭隘理解“信托责任”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改变这一成见。
问题2:公司毕竟有“价值最大化”的本质属性。如何使公司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您有什么建议?
哈特:我并不是说赚钱不重要,而是要把决策的范围扩大。有些问题,可能30%的小范围股东认为是“干净的”,但是在60%的股东看来,却是“脏的”。因此,决策过程和测度都很重要。
正如我之前所说,测度股东福利很难,但是向股东问一问“某个决策背后的取舍”并不难。我认为,公司不应再找借口去做错事,而是应该抓住机会变“干净”,特别是提高环保意识。
另外,变“干净”与“赚钱”并不矛盾。公司积极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会创造更有意义的市场价值。“干干净净赚钱”不但是乐事,还是好事。
问题3: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包含了社会福利。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市场机制,即如果某个公司做出了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人们就会拒绝购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股票。您怎样看待市场在调和公司目标与社会目标关系中的作用?
哈特:上市公司都会声明自己承担“社会责任”,但实际上,这个“社会责任”指的是上市公司会关注消费者、股东等关联方的利益,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盈利。
当然,你讲的机制是存在的,但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公司的行为破坏了环境,人们就不再购买其产品或者股票;或者公司做了好事,业绩就会增长,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的,“赚钱”和“做好事”就不矛盾了。此时,股东投票会一致同意公司“尽力赚钱”。
而实际上,一些公司的行为产生了污染或者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市场并没有起作用。我们所说的“倾社会”股东仍然会乐于持有烟草公司股票,消费者也仍然会购买“做坏事”公司的产品,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决策程序,所以他们感觉公司的行为与我无关,我只要享受最大化价值就可以了。
“倾社会者”是否能够通过市场影响公司决策,或者需要“倾社会者”持股达到多少占比,才能推动公司做“好事”,这又是一个实证研究的任务了。不过,我个人对这种市场机制仍然表示怀疑。这种机制可能有益,但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问题4:外国股东不会特别关心公司行为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后果。推而广之,您怎样将外国股东纳入到决策机制,推动公司做好事?
哈特:首先,我们当然可以将公司行为的危害性扩展到世界范围,或者我们的投票也可以是关注全球事务的,例如污染往往是国际性的,这样可以不必在意股东的国别异质性。其次,我也必须认同,必然存在外国股东不关心本国社会利益的情况。不过我们也不必强求,他们这样做也有合法的一面。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我们都有一份责任,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