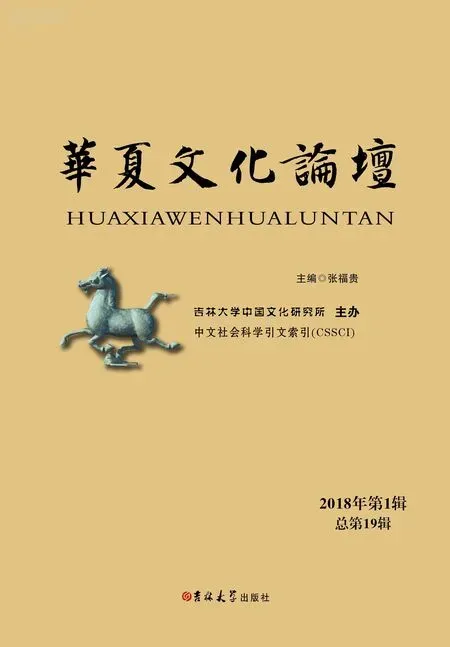水仙、良药与吉兆:中古时期“蜘蛛”的文化意象
——从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谈起
周能俊
【内容提要】中古时期“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是当时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对自然生物与现象规律性认识不足而产生的神秘主义理解。在中古人们的认知体系中,“蜘蛛”的文化意象与道教水仙、女性、毒药、良药、吉兆、乞巧节乞巧的重要道具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的创作者为该仙话的文学创作需要描写了女性水仙的蜘蛛形信物,利用“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帮助仙话中元柳二人帮助该水仙寻亲等情节的顺利展开。仙话作者之所以得以利用“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推进仙话情节发展,是与中古时期人们对于“蜘蛛”特殊文化意象的广泛认识以及道教等宗教神秘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整个中古时期,利用“蜘蛛”等自然生物与现象的特殊文化意象进行文学创作的情况多有发生,且大部分创作者均对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而中古时期“蜘蛛”特殊文化意象的广泛认同与传播,也反映了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逐渐被纳入道教等中古宗教信仰与认知体系构建的历史进程。
在著名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中有一段涉及蜘蛛的细节描写,南溟夫人派一位水仙使者送元、柳二人返家时,“使者谓二客曰:‘我不当为使送子,盖有深意,欲奉讬也。’衣带间解合子琥珀与之,中有物隐隐然若蜘蛛形。谓二子曰:‘我辈水仙也。顷与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岁,合弃之,夫人令与南岳郎君为子矣。……’……战慄之际,空中有人以玉环授之,二子得环送于岳庙”。其中特意强调了作为水仙嘱托信物的琥珀盒子里面的事物乃是蜘蛛形的,可见,在中古时期的道教认知体系与社会传统中,蜘蛛是有着十分特殊的文化内涵的。本文拟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探讨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中所涉及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分析中古时期人们对于蜘蛛的传统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管窥中古时期道教等宗教神秘思想的发展与社会认知及生活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蜘蛛的定义

一为结网。如“蜘蛛作网以司行旅”,以及“蜘蛛南北巡行,罔罟杜季利兵,伤我心臂”等。
二为“长踦”,即蜘蛛腿脚特别长的形态。如“蟏蛸,长足蜘蛛也”,与“蟏蛸长踦,音崎㠊之踦,小蜘蛛长脚者,俗呼为喜子”等。
在中古时期,由于人们缺乏对自然生物与现象的规律性、科学性认识,因此对于蜘蛛的认知只能停留在部分现象或个别共同特征等浅层次的概括归纳之上。由此而产生对蜘蛛等自然生物与现象理解的片面与偏颇,甚至谬误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故而当时社会有一种主流观点就认为蜘蛛对人是无益的,如“蜘蛛之务,不如蚕之緰。测曰:蜘蛛之务,无益于人也。……范曰:‘蜘蛛有丝,虽其勉务,非人所用,则不如蚕一緰之利也’”。唐代著名诗人孟郊亦作诗讥刺蜘蛛“万类皆有性,各各禀天和。蚕身与汝身,汝身何太讹。蚕身不为己,汝身不为佗。蚕丝为衣裳,汝丝为网罗。济物几无功,害物日已多。百虫虽切恨,其将奈尔何”。
但从《南溟夫人传》的记叙来看,那位水仙使者的行为显然与蜘蛛“济物几无功,害物日已多”的形象大相径庭,可见其对于蜘蛛所代表的文化意象有着不一样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可能也广泛地存在于中古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与社会认知体系之中。这一互相龃龉的现象,颇有值得研究的必要。本文即试图以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中有关蜘蛛的记述为出发点,解析中古时期人们对于蜘蛛的社会认知,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文化意象等相关内容。
二、水仙与女性
道教典籍中关于“水仙”的记述颇有语焉不详之处,且“水仙”本身也有许多含糊难明的地方。如葛洪认为的水仙应该是服食金液斋戒百日而不想去世的修道者,“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其经云,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于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斋戒百日,不得与俗人相往来,于名山之侧,东流水上,别立精舍,百日成,服一两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斋戒百日矣”。孙思邈则指出水仙与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夫天生五行,水德最灵。浮天以载地,高下无不至。润下为泽,升而为云,集而为雾,降而为雨。故水之为用,其利博哉。可以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寻之莫测其涯,望之莫睹其际。故含灵受气非水不生,万物禀形非水不育。大则包禀天地细则随气方圆,圣人方之以为上善。余尝见真人有得水仙者,不睹其方。武德中龙赍此一卷服水经授余,乃披玩不舍昼夜。其书多有蠹坏文字颇致残缺,因暇隟寻其义理,集成一篇好道君子勤而脩之。神仙可致焉”。由此衍生出“在人谓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变化之曰神仙”的叙述。可见,在中古时期的道教神仙体系中,水乃是道教水仙成道的重要因素与典型标志。
再徵诸现存中古时期有关水仙的“子胥死,王使捐于大江口,乃发偾驰腾,气若奔马,乃归神大海,盖子胥水仙也”“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唯念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思伯奇,作《子安之操》”“(孙)恩穷戚,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等记载。可以进一步肯定水仙与江河湖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甚至因水而生、凭水而居、依水而活、由水而神。
与此同时,在中古时期的生活传统与道教认知中,蜘蛛与水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据《淮南万毕术》载,“蜘蛛涂布而雨自晞。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煞以涂布,而雨不能濡也”。可见,在中古时期的生活传统与社会认知中认为将蜘蛛进行一些处理后涂抹在布上,可以使布匹具有防水的功能。同书亦载,“取蜘蛛涂布,天雨不能濡之”。可知,中古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中蜘蛛具有防水特殊功用的观念是确实存在的。
又据《淮南万毕术》载,“取蜘蛛与水狗及猪肪置甕中,密以新缣,仍悬室后百日,视之。蜘蛛肥,杀之以涂足,涉水不没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内甕中合肪百日以涂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涂足,不用桥梁”。可见,时人根据蜘蛛具有防水这一特殊的功能,衍生出蜘蛛乃是合成人肉身涉水神方重要构成材料的认知。而中古道教修炼体系显然也采纳了此种认识,“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马,以合冯夷水仙丸服之,则亦可以居水中;只以涂蹠下,则可以步行水上也”。又据“冯夷,弘农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河伯。又一说,华阴人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的记载,可知《抱朴子》所载的乃是以冯夷这位传说中的水仙河伯命名的神药,服食即可安居水中,涂于足下亦可肉身涉水行走,而其主要的材料就是赤斑蜘蛛。由此可知,在中古道教修炼体系中,蜘蛛乃是水仙修炼成道的关键元素。
再细检《续仙传》所录该仙话,水仙使者与元、柳二人对话中增加了“水仙阴也,而无男子”的道教水仙介绍。该解释明确指出了道教水仙的两大特征,即偏阴属性与女性特质(从上文所引葛洪、孙思邈等记述与伍子胥等水仙记载可知中古道教水仙并无限定非女性不可的特质。然该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故述而不论。但此种关于水仙颇为矛盾的表述亦可证明上文所述中古道教认知体系对于水仙定义的模糊不清和语焉不详)。从物质的阴阳属性上来说,中古人们认为蜘蛛的习性是“利在昏夜”,以及“炉冷蜘蛛喜”。由此推论,普遍地认为蜘蛛属性是偏阴寒的。与此同时,在中古医书中,蜘蛛属性也比较偏阴寒的。《名医别录》中即有“蜘蛛,微寒”的记述。而“蜘蛛,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为蜘蛛”的记载,似乎也可以推测在道教认知体系中蜘蛛也是较为阴寒的属性。而蜘蛛此种偏阴寒的属性恰好与道教水仙的偏阴属性一致,两者在这一方面具有同质性。
另一方面,从女性特质的角度来看,在中古的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体系中,蜘蛛的某些形态习性与中毒反应等也常常被与女子孕妇联系在一起。如“䵹鼄为大腹,其性然也。梦见蜘蛛,忧怀任妇人也”。显然是认为蜘蛛的形态与怀孕妇女大腹便便的样子很类似,才有梦见蜘蛛就像是看见怀孕妇人的错觉。又如“又有赤腰蜂,养子于蜘蛛腹下”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妇人养育婴孩的情况。再如“《经验方》治蜘蛛咬,遍身生丝。羊乳一升饮之。贞元十年,崔员外从质云:目击有人被蜘蛛咬,腹大如孕妇。其家弃之,乞食于道。有僧遇之,教饮羊乳。未几日而平”的记载中,被蜘蛛所咬的人中毒后腹部鼓胀如同孕妇,而这也让中古人们怀疑蜘蛛是否与孕妇在属性或形态上有某些相通之处。正因为蜘蛛在形态等方面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生养子女,而这在中古时期恰恰被认为是妇女的天职,因此,蜘蛛也就自然被与妇女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在某些志怪杂谈中,总是认为幻化成美貌女子魅惑青壮男子的妖怪有很大一部分是蜘蛛变化而成的。如“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往来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燕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的故事就是蜘蛛幻化成美貌妇人迷惑男子的典型叙述。由此可见,在中古时期的人们的认识里,蜘蛛的文化意象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在中古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中,蜘蛛具有防水的特殊功能,而这正是因水而生、凭水而居、依水而活、由水而神的水仙所需要的。与此同时,蜘蛛更是道教水仙修炼成道的关键元素。加之,蜘蛛在偏阴属性与女性特质上与道教水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同质性。由此推测,《南溟夫人传》中的水仙使者以蜘蛛形的信物代表自己作为女性水仙的特殊身份是极为契合与恰当的。
三、毒药与良药
在中古人们的普遍观念中,蜘蛛是一种毒性十分剧烈的生物。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就曾记述“巴蜘蛛,大而毒。其甚者,身运数寸,而踦长数倍其身,网罗竹柏尽死。中人,疮痏潗湿,且痛痒倍常。用雄黄苦酒涂所啮,仍用鼠妇虫食其丝尽,辄愈。疗不速,丝及心,而疗不及矣”。可见此种巴蜘蛛的毒性之强,对人危害之大。又如“顷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为网,其形绝大。此僧见蜘蛛,即以物戏打之,蜘蛛见僧来,即避隐。如此数年。一日,忽盛热,僧独于房,因昼寝。蜘蛛乃下在床,齧断僧喉成疮,少顷而卒。蜂虿有毒,非虚言哉”。该故事情节自有其荒诞不经之处,但文末“蜂虿有毒,非虚言哉”的感叹亦深刻反映出中古人们对于蜘蛛剧毒的戒慎恐惧之心。复如“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复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于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为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视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焉,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舆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悟所梦。觉为梦日,果其杀蜘蛛于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该故事虽是传奇仙话,但文中一再述及蜘蛛有剧毒、“虽小,螫人良药无及”等言辞。可见,中古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中,对于蜘蛛有剧毒且极具报复心理这一认识的广泛程度与深刻记忆。
甚至在许多中古时期的医学典籍里,亦有如“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的记载,提醒医者与病人注意蜘蛛的毒性。不少医书中更有治疗被蜘蛛噬咬中毒的药方,如“取大蓝汁一碗,入雄黄、麝香,二物随意看多少,细研,投蓝中,以点咬处。若是毒者,即并细服其汁,神异之极也。昔张员外在剑南为张延赏判官,忽被斑蜘蛛咬项上,一宿,咬有二道赤色,细如箸,绕项上,从胸前下至心,经两宿,头面肿疼,如数升碗大,肚渐肿,几至不救。张相素重荐,因出家资五百千,并荐家财又数百千,募能疗者。忽一人应召云:可治。张相初甚不信,欲验其方,遂令目前合药。其人云:不惜方,当疗人性命耳。遂取大蓝汁一瓷碗,取蜘蛛投之蓝汁,良久方出,得汁中,甚困不能动。又别捣蓝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之,至汁而死。又更取蓝汁、麝香,复加雄黄和之,更取一蜘蛛投汁中,随化为水。张相及诸人甚异之,遂令点于咬处,两日内悉平愈。但咬处作小疮,痂落如旧”。可见,中古医药界对于蜘蛛剧毒亦有十分深刻的认知,且治疗蛛毒乃是对当时医者医术的极大考验。
与此同时,在中古医典与道教典籍中,蜘蛛是一味十分重要的药材。如“疗人心孔塞,多忘喜误。七月七日,取蜘蛛网著领中,勿令人知,则永不忘也”。尽管此方法以现代医学来看其疗效恐怕很值得怀疑,但却可以管窥在中古的医疗观念与道教认知中,蜘蛛有其独特的医疗价值。而《名医别录》亦载,“七月七日取其网,治喜忘”。显见,在道教认知与医疗体系中,蜘蛛治疗健忘的认识亦是长期存在并影响深远的。
除此之外,蜘蛛还被认为可以治疗疟病、中风、疝气、脱肛等多种疑难病症。
综上所述,在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中,蜘蛛有剧毒且极具报复心态的形象是深入人心的。且在中古医药与道教典籍记载中,蜘蛛作为一味重要的药材对治疗多种疑难病症具有突出的疗效,特别是在治疗健忘病症时有奇效。由此推测,蜘蛛的这些认知特征可能也恰好符合该位女性水仙期盼丈夫孩子始终挂念自己的希望,以及警告家人若背叛自己将会受到最恶毒报复的威胁。
四、吉兆与乞巧道具
据《西京杂记》所载,“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灯火华得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则咒之,火华则拜之,乾鹊噪则餧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将蜘蛛认为是诸事有喜的瑞应或吉兆。而 “蜘蛛集于军中及人家,有喜事”的记述更加明确地指出蜘蛛聚集在军队驻地或个人家中意味着有喜事临门,显见在中古的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中,蜘蛛乃是代表着十分吉祥与顺利的瑞应。那么蜘蛛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吉兆呢?
其一为预示有亲朋拜访。如“一名长脚,荆州、河内谓之‘喜子’,云此虫来着人当有亲客至,亦如蜘蛛为罔罗居之”。
其二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的徵验。如“(张)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蜘蛛大如栗,当寝门悬丝上。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
其三为乞巧节乞巧的重要道具。六朝时期,荆楚地域的人们就有乞巧节“是夕,人家妇人结綵缕,穿七孔鍼。或以金银鍮石为鍼,陈瓜果于庭中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的传统习俗。其中就将蜘蛛在瓜果上结网视为乞巧节最好的吉兆。进入唐代,特别是唐玄宗时期,乞巧节将蜘蛛结网疏密作为乞巧多少瑞应的影响更趋广泛。如“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的记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延至五代时期,洛阳的百姓仍然延续了“乞巧使蜘蛛结万字,造明星酒,装同心脍”的传统。可见,蜘蛛结网以为乞巧瑞应的习俗贯穿于整个中古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综上所述,在中古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中,蜘蛛被认为是预示着“亲客至”、加官晋爵的吉兆,更是乞巧节进行乞巧活动的重要道具。由此推测,《南溟夫人传》中的水仙托付元柳二人将蜘蛛形信物给其子时,想必也隐含了该水仙期盼家人团聚、子孙前途远大等的美好祈愿。而这些祈愿恰好是与中古时期人们认知体系中蜘蛛所预示的吉兆相吻合的。
结 论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类“寓意之文”,“要在分别寓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穿凿附会之讥固知难免,然于考史论文之业不无一助”。结合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所处中古时期的社会背景,可知蜘蛛这个“纪实”点正可以用来解读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这个被“加密的未来”。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中,该仙话的创作者利用“蜘蛛”在中古时期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中丰富而特殊的文化意象,在南溟夫人派该女性水仙送元柳二人返程的特定时刻,该水仙将隐喻自身特殊身份、对家人美好祈愿与警告寄望完美结合的蜘蛛形信物托付元柳二人交给自己的后代。元柳二人因之得以取信水仙之子,得到了许诺的酬金。这一仙话情节在推论创作者利用中古时期“蜘蛛”的文化意象隐喻水仙的身份与期望,以推动仙话情节的发展后,随即豁然开朗。《南溟夫人传》的创作者利用“蜘蛛”在中古时期社会认知体系中的特殊文化意象作为女性水仙隐喻自身特殊身份和殷切期盼的信物证明,使得该仙话的情节可以自然随着元柳二人前往南岳寻仙而进一步深入展开,故其设计是成功的。
道教仙话《南溟夫人传》作者之所以能够利用“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作为该仙话情节展开的关键细节,实由于中古时期在社会认知与生活传统中对于“蜘蛛”特殊文化意象的广泛认识。中古时期的人们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对于以蜘蛛为代表的自然生物认识不多不深,对于自然现象和规律也多因神秘难测而误解迷信;随着汉魏六朝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的发展,加之传统天人感应思想的桎梏,对蜘蛛等自然现象的误解与想象更趋复杂,因而《南溟夫人传》作者得以利用“蜘蛛”的文化意象进行文学创作。《南溟夫人传》的创作者也并非中古时期唯一利用“蜘蛛”特殊文化意象进行文学创作者,《异苑》《宣室志》等中古典籍所录有关“蜘蛛”故事均试图通过自身对中古社会认知和生活传统的理解,利用“蜘蛛”的特殊文化意象开展文学创作。
由此可见,中古时期,“蜘蛛”等自然生物与现象的特殊文化意象的演化与传播,大多由于认知水平的局限以及由此引发的想象与误解。与此同时,以“蜘蛛”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与现象的特殊文化意象之所以在中古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中大行其道、经久不衰,除了中古时期自然科学认知水平的局限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以道教为代表的宗教神秘思想在中古兴起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吸收了中古时期社会认知体系与生活传统中的大量要素,融入其逐渐构建完善的宗教信仰与认知体系的历史进程。而这些宗教信仰与认知体系在形成以后,亦对以“蜘蛛”等自然生物与现象的特殊文化意象的演进与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