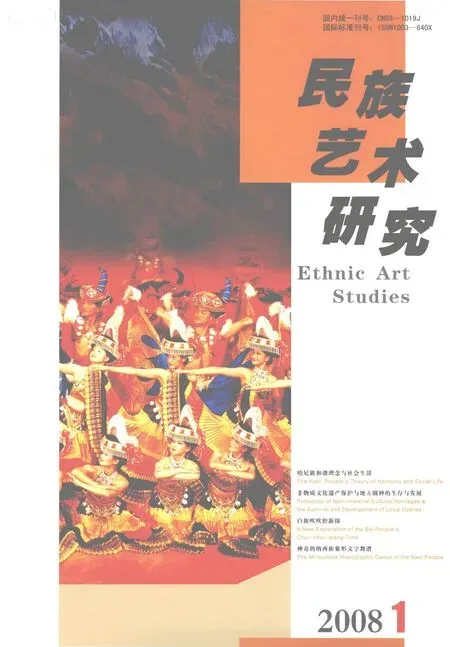那片土地,那片星空,那些路
李宝群
近些年,我一直关注西部,先后去过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陕西等地。或是与当地剧院团合作创作剧目,前去采风搜集创作素材;或是加入“背包族”漫游远行。西部独特的历史文化,奇异的自然地貌,别样的风俗民情,质朴醇美又充满浪漫气息的少数民族生活,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时冲撞着我的内心,唤起我的创作冲动……
著名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最让我着迷。即便回到北京,我也经常查阅相关资料,经常沉浸在想象之中:遥远的年代,遥远的西部,驼队在夕阳中走来,马队在晨光中上路,漫漫长路之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来自不同宗教国度的僧侣,也有苦守关卡的将士,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土著居民,也有强人悍匪、江湖侠客……长路漫漫,岁月滔滔,其间有多少浪漫故事、多少生命传奇。我渴望着,梦想着有一天能把它们变成文字,呈现于舞台。
一、从丝绸之路和《丝路天歌》说起……
那一年,我和宁夏演艺集团合作了话剧《丝路天歌》,整个过程让我终生难忘。接受创作邀请之初,宁夏方面只是提出创作一部反映民族团结、展现党项羌人历史的戏,写哪一段历史、讲什么故事没有具体限定。看过若干历史资料后,我便动身前往宁夏采风。在宁夏,我看到广袤的平原、无尽的沙漠、时而湍急时而平静的黄河、雄阔绵延的贺兰山,也看到了古西夏王陵、古岩画和很多历史遗存,更有与汉文化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也了解了很多西部的历史——这历史,如一部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在我面前。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在西部辽远的土地上,有过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过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和中原文化为背景的汉民族一起书写了一段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我的思绪穿过现实,走进一个个遥远的朝代……
我要写的党项羌人最早发源于黄河源头一带,后被日益强大的吐蕃打败,被迫离开故土,颠沛流离,不断迁移,最后定居宁夏地区,这里肥美的牧场,适宜的气候使他们繁衍壮大。党项羌人建立了西夏王朝,这一王朝与宋、吐蕃、辽、金并存,直到被强悍的蒙古大军所亡。本来,在采风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构思。在党项羌人与汉人的交往史上发生过一件大事: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曾有过一次灵州之行,在宁夏灵州城,李世民会见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众多首领,史称灵州会盟。这一盛会使战乱不断的西部边陲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宁。我最初的构思是正面写唐太宗的灵州会盟,但这么写很有可能是一出很常见的历史正剧,而且很容易落入陈旧的写作套路之中——无外乎写唐太宗出长安,如何渴望缔造汉与西部各族的和平,而各族首领心想不一,或愿结盟,或反对结盟;再写大唐官员意见不一,经过一些波澜一些会合,最终实现了结盟。这么写可以顺利通过完成任务,但极有可能是一部很平庸很一般化的作品。正在困惑苦恼之时,“丝绸之路”闯进了我的视野,深深地吸引了我。著名的丝绸之路以毗邻宁夏的陕西长安为起点,横跨西北数省,穿过大漠戈壁,祁连雪山,河西走廊,一直通往遥远的西方各国,纽带般联结起了东西方两大文明。而宁夏也是其中一部分,远道而来的旅人多经此去往长安,他们在这里看到了黄河和两岸的农田和生活其中的人们。
丝绸之路最鼎盛的时期是唐朝,而唐贞观年间,正是党项羌人苦苦寻找新家园的时段,党项羌人的几大部族相继归附唐朝,一些未归附的小部落也在向往着强盛的大唐。
我又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史料,请教了有关专家。最后,我痛下决心彻底推翻原来的构思,另辟新路。故事仍发生在大唐贞观年间,但不正面写灵州会盟,只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全剧的重要背景,也不正面写唐太宗及各族首领等政治家大人物,而是把写作的焦点集中到若干民间小人物身上,以行走在漫漫丝绸之路上的各色人物为主要人物形象。剧中大部分场景是风沙漫天的大漠戈壁、暴雪险峰、古堡客栈,这将是一部西部特色异常鲜明的民间传奇剧。创作就是这么神奇,“丝绸之路”这条神奇之路的“出现”,迅速打开了我的想象,也点燃了我创作的激情。我设计了一群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身世背景、怀有不同动机出现在“丝绸之路”上的旅人行者——他们中有苦苦寻找新家园的党项部落老首领及其儿子、女儿,有吐蕃族派往大唐的将领及其随从,有千里跋涉前往长安做生意的波斯人及其向导,还有漂泊异域、渴望返回故乡长安的汉族文人,还有契丹和汉族混血的牧羊女……一场大风沙暴让这些性格各异、信仰不同的人物意外走到了一起,由此展开了一段段曲折跌宕的故事。这些人物之间有的世代结仇怨、随时可能刀箭相向,也有相亲相爱的生死恋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想去长安,去大唐,只好一起上路。这既是一次朝圣之旅,也是一次归乡之旅。一路上时而是千里戈壁茫茫大漠,饥渴、酷热,干旱缺水;时而是狂风怒雪,野兽来袭;时而是荒凉古堡;时而是繁华边城。大生大死大仇大爱渐次展开,每个人都展露出不同的人性,每组人物关系都在渐渐发生变异。同遇危难、同生共死,使仇恨在消融、友爱在生长,内心对彼此仇杀的厌恶、对和平友爱的向往使他们彼此走近,终于结成兄弟,一行人走到了黄河边,走向了长安。这当然是一部表现民族团结的戏,同时,它也是一部与人性有关的戏,一部化仇为友、化恨为爱的戏,也是一部展现丝绸之路独特自然人文风采的戏。独特的内容必然要求独特的形式,在这部剧本中,我尝试了诗剧的写法,很多语言、场景是诗化的,舞台样态也是写实与写意结合、再现和表现结合的。而且,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丝绸之路”上,人物大多处于跋涉行走状态,这种写法在国内主流戏剧中还不多见。这也要求舞台呈现势必不同于传统话剧的演出样态,包括时空变化、场景迁换,都要“因戏而变”。剧作中还揉入了当时的舞蹈、民歌民谣、汉人的诗词等民族性、地域性元素,全剧因此更具历史质感和地域特色。
宁夏的文化主管部门认可了这个“以小写大”“以小人物写出大的时代走向,大的历史趋势”的写法,导演吴晓江、舞美刘科栋等主创人员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经过艰苦的排练,整个演出呈现出极强的历史质感和民族地域特色,也颇具现代戏剧的审美品质。
《丝路天歌》推出后,受到了宁夏观众的欢迎,后几进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原创话剧展,得到了戏剧界专家和北京观众的认可,并入选国家舞台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这出戏的创作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触动,也让我有了一个重要收获。我真切地发现,也更坚定地确信——中国的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古老的丝绸之路蕴藏着丰富的写作“富矿”,它可以开启创作者的灵感之门,使创作出现不寻常的变数,更具有燃烧创作者激情的力道。
二、继续寻找我心中的“丝绸之路”
《丝路天歌》只是一个开端,我从此走上了研究西部、探访丝绸之路的旅途。
这几年,我多次前往西部,每次前往都有很多收获。我发现,西部这块土地上有太多可供戏剧写作的创作素材。我也感叹:中国戏剧界,特别是中国的戏剧编剧真是拥有着极为丰厚的写作资源,只要我们用心去开掘,去发现,去书写,完全可以借助西部这块土地,借助古丝绸之路积淀下来的历史宝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进入甘肃,经兰州,去张掖,奔敦煌。一路上,绵延不绝的祁连雪山,辽阔无际的牧场,雄奇的古长城,一座座边城重镇,我看到了很多,想到了很多,头脑中刮起了 一场场风暴……丝绸之路哪里只是一条商贸之路,文明交流之路?它也是一条华夏民族展现开拓精神之路、一条无数知名不知名者用生命书写的历史长路,无数星星缀满了雪山大漠上的星空。
张骞,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第一人。此前很多文艺作品都书写过他的故事,舞台剧也很多——歌剧、舞剧、话剧、戏曲,我看过许多部。大多写的是一位不辱君命、不负重托,吃尽苦头、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伟业的大英雄;但真的走近这个人物,了解他的人生轨迹,感受他的心路历程,我却看到了另一个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前其实只是长安城中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朝中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官员。他应募出使,被俘留在西域十余年,几乎被大汉的上上下下忘掉了。汉武帝几度用兵西域,远征匈奴,均不顺利,那时也没有人记得那个若干年前的使臣。而张骞也已在匈奴娶妻成家,当他逃出篱笼,辗转回到长安,初见汉武帝和满朝文武时,也没有人对他的归来寄予希望,只是当他献上用命换来的西域各国的详尽情报之后,人们才对他刮目相看。他帮助霍去病等人大败匈奴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他后来又因误了军机被贬为庶民。此时的张骞完全沦为一个寻常百姓,又成了一个落魄之极的小人物。历史舞台上的追光仍未照射到他的身上。只有当霍去病等人横扫匈奴、平定了河西走廊之后,张骞再以庶民之身领命出使西域,最终完成了打通西域的“凿空”之旅,万邦来朝之时,他才成为历史的大功臣。在无比漫长的日子里,他的妻子死了,他在西域同生死共患难的匈奴挚友死了,他内心有多少煎熬、多少苍凉、多少辛酸、多少苦涩,那是有多么丰富的内心活动,可惜的是很多表现张骞的作品里我们都不曾看到——怎么把一个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丰富复杂的“人”,我们的戏剧还没有回答好这个课题,戏剧人还没有交出一份最好的答卷。
霍去病,另一位风云人物。我们的戏剧多少次表现过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军事奇才,但留在我记忆里的却几乎是零。我们真的写出了真实的霍去病吗?真写出他的内心世界了吗?当他铁骑突进、横扫千军,一次次血战之后,伫马苍茫天宇,回看死尸无数的战场,面对天空中飘动的无数亡灵之时,他曾经有过怎样的心境?他的英年早逝是一个极大的历史事件,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历史学家难解,剧作家其实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各不相同的表达。
还有,汉武帝,真实的汉武大帝,被我们的戏剧作品呈现出来了吗?他对华夏之外的世界充满了了解的热望,这是一个极想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在大汉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不寻常国家的帝王。他的目光和胸襟远远不止于如何荡平匈奴、如何安靖西陲,他心中有很大的梦想。他代表了一个正在上升的民族渴望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看到同在天宇下生活的其他人类族群。
继续寻找,很多有价值的素材继续进入我的视野。
莫高窟的王道士,那个身材矮小、有些委琐、可怜可恨可叹可悲的古老文化的看护者,他的故事难道不是一部沉甸甸的好戏吗?通常我们都把王道士看成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莫高窟珍贵文物遗失的“首恶”,但是,当我们细细了解那段历史时就会发现,他有过许多无奈、许多无助。当他意外发现了窟内存有大量宝物时,曾多次向当地政府官员请示、求助,但各级官员却一再推诿,不管不顾毫不重视,草草应付了事,谁也不愿、谁也不想担当责任!可怜的王道士凭一己之力是完全无法保护这些宝物的,何况愚钝无知的他也根本无从知道这些东西到底价值几何。他将宝物卖给外国“猎宝者”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得到些银两用于维修荒芜不堪的莫高窟。于是才有一场天大的悲剧降临,他也成了千古罪人,担起了一世世的骂名。整个过程令人心痛,令人扼腕叹息。这完全是一出大戏,一部骨子里有些荒诞又令人异常沉重的悲喜剧——这样一出戏可以给后人多少思考,多少警醒?
继续寻找,仍然有很多东西撞击我的心。
在青海,当年文成公主去往吐蕃的漫漫长路上,到处都是关于她美丽、浪漫、悲情的传说,连泉水、山峰都与她有关。望着那些山峰,我感触良多:有多少人写过文成公主,有多少戏演过文成公主,可这个女子仍然是写不完的。从长安出发,远赴吐蕃这条长路,也是文成公主的一条心路。文成公主自身其实就是一条“丝绸之路”!这个女人最美好的身体、最动人的青春、最宝贵的生命变成一条长路,连接起了汉藏两族,应该有一出更感人的好戏来展现她。昆仑山,被称为万山之祖,那里还有很多西王母的传说,这些传说中的王母娘娘竟然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个王母娘娘。还有,格萨尔王的传说,仓央嘉措的传说也精彩异常,这些都是戏剧创作的绝好素材。还远不止这些,西部的现代生活也异常丰富,一座座城市,一处处乡村,一处处牧场,到处都有鲜活的当下故事。每一段旅程,我都遇到了许多人,倾听他们的身世,他们的故事。
在敦煌,风狂沙涌的鸣沙山下,一个牵骆驼的小向导成了我的朋友,他还不满十七岁,身体面容还是一少年,但热情周到老练,全然是一个“老江湖”了。他边走边讲述他的故事,因为家庭贫穷,他很小便辍学了,当向导挣钱已经三年。他讲到了他一家艰难的日子,他多病的父亲、母亲……他说他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他喜欢他的骆驼,为每头骆驼都起了绰号;他也喜欢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让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很多事。他将来的梦想是干好这份工作,照顾好父母,以后也要找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张掖,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讲张掖城的历史,讲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未来的计划和梦想,他还请我见了他在家里养羊的妻子……他们夫妇俩一个在外开车拉活,一个在家养羊,供孩子们读大学。他们经常梦想着有一天孩子们大学毕业,家里的积蓄多起来,买更多的牛羊,也能有一片属于他们的牧场,梦想着他们下一代生活更加美好。
沿途,随时能见到各样的人——有性格爽朗的牧民、木讷憨厚的山民,有从外地来打工多年的饭店老板、经常驱车前往无人区的退役军人,还有来自各地的旅游者。更让我难忘的是可可西里无人区里的环境保护站,简陋的堆满生活用品的房子,远离家乡的志愿者。他们长年在无人区里用心保护珍稀动物和自然生态,而最早的志愿者已经牺牲在盗猎者的枪下,长眠在藏羚羊出没的地方。还有保护站外有许多石头,上边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对守护者的深深敬意,对保护好这片大地的生态的深深祝福……
活在当下的人同样是一本本厚厚的书,他们的故事同样是一部部相当精彩的好戏。我一直认为,人类有两部历史——一部是写满英雄名字的历史,记录的是帝王将相各种重要历史人物;还有一部是民间史,是由各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小人物书写的。后者对艺术家来说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那里埋藏着更丰富的人性、更多样的人生。
徜徉在西部的土地上,行走在西部的山川河流之间,感受着这里的人与自然,我发现,西部的历史与现实凝聚和高扬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魂魄与精神。这里,一方面别有一番辉煌,也格外厚重和雄浑,一代代先人在贫瘠荒蛮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奇观,构建了绚丽的生命风景;一方面又异常沉重,流淌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血与泪。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必须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其中缺少不了中国西部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戏剧人需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这片神奇的天空,这块丰厚的土地。
三、另一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走近西部,研究丝绸之路和西部历史时,常常有一个形象跃入我的视野——那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近些年,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专家都指出,古中国不仅有汉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明郑和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古商贸之路,那就是茶马古道。有的专家称之为“第三条丝绸之路”。称茶马古道为“第三条丝绸之路”,当然是形象的说法。茶马古道上贩运的是茶叶和马匹等;但这条古道同样重要,同样充满了各样的传奇故事。
茶马古道,源于中国古代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学界通常认为有两条,一条是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等地;再一条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德钦,到西藏拉萨,再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也有一些学者将茶马古道分为滇藏、川藏、青藏、陕康藏等多条线路。这是中国西部各民族、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之间另一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世界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古道之一。它以马帮为主,主要运输方式是马队,形成了独特的马帮文化。抗战中后期,这条古道成为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国际商业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云南,苍山洱海让我感动,异域风情令我沉醉,茶马古道则是我最感兴趣、最为关注的。我先后参观了几家博物馆,最让我流连忘返的便是关于茶马古道的部分。有意思的是,在云南的日子里,我发现好些地方竟然都与茶马古道有关。参观著名的大理严家大院,想不到大院的主人竟是靠贩茶起家,一点点积累起家产,盖起了名震四方的严家老宅。富甲一方的严家一边开商铺兴实业办教育,一边还在做着茶马古道上的商贸生意。参观另一处民宅——大理东莲花村的马家大院,又与茶马古道相遇。马家是当地有名的回族人家,整个家族竟也是靠马帮行走于茶马古道起家,慢慢发展壮大起来的。马家大院里还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马具、马灯,马帮出行时的旗帜、服装等实物——详尽地介绍着马帮的人员构成、内部分工,各样的帮规、各样的禁忌以及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示着鲜为人知的马帮文化。这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神秘人群。他们虽是民间商队,却有着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不如此则难以在漫长的旅途中应对各样意想不到的险境、绝境。这是一群用生命行走的人,他们沿着崎岖的古道一走就是许多天,面对的是多变的天气、艰险的地段、各样的野兽、各样的疾病,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劫路悍匪、全副武装守卡子守关口的官兵。赶马人风餐露宿,行进在丛林中、山谷里,很多人倒在了路上,活下来的人继续前行,到达目的地完成了交易,驮上新的货物踏上归途……如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不完的长路,走不尽的马队,在哪里歇息哪里就是他们安顿疲惫身心的临时家园,一瓢水、一眼泉、一块馕都成了琼浆美味。茶马古道正是由这样一些人,一代接一代,用他们疲惫的脚步一步步走出来的。如果说从长安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张骞、霍去病、汉武帝这些历史名人耸立其中、名载史册,那么茶马古道则是由许许多多普通人开拓出来的,他们名不见经传,却书写了这条古道上的历史与文化。
茶马古道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但那些山还在,那些古道还在。我在向导的引领下走了一段茶马古道,山深林密,道路险峻,时不时要手脚并用攀爬而行,还要防备蛇虫袭扰……只走了一段路便让我气喘吁吁,当年的赶马人在这条古道上该是怎样地艰辛、不易?
我看到了很多张已经褪色的老照片,照片中的马帮汉子朴实强壮,脸上烙刻着岁月的印痕,眼中别有一种坚忍和勇悍。那是只有走过漫漫长路的人独有的神色。我也听到了当地人绘声绘色的讲述,他们给我讲着先人们的各种传奇往事——如何对付土匪,如何对付官兵,如何和异域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处朋友,如何在生死极境中兄弟般相互照应帮助,回到家中如何与亲人重逢团聚……这些生动的故事,听得我十分入迷。
这是一片多么值得艺术家去表现,去开掘的生活啊!
多少年来,我们的戏剧舞台还很少看到茶马古道上“马帮”的生活,很少有人讲述“马帮”的故事。至少我从事戏剧这些年始终没有看到过一出这样的戏。茶马古道何时才能成为戏剧的主角?今天的人们何时才能听到舞台上响起遥远动人的马铃声?
茶马古道的另一特色是,沿途多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在云南这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分布在茶马古道经过的路线上。这又是一片可以挖掘的写作宝矿,这条路也是各少数民族心中的神奇之路。马蹄声声,马铃声声,响在沿途各族人民的梦中。长路漫漫,一处处村寨,路边的一户户人家,还有一所所供马帮歇息的小客栈、小驿站,在黑夜中亮着灯火。那里有火、有水、有干粮吃食,也有孩子们的笑脸、女人们动人的歌声、老人悠长的民谣,这一切一切让披星戴月长途跋涉的马帮感到了别样的温暖、感到了生命的动人,重新有了继续走下去的渴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习俗,在这条漫长崎岖的古道上会“生成”出多少如诗如画的场景,积淀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民间故事,奏响过多少充满浪漫与诗意的生命诗章。
我已经写过了《丝路天歌》,写的是黄沙漫漫、风雪满天的古丝绸之路上的行走故事,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写一写茶马古道上的故事。
结 语
我一直坚信,中国戏剧虽然还有很多问题很多缺欠,还处于重重困境之中,但是我们仍然拥有各种各样的潜在资源,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拥有着大量“唯我独有”的创作资源,很多绝好的素材深埋于我们的历史生活中,深藏于我们的民间生活中——那是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所没法拥有的,只属于中国的艺术家。比如丝绸之路上的生死情仇,比如茶马古道的生命传奇,比如西部世界的林林总总,纵然我们这一代不去开掘不去发现,后人也终会发现。而我们有责任做这件事,书写这些历史与现实中的人和事,展现人和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开显出人性的光芒,让人们领略到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生命之真生命之美。
必须承认,我们这代人远没有做好这件事。我们的戏剧远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源。
我经常不断地追问自己:生活本身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开阔,它就活生生地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的戏剧创作之路却是那么狭窄、那么功利?我们常常为“我应该写什么”而纠结苦恼,我们原本置身于“宝藏”和“富矿”之中啊!为什么常常视而不见、漠不无心、全无所动,只习惯于写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抑或,有些创作者写到了这些题材,也下了功夫,却没有写出令人难忘的优秀作品,反而严重缺少含金量,这又是为什么?
我也这样追问自己:“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开发西部,振兴西部”的发展战略,是国家的国策,是国家发展框架之一部分。我们的文化和艺术应该怎样借此机会发现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思考我们当下艺术的发展?怎样打开我们的艺术视野,激活我们的创作思维,开辟和创造出全新的艺术世界?我们又该怎样从丰富的民族民间生活中,从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寻到宝藏,发现金矿,并以强有力的艺术开掘力、锻造力淬炼出“真金白银”,“祭出”我们这一代无愧于自己的戏剧来?
戏剧艺术,从来都离不开生活的滋养,从来都离不开艺术家脚下土地的给予。中国戏剧存在许多问题,有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戏剧的小圈子小格局之中,那样我们会自闭在“笼子”里益发苦恼,益发感到无奈无助,益发感到很多问题近乎“无解”。也许,应该让我们的思想闯进大千世界中去,走到生活深处去,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戏剧圈子给予不了我们的新所在新天地——打开心灵的窗子,让窗子外边蓬勃的生命涌进戏剧中来,鼓荡和洗涤有些疲软、有些苍白、有些贫血的戏剧,戏剧才会有新的生气和活力。
还有,戏剧从来都是戏剧人用心灵去建构的。假如我们的心灵出了问题,锈死了,干涸了,我们就会不断走入困境,不断被困扰被扭曲——被困扰被扭曲的心灵是写不出好作品的。也许,我们要做的许多事情之中有一件事更为重要,那就是用心灵接通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接通天与地、山川与河流,接通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让戏剧创作与生活真正“链接”起来,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唤起,重新燃烧,那样,我们或许会写出很多更好的作品。
面对西部,面对那片土地,那片天空,那些路,我时常有一种被燃烧被灼伤的感觉。
我去的地方还太少,了解的东西还不够多。而西部,那是一本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奇书,我才刚刚开始读它。我希望继续走进去、读下去,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写出一些关于西部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