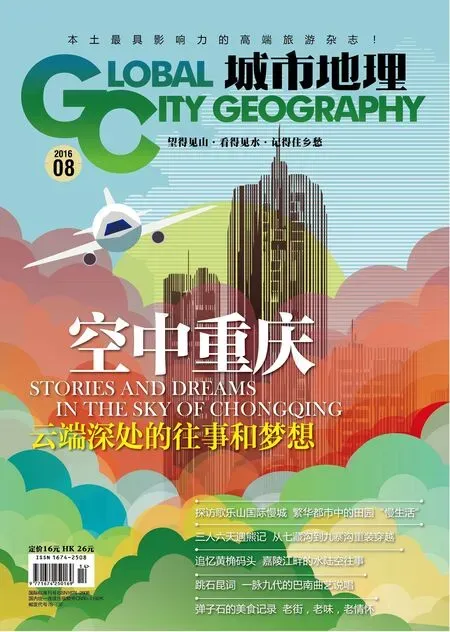十字路口
文+
星球转动
傍晚开车去车站接他,
仪表台上电子狗的语音提示,
似乎比往常更像
一个知书达礼的女人。
三月里他来看我说起一件心事,
猜不透他,是忧是喜,
只觉得比上次见面胖了一些。
不知他会不会后悔,
说了那件事,
是否担心我做不到守口如瓶。
这些天我的每一分钟,
都花在看不见的客人身上,
有时,叫不出名字的鸟飞过,
带来无中生有的漩涡,
一下子就浪费了半个小时。
这次我要带他,
登上灯火辉煌的城市最高的大楼,
看看夜晚的全部,看看我们
来早了还是来迟了。
感受星球转动时自身的光辉。
希望他曾经和我一样,
并且理解时光消逝,
任何一次失败,
都有不可逾越的高度。
小市巷
下午我独自逛到小市巷,
买了烧饼夹臭豆腐。
甜品店里小姑娘低头玩手机,
柜台上蓝牙音箱播放歌曲。
很久没来这条街,
臭豆腐的香味唤醒了记忆。
那次我与北京来的朋友深夜经过,
送他去酒店,夜雾笼罩的街道,
路灯在光晕中飘浮。
观凤商场建成前,
街角上曾经是新华书店,
我买过一本叶赛宁抒情诗选,
可是我并不喜欢他的忧郁。
当年有一位朋友住在小市巷,
我和他吃过晚饭,
喝茶聊天,翻阅他的书,
柜子上摆着一幅油画,
是他画的初恋女友。
在一个雷雨天我来找他,
进入楼梯口,
旁边的平房传来录音机播放的歌曲,
是哪首歌忘记了,
我转身看见一位姑娘靠在门边发呆,
她卷起裤脚,
好像刚从外面回来。
后来我与做建筑的朋友来过几次,
在巷子另一头的小饭店吃饭,
他们说老板娘
又漂亮又会卖弄风骚。
而今,老房子全部拆掉了,
从前的朋友也难得见面。
一个时代过去,
新的一代将来如何回忆现在,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星巴克门口
吃过中饭,看时间还早,
我们到星巴克,买了咖啡,
坐在遮阳伞底下,
旁边,一群年轻人在拍照,
举着反光板。
我指指对面几幢高层公寓说,
五年前,一个女人
从窗口纵身跃出。
你问哪一幢?我不知道,
不过她曾经是我上司,
大致了解她的经历。
我们经历的越多,知道的
可能反而越少,
因为世界并非是我们看见的
这个样子。
那些年轻人又说又笑,
一个女孩戴着帽子,
斜靠在藤椅里,
拍完照片之后走了,
只剩下我们坐着。
十字路口
好久没有来到十字路口的感觉了,
而今天我身临其境。
迎面一块招牌—超音速网吧,
右侧的建筑公司办公楼依然如故。
我仿佛看见十年前的我,
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
记得那是一首爱尔兰民谣,
已经想不起名字。
街头行人熙熙攘攘,
直到今天,
才知道一个人害怕独处的原因。
我的朋友,那年我
将这首民谣拷到你的电脑中,
你的房间就弥漫着歌声,
后来还有几次我听过这首歌,
但那样的日子不知不觉反复出现,
那时的我不复存在。
我曾经竭尽全力,
用付出和给予改变了命运。
金羊毛
超市里的羊绒衣货架旁边,
一幅广告画,夕阳下的羊群,
涂上了一层金色。
我第一次发现,
金羊毛不是遥远的传说。
在冬天的傍晚,所有的
希望从眼前的近景中涌出,
一种永生的期待围绕我。
我也一样,曾经寻找金羊毛,
有过向前的勇气,
在不眠之夜来到梦中的海岸,
有过与生俱来的不朽和礼物。
可是现在我并不相信奇迹,
心中有的,已经有了。
最初那个世界现在无法还原,
而最初那些人喊出的最初的声音,
我仍旧听得见。
也算旧地重游
掏出连锁酒店会员卡,
我拨通预订热线,
为我们一行六人订房间。
接线员报出的就近地址,
激活了记忆。
多年前几次来上海,
住过这家酒店,
我熟悉周围的环境。
酒店的停车场很狭窄,
如果来得晚,
只能停在对面的小路边,
一个晚上二十块钱。
这条路往北左转,
就是南北高架,
路口有一个地铁站,
星巴克,肯德基,
从酒店往南,
也有一家星巴克,
再过去,有川菜馆,
和几家小酒店。
黄昏的街头,路灯下,
来了许多影子,
提醒我这几年发生过一连串的事,
我尽量不去多想,
用力压缩时间的长度。
我不喜欢旧地重游的感觉,
但清晰地记得,
曾经在这家陕西酒店里,
点过一份白煮羊肉,
蘸上调料后,
仍旧难以上口。
背景声音
拿着手机打电话,我时常
为那边的背景声音分神,
风声,关门声,
犹如闭上眼睛看电影。
一次与朋友刚说了三句话,
隐约听得啪嗒一响,
像打火机点烟,
害得我在房间里到处找香烟。
另一次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诗人悲惨死去的消息,
听上去他似乎在抽泣,
后来我觉得也可能是吸鼻涕。
我至今不敢肯定,
这些背景声音是真是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