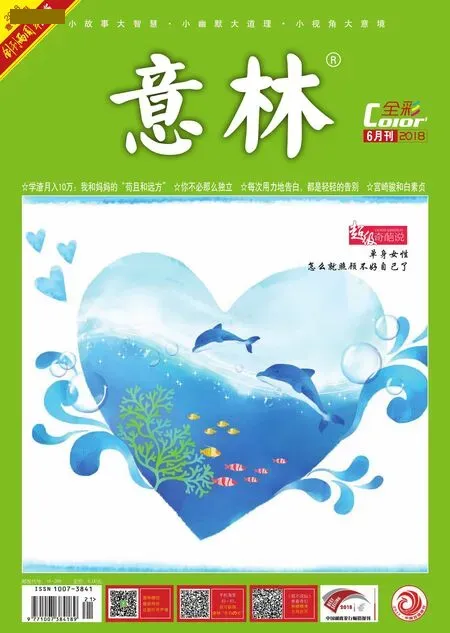一直以为是我在保护你,直到自己被你治愈了
□张佳玮

去年初冬,我去郊区某农场练骑马。
农场颇大,容得下几匹马散步放养,争风吃醋;容得下四只鸭子并排走路,看见人就饶有兴致地围观;也容得下一窝野猫。
众所周知,猫妈妈养了一段时间孩子,便会母性消退,驱赶孩子。它的三个孩子,老大老二都膀阔腰圆、威风凛凛,最小的那只小母猫相形之下则柔弱娇嫩。农场主隔三岔五来,给猫们喂一盆猫粮;猫妈妈与老大老二埋脸入盆,吃得吱吱有声。小母猫在外围转着,嘤嘤柔柔地叫一声。大哥二哥回头朝它“唬”一下,它就回头跑几步,呆呆看着。
但它对人类有奇怪的好奇心。我在骑马时,它穿过栅栏,过来看着我们。我朝它伸手,它呆呆地看着,小心翼翼地用脸蹭了蹭。我要走时,它在大柳树下看着我,又柔柔地叫了一声。
入冬了,天气寒冷。我出去跑步,已觉朔风如刀。看公园里鸭子们都哆哆嗦嗦,不知怎么,我想起那只小猫来。
但我知道养猫有多麻烦,不太想真养……但是入冬了,那只小猫怎么办呢?
我带了一个专业的猫包,坐上小火车去了郊区农场。远远看见大柳树了,听得一声叫,再看,小母猫已经朝我跑来了。
我抱起它,先喂了点猫粮,摸摸它的脑袋。我拉开猫包拉链,它自己钻了进去,还挺享受似的趴平在绒毯上。
我拉上拉链,朝车站走。它大概觉出不对,开始哀声叫唤,挠包,我也不管。
上了小火车,我料它逃不走了,这才拉开拉链,它伸出个脑袋,呆呆看我。我也不会猫语,只好柔声对它说:“乖,带你去一个暖和的地方。”
从此直到我进家门,它在猫包里一声都没吭。
它以后要有个名字了,嗯,就叫Shiva吧。
Shiva到家的第一天,看见猫粮盆如不要命。大口吞咽,须臾不停,让我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里,那个饿过之后胡吃海塞,还在被褥枕头下面藏面包的人物。平时它胆子很小,家里有人来回走,它就缩到床下,唯恐拦了我们的路。
到家第二天早上,它喵喵叫着把我引到洗手间,让我看昨晚备好的猫砂——它已经排过便,又仔细扒拉过猫砂了,仿佛在怯生生跟我说:“你看,我这么操作对吗?”
我给它喂了一嘴鱼干,它高兴地舔了舔我的手。
经过了头半个月的报复性暴饮暴食,Shiva变得放松了。
大概发现了猫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发现了主人对它的好并不是片段给予的,它变得温和了。我在灶台做饭时,它呆呆地在旁打量,疑惑地闻闻食材——Shiva从不偷吃,它只是总带着种“不可以瞒着我偷吃好吃的哟,我要看着的”的神气。
若和我同去逛街,买了玩具,买了猫窝,买了自动喂食器,买了自动饮水机。
玩具,Shiva玩得很开心:它喜欢练习狩猎技能——虽然这辈子未必用得上了——但依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跑,时不时朝我们叫一声,俨然“你看看,我可能耐了”!自动喂食器每天定点一响,它就下楼去吃。饮水机,它瞧着新鲜,会像文人墨客看小桥流水似的,长时间看着流动的水,小心翼翼地舔一舔,再舔一舔。
这个冬天,我经历了几年来最深的一次季节性情绪失调——原先就有这毛病,只是这次在1月下旬加深了。我自己一向的对抗方法,是提升光线,提升体表温度,是喝水,是好好睡觉,是自己做饭摄入大量蛋白质与水果,是收拾屋子,是运动。
但在这年冬天,这些招都不太有用。尤其是,Shiva总是在凌晨五点半就挠我起床,让我缺觉。而缺觉对抑郁是加深的。
但我回头想了想,既然Shiva可以接受从农场到家居的环境变化,我大概也……可以?
我开始每晚提前到十点甚至九点半睡觉,次日五点半起床。天还没亮,喝一碗粗绿茶,开始写东西。期间,Shiva有时跳在我膝盖上睡回笼觉,有时嘤嘤叫着要吃鱼干。我经常在早上八点半就完成了当天需要的大多数写作内容,然后可以安心地继续给它营造生活环境。——“不要抓!给你把玩具装好呢!”“不要舔!!这不是吃的!!!”
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是儿童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消极的社会性行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体侵犯,即利用身体的一些部位攻击他人;二是言语攻击,指通过语言取笑、讽刺、诽谤、谩骂他人;三是关系侮辱,是指通过恶意造谣和社会拒斥等方式使他人在同伴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儿童攻击性行为往往造成人际间的矛盾、冲突,阻碍儿童的个性和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儿童集体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甚至于影响以后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安宁。
二月到三月,我翻译完了一本120页的法语画册,写完了一本书——都会在夏天出版。
除此之外,我学了点西班牙语,掉了五公斤体重。而Shiva到了三月中旬,也终于可以放弃一点依赖了——它乐意躲到钢琴凳下的猫窝去躺一会儿,不再一味跟屁虫似的跟着人转。
3月下旬,我回上海见朋友。说起Shiva,眉飞色舞。
说到怎么给它构筑生活环境,说到怎么让它从农场的寒冷环境里的野猫变成一只温柔的猫。朋友提醒我:
“你好像也变了。”
“是吗?”
“嗯,真的变了。”
我想想,似乎,是的。
世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改变从来是相互的,而世界如此纷繁不同,所以才值得我们去慢慢建设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