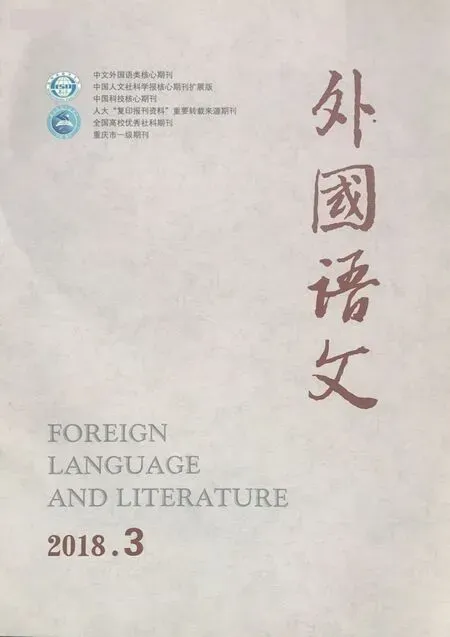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
潘琳琳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48)
0 引言
翻译学与符号学是两门各自独立、又具有一定同质化倾向的学科,二者均为研究交际和意义的科学,均涉及符号的使用、阐释与操纵。符号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翻译实践研究对符号学又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国内对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多数研究囿于以符号学术语诠释翻译现象,而且目光仅聚焦于语际翻译范畴,忽略了广义翻译范畴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双向转换。在此背景下,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探究广义翻译范畴下的符码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就显得必要且迫切。于是,符号学之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应运而生。翻译符号学主要以符号三元观为骨架,以符号转换与流动为实质,突破了语言符号的静态研究,将翻译置于动态的、开放的、递归的符号阐释过程之中,有效地将翻译的过程与行为融入符号学研究的版图。本文以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概念和理论内涵为基础,尝试建构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的一般性模式,重点探讨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和分析工具。
1 翻译学与符号学联姻的理据
翻译学与符号学之所以能够联姻,是因为二者存在天然的逻辑关联,翻译符号学的建构代表着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的诞生,是符号学与翻译学内在发展的必然诉求。二者联姻的理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翻译学与符号学都是学科汇合与学派融合的产物,都具有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性质,都属于开放的、综合性的学科,这为二者的联姻提供了前提条件。翻译研究一向依赖于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翻译行为、分析翻译活动和评价翻译产品,符号学则被称为“文科的数学”,其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已成为众多人文科学学科的重要分析工具。巴斯内特(1991:13)指出:“尽管语言活动是翻译活动的核心,但将翻译纳入符号学研究最为合适,因为符号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符号系统或结构,符号过程和符号功能。”翻译研究必然涉及承载信息的符号之间的转换,因此,符号学对翻译研究有指导意义,符合翻译实践发展的需要。
第二,翻译学与符号学均涉及符号的使用、阐释与操纵,存在互动、互融的基础。若从雅各布森的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三分法算起,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融合研究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其间格雷率先较为系统地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阐释了翻译现象,拓宽了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维度,而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了这一领域,如特洛普、佩特里莉、斯达克尼、罗宾逊等。符号学与翻译学一直处于相互影响之中,“一方面翻译理论不能忽视符号学,另一方面符号学理论也从翻译理论和实践中获得益处”(Petrilli,2007:311)。
第三,多介质、多符号和多模态文本的出现,凸显了基于语言符号的翻译理论的局限,语言学本身已经不能解释所有的翻译现象,多模态文本的生产和发展需要调动更大范围的符号资源和模式,翻译应该被放置到更广阔的符号学视阈下加以研究。在新时代高科技与信息化的语境中,一个文本很难是单一符号的,文本中多种符号系统的共存和协同就变得必不可少,而在此过程中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之间,抑或是非语言符号之间所产生的意义就需要被翻译。“符号学方法的优势是可以运用恰当的概念工具来操纵不同的‘世界’,因为它允许译者整合来自不同符号系统的符号。”(Guidère,2008:58)符号学可使我们重视文本的多媒介性,促使翻译的定义与观念发生质的改变。传统意义上,文本被理解为主要且仅由文字符号构成,而符号学证明了“文本是符号的集合”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指出文本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有组织的集合,包括语言的、听觉的、视觉的、思维的,等等,而这些符号的意义需由译者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和媒介加以梳理和分析。
第四,符号学理论为解释与分析翻译的核心事件提供了可操作的逻辑框架。皮尔斯将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关联起来,以符号学三元观来审视意义的产生、阐释与转换,可将意义解构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可以对应三元关系中的一点,这无疑为理解文本的本质,以及深入考察文本中生成和转换意义的认知过程提供了契机。在这一框架下,翻译过程中符号指称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因为符号与对象之间不再是一对一的固定逻辑关系,而是由解释项参与并调节的一对多的多重阐释关系。
第五,符号学为解决翻译中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等值问题、翻译的损失问题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皮尔斯符号生长理论认为,符号阐释过程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翻译过程是源源不断受符号解释项“驱使”的过程,从而意义得以产生、阐释、转换和生长。符号转换中绝对意义的等值是难以实现的,如果符号和对象达至等值,那么符号活动就宣告停止,符号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另外,通过研究和阐释原文本,译者需要决定目的文本应从哪个角度阐释原文本。很显然,一旦译者做出了选择,其他可能的诠释角度就被暂时排除在外,但不能由此得出“那条未被选择的路”就是一种翻译损失。目的文本没有反映或展示出原文本的某个部分,不能称之为一种损失,而是译者永远无法获得的东西。有关翻译损失的论述实质上与翻译的符号本质相悖,原文本具有无限被解读和被阐释的空间,理论上翻译是永无止境的符号链中的一环。
翻译学与符号学的结合不仅是可行的,同时也是理想的选择。翻译学与符号学的跨接,将我们引向文本和话语的领域,开阔了我们对文本的组成部分、文本的意义和文本的翻译策略的认识,这样,翻译就冲破了语言符号的疆界,上升到意义科学的高度。
2 翻译符号学学科概念的衍化
图里(1980:12)使用semio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术语来指称作为一种符号活动的翻译(Toury,1980:12)。1986年他为《符号学百科辞典》撰写“翻译”词条,论述了翻译的符号学性质,并将翻译的符号学方法定义为“一种跨越系统边界的行为(或过程)”(Toury,1986:1112)。
1990年格雷在意大利安达卢西亚符号学会国际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翻译即叛逆:论翻译符号学》,提出“翻译符号学”这一术语,后改称为“符号学翻译”(贾洪伟,2016a:95)。1994年她提出了符号翻译这一术语的定义:“符号翻译是一个单向、未来趋向的累积性不可逆过程,即连续地朝向更高级别的理性化、复杂化、连贯性、清晰度和确定性迈进的过程,同时不断地和谐了混乱、无组织的问题译文,中和了可疑、误导的错误翻译。”(Gorlée,1994:231)罗宾逊(2016)以批判性的视角,分析并评价了格雷的符号翻译定义,重构了符号翻译理论框架及研究范式,指出符号翻译是一种集体式的情感—意动—认知或本能—经验—习惯的指号过程,集体的规范操控着译者思维中的解释项,使之规范化,理想化。
自1994年起,特洛普一直致力于推进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发展,在其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反复使用了semiotics of translation和translation semiotics来指涉翻译符号学。2008年他发表专文,论证翻译符号学正走向一门独立的学科(Torop,2008)。2010年,他又重新定义了翻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将翻译符号学归类为文化符号学的分支学科(Torop,2010)。
1998年《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一版(Baker,1998)收录了 “semiotic approaches”词条(Eco & Nergaard,1998:218-222),第二版(Baker & Saldanha,2009)则收录了“semiotics”词条(Stecconi,2009:260-263),尽管两个版本的学者们使用了不同的视角来阐释翻译与符号学的关系,但都将semiotics of translation或者translation semiotics作为一种研究翻译的理论方法。
综上所述,国际学界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入手,探讨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关联性,将翻译符号学定义为一种活动或行为(Toury,1980;1986),一种方法(Gorlée,1994;Eco & Nergaard,1998;Stecconi,2009),或者一门新的学科(Torop,2008)。客观地讲,翻译符号学这一术语早已有之,但尚未建立统一的术语体系,关于翻译符号学的定义也尚未达成共识。这是由于学界没有找到翻译符号学的学科落脚点,没能将其建立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因此很难将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充分地应用于翻译现象中符号因素的系统化分析和翻译过程中符号转换的深度解读。只有承认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权利,该领域的学者们才能摆脱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朝着共同的目标形成合力,而不再似散兵游勇般无法系统地论述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属性和本质特征,研究的深度、广度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正因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近30年的历史积淀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于近两三年提出将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探讨,王铭玉(2015;2016)、贾洪伟(2016a;2016b)等从一门独立学科的角度界定了翻译符号学,指出翻译符号学是以符号学基本原理为依据,以符号学方法论为指导,专门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码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符号学的分支学科。
从当前符号学和翻译学的联姻程度来看,翻译符号学尚属初创阶段,旨在建构广义翻译中符号转换(有形符号与有形符号之间,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理论体系。翻译符号学以符指无限延展,阐释不断进行为出发点,相对于一般翻译研究而言,在术语指称范围和翻译类型层面都做出了扩展和延伸,探讨的是“大翻译”视野下广义符号之间的转换。这意味着翻译符号学具有跨学科和跨符号域的特征,它的视觉效果是马赛克式的,非远观而不能窥其全景。
3 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
我们从翻译符指过程的发生机制、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及译域划分三方面来阐释翻译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并由此构建适用于研究翻译发生过程中符码转换和文本阐释的翻译符号学模式。
3.1 翻译符指过程的发生机制:从符指过程到翻译符指过程
皮尔斯将符指过程理解为一个三元关系,符号三元互动关系始于皮尔斯之符号—对象—解释项的存在关系划分,以及象似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之符号属性划分,进而衍生出与象似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一一对应的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三个符号范畴。由此可见,符指过程是符号、对象与解释项三者之间的符号指称过程,是符号阐释的过程、意义生成的过程、符号成为符号的过程。其中,解释项在符号与对象之间起调节意义的作用,三者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符号三元关系(艾柯,1990:67)
符号的这三个关联因素互相影响,互为依赖,构成符号“三位一体”的本质属性。在符号阐释过程中三要素不可或缺,其中解释项的存在是符号之所以能成为符号的条件。符号只有处于与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中,符号之间的阐释与转换才能成为可能,那些不能与表达它、阐释它的事物建立联系的符号,就不能称之为符号。
皮尔斯区分了符指过程中的两个对象:即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直接对象是在特定符号使用中直接指称的对象,直接对象是“符号内在之对象”(Peirce, 1907:70〔318〕),是符号最终能指称动态对象的线索。动态对象是符号非直接呈现的对象,亦被称为调节对象或真正对象,动态对象本质上是“符号外部之对象”,属于符号的现实意义,只能通过对时空语境下的直接对象加以“无限的终极研究”(Peirce, 1931—1936:8)才能够获得,因而它是符指过程的终端产品。“要想获知符号的动态对象,就只能去感觉、研究和尝试理解直接对象背后隐藏的信息。”(Gorlée,1994:177)这就意味着:阐释者对特定现象、事件了解得越多,阐释得越充分,越深入,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就越会趋同。
皮尔斯还区分了符指过程中的三重解释项:即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
直接解释项是指在解释者脑中形成的一系列模糊和非分析性的解释项,代表符号的生成能力,是“可能性”猜度,是在一级符号范畴内呈现该符号的解释项。
动态解释项已经超越了可能性的问题,是解释者结合现实,通过实验和分析来检验直接解释项的效度,并得出更为清晰且具有指示性的解释方案,属于真正发生的阐释性事件,是“现实性”确认。动态解释项是二级符号范畴内呈现该符号的解释项。
最终解释项是指解释者在全面考虑符号所有的意义潜势后,得出的对符号抽象的、逻辑的解释,标志着符号阐释活动的暂时终止。最终解释项的本质是生成阐释的规则与习惯,是“肯定性”强调。最终解释项是三级符号范畴内呈现该符号的解释项。因为阐释者可从各种角度与层面切入,反复不断地阐释符号,生发出全新的意义,所以符号的完整意义在理论上永远无法获得。有关符号的两个对象和三个解释项的关系,见表2。
(6)观察和记录深、浅标记的连续读数,当数据处于稳定水平时,将其作为初始读数。之后,开始注水,将水位保持在30~40 cm。为了使每天的用水量都很清楚,该实验配备了精度为0.1 m3的水表,并运用水平仪进行连续观测,通过深浅标点上标尺和基准点读数的变化记录沉降。

表2 一个符号、两个对象、三个解释项
从符号与两个对象、三个解释项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符号意义的生成与生长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递归、循环式的。在符号—对象关系中,符号受到直接对象与动态对象的影响,在符号—对象—解释项的动态、三元关系中,符号的意义受制于识别、确定和操纵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的三种解释项。
上述有关皮尔斯符号“三位一体”和符指过程的论述,为我们描写和阐释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框架。在翻译符号学视阈下,原文本为符号,目的文本为对象,而译者对符号与对象关系的阐释是解释项。对于译者来说,原文本符号是译者无论如何思考都无法改变的对抗式文本,具有直接呈现的意义和非直接呈现的意义,分别指向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当原文本的信息被译者接收、理解和阐释后,译者了解了符号信息真正意指(即动态对象),创生出的目的文本就从原文本的直接对象逐渐变成了原文本的动态对象,指称原文本符号真正的意义。
待到译者以源语语言为工具获取原文本,以符号文本层面的指称关系、意义建构和文本组织形式为参考,以目的符号形式建构一个全新的符号文本时,译者首先在其思维中形成直接解释项,这是译者对原文本的第一反应,是译者瞬时或尝试性的想法,属于对原文本初步的、直觉式的解读。接下来,译者需要结合现实因素,将“可能性”猜度转化为“现实性”确认直至“肯定性”强调,也就是将直接解释项衍变为动态解释项,并转化成最终解释项,呈现于目的文本之中,目的文本就成为可以充分展现原文本符号意义潜势的所指对象。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翻译过程是递归、循环式的,译者首先解构原文本,使之退化为最真实、最本质的面目,并分辨出原文本之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然后,译者需不断地审视思维中的解释项能否合理地、充分地阐释原文本的意义潜势以及目的文本应该从哪些方面呈现原文本,如何从原文本的直接对象衍化为动态对象。这一行为产生崭新的、可充分展示原文本意义潜势的解释项,然后再不断地回指原文本,产生新的解释项,这也是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最终解释项动态衍化的过程。翻译的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不会结束,在实践中符号表意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因为解释活动随时可以重新开始,最终的解释方案永远不可能达成,而任何解释项都只适用于特定的语境。换言之,原文本(符号)与目的文本(对象)之间的关系,须由翻译符指过程加以协调,使得一者得以成为另一者的逻辑推理结果。有关翻译符指过程,见表3。

表3 翻译符指过程
3.2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
皮尔斯从哲学的角度确立了三分式逻辑推理模式,即溯因(abduction)、归纳(induction)、演绎(deduction), 三者分别对应一级符号、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
溯因是象似性推理,即从未被解释、毫无头绪的数据中,做出推测性解释,并提出假设。皮尔斯认为在三类推理模式中,唯有溯因“将新思想引进学术探索之中”。尽管在溯因中,供阐释者推测的数据是无组织的、不系统的、不清晰的,形成的假设也只是阐释者自认为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一推理模式却为论证的程序融入了原创性的元素。归纳是指示性推理,因为在前提与结论之间建立了显性的因果关系。阐释者通过这一推理模式在现实的情境中验证溯因所得出的假说正确与否。皮尔斯认为归纳是“一项实验性研究”。演绎是象征性推理,是在溯因、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抽象的、清晰的、复杂的理论。这一推理模式是“唯一的强制性推理”,终极目标是产生某一公认的法定性惯例或通则。
在皮尔斯的理论框架内,溯因—归纳—演绎三元推理模式可普遍地应用于所有符号过程,翻译过程也不例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面对原文本中无法理解的词语、词组、句子、篇章时,首先通过一级符号的溯因推测符号文本的指称意义,得出一种直觉式的假设。在这一阶段,译者面对棘手的翻译任务会感到困惑,但仍然凭借象似性的推理,在尝试与摸索的过程中,去理解并阐释原文本的意义潜势。
随着译者翻译进程的推进,译者开始在不同的语境中,结合符号本体外部的语用文化信息,使用二级符号的归纳,来检验溯因提出的有关翻译问题的尝试性解决方案。译者接触的有关原文本、源语符号系统、目的文本、目的语符号系统等之间的对应与合成关系的信息越多,归纳也就越顺利。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足够多的模式时,就会变得有信心去做出翻译经验的总结或普遍性的概括,三级符号的演绎就开始了。比如,在原文本中的符号组织形式X通常会转换成目的文本中的符号组织形式Y。这样,演绎的结果就是形成翻译方法及理论。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逻辑推理是从溯因中得出针对翻译问题初步的、可能性的解决方案,随着译者翻译经验的积累,相似问题会再次出现,然后逐步落入某种模式中,这就是归纳。当译者开始注意并表达这些模式、规则、原理时,演绎推理就开始了,最终就形成了翻译的理论化。
与译者溯因—归纳—演绎的推演模式密不可分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本能—经验—习惯的认知过程。本能是一级符号,依赖瞬时的直觉或感觉;经验是二级符号,建基于现实世界;习惯是三级符号,通过整合本能和经验而形成。译者在溯因时,借助本能来形成对原文本最初的、模糊的、无导向的印象,即思维中的直接解释项;接下来译者借助经验来展开归纳,使得本能的准备能够获得现实世界中经验的引导,即形成思维中的动态解释项,但由于经验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阶段译者仍然没有形成行为的倾向;最后,译者在演绎中,译者的本能被经验所丰富才能形成习惯,也就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做特定事情的习惯。比如,以特定方式翻译特定文本,即形成思维中的最终解释项。所以翻译过程中译者溯因—归纳—演绎的推演过程,也是译者从本能出发,通过经验,形成习惯的认知过程,对于皮尔斯而言,当习惯或信念停止之时,思考的新起点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经验的专业译者,具有丰富的习惯,看起来似乎在用本能做翻译的抉择。这样,我们所建构的翻译符号学逻辑推理模型就将译者本能—经验—习惯的认知过程、译者溯因—归纳—演绎的推演过程以及译者思维中的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的阐释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参见表4。

表4 翻译符号学的逻辑推理模型
举例来说,译者在进行英汉翻译时,遇到一个生僻词语A,他会出于本能,运用溯因凭直觉假设原文本中词语A的意义,即词语A的直接解释项,但当他通过调研获取不同语境中词语A的各种意义,译者会逐步获得该词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语用含义,这就是译者通过归纳而获得的译者的经验,并形成词语A的动态解释项。当译者积累了大量社会文化语境中该词语转换方式的经验,他逐步通过演绎在思维中形成翻译该词语的某种特定的模式、规律或方式,习惯也就形成了,亦即词语A的最终解释项。习惯形成之后,译者再次遇到词语A的转换时,习惯就会衍变为能力(是本能的一种升华),从而在各种语境中可自如地转换词语A,如此循环往复。翻译符指过程的逻辑推理模型本质是将译者的身心体验纳入到追求逻辑真理的无限递归性指号过程中。
3.3翻译符号学的译域划分
雅各布森受到皮尔斯符号学三元观启发,他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分法,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为符号转换的译域划分和理论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但是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究其本质是对语言符号的三种阐释途径,并未界定符号与翻译的概念,因而产生了“语际与符际翻译界限不清、标准不明的学理问题”(贾洪伟,2016c:13)。
我们参酌洛特曼“符号域”的概念,并结合贾洪伟(2016c)的域内、域际和超域翻译的分类方式,对雅各布森翻译三分法加以再阐释,力图进一步理清“域”的概念所指,更为清晰地区分域内、域际和超域翻译范畴之间的界限,重构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研究的译域范畴。
“符号域”是洛特曼于1984年在《符号域》(On the Semiosphere)一文中首次提出,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概念。符号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同一民族文化的各种符号及文本存在和活动的空间。符号域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即是语言符号,是符号域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以洛特曼符号域中最重要的语言符号为切入点,将“域”重新界定为承载民族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互动与转换的空间。
符号是承载和传递民族文化信息的物质化形式,而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还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相互转换都离不开符号主体大脑神经系统作为内部介质的思维无形符号。这样,我们所界定的“域”的概念所涉及的符号形态不仅包括有形符号,还包括无形符号。不论是有形符号还是无形符号,均是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符号与对象两个底角的关系必定由解释项这一顶角来支配,在翻译符指过程中,原文本和目的文本两个有形文本的互动,离不开译者思维中作为无形符号的解释项。因此本文所重构的域内、域际、超域翻译的每一类译域中都包含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
域内翻译是指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可细分为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以及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转换过程中必然涉及的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思维符号(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
文化不但是符号域赖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更是区分符号文本边界的主要因素,域内和域际翻译的区别在于语言符号活动所依存的民族文化空间。域际翻译是指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可细分为语言(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以及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语言符号(有形符号)转换过程中必然涉及的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思维符号(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
相比域内翻译和域际翻译,超域翻译的本质和内涵要更为丰富且复杂。超域翻译是指同一民族文化范畴或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下符号文本超越语言符号所组成的“域”的边界而进行的转换,涉及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之间,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复合性符号(由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构成的有形符号)之间,非语言符号(有形符号)与复合性符号(由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构成的有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以及上述有形符号之间转换过程中必然涉及的有形符号与思维无形符号之间的双向转换。有关翻译符号学的译域模型,见表5。

表5 翻译符号学的译域模型
4 翻译符号学文本阐释模式的解释力
第一,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可解释各种翻译类型(域内、域际及超域翻译)中不同性质的符号(有形符号、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规律与内部机制。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只要符号从一种类型转换为另一种类型,从一种媒介转向另一种媒介,从一种文化通向另一种文化,就属于广义的翻译行为,只要理解、阐释符号文本,就会涉及无限衍义、递归循环的翻译行为与过程。在符号系统复合化表达的语境中,文本中多种符号系统的协同和共存之现象就变得更为普遍。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将符号学原理充分应用于翻译过程的解读与翻译现象的系统化分析,可以运用恰当的学科方法论来操纵不同的“符号世界”,为阐释域内、域际及超域翻译中的符号转换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它允许符号主体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和媒介梳理、整合、操纵及分析来自不同符号系统的符号。这一模式除了可描写翻译过程中的有形符号转换行为与结果,还可透视符号意指的微观过程,关注从思想勾勒到文本呈现,以及从文本阅读到形成大脑思维文本的无形符号与有形符号之双向转换。
第二,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对于译者这一要素的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认为符号阐释的过程脱离不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翻译过程中的文本阐释是译者在综合考虑符号文本内部的文本组织与意义建构,以及符号文本外部的语用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以目的符号形式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的过程。译者对原文本的阐释是相对自由的意义潜势阐释,这其中涉及符号—对象之间的动态的、开放的阐释关系。我们所建构的翻译文本阐释模式注重解释和预测符号主体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逻辑思维活动,将译者本能—经验—习惯的认知过程、溯因—归纳—演绎的推演过程和译者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动态解释项的阐释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译者的身心体验融入翻译符指过程的文本阐释中,对译者的主体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论观照。
5 结论
本文在论证翻译学与符号学联姻的理据和翻译符号学学科概念的衍化的基础上,从翻译符指过程的发生机制、翻译符号学中的逻辑推理模型和译域划分三方面尝试建构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的一般性模式,为翻译发生过程中不同符号系统表意实践共存、互动甚至对抗提供全面的、动态的、开放的空间,翻译过程中符号的异质性与译者的主体性均可获得足够的关注。这一模式观照下的符号之间、符号文本之间受到持续性的交互变化的影响,翻译过程中的指称意义因此存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无限性。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1991.Translation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Eco, U. & S. Nergaard.1998.SemioticApproaches[G]∥Mona Baker.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18-222.
Gorlée, D.L.1994.SemioticsandtheProblemofTranslation: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SemioticsofCharlesS.Peirce[M].Amsterdam-Atlanta: GA.
Guidère, M. 2008.IntroductionlaTraductologie[M]. Bruxelles: De Boeck.
Lotman, J. 2005. On the Semiosphere.[G]∥ Translated by Wilma Clark.SignSystemsStudies, 33(1): 205-229.
Robinson, D. 2016.SemiotranslatingPeirce[M]. Tartu: Tartu Semiotics Library.
Stecconi, U. 2009. Semiotics [G]∥ Mona Baker &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 London: Routledge:260-263.
Torop, P. 2008. 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J].SignSystemStudies, 36(2): 253-257.
Torop, P. 2010.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J].AppliedSemiotics/SémiotiqueAppliquée(24): 1-21.
Toury, G. 1980.InSearchofaTheoryofTranslation[M].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Toury, G. 1986.Translation:ACultural-SemioticPerspective[M]. Thomas A. Sebeok.EncyclopedicDictionaryofSemiotics, vol. 2. Berlin: Mouton deGruyter:1111-1124.
Peirce, C.S. 1931-1936.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G]∥ Charles Hartshorne, Paul Weiss & Arthur W. Burks (eds.) 8vols.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S. 1907.UnpublishedManuscripts.PeirceEditionProject[M].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at Indianapolis.
Petrilli, S. 2007.Interpretative Trajectories in Translation Semiotics[J].Semiotica, 163(1/4): 311-345.
艾柯. 1990.符号学原理[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贾洪伟. 2016a.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外语教学(1): 94-97.
贾洪伟. 2016b.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J].山东外语教学(3): 90-100.
贾洪伟. 2016c.雅各布森三类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 11-17.
王铭玉. 2015. 翻译符号学刍议[J].中国外语(3): 21-23.
王铭玉. 2016.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 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