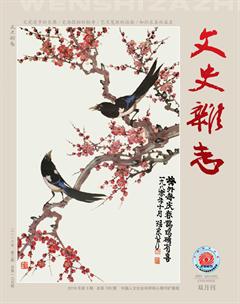绵阳《唐故天水赵氏墓志》再探
李硕
摘 要:《唐故宣德郎守成都府广都县主簿太原王公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于2012年出土。据墓志,赵氏祖上三代皆在四川地区担任地方官,且在政治地位上呈现上升趋势。其家族作为北方天水赵氏的分支,因宦徙居,迁居成都地区。他们的活动,说明中唐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上出现的新形势,成都崛起为西南区域中心城市,故对任官于西南地区的北方士族有重大影响。另外,墓志还包含了唐文宗太和三年南诏侵蜀战争及唐代女子主办父母丧葬现象的部分史实。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关键词:天水赵氏墓志;因宦徙居;成都崛起;祔葬未从;南诏侵蜀
2012年在绵阳市经开区南塔社区中水地产工地上出土一方《唐故宣德郎守成都府广都县主簿太原王公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此墓志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此前已有学者对墓志进行了解读,但主要针对其中包含的唐代官制及四川地区地方行政建置信息。[1]笔者认为本墓志尚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因此拟对该墓志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墓志形制与录文
《唐故宣德郎守成都府广都县主簿太原王公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墓盖边长0.4米,3列3行,篆刻九字:“唐故天水赵氏之墓志”。墓志边长0.6米,24列24行,楷书,525字。此墓志有“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纪年,是绵阳境内首次出土的有唐代纪年的墓志。现据墓志拓本移录并标点如下:
唐故宣德郎守成都府广都县主簿太原王公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
河东薛磻撰/
夫人姓赵氏,天水人也。源本洪遂,族望显清:内行外行,时所称/举。其达仕者详于国史,不达仕者备于私传,余无赞焉。曾祖成,/皇朝散大夫兼监察御史、渝州司马,赐绯鱼袋。/祖重光,皇太中大夫兼监察御史、眉州司马,/赐绯鱼袋。父珦,皇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梓州长史,赐绯鱼袋。/夫人聿遵阴化,自合经礼;才淑旁综,德履柔明。既笄之岁,归于/故宣德郎守成都府广都县主簿太原王公讳岌。靡出阃之言,/动容成纪;噰噰穆穆,克和克鸣。已至公殁,训育孤幼,保乂大家,/劾顺蒸尝,弥载洒扫,哀必昼哭。二门增光,周旋母仪;四氏仰则,/宜登寿域,永延清风,阴骘或欺,沉疾缠迫,奔于道里,以索医方,/天厌令图,竟钟所苦。以大和三年十月十二日终于成都府逆/旅舍,享年六十八。悲夫,神之报施何其寡欤。夫人无子,有二女。/次适邛州火井县令冯翊严公翱,长适前荣州旭川县令陇西/李公寰。公帝王景胄,仁义是持,悲激于衷,食未常饱。长女始自/成都护丧,归于涪上,实李公之深意也。复以卜筮靡吉,祔葬未/从;苟侚固坚,议以封树。即以其年十一月八日权窆于巴西县/东度乡安阳里,盖殡也,从宜也。呜呼,杯圈慕永,泣血茹表,哀随/晓风,声恸飞走。爰讬丰石,以勒铭志。铭曰:
茫茫逝水兮去无归,/百鸟兆吉兮泉启扉,夜舟难守兮露易晞,化穷数尽兮号匪依,/无子可抱兮女主宜,隙光销尽兮婺减辉,既葬皇皇兮恍如疑,/同穴九原兮他年期。封树已终兮辩高卑,桑海变兮铭于斯。
二、墓主世系与生平
关于墓主的出生时间,志文没有明确的记载,志文云:“以大和三年十月十二日终于成都府逆旅舍,享年六十八。”按其卒年向前倒推,赵氏应出生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其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关于“天水赵氏”,《元和姓纂》载其源流云:
帝颛顼伯益,嬴姓之后。益十三代孙造父善御,事周穆王,受封赵城,因以为氏。衰、盾之后分晋,为诸侯,都邯郸。王迁,为秦所灭。子代王嘉,嘉子公辅,主西戎,居陇西郡天水西县。[2]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天水赵氏家族列为四房,分别为天水赵氏(史书记载天水正统赵氏家族)、新安赵氏、南阳赵氏与敦煌赵氏,而《元和姓纂》则分有八房,即天水赵氏、平原赵氏、中山赵氏、新安赵氏、南阳赵氏、陕郡河北赵氏、河东赵氏、长平赵氏。墓志不载其家族聚居地,因此可以大致断定墓主赵氏应当只是以天水作为其郡望。
唐代天水赵氏家族,《元和姓纂》中将其列为“小”,而其家族仕宦情况,《唐代天水赵氏家族研究》根据墓志及其他相关资料统计:“在安史之乱以前赵氏家族有38位任职在五品以上,26位在五品以下,安史之乱以后有22位在五品以上。18位在五品以下,不详时期的赵氏成员有8位任职在五品以上。11位任职在五品以下。另有不详品阶者10人。总共在这134位成员中,有68位在五品以上,这个数字对于接近三百年历史的唐代来说,也就是平均每三年就有一位天水赵氏家族成员活跃在唐代政局中。也说明了天水赵氏在唐代政坛颇具实力。”[3]根据墓志记载赵氏曾祖父赵成担任过渝州(治今重庆市)司马,祖父赵重光担任过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司马,父亲赵珦担任过梓州(治今四川绵阳)长史,其祖孙三人,两唐书皆无传。综合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可知,眉州、梓州为上州,渝州为下州。[4]另据《唐六典》所记各州官吏官品,则其曾祖父为从六品上,祖父为从五品下,父为从五品上,而三人都被赐予过绯鱼袋(唐制规定五品以上佩绯鱼袋,不足五品赐绯鱼袋则表示宠遇),可见其家族在唐代政坛中处于上升趋势。
墓志还记载赵氏“既笄之岁,归于故宣德郎守成都府广都县主簿太原王公讳岌”,即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出嫁王岌。《唐代天水赵氏家族研究》一文认为:“从已有的墓志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作为小姓的天水赵氏在婚姻方面多选择世家大族和当时名臣子女作为对象”[5],绵阳赵氏墓志恰可佐证这一观点。赵氏之夫王岌出身于赫赫有名士族的太原王氏,却只做到一个次畿县的主簿,官品甚低。尽管如此,唐代旧的士族虽衰落,但婚嫁重阀阅的风气并未改变。唐代士族婚姻重阀阅由来已久。太宗时为打击旧的门阀势力就曾编写《氏族志》,推重当朝冠冕,并规定:“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6],但效果并不理想。之后“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7]一直到了唐文宗时期仍是“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8]的情况。因此赵氏家族选择太原王氏作为姻亲对象,符合唐代社会士族婚姻重门第的观念,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天水赵氏作为一个不算太大的士族为提高自己家族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表现。
墓志记载赵氏的丈夫在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去世,赵氏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成人,长女嫁给前荣州(治今四川自贡)旭川县令陇西李寰,次女嫁给邛州(治今四川邛崃)火井县令冯翊严翱。李寰、严翱二人两唐书无传,从墓志得知二人家族出自陇西李氏和冯翊严氏。李寰,墓志中描述他:“公帝王景胄”,查阅《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只有“蒋王房”一脉有李寰之人,蒋王李恽为唐太宗十四子之一。然《宗室世系表》中未载李寰官职,若墓志所记李寰与世系表中为同一人,则墓志中言其曾官“前荣州旭川县令”正可补世系表之阙。此外陇西李氏和冯翊严氏在当时都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士族,与这两个士族成员通婚也符合天水赵氏在婚姻方面多选择世家大族的传统。
三、对墓志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一)四川地区的太原王氏与天水赵氏:因官卜葬和因宦徙居
从墓志中可以了解到赵氏的丈夫王岌是死于成都府广都县主簿任上,之后应当没有归葬北方太原王氏家族墓地,而是在成都地区安葬;因为赵氏仍旧生活在成都,否则不会因病死于成都府的逆旅之中。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因官卜葬”,并指出“唐代十之八九的太原王氏成员,卒葬地都有因官卜葬的特征,这是太原王氏城市化和官僚化的集中反映。与之相反,太原王氏死后的卒葬地位于太原及其周边地区者极为罕见。墓葬地因官卜葬的实质,正是太原王氏丧失六朝时期的自立性和乡里基础,沦为帝国的专职官僚,从而表现出寄生性和依附性。”[9]当时成都地区是否存在王岌太原王氏家族墓地,墓志没有明确反映,但笔者认为存在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墓志记载赵氏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基本都在四川地区担任地方官,又赵氏嫁与生活在成都地区太原王氏家族成员,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家族聚居地当在四川地区。其家族作为天水赵氏房支之一,当是由于国家的强制迁徙即地方官吏的任免,迁居到四川地区的,即“因宦徙居”。士族迁徙是隋唐时期国家重建和中古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毛汉光先生曾依靠墓志资料对唐代士族籍贯迁徙作了卓有成绩的探讨,并提出“唐代士族中央化”的观点,即士族从自己长期经营的州郡乡里转移到当时行政中心的长安、洛阳地区。笔者认为“唐代士族中央化”只是中古时期士族政治生活变迁的一部分,起码是不能完全反映本篇墓志的内容;因此与其说是“唐代士族中央化”,不如说是唐代士族向当时政治中心城市靠拢。唐代长安和洛阳地区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政治中心,故而从其他地区迁徙到长安、洛阳的士族比比皆是。如《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王绍传》载:“王绍,本名纯,避宪宗讳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万年。”王绍即以太原王氏成员徙居京兆万年县。还有李观“其先自赵郡徙洛阳,故为洛阳人”[10],此即赵郡李氏迁居洛阳的案例。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新形势(藩镇林立和经济重心南移),许多新的城市崛起为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既是藩镇节度使的治所,也是这个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因此这些城市往往兼容政治、经济等中心的多重职能,故许多士族在这些地区担任地方官之后会就近选择这些中心城市作为其家族迁居地,而不再只是迁往长安或者洛阳。
成都作为西南首屈一指的重镇,在唐前期往往只在经济上受到重视,如陈子昂在向武则天奏疏中写道:“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11]安史之乱后,玄宗奔蜀,成都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加之中唐以后边防形势的变化,防御吐蕃和南诏的侵扰成为重中之重,因而西川在唐政府的政治版图中愈发重要,进而成为“宰相回翔之地”[12]。如段文昌早年在西川韦皋幕府任职后在穆宗初年入相,不久又以使相身份出任西川节度使;又,晚唐名相李德裕于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出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太和六年(公元832年)被文宗召回朝,不久即拜相,加授同平章事。可以说正是由于成都西南地区政治中心城市的确立,加之其文化经济依旧繁荣,吸引了众多北方人口南迁于此。高适在《西山三城置戍论》中指出:“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於蜀人矣。”[13]此外不少曾在四川担任地方官的北方士族成员也选择在成都地区定居,如南宋晁公溯所撰《宇文蜀州墓志铭》对宇文虚中家族历史的描述:
炎帝有尝草之功,北方谓尝草为俟,并人语转为宇文,子孙以为氏。始著见于拓跋魏,其后建国,为尽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闻者累累有焉。唐太和间,有讳籍者为谏议大夫,佐武元衡节度剑南西川有功,则以文显矣。谏议之子讳从礼,终渠州司马,因家于益州。[14]
宇文虚中为两宋之际名臣,根据墓志记载,其家族为北方老牌士族宇文氏,其先祖曾在唐文宗太和年间在渠州(治今四川达州)担任司马一职,其家族因此定居益州(治今成都),自后繁衍数代一直到北宋末年,仍居住于此。晚唐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就写道:“况赤府畿县,与秦洛并,故非上将贤相,殊勋重德,望实为人所归伏者,则不得居此。”[15]可见成都地区在中唐以后已经成为士族重要的迁居地之一,其政治地位不输于北方的长安和洛阳。
韩昇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迁徙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唐代士族中央化”观点做出了修正,认为:“士族的迁徙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既向中央的集中,也有向地方的转移,总的来说,是从乡村向城市移动。”[16]本文墓志中的天水赵氏和太原王氏两个家族实际上就是唐代士族向城市移动的具体体现。天水赵氏家族祖孙几代都在四川地区任官,可以说天水已经与他们没有太大的联系,天水郡望只是他们标榜门第,提高声望的手段,赵氏家族已经把四川成都地区作为自己新的家族聚居地。但是这些北方士族却并不看重成都本地的乡党宗族,这也是为什么天水赵氏会选择与太原王氏联姻而宗族内的女性也嫁入陇西李氏和馮翊严氏两个北方传统士族的原因。
(二)赵氏没有祔葬的原因
赵氏死于成都府逆旅,而其夫家族墓地当在成都地区,就近祔葬应该很便利,但最终却是“权窆于巴西县东度乡安阳里”,其没有祔葬原因着实耐人寻味,值得思考。刘先维《墓志资料所见唐代归葬习俗研究》一文曾对唐代妇女死后未祔葬的原因作了归纳,具体有四点:
1.信仰佛教。
2.在夫家地位没有得到肯定或觉得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完成应尽职责,如没有子嗣。
3.因夫早卒而与夫没有感情或生前与夫感情不佳。
4.一些在家庭地位中“女尊男卑”的特殊妇女,如公主。[17]
首先从墓志内容来看,赵氏并未信仰释教,其在整个家庭中也不具有特殊身份地位,这两点原因排除。墓志里对赵氏生平的描述是:“夫人聿遵阴化,自合经礼;才淑旁综,德履柔明。”“靡出阃之言,动容成纪;噰噰穆穆,克和克鸣。已至公殁,训育孤幼,保乂大家,劾顺蒸尝,弥载洒扫,哀必尽矣。二门增光,周旋母仪;四氏仰则。”排除墓志撰写者对墓主的溢美之词,可以看出赵氏在当时是遵守妇道、“贤妻良母”一类的女性,当不会与夫家有矛盾。因此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子嗣,而墓志也明确写道:“夫人无子,有二女。”我国传统社会的孝道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赵氏嫁与的太原王氏又是大的士族,对这方面规定可能更加苛刻。因此,赵氏不能祔葬其夫的家族墓地,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三)赵氏权窆巴西县的原因探析
从墓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赵氏被安葬在巴西县实属无奈之举,而具体原因墓志并没有涉及到。文中先是说:“长女始自成都护丧,归于涪上,实李公之深意也。”可知灵柩是在其女婿李寰的授意下由她的长女护丧归葬(归葬的目的地可能是其娘家),以尽孝道;但因为某种原因只能就近在绵州(治今四川绵阳)巴西县安葬,以待他日再行迁葬。在古代,归葬的选择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如经济条件、季节、风水、政局等。从墓志中我们没有看到李寰夫妇受经济条件制约的信息,此条暂且不论。文中提到:“复以卜筮靡吉,祔葬未从;苟侚固坚,议以封树,即以其年十一月八日权窆。”可知赵氏之所以没有归葬,是受到风水占卜的影响。在唐代,风水占卜术发展已相当成熟,不仅有较为完整的理论,还有诸多专职从业人员,据《通典》卷一百三十八引《开元礼》,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已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因此占卜如遇到“卜葬靡吉”的情况,就要改时归葬,这样的例子在唐代有很多。
此外笔者认为,这或许也与当时蜀中的政治形势有关。《资治通鉴》太和三年十一月丙申条载:
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18]
由于杜元颖治蜀不善且专务积蓄财富,不体恤士卒,致使南诏在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大举入寇四川地区,并且在唐守边部分军卒的帮助下进展神速,短时间内就攻陷了巂(治今四川西昌)、戎(治今四川宜宾)、邛三州。唐廷在得知南诏大肆侵蜀后,“遣使起荆南、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赴援蜀川。以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仍权东川事。”[19]随后又遣中使宣慰南诏王蒙丰佑并命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西川行营都知兵马使,统帅左右神策军及进援诸道兵马赴蜀中。但南诏军很快从邛州直抵成都城下。史载:“兵及城下,一无备拟,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20]而杜元颖身边只有三千余“徒有其数,实不可用”[21]的新募士卒,在南诏军面前不堪一击。南诏军攻陷成都后:
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22]
可见成都地区遭受到战火惨烈地摧残。之后南诏军统帅嵯颠遣使上表诉说杜元颖治边无方,致使两国兵戎相见。文宗贬杜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神策军及诸道兵马各归本处,又遣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修好,至此太和三年南诏侵蜀战争才基本结束。
据墓志记载赵氏的长女婿李寰曾任荣州旭川县令,荣州就在巂、戎二州之北,也在这次南诏入侵威胁之下。此外,当李寰夫妇在绵州的时候,南诏军实际上已经兵临梓州,史载“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郭。郭钊兵寡弱不能战”[23]。梓州就在绵州之南,两州紧邻,形势可以说是万分紧急了。李寰夫妇可能就是出于对当时蜀中局势不乐观的看法,认为南诏兵很快就会攻到绵州来,如不及时安葬必将受到战火的影响,因此就权窆赵氏灵柩于巴西县,待到他日时局稳定后再行迁葬。文中“盖殡也,从宜也”可以说明这是权宜行事。
四、余论
绵阳天水赵氏墓志描述墓主出身北方大士族天水赵氏云云,其所叙家族历史与当时流行的《元和姓纂》所记天水赵氏并不相符,应不属于当时天水赵氏八房之中,但可能属于天水赵氏的其他较小房支,或者说是从天水赵氏中分离发展出的一支。墓主赵氏祖上三代皆在剑南地区做官,与北方天水赵氏的谱系存在明显的断裂;而攀附望族是中古士族标榜自身门第的惯常手法。因此赵氏家族是否真的出身天水赵氏,仍然需要更多的史料去佐证。
关于赵氏归葬的地点,文中基本没有描述,只是说“归于涪上”,一般唐代墓志中“归于”后面都是具体的地点,如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丹旐素车,归于上京”[24]及《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十有一月,遣车归于洛师”[25]。“涪上”这个名词,在唐代出现得很少,晁公溯在其诗文中有所使用,如:“予己未十月二十有二日去涪上,越明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以事再來,观山川之胜,无异于昔,而予之幽忧抑郁亦自若也。”[26]有学者根据晁公溯为官履历,认为“涪上”即涪陵。[27]涪陵在唐代隶属山南西道的涪州,与成都相距较远。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涪陵在隋开皇年间曾一度为渝州属县,唐武德元年另置涪州以后方才改属;而赵氏曾祖曾在渝州做官,因此其家族墓地或当位于涪州。笔者在此聊备一说。
由于墓主赵氏没有子嗣,因此本文亦是出嫁女主办父母丧葬个案之一,可以看出赵氏的长女在处理母亲丧事中表现出高度责任感;而其女婿李寰在志文中亦得到高度评价,后者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胡娜在《唐代女子主办父母丧葬现象考略》中认为:“在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社会里,对这种因无嗣子而不得不由出嫁女及女婿来操办身后事的现实,唐人心理活动颇为微妙。”[27]但从本篇墓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夫妇二人同心协力,在背景复杂的情况下把母亲安葬,并没有所谓“女婿插手妻家丧事的微妙心理”。可见对唐代女子主办父母丧葬现象的研究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注释:
[1]唐光孝:《绵阳唐天水赵氏墓志初考》,《乾陵文化研究》2017年第11辑。
[2](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52页。
[3][5]刘鹏:《唐代天水赵氏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第38页。
[4]《舊唐书·地理志》载眉州、梓州为上州,《新唐书·地理志》载眉州为上州,梓州、渝州为下州;《元和郡县图志》载眉州、梓州为上州,渝州为下州。
[6][7]《新唐书》卷九十三《高俭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42页,第3842页。
[8]《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杜兼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06页。
[9]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2页。
[10]《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六《李观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03页。
[11]《陈子昂集》卷九《谏雅州讨生羌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9页。
[12]《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唐宪宗元和二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41页。
[13]《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8页。
[14]晁公溯:《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五十三,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45册,第796页上栏。
[15]《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8册,第7703页上栏。
[16]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7]刘先维:《墓志资料所见唐代归葬习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48页。
[18][21][22][23]《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唐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太和四年十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67页,第7873页,第7868页,第7868页。
[19]《旧唐书》卷十七《文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3页。
[20]《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杜元颖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64页。
[24]《柳宗元集》卷十二《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页。
[25]《柳宗元集》卷九《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页。
[26]晁公溯:《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十四,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45册,第640页上栏。
[27]李朝军:《晁公武兄弟在渝事迹考》,《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28]胡娜:《唐代女子主办父母丧葬现象考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