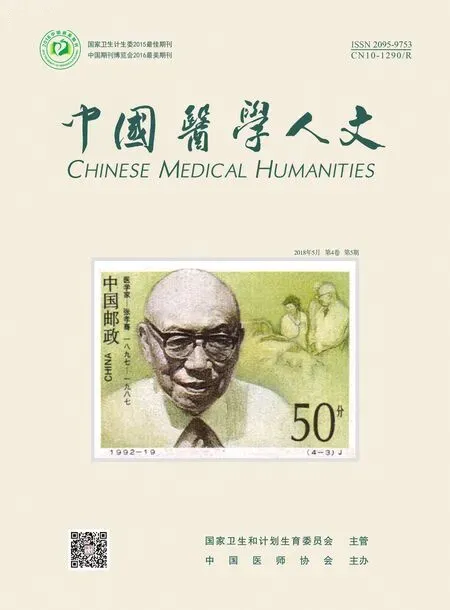ICU里的指南与找北
——在美国做医生的经历
文/乔人立
作者单位/美国南加州大学PCCM专科
在大学医院里做主治医按月排班。那个月我接下加强病房(ICU)乙团队(Team B),率领实习医、住院医、Fellow和医学生共14人管24张床。第一天查房,住院医报告说D先生是我们团队管下的重病号而且是重点病例。D先生被给予的诊断是结节性多动脉炎(Polarteritis nodosa,PAN)。PAN是一种罕见的结缔组织病,表现为三联征,即同时发生发热、皮疹和器官供血不足。PAN的治疗要用大剂量激素,但效果难料。D先生情况严重,心肺肝肾脑多器官功能衰竭。尤其是,D先生尽管用着大剂量激素和多种抗生素,却已经持续高热3周多,每天体温几乎都在40度以上。
D先生56岁,患糖尿病15年,3周前出现足底溃疡感染。足底溃疡是糖尿病后期常见并发症,门诊医生给他开了抗菌素控制感染。3天后,D先生出现高烧皮疹,被收住院。为了鉴别皮疹发烧的原因,内科病房请结缔组织病(CTD)专科会诊。CTD当班主治是R医生。R医生是专科教授,熟读医书,看了D先生的情况立刻就想起书上说发热皮疹的鉴别诊断中包括PAN。为了证明她的设想,R医生为D先生取了皮肤活检。病理报告回来,见到小动脉壁上有白细胞浸润,和PAN的病理变化一致。R医生认为病理检查支持PAN诊断,与她的判断相符,立刻给D先生用上了大剂量激素。R医生显得很激动,把有关PAN资料文献详细地总结,收在病历里,还告诉住院医,她虽然是CTD专科教授,从初发症状起从头建立PAN诊断却还是第一次。
D先生就此成为一名PAN患者,而R医生则就此成为一位会诊断处理PAN的医生。
大剂量激素全面抑制免疫系统,使身体失去对感染的抵抗力,病人原有的感染一般都会加剧。因此,使用大剂量激素治疗指南上指出,应该积极寻找病人身上是否有结核、细菌或其他微生物感染的证据并相应处理之。X光显示D先生右肺尖纤维化,表示他可能得过结核病。而且D先生去过墨西哥,那里医学落后治疗不规范,耐药结核菌常见。考虑到这一情况,R医生根据耐药结核病治疗指南给D先生开了5种抗结核药综合治疗,还加上了维生素B6以防止副作用。D先生的病起自足底溃疡,后来出现高热,虽不能肯定或否定感染播散,为保险起见,还同时用了另外两种广谱抗菌素。
一周后,D先生足底溃疡倒是愈合,皮疹减退,他的病情反而加重,高热不退,意识逐渐丧失,出现器官功能障碍,转入ICU。由于抗生素菌谱中已经覆盖了结核和细菌,D先生又被加上抗病毒的药,并邀请传染科会诊。传染科有处理免疫抑制病人高热的指南,上面说此类病人如果抗菌素治疗超过7天仍然高热,必须考虑并发真菌感染。为此,D先生方案中又加上了抗真菌药。
D先生持续高烧近3周,血压降低。他的治疗方案包括9种抗生素,还有激素、升压剂、退烧药、镇静剂、营养物和液体。为给这些东西,3条静脉通路24小时连轴转。再加上肺动脉插管监测心输出量,桡动脉插管监测血压,气管插管连接人工通气,股静脉插管血透析以代替衰竭的肾脏排除代谢产物。此外,还有心电、血氧、体温连续监护,各种信号要两个荧光屏才放得下。除了ICU病人各种监测和维持生命的管子线路之外,D先生身上还盖着冰毯物理降温,阵势着实唬人。
D先生的病例动员了所有专科,监测着几乎所有现代医学能监测的指标。他的护理要一个护士外加一个助理才忙得过来。因为各科都有住院医例检再继以主治医查房,D先生的病房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几乎要排队。这就是住院医为什么说D先生是重点病例。
可是,D先生病情却在继续恶化。

看完D先生的病历,我觉得R医生倚重病理报告虽然没错,却忘了病理检查来自皮肤活检,取材很小而且不是重要器官,局限性自然很大。况且病理报告中用“和PAN一致”,是一个保留成份很大的措辞,意味着病理科实际上没有把握。D先生发热皮疹出现的时间和他用第一组抗菌素吻合,但从头上就没排除药物反应的可能性。后来皮疹消失而高烧反而加重,更说明现在的发热和皮疹已无关系,因而PAN的三联征已不成立。D先生每天接受的药物近20种,这些高纯度化学物质都得在他体内吸收代谢,完全有可能导致药物热。而且,最重要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药物治疗都已经证明无效。因此,不妨试试停药。
我吩咐住院医和参与D先生治疗的各专科医生取得联系,征求同意。这是职业礼貌,表示对同事的尊重,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讲究之一,尤其是意见有所不一致的情况下更是重要。各科反馈回来,竟无一人同意。但明摆着D先生的情况已经穷极现代医学之所能,已经没药可加,所以也没人反对。病理科负责D先生报告的医生向我证实,如果没有临床证据她并不能肯定PAN的诊断。参与D先生专科会诊中牵涉最多的是CTD科和传染科,于是我亲自联络了这两科的主治。
R医生已经不在班上,接她班的主治对D先生的PAN诊断不是很肯定,但对停药同样不置可否。传染科的当班主治T医生是他们的主任,是个不笑不说话的老头,每次一笑,婴儿般面颊上的粉红色便沿着皱纹一直延伸到光秃秃的脑顶。他听了我的分析,笑眯眯地说,“这是个新想法。可是怎么解释D先生的多系统功能衰竭呢?”
看得出,T医生认为我的想法是医学生的水平。我解释说,D先生的器官功能障碍出现在持续高热一周之后。持续高热使蛋白质结构改变,自然可以影响器官功能,不需要另外寻找原因。
T医生提不出来别的问题,笑笑说,“很有意思。可惜没有什么时候该停药的指南。”
T医生显然已不反对停药,只是在避免出头承担责任。我是ICU主治,是主管医生,我决定按自己的判断行事。首先停掉了抗结核的5种药。一天后,D先生情况未见变化。我们又把所有抗生素和激素全部停掉,D先生的医嘱一下子只剩下营养品和镇静剂。24小时以后,D先生情况仍未见好转,但也未恶化,各项指标保持原状。住院医告诉我,D先生的体温成了天气预报,是大家的眼光每天盯着的目标。我吩咐维持现状,继续观察,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第三天上午一进ICU,我的团队都聚在D先生门前。看我来了,十来个人一起欢呼,Hurray!今天,D先生体温37度,白细胞总数降了一半。我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给D先生停药凭的完全是判断,等于摸着石头过河,谁也没有把握。所幸判断无误,我自然也就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此后两周,D先生情况逐渐好转,各种管子逐一拔掉,意识恢复。由于已无需要,会诊各科纷纷退出,我们准备把D先生转出ICU。
不想这天下午,我的Fellow传呼我,说是R医生来过,有了麻烦。原来R医生做完那个月的主治轮转,已赶着把D先生的病例写成报告,准备投稿。完稿后,R医生回到ICU探视R先生情况,毫无心理准备地发现有人搞了“政变”,不免义愤填膺。
我赶去ICU,R医生已离去,在病历上写下这样的话,“D先生是ICU病人,你当然有权力按你的判断处理。可你既然请人会诊,就应该尊重别人的意见。D先生的PAN诊断有临床和病理依据,停掉激素是用病人生命在冒险。”
看了这话,我不免目瞪口呆。且不论医术医德人品风格,这美国虽然号称谁想说什么都行,两种情况下是最好不要张嘴的:一是面对找你麻烦的警察,二是在成功的事实面前。(Never argue with policeman.Never argue with success)
D先生的病情好转,R医生本来最应该庆幸她的武断没出了人命,她却还在坚决捍卫她那显然已站不住脚的诊断,而且把这有争议和威胁性的话写在了病历里。病历是法律记录,不能更改,R医生等于是在挑起不良医疗诉讼,而且在授人以柄。话说到这种份上,我也没法去找R医生解释,当时停药不是没有和CTE科事先交流过。本来在教学医院做医生,讲的是团队精神,大家一起负责。D先生病例牵扯的大小医生有几十个,R医生却如此顾忌自己的面子,实际是愚蠢地非把错误明标在自己名下。
无奈,我一面安抚我的团队,吩咐仍按原计划安排D先生出院,然后把R医生的话复印下来,写成报告,交给了大内科主任。主任约见,告诉我科里正在考虑安排R医生强制性提前退休,原来类似情况R医生早有前科。于是我撤回了报告。这样做虽然我对R医生的指责没有在案反驳记录,却避免使自己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以后想起来不忍心。R医生的为人虽让人生气,她却是在按照她的原则办事而且敢作敢当,亦不失有其让人佩服之处。
无论在哪,医生的本心都应该是治病救人,只有这样才可算作好医生,所以我一点不怀疑R及T医生也想治好D先生。而美国的医学属于公认的世界领先,我们的医院有1 200个床位,规模在美国排在前5名,因此可以不用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一所好医院。参与D先生治疗都是各科的主治,好几位教授,T医生还是US NEWS所排100名美国最佳之一。因此,D先生的病例管理堪称美国医学的一个缩影。可是,很显然D先生的病例管理中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小,因为D先生险些不保。R医生虽然奋不顾身引火烧身,可是D先生发烧3周,每一个参与治疗的医生都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纠正,却什么没做。D先生的发烧本出于很简单的原因,检查治疗弄得轰轰烈烈,惊师动众,结果却是几至骑虎难下。
和中医截然相反,美国推崇证据行医(Evidencebased Medicine)。中医讲究辩证论治,阴阳五行解释一切,所以行医的中心在于医生的理念思维,医书大多是记载医生个人的心得经验。为此,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开个方子也要拉上君臣佐使。为此,一部经书传了几千年仍然可以从中体会发掘出新的解释。同样为此,教育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就可以等同甚至超过教授医学知识。而美国医学讲究证据知识说话,证据来自科研。重要的教科书每2-3年就要翻印重写,各专科每隔一定时间还要组织本科的权威,总结当前科研结果,发表各种指南。各科医生处理病例,无论服务态度如何,医学上都要以这些指南为准。如果出现不良行医诉讼,这些指南则是判决的主要依据。医学生毕业只是告别了课堂和教科书。医生每年都要有规定数量的后续教育(CME)记录,也就是胸中装满更新的指南,才能维持他的行医执照。证据行医是美国医学领先的原因,也是D先生病例问题症结之所在。
一切以客观证据为准,这种行医方式的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一部宪法,所有的人都以此为准。美国把医生和患者关系清清楚楚地定位成契约。医生没有接受病人的义务,但是一旦接下病人就得承担医患契约的制约:医生有提供最好服务的责任,患者有为自己享受的服务付费的责任。无论怎样定义,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掌握着知识,患者是弱方。一个病人落在一个医生手里,怎么才能保证自己得到的服务是最佳治疗呢?于是指南一类便犹如法律应运而生,提供一个客观的,人人可及的,人人受此规范的准则。这是保证患者权益的最有力的办法,因为发表成文的东西使得诉讼发生之前就已有了评判标准,而且发表过的标准不只是装在什么人的脑子里,任由一方单方面发挥。
行医指南是医学标准化。标准化可以使国家法制,市场规范透明,工业自动化,因为行医一旦有准则可寻,也就有了靠背书吃饭的天地。标准化的作用如此之大,一个病例一旦有了诊断,好比产品送上了流水线,人和机器的作用区别不是很大,仿佛人人都有雷锋精神甘当螺丝钉。证据行医原则对行医方式的影响在D先生病例中处处可见。R医生处处是指南挥手我前进,而T医生则大概根本没想过他是在一条错误的流水线上操作。
换句话,如果D先生持续高热,最终导致诉讼,T医生是肯定没事,因为传染科的责任是帮着选择抗菌素,而D先生病例中抗菌素的选择无可挑剔,虽然药不对症反而添病。R医生如果不坚持PAN诊断大约也不会有事,因为她既有病理诊断为凭,又有指南可循。但停了药,如果高热不退或是D先生病情恶化,从而导致诉讼,要捍卫停药人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不定因素就很多,因为无据可凭,谁也没有把握。
证据行医固然利多,医生的本事仍然不能只是背书背指南。说到底不管干什么,踩着别人的脚印虽然路好走却只能去别人去过的地方。人体乃是造物主在这世界上最复杂的创造,人迹所未能及之处甚多,医生治病自然也就不能只是坐在前人遗址上叹一声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