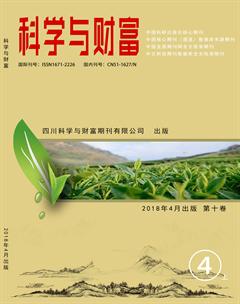后殖民视阈中的上海想象
温雅红 曹慧
摘 要:上海是中国文学史书写最多的双城之一,也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原乡。与其说《台北人》是书写离散在台北的大陆人的凄凉晚景,不如说是在情景移置中重温昔日繁华,故乡愿景借重记忆的想象性重構达到精神慰藉。后期创作的《纽约客》直面西方,以世界性视角洞察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关于乡愁的寓言,因离散的生命经验赋予了上海不同于大陆作家的想象视景。
关键词:《台北人》;《纽约客》;上海想象
无论是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还是四十年代的孤岛文学,上海都给了作家探索与施展的舞台,它凭借着自身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成为象征性的符码,在浸润本土作家的同时,以怀旧复古的繁华气息吸引着离散作家。在白先勇小说中,上海是或隐或现的叙事背景,抑或是人物命运的转捩点,正如作家本人身份认同的历程之艰,上海曾被殖民的历史记忆令其文化指认变得更加繁复,因而白先勇的上海书写在后殖民视阈中具有复杂多元的内涵。
一、怀恋:“她者”形象建构
在《台北人》中,上海始终以缺席的在场者姿态呈现,主人公多是红极一时的上海舞女,她们在大洋彼岸的台北作为旧上海的符号存在着,凭借着女性细腻的情思和八面玲珑的社交手腕,成为异乡人重温往日繁华的现实幻境。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选取女性为中心视点展开,形成舞女——旧上海的对应图式。
女性与城市是有着先天的联系的,女性凭着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更易于适应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正如王安忆所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1在白先勇的笔下,游弋于十里洋场的女性具有与之相应的城市品格,以“她者”的塑造建构自我的上海想象。
其一,世俗中的实用功利主义。不平等两性关系中的自我保护和以身体美色换取生存资本的现实境遇迫使她们在声色犬马之中精打细算,维护着自己狭窄的生存空间,在情人徐壮图的葬礼上,尹雪艳冷静得近乎无情,例行礼节而不流一滴眼泪,傍晚的尹公馆又照例响起麻将声。男人来去周而复始,唯有在物质的依附中保有精神的独立才能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中茕茕绝立,舞女的无情是金钱社会中被迫练就的金刚铠甲。其二,冒险机器中的虚与委蛇。她们对男女之间情爱游戏熟捻于心,八面玲珑地周旋于上流社会各色男人之间,欲拒还迎,是危险的小兽但又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力。金兆丽个性泼辣,敢于与经理针锋相对,年逾四十依然觅得良枝。桂枝香和蓝田玉更是直接从低等的卖唱女晋升为将军夫人,在上海这座冒险机器中,太多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算计,人与人之间见不得一点真心,虚伪是金钱社会的生存法则。其三,离乱中的温情底色。她们虽世故但也不乏可爱之处,宽容而充满爱心,帮助身陷困境的人,如尹公馆成为旧雨新知的聚会场所,尹雪艳不厌其烦地招待各色客人,精美的茶点,熟悉的室内陈设,为流落台北的故乡人营造熟悉的记忆,无论是太太们还是商界精英,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已失往日荣耀的没落者都能得到尹雪艳的尊重,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优越感。她对待垂垂老矣的吴经理的耐心和关怀是浮华之中那一点本性的纯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
女性作为被想象的她者,因其文化和性别的独特性成为一种隐喻。小说中的这些女性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跳脱于家,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她们貌似独立却难掩本质的依附性,以金钱抬高身价后仍以嫁作他人妇为最好归宿,在作者或调笑或温情的笔调下,寄寓者对这些女性深深的同情,她们始终未脱离不平等男性的“他者”镜况,这与白先勇及其父辈的文化漂浮状态同构,这些女性的命运亦是流落台湾的“外省人”的真实写照。
二、矛盾:上海想象的隐性症候
对于白先勇而言,上海无疑代表着对于中国的记忆,在《第六只手指》中他自述道“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控排也印下了千千白白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2上海是身处双重“他者”镜况的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凭据,但具有荒诞意味的是,作为白先勇怀恋对象的“她者”却并非纯然的家园,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虽并未完全沦落为殖民地,但是却处于一种半殖民的状态,更像是“杂交”意义上的殖民和中国因素的混合,霍米巴巴将这种状态相当微妙而模糊地定义为“殖民戏拟”,3这构成一种后殖民状态下的文化纠结,因而他笔下的上海想象在不其然之中隐含着欲望迷失的焦虑和“失根”的无所适从之感。正如“东方巴黎”这一称号,上海同时带有东方和西方的双重属性。蕴含在矛盾之中的是白先勇独特的文化因子。呈现白先勇上海想象的共有五篇小说,其中《金大奶奶》作为白先勇初涉文坛的处女作,描写了一个被上层社会压迫的悲惨妇女形象,时值台湾新文化运动,提倡继承五四优良传统,因而有启蒙大众的意图,暂且不予以过多考量。其余四篇小说所构筑的上海世界均为繁华的大都会形象。
首先,“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可是我真想得厉害。”4作家的创作来自于个体的经验和记忆,40年代那一场重大的家国动荡使白先勇一家从故乡迁居台湾,大家族得以保全但却失去了昔日的尊贵和权势,父亲白崇禧甚至被当做特务监视,加之背井离乡融入新的城市,白先勇的心境可想而知。他自小随父母迁徙,不知道故乡究竟在哪方,亦不知该怀恋何地,记忆中留存的是童年对于上海的鲜活触碰,这在潜意识中构成了白先勇对于家的想象。旧上海上流社会的生活故景成为他追忆、怀念的理想家园,而曾经的繁盛亦可唤起微妙的自尊,在孤寂中寻得一份慰藉。因而不同家国叙事的宏大想象,白先勇将小说的战争背景做了虚化处理,人物更多沉浸在一种感伤、无奈的氛围当中,颓废而无锐性。
其次,在这五篇描写上海的小说中,仅有《金大奶奶》一篇在台湾写成,其余分别在1965-1970年在美国创作,此时他到纽约至多不过7年而已,从大陆到台北,从台北到纽约,白先勇经历了“双重流放”,人生的动荡飘零之感此时最甚,一方面怀旧感伤,一方面突然遭遇西方文化,挣扎在身份认同之中,“上海怀旧”书写成为必然,虽然白先勇最初的目的在于文化乡愁,但却在客观效果上陷入后殖民主义东方化的窠臼,成为西方世界想象中国的“他者”,在这几篇小说中我们都可隐约窥见现代性焦虑。尹雪艳和金大班都与“海派”背景的男子知遇,尹雪艳的老练世故使她在与徐壮图的两性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高贵而不为所动,但无惧世俗非议出现在徐壮图的葬礼上已表明尹雪艳对他的青睐。金兆丽在夜巴黎的最后一晚邂逅了身着沙市井西装的男大学生,红舞女放下身段教其跳舞,耐心与温柔仿若回归当初那个与月如相遇的女子,“她把年轻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地数着……”此外,《孤恋花》和《游园惊梦》中均出现了鲜明的现代化意象,娟娟被关进了带有西方机器化性质的精神病院中,钱夫人游园梦醒时分那一声惊叹“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5都象征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碰撞。我们不能断言白先勇选择曾经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作为自己怀乡的切口是因为自己身处异国他乡的文化尴尬和焦虑,但两者确在冥冥之中形成某种暗合,也许这就是蓝棣之先生所言的心理症候。
三、放逐:认同危机与世界性视野
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上海亦是作為一个重要的意象出现,小说主人公黄凤仪和李彤都是出生于上海上流社会家庭中的小姐,由于战乱而流落海外,一个被称为“蒙古公主”,一个被视为“贵族小姐”,相比较《台北人》中的舞女形象对上海想象的构建,《纽约客》中的上海主要是内化在黄凤仪和李彤这类流落异国的贵族小姐的文化因子中,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本性善良而单纯,未曾混迹于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当然也不具备尹雪艳之类八面玲珑的生存手段,当战乱把她们抛向异乡纽约,她们陷入巨大的文化割裂状态,无所适从,黄凤仪沦落成为妓女,李彤醉生梦死,最后投海自尽。值得注意的是,白先勇将富有历史含量的中国符码巧妙地放置在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身上,她将自己命名为“中国”,而李彤打牌时的对话听来也别有一番滋味:“我这个‘中国逢打必输,输得一塌糊涂。碰见这几个专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败仗的份。”除却上海的文化烙印,她们代表了中国。她们是沦落到人间的“谪仙”,白先勇将少时的经历投射到人物身上,只不过镜况更为惨烈。与《台北人》中的浓烈的怀旧气息不同,《纽约客》中是深深的萧索和苍凉,白先勇对黄凤仪和李彤更多的是一种悲悯之情。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谈及“流放存在一个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它处于与旧系统半牵连半脱离的位置,它一方面是怀旧和感伤的,另一方面又是模仿的能手,并偷偷地放逐。”6怀旧是寻根的寄托,而寻根带来的是更深刻的流放,在彻底放逐之中拥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在放逐中获得超越是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流放”的另一半位置,也是更高层次。如果说“双重流放”并非完全的悲剧命运,那么就是这种流放给白先勇带来了一种有活力的文化身份,使他拥有了更为多元的文化视野,在这种“第三空间”中白先勇悄然之间完成了对后殖民的解构。他用冷静的眼光关注心灵放逐的漂泊者,悲悯着那些异乡人的愁苦,在海外华文的世界中记重铸上海想象,抒发隐现的乡愁。
同时,这豁达的世界性视野也给了他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契机,他像是患了“文化饥饿症”,迫切地捧读起中国的历史和文学来,包括在台湾很难看到的“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在世界性格局和普世文化视野中,离散的个体反而找到了历史的归宿,被消解的文化家园反而得以建构,那种顿悟的发生是令人感动的一个瞬间“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7
四、结语: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带着表面的浮华和深深的腐败;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社会,极度的奢华与极度的贫乏并存共生;一个半殖民地,一小撮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践踏着中国的普通百姓;一个混乱的地方,枪统治着拳头;一个巨大的染缸,乡村来的新移民迅速地被金钱、权势和肉欲所败坏。简言之,这个‘老上海是一个带着世纪末情调的都市。”8上海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化中心,素来是作家偏爱的场域,在穆时英的笔下,上海是造在地域上的天堂,在张爱玲的世界里,上海是兼具梦幻和现实的情感竞技场,而在白先勇的想象中,上海是寄寓着乡愁的文化幻影,亦是童年最怀念的时光,上海沉淀在其记忆中,从最初的怀恋到成长中对故乡复杂性的体认,以至年老后回望命运所拥有的超脱世俗的世界性视野,白先勇在不断成长,上海也在不断剥离虚假的文化符号,还原真实的面容。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7页。
[2]白先勇:《上海童年——代序》,收入白先勇《第六只手指》,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3]殖民戏拟就是对一个变了形的但可辨认的他者的欲望,他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个差异的主体……这种欲望,通过复制部分的存在……表达了文化、种族和历史差异所引起的骚乱,这些差异或者威胁着殖民权威的自恋倾向。霍米·巴巴《论戏拟和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见他本人的《文化定位》,伦顿和纽约儒特爵父子公司,1994,第86-90页
[4]白先勇:《白先勇回家》,收入《蓦然回首》,尔雅从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168页。
[5]白先勇:《游园惊梦》,收入《台北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6]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7]白先勇:《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77页。
[8]伍湘畹:《回到未来:想象的怀乡愁和香港的消费文化》,系她于亚洲研究协会在新英格兰召开的年会上宣读的论文,1996年10月19日,费蒙特大学。第10页,引用经作者同意。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328页
作者简介:
温雅红(1992-),女,汉,山西太谷人,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