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床
◎阮红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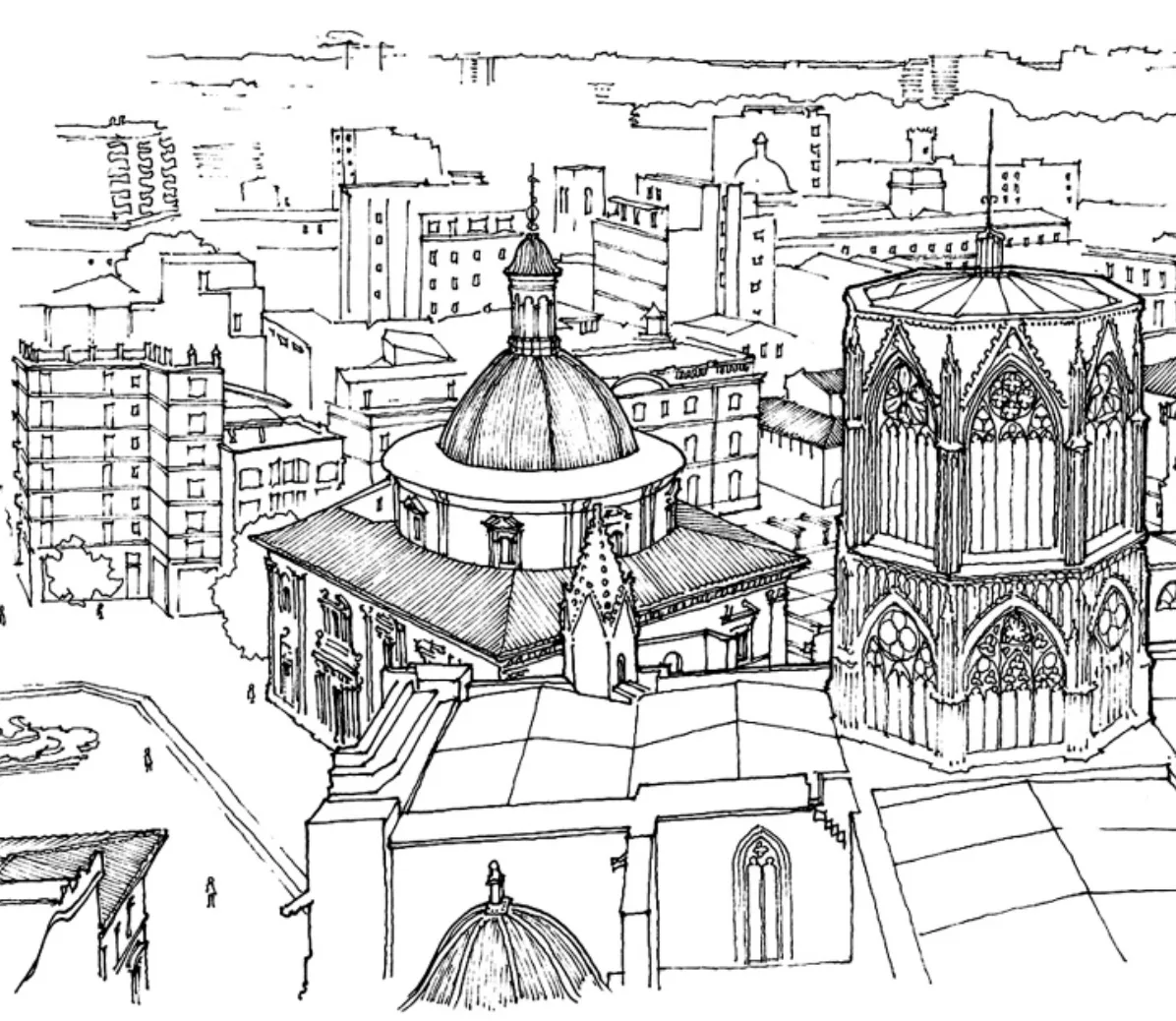
张天保陪局里来的客人喝了几杯,回家时天已经麻麻黑了。
局里的食堂很上档次,与城里的酒店比,除了硬件差点,吃的质量一点不差。而且安全,不怕纪委盯上。吃过饭就散了,大家都是明白人,歌吧澡堂是不能去了,麻将也不敢打了,大家嘻嘻哈哈地说:“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
张天保的家在县里的渡口镇,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房。从局里开车到家,如果道上不堵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娘的,如今县城也堵车了,而且是乱七八糟地堵,堵得没有天理。一半是新手违章造成的堵,一半是摩的乱窜造成的堵。小城的交警又是那么少那么忙,晚上各要道基本看不到人影,就造成了令人绝望的堵。要是前几年这般堵,张天保是不回家的,现在感觉有点闲了,天天都想回家。
家里有宝,宝就是娇妻。他在家里不喊妻子的名字,也不喊妻子的乳名香香,喊娇妻。妻子艾香香小他十岁,在渡口镇医院当医生。职业好,人也好,又长得标致。年轻时不懂女人的好,人到中年,开始懂得女人的好了。但是,当他有心情娇宠女人时,女人不经宠,有点不对劲了。妻子有洁癖,最见不得他一身酒气。以前只是撒娇一般撒点小脾气,现在不了,来真的了,小题大作了。因喝了酒造成夫妻吵架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了,更让人痛苦的是,只要沾酒,就别想房事。
可是今天又喝酒了。为了夫妻和睦,他想过戒酒。有公干,又当着局长,戒酒基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准大吃大喝么?革命工作不吃饭不喝酒怎么行,人情世界,小酒还得喝着,只是转移了战场,从高档酒店撤退到了单位食堂。中午是共产主义生活,全局人员工作餐,晚上是小灶,局领导要研究工作,加班餐。
张天保爱吃加班餐除了对往日生活习惯的怀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呢,也不知怎么了,妻子完全不把他当局长看了,把他当成了机关小男人。动不动就使小性子,要他学洗衣服学做饭。她说:“我们都在上班,都辛苦。再说,我的工资又不比你少,凭什么要我服侍你!”
道理是不错。这几年,自己的收入缩水严重,个人收入的确比妻子强不了多少了。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别说小局长,就是县长在家里也不好使,没真金白银往家里搬,在妻子眼里也不过一机关小男人。但是,让局长洗衣服做饭是不可能的,在家是机关小男人,在外面也是局长呐。宁愿半夜在被窝里被妻子用脚踹用长指甲抓,白天也不会妥协。打死骂死也不洗衣服,不做饭。
夫妻就是这样子的啦,小打小闹才是情趣。
回到家,张天保到车库放好车,一路小跑来到门前。开门时,发现自己竟然捏着钥匙套忘了家门是哪把钥匙,选看了半天,试了半天,打不开门。于是,趴门边叫道:“娇妻,你老公回来啦,开个门噻。”过去不是这样子的,过去只要听到车喇叭响,妻子就笑吟吟地迎出来了。一边对久违的老公嘘寒问暖,一边从车后备箱里帮着拿东西。手里再没空,也会帮他拎着公文包,而且直接将公文包拎进他的卧室。他呢,总是喊累,进门就恨不得歪床上。更多的时候是幸福地歪卧室的沙发上,瞧妻子检查他的包……然后,像老爷一样,被仆人妻子拎来拎去,一会儿被拎到了饭桌上,一会儿被拎到了洗澡间,一会儿被拎到了被窝里,一会儿怀里静悄悄偎进了一个美人……啊,多么幸福的时光!
艾香香穿着睡衣开了门,只是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伸出脑袋瞅了他一眼,马上又将脑袋伸得更近,在他身上闻了一下。门,无情地关上了。里面说:“我对酒精过敏,你醒了酒再回吧。每天有事无事喝酒,烦死了!”
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张天保站门外检讨了半天,才捉到线索。上午老婆打过一个电话,说是自己四十岁生日要到了,让张天保张罗一下。
“不行啊,老婆,现在有规定,不准操办这种事。你可能不知道,局里有个科长前阵子为母亲祝寿躲在乡下摆了几桌都被人举报了。我没去,也不知情,也写了检讨。”艾香香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发炸了。你说你这个鬼局长当着有什么意思,成天怕这个怕哪个的。打老虎也好,打苍蝇也罢,蚊子不一样照样来劲。我告诉你,现在当个蚊子村主任也比你这个苍蝇局长活得来劲。
张天保在电话那头气得脸色刷白,心想,老子当个局长还当出鬼来了,动不动就拿这个说事。不好说什么,把电话摔了。
张天保生着闷气,背着手瞎转悠,七转八转,转到了副局长张胖子家。
张胖子是他在局里的副手,也是朋友,友情相当牢固。当年买地建房时,张胖子还是渡口镇的副乡长,两人因为买地发展了友谊,房子做到了一块,最后到了一个局,最后成了朋友。张天保家里有事,都是张胖子在照应着。比如夫妻吵架,张胖子就是和事佬。张胖子总说:“张局长,咱们都姓张,是一家门,谁跟谁啊!”
朋友加上这么一层莫须有的血缘,那关系就很不一般了。
张胖子家这会儿灯火通明,连门口都挑起了门灯,门前有木匠在打夜工。记得张胖子说过,老娘身体不好,怕是撑不了几天,得给老娘赶制寿材。虽说现在都要求遗体火化,但当地风俗,出殡还是老传统,吹吹打打绕几圈,用棺材送亡人到殡仪馆。
张天保来到门口的时候,张胖子正躺在棺材里试尺寸,听到局长的声音,忙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老张,你怎么可以睡在棺材里呢?”张天保惊讶地问。
张胖子拍打着身上的木屑,笑着说:“局长,你这个城里人就不如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了。棺材为什么不能睡活人呢?你知道老辈人把棺材叫什么?叫福寿床呢。活人睡了添福添寿,病人睡了冲邪去病,小孩睡了消灾避难呢。”张天保被张胖子一席惊世骇俗的话说得好奇心大发,也忘了心中的不快,将信将疑地说:“是么?老张,这话听着稀奇。”忙活的木匠插话说:“这话一点不假,寿材做好后,重病人还睡一段时间,冲冲邪,有人还真睡好了,不稀奇。”张天保一听,若有所思,扭了扭腰,拍了拍肾说:“真的啊,我的腰一直不怎么好,不知睡一下这福寿床效果怎么样?”
说着话,人已爬进棺材里站着。张胖子忽然想起局里什么事,凑过来说:“局长,有个事我正要去找你呢,局里……”张天保打了个暂停的手势,不耐烦地说:“老张,下班以后不谈工作,天大的事,明天上班再说。八小时以外,我什么也不是,是个闲人。”张胖子笑眯眯地说:“对对对,闲人。”张天保摸着一身泡泡肉,蹲下也很困难的样子。张胖子忙跑过来扶住,让张天保在寿材里慢慢躺下。
张天保小心翼翼地往下躺,心想,天下的好床自己基本睡过,总统套房的床也不过是一张床,这福寿床还真没睡过。身子一挨棺材板,肌肉一紧一松,睡踏实了,就完全放松了。人这一辈子,豪宅也罢,五星级宾馆也罢,最后只要这么小一个地方就行了。张天保屈腿躺着,不敢伸直腿,怕自己一伸腿就跟死人一样了。也许是吸了木板的凉气,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有了尿意。赶紧爬起身跑到卫生间撒了一泡牛尿,酒也醒了,头也不昏了。张天保不由得大喜,拍着张胖子的肩膀说:“奇了,没想到这阴物还有醒酒的功效哩,我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这事就当一个玩笑,很快就过去了,张胖子也没放在心上。但张天保放心上了,在棺材里躺了这么一次,只不过五十岁的他,怕死了。
张天保虽说出身在城里,又受过高等教育,却相当迷信。他一直认为自己从一个市井弃儿成为今天政府重要部门的局长是神助的结果,业余时间看得最多的就是易经、梅花易数这类风水书,他的“业余爱好”不是什么秘密,局里都知道。局里有人建新宅,偶尔还请局长帮忙选选地方,都认为这是一种情趣,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张天保十三岁没了父亲,对母亲几乎没什么记忆。父亲是个盲人,每天起早贪黑,跑到车站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着,给南来北往的人抽“彩头”,也有叫抽签的。这是大多数盲人的生计,解签的水平非常可疑。但父亲却是个奇人,属于真正的半仙。年幼的张天保经常目睹父亲在家里做功课,抱着一个小录音机,一动不动地听各种人说话的声音。他从不同的声音里倾听人生,从而推测人的命运。偶尔也坐在小院里听鸟叫,有一次他听到院里草丛中一只斑鸠的叫声,自己摸过去把斑鸠给捉了。
“这只斑鸠受了伤,已经不能飞了,但我看不见它伤到了哪里。”父亲对儿子说。张天保能看见,斑鸠的背上的羽毛有暗红的血迹,不过叫声跟健康的鸟叫没什么区别。
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一直拒绝就医。他说:“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最清楚,医不好的。”当生命的大限到来时,几乎没什么征兆,他每天还是按时出门,按时回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父亲没有出门,而是搬了把躺椅静静地躺在院子里。
“你今天别去上学,我已经托人到学校给你告假了。”父亲对正要上学的张天保说。同样没有上班去的是张天保的叔叔,一大早就到张天保家来了。大约是正午吧,一直叽里咕嘟自说自话的父亲猝然大叫一声:“到点了。”头一歪就告别了人世。
从此,张天保就一直跟着当搬运工的酒鬼叔叔。跟着叔叔什么也没学会,学会了喝酒,小孩子家喝半斤白酒也不醉。求学时成绩一般,高考却如有神助,奇迹般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连班主任也惊诧说:“我班上成绩最好的几个尖子都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成绩中游的张天保却创造了奇迹!”大学毕业以后,毫无背景与人脉的张天保被家乡的一家国企录用,成了车间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车间主任是也姓张,按年龄应该是张天保长辈。由于从小缺少家庭的温暖,张天保成天将车间主任叫“干爸”,当时也只是叫着玩。没想到这个干爸了得,从主任一直升到了总厂的厂长。“干儿子”张天保也从技术员升到了总厂的团支部书记,从此开始他的平步青云。官场历来是第一步最艰难,从地上爬到椅子上就行了,从椅子上爬到桌子上比从地上爬到椅子上要容易得多。因为你站在地上谁也看不见,但你站在椅子上就容易被人看见了。
回忆往事,张天保一直认为自己当年喊车间主任“干爸”不是灵机一动,而是神来之笔。他私下里对艾香香说:“我的幸运就是叫那声干爸开始的,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了这个口,但有一点很清楚。我并不是觉得老家伙亲切,而是很怕他。对一个小技术员来说,车间主任就是我的皇帝,可以决定我的饭碗可以随时不要我让我下岗重新一文不名流落街头。因此,我怀着恐惧认了这个干爸,并像孝敬父亲一样对待他。当时,我内心住着一个神,时时提醒我,要对这个人好我自己才能活得更好。”
张天保当上局长后,并没有饮水思源去谢干爸,而是去了城郊最大的寺庙。
正是那天在“福寿床”躺过以后,张天保的人生观与生活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局里,他不再大权独揽,将更多的权力让给了分管一面的各副局长。他每天神出鬼没,很难在局里见到他的人。以前也很难见到人,那是因为忙。到县里开会、到分局、下乡、各种应酬……总是忙得在局办公室坐不上半小时。后来就不怎么忙了,因为他的应酬越来越越少了。局里发现,少了应酬的局长其实是不忙的,已经有时间在办公室悠闲地喝茶,偶尔还在局机关大院溜达。
张天保现在对局办公室交待最多的是,我下乡了,有事打我电话。
他的确是下乡了。但他不是有公干,而是有心事。“福寿床”的功能,他还要找更可靠的依据,他最信任的张胖子的话,他只信一半。其实这种事,他问一个人就行了,就是当医生的妻子艾香香。但他信不过妻子,也不相信医学。
艾香香当了十八年医生,开始是门诊医生,后来是住院部的主治医生,再后来是专科主任。但在艾香香心理轨迹上不是这样的,她认为自己当门诊医生时相当一个专家,百病都能攻克。当主治医生后,觉得医学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学问,穷尽一生,也许能学点皮毛,当科主任后,她认为自己其实更像个护士了。
“在专业上,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无知,对疾病有点无可奈何了!”艾香香私下对丈夫说。她说的是实话。医生与教师最大的不同,是教师可以用同一个教案教几代学生,医生不能,医生的病案没有范例。同样是小感冒,在一百人身上有一百种不同的生理反应,有人不用药就好了,有人很可能病情迅速变异而致命。医学的进步与生命的复杂相比,太轻飘太微不足道了。事情往往是这样,高明的医生面对疑难杂症,有时比病人还困惑还恐惧。做的工作与其说是治疗疾病,不如说是在护理病人。
因此,艾香香在家里做得最多的是对丈夫的护理,张天保真的病了,她也会吓得像一般主妇那样,送医院,送更好的医院。她不是不能治,是没把握。对亲人来说,治疗仪器是可疑的、药方是可疑的、剂量是可疑的……自己的治疗办法更是可疑的。对一般病人没把握她可以信心满怀,可以寄希望于运气,可以为了战胜疾病往死里治,或者说可以装,对亲人,她连装的勇气也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减少恐惧。
医生对疾病的无奈与专业的脆弱,只有配偶才能近距离感受到。走出家门,医生仍然是能够战胜一切恶魔的天使,是起死回生的神仙。
“其实,更多时候,是病人自己医好了自己。”艾香香这句话不只是对丈夫说过,也对创造生命奇迹的病人说过。在一般人听来,这只不过是一句客气话。
张天保不认为这是客气话,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病痛,除了仪器检查,最了解真实状况的是自己。张天保身上也有各种不适,比如总是头晕、气喘、骨头疼等,也检查过,查不出什么结果。但他认为这些不适正在吞噬自己的生命,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在民间,张天保走访了一些江湖高人与高寿老人,验证了“福寿床”的神奇功效。材与财同音,古时候有送寿材之礼。当然不是真棺材,是那种袖珍棺材,一般送给走霉运或破财之人。古时候的江湖医生,经常让那些不久于人世或沉疾已久的人睡一睡“福寿床”,偶尔就有奇迹。有些富豪与高官,为了避邪消灾,早早备下 “喜木”,也就是棺材,漆成大红色,头板与脚板都绣上金色的“寿”字,当床睡。
张天保对这些江湖传说深信不疑。他收集这些,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更不能与外人道的秘密。他总认为自己要出事,出大事。像他这种在官场毫无根基的人,一出事就不是小事,如秋风吹枯叶。
张天保在一家寿材店订制了一副上好的“喜木”,神不知鬼不觉运到家,放在了自己车库旁的小屋子里。连艾香香也瞒过了,这事儿是趁她出去旅游时干的。
“喜木”放在车库旁的小屋子后,为了隐蔽,他没有将屋里的杂物清出来。就是有人发现,也会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副备用的普通寿材。他每当感到身体不适或心神不宁的时候,就会悄悄地在“福寿床”躺一躺。
这期间,局里出事了,常务副局长老周被查出经济问题。老周有个外号叫“周百万”,号称是局里最有钱的人。他的钱,是业余时间炒股赚来的,十年前就是百万富翁了,外号也是那时得来的。那时他还不是常务,是很靠边的副局长。在局里,他是坐班最认真的人。他的办公室门经常关着,有事找他,他经常都在。都知道他在办公室炒股,有闲话,但也拿他没办法。人有了钱,就有了底气,大不了这个副局长不干了,他不稀罕。也有人说他是怀才不遇,能炒股赚大钱的脑袋,应该在局里有更重要的位置,但其它副局长或提或另调,就没他什么事。张天保上任以后,重用了老周,让他当了局里的常务。老周当上常务,大伙理解又不理解。理解的是,老周的确有能力当常务。不理解的是,老周“不管事”在局里是出了名的,分管个工会,几年来一次活动都没搞过。张天保看重老周当然不是看中了他的才干,他私下里对艾香香说:“这个人当常务有两个优点,一是有钱,见过钱的人与没见过钱的人不一样,他不会再见到钱就两眼发绿。二是他不爱管事也不惹事,在局里的关系简单。”常务是干什么的,除了主持局里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管财务。二把手不管事,对一把手来说不是什么缺点,从某种角度说还是优点。
当上常务的老周不再窝在办公室炒股干脆回家炒股去了,他经常请“病假”,经常“出差”。是不是真病了真出差了,只有一把手张天保最清楚。张天保准假了,老周就是真病了,张天保说老周出差了,老周就是出差了。
两人愉快合作四年后,张天保才放权。事情的巧合在于,老周挪用公款炒股的时候,正是张天保让权以后。过去,主管财务的老周只不过是个摆设,局里的资金动向,没张天保点头,一分钱也动不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张天保没精力也没兴趣过问财务了,也觉得没必要再操这个心了。于是,让老周当了局财务“一只笔”,所谓“一只笔”,就是老周签过字的,就相当于一把手签过字。张天保与老周换了个角色,开始悠闲地当着“没权”的局长。几个副局长不但没意见,比以前更尊敬他了。局里只要干出了什么成绩,上级奖励时,功劳全安在他脑袋上。
老周出事了,却跟他没多大关系。翻出当时的局党委会议来看,记得明白着呢,职责划分非常清楚,老周“一只笔”,大家都是举了拳头的。
最后,老周进去了,张天保负监管不到位的责任,受了个不痛不痒的党内警告处分。
张天保平安无事继续当着“没权”的局长,该有的一样没少,不该有的他装聋作哑。事实证明,他“收手”是明智的,而“收手”的念头,正好是睡了“福寿床”以后的觉悟。
张天保出事那天,阴差阳错也是睡在“福寿床”上。
那是秋后的一个周末,张胖子请几个局领导到他家聚聚,聚的理由是他埋在自家院子里的一坛老酒要开封了。市场上时兴的年份酒让他成了有心人,他从一家知根知底的酒厂购了一坛十五年陈酿,在自家后院又埋了五年。二十年陈酿在市场上是有,但那年分却相当可疑。自从规定局招待不准上高档酒店后,大家好久没喝到上好的陈酿了。于是,有了这个题目,喝酒的不喝酒的,退了的和没退的,一共七个局领导爽约来到了张胖子家。
七个人中有两人早宣布戒酒了,另五个中,数张天保最能喝。那坛陈酿与其说是招待大家的,不如说是招待他的。
张天保就喝高了。
张天保晃晃悠悠向自己家走去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因为喝多了酒,张天保不敢进屋,倒不是怕艾香香揍他,怕艾香香的唠叨。女人的唠叨有时比挨顿揍更让人痛苦。他就进了车库旁边的杂屋,想在“福寿床”上躺躺,醒了酒再进屋去。谁知一躺下,就睡着了。
半夜,张天保被一阵不寻常的响动给惊醒了。他感觉杂屋里有人走动,又感觉好像在搬什么东西,最明显的感觉,是“福寿床”的盖子给合上了。他感觉陡然间出气不畅快了,惊恐得打了个尿惊。但是他不能动,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福寿床”的盖子合上后,他骂了一句,估计也迷糊不清,发出的声音如梦中人的呓语。要不是“福寿床”的脚部留了气孔,估计他连呓语的机会也没有了。
“福寿床”开始晃悠起来,像摇篮一样。张天保想挣扎一下,却在舒服的晃悠中再次沉沉睡去。
张天保再一次被惊醒,是一次猛烈地振动,就好像平日妻子烦他,连人带被子把他给掀起来。这次肯定不是妻子掀被子,是地震。不知自己是从地球上掉下来了,还是从月球上掉下来了,反正是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掉。他开始翻滚,不是,是“福寿床”在翻滚。“砰”的一声,“福寿床”的盖子飞了,一般清新的冷风吹进来。张天保贪婪地呼了几口新鲜空气,发现自己躺在冰凉的泥地上,接着“呼”的一声,他感觉自己被“福寿床”给扣住了,又出气不畅快了。
躺在冰凉的泥地上,他酒醒了。他弄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明白自己怎么被“福寿床”给扣住了。他像作俯卧撑那样,试着用背顶了一下“福寿床”,背部像顶着一块巨石,纹丝不动。他竖着耳朵听了一下动静,什么也听不见。“福寿床”扣得太严实了,好在地面高低不平,给他留下了生命的缝隙。他马上想到了报警,在口袋里很快摸到了手机。但是手机黑屏了,开不了机,按了几下,才发现没电了……
他遭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后来都是听妻子说的。
张天保在张胖子家喝酒的时候,一个送煤球的汉子拖着半车没出售的煤球来到了他家。
家里是烧着煤炉的,艾香香值夜班时,白天喜欢生着煤炉喂汤。妻子对丈夫的照顾,也体现在常年的煨汤功夫。艾香香认为,煨汤除了锅具,就是火。柴火最好,炉火次之,电火最差。因此,在不方便再用柴火的情况下,她选择了炉火。
平日里放媒球的地方在厨房外的屋檐下,因为夏天风大雨猛,煤球总是被淋湿,艾香香想到了车库旁边的杂屋。打开杂屋,她惊讶地看见了张天保藏在里面的“福寿床”。想到自己的父亲已经年近七十,身体也不是很好,以为张天保是为自己的父亲准备的寿材,只不过忘了告诉自己。送煤的汉子也看见了,一连搬煤球,一边夸“好材”。说这种檀木做的寿材在乡下不便宜,用料这么扎实,做工这么精细,可能要上万的钱。艾香香对上万的钱不惊讶,惊讶的是张天保这么有良心。这几年自己没给他好脸色,他却还是对自己这么好。
送媒球的汉子惦记上了这口上好的寿材。平日里走乡串户送煤球,干过顺手牵羊的勾当,那都是小打小闹。家里四兄弟,正为老母买棺材的费用问题扯皮拉筋。瞧见这口上好的寿材,送媒球的汉子心动了。
当天半夜,送媒球的汉子四兄弟带好绳索扁担摸到张天保家。院门只是虚掩着,好像主人夜出未归,一推就开了。杂屋没上锁,白天就瞧明白了。黑暗中,兄弟几个摸进去,也不敢照明,摸索着找到棺材盖,扣好。捆的捆,绑的绑,两根杠子就将棺材从张天保家给抬了出来。
道上遇上好几个夜行人,人家以为是哪家死人后怕火葬,偷埋人,就没心情管闲事。
路过一段河堤的时候,最瘦的老四一不小心踩空了,跌了个嘴啃泥,其他几兄弟也跟着跌了个东倒西歪。棺材也被摔到堤坡上,棺材飞滚着,棺材盖摔得飞出去。四兄弟被摔得呼爹喊娘,有一个伤了腿筋,另一个扭了脚。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口棺材这般重,四条壮汉抬着也止不住晃。现在伤了两个,要把这么重的一口棺材从堤坡下弄上来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四个贼骂骂咧咧回家了。
这事儿要是艾香香不张扬,也就是虚惊一场。但是艾香香张扬了,不张扬是不可能的。她夜里至少给张天保打了十几个电话,都关机。第二天一早,怒气冲冲跑到张胖子家去寻人。张胖子说大伙吃完饭就散了,张天保回家了。艾香香以为张天保临时有什么事到局里了,也许睡办公室里了。跑到局里,局长办公室门锁着,敲了半天也没人。正好局里都陆续上班了,办公室主任打开了张天保的办公室,里面真没人。张胖子和几个副局长捧着手机不停地拨打,还是关机。
艾香香心里就慌了。更慌的是几个副局长。局长失联,这不是小事。于是,大伙分头去找,估摸着张天保有可能去的地方,都去找了。
中午,艾香香没回家,几个副局长也没回家。大家商量了一下,如果下午还不见张天保回来,只好报警了。艾香香已经等不及了,要求局里不要等了,马上报警。
张胖子迟疑着。张天保是在他家喝酒后失联的,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脱不了关系。再说,局长失联可不是闹着玩的,按照组织程序,这事还得马上报告县委。
于是,张胖子将利害关系向大家说明以后,坚持再等等。
局长失联的事,除了几个副局长,向外严格保密了一整天。
下午,张天保还是没有回来,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张胖子这才让艾香香报警,自己与几个副局长,则开车到了县委。
这事很快惊动了县城的各片区派出所,也惊动了县委书记。
好在各派出所出警不到一小时就有了结果。在城郊一处人流量稀少的堤段,民警发现了堤坡脚下一口倒扣着的棺材。因为杂草太深,棺材只露出了三分之一。堤上就是偶有行人经过,也很难留意。民警包围了棺材,首先小心地在外面敲打了一下,里面很快就传出一声沙哑的 “救命”声,如果耳朵不贴着棺材缝,完全听不清。翻开棺材,气息微弱的张天保面无血色地出现在民警面前……
在派出所调查取证的阶段,张天保在家里闭门躺了两天。
第三天,县里就下了文件,张天保被免职。文件用字相当简捷,没有提任何免职的原因。几个副局长也只知道张天保被免职跟他失联一天有关,再不知其它细节。
很久以后,在县里一次干部理论学习会议上,县委书记沉重地谈到党员干部的信仰问题,顺便提到了张天保,大伙才知道“福寿床”的奇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