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以一手史料见长的《丁玲传》
——李向东、王增如版与蒋祖林版《丁玲传》对读
阎浩岗
河北大学文学院
从2015年5月到2016年10月的一年多中,先后又有两部重要的丁玲传记出版,即李向东、王增如夫妇的《丁玲传》(以下简称“李传”)和蒋祖林的《丁玲传》(以下简称“蒋传”)。这两部传记与迄今为止出版的其他丁玲传记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所披露的一手资料多、信息量大。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作者的特殊身份或位置有关:蒋祖林是丁玲的儿子,王增如是丁玲晚年的秘书。他们凭着自己与丁玲的零距离接触,获取了一些别人难以得到的资料。因此,尽管已有二十种左右丁玲传记行世,其中有些已写得相当好,但李传与蒋传的出版仍引起丁玲作品爱好者与丁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那么,这两部丁玲传记究竟给读者哪些新的史料、新的理解?其独特价值具体何在?我们可以围绕丁玲一生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将这两部著作对照阅读,看它们是如何解答、如何表达的。
关于丁玲的婚恋
丁玲一生感情经历曲折,其婚恋生活较有传奇性,她的选择反映了其鲜明独特的个性,并与其人生追求密切相关,因而是一般丁传不会忽略的问题。只不过以往丁玲传记大多突出表现她与胡也频以及陈明的恋爱婚姻经历,重点突出革命爱情的纯真高尚,有些则捎带提到冯雪峰。而在这方面,李传和蒋传各有新的发现或“爆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蒋传对丁玲、瞿秋白之恋的披露与李传对丁玲、陈明与席平三角恋情的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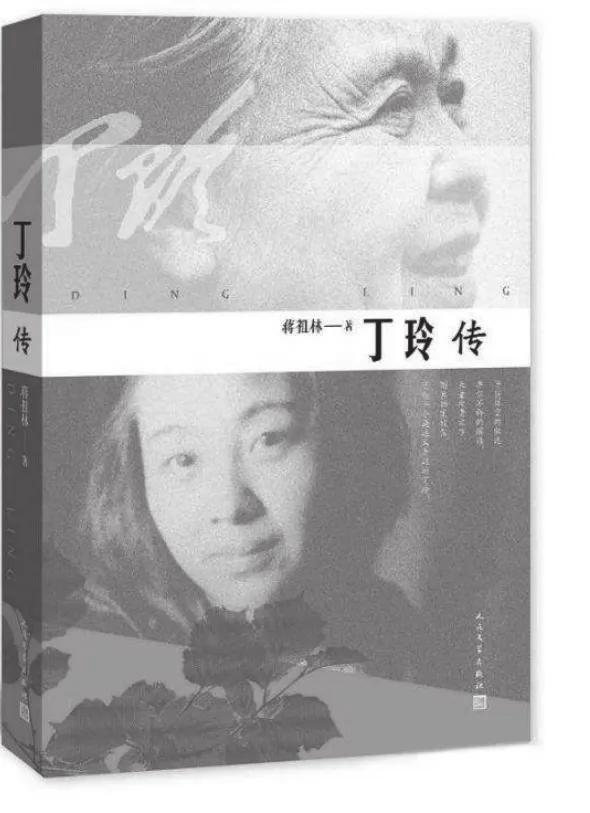
蒋祖林著《丁玲传》
直到李传出版,各种丁玲传记在述及丁玲与瞿秋白的交往时,只写丁玲对瞿秋白与王剑虹恋情的成全,而丁与瞿之间的感情,则被写成一般的友情。蒋传却依据作者与传主的私人谈话(母子夜谈),直承丁与瞿之间的感情已超越了普通的朋友之情,而属于纯粹的恋情:
有一天谈到她和瞿秋白之间的事,她若有所思地稍稍停顿了一下,随之说道:“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王剑虹。”她又说,“我看到王剑虹的诗稿,发现她也爱上瞿秋白时,心里很是矛盾,最终决定让,成全她。”
母亲向我说到她把诗稿拿给瞿秋白看时的情景:“瞿秋白问:‘这是谁写的?’我说:‘这还看不出来吗?自然是剑虹。’他无言走开去,并且躺在床上,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问我:‘你说,我该怎样?’我说:‘我年纪还小,还无意爱情与婚姻的事。剑虹很好。你要知道,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你该走,到我们宿舍去……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更向他表示:‘我愿意将你让给她,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啊!’他沉默了许久,最后站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听你的。’”
我听后,实在觉得这是一个纯洁、高尚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
蒋传特别指出,丁玲1980年写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的有关描述并不完全符合实情,丁玲在这里有所掩饰。这件事起码说明,作家回忆录之类不可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作为唯一的史实依据。对于自己所披露这件史实的可靠性,蒋祖林提出的旁证,一是其妻李灵源也曾听丁玲本人讲过一次,二是从丁玲那篇回忆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笔者以为蒋传的说法是可信的:从丁玲角度说,母子之间的谈话应该最掏心,从蒋祖林角度说,对这件事也没有必要虚构或隐瞒。但是,读者或许会产生另一种疑问,即作为儿子为母亲撰写的传记,蒋传为何要披露这一史实?这不是为本来就有各种猜测和传闻的丁玲恋爱故事,又多了一个谈资?不能认为作者只是为了还原史实,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传主信息,因为在同一部传记里,作者对丁玲最后一次恋爱,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段婚姻——丁玲与陈明的相关交往与经历,涉及就很少。而在此前不久出版的李传中,丁玲和陈明的故事却是被突出呈现的。笔者认为,蒋传如此处理,恰与李传有关,即出于与李传“对话”的需要!二者的互文关系很明显。
在写到丁玲与王剑虹及瞿秋白的交往时,李传的说法与丁玲那篇回忆文章基本一致。李传写到丁玲婚恋经历时的最引人瞩目之处,是延安时期丁玲与陈明交往及恋爱和婚姻的经过。在这段书写中,李传揭示并凸显了恋爱时的丁玲性格强势的一面,而蒋传是为凸显丁玲恋爱时的无私与对友情的看重。
李传所叙,也是依据一手资料——当事人当面主动对其所谈,或对当事人的当面采访:
陈明2007年夏天在上海参加丁玲国际研讨会时对笔者说:“在西战团时,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我们都坐在炕上,我跟丁玲说,主任,你该有个终身伴侣了。她说,你看我们两个怎么样?我吓了一跳。后来我还在日记里说,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丁玲看到我的日记,说,我们才刚开始嘛,为什么要结束呢?”
这只是其中一说,即丁陈之恋中,丁玲是主动的,陈明开始并未爱上丁玲。但接着李传又讲到了另一种说法,所据史料是丁玲当年的“小姐们”罗兰的相关讲述:
2003年1月13日,陈明带李向东去北京和平里,看望84岁的罗兰老太太,当着陈明的面,罗兰对李向东说起一些往事,其中说到:“三八年在西战团,陈明告诉我,说爱上丁玲了。我说那不行,第一丁玲是作家,第二她比你大。塞克在旁边看到我们两个说悄悄话,还问,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两种说法看上去矛盾。按常理推断,应该是两人互相都有意,但面对年龄和地位的差异及传统观念、周围舆论造成的压力,陈明抗压能力较差,所以选择了退却。为了疏远丁玲,他主动提出调离。“丁玲却紧追不舍,不肯放弃。”李传说:“在这场颇受非议的婚姻中,我们看到了丁玲不畏人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倔强个性”,这一判断应该是基于曾经与丁玲近距离接触而获得的对丁玲性格的了解。李传还披露,后来陈明爱上了剧社一个搞音乐的姑娘席平,二人在陇东的庆阳结婚。罗兰亲口告诉李向东,丁玲得知陈明另娶他人后非常痛苦。丁玲对罗兰说是席平先找的陈明,陈明一听好话就心软了。罗兰为丁玲不平,跑去找陈明吵了一架,并把席平骂了一顿,要求席平离开陈明。第二天她就把陈明带回了延安。席平是彭真的姑姑的干女儿,笔者揣测,后来彭真对丁玲似乎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不好印象,除了伦理与审美观念所致对文学作品理解的差异以及周扬的影响,也许还与此事有关。李传作者虽然更亲近丁玲,但对悲剧人物席平也寄予很大的同情与敬意,并写到了陈明晚年表露的对席平的愧疚之情。另一方面,李传又肯定丁玲对陈明的选择是正确的:

李向东、王增如著《丁玲传》
后来的发展说明,丁玲的眼睛真是“毒”得很,从她选定了陈明那一刻起,就把后半生的幸福紧紧攥在了手里。
此可谓持平之论。我们都知道丁玲后来的诸多不幸,但是她与陈明的关系几十年如一日,起码保证了家庭的和谐幸福。
相比之下,蒋传对丁玲与陈明之恋的交代,却非常简略,只在第287页用三个小自然段带过,未加任何有感情色彩的评论,只订正了一个史实记述讹误:丁玲与陈明结婚的日期是1942年11月7日,而非那年的春节(2月15日),并以自己当时的亲历为证。李传依据黎辛的回忆并旁证以蒋祖林的说法,也持此说。两部传记共同纠正了陈明本人的记忆。蒋传对丁陈情感经历的淡化,应该与传记作者本人的情感态度有直接关系——这从最后叙述丁玲晚年办《中国》时,写陈明“夫人干政”之事可以看出。
如果说在丁玲、胡也频之爱中,丁玲已显示出其强势一面,但仍有一定“小女人”气,丁玲找冯达为伴是为“娶个太太”,那么,丁陈之爱既显示了丁玲非同寻常的“丈夫气”,又是双方情感的对等互动。蒋传爆料丁瞿之爱,除了还原历史真相,估计也为“矫正”李传所披露的丁陈之恋中丁玲因“爱情的自私”所造成的过于强势的形象。不论意图为何,蒋传对丁玲瞿秋白情感的揭示,给我们提供了一段新的可贵而可信的史料,其价值正如李传所“爆”丁玲与陈明之恋缘起之“料”。综合来看,能让我们看到比以往丁玲传记更为丰满的丁玲形象:她早年初恋时对王剑虹的“让”,既是因为闺蜜挚情,也因她可能直感到,以自己的强烈个性与强势性格,也许与瞿秋白这样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不太合适——作为重要历史人物的瞿秋白,是不会成为一个男性“太太”、“贤内助”的,而胡也频、冯达和陈明都是唯丁玲马首是瞻的“贤内助”型男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可解释为何丁玲最终没有与她“最怀念的”冯雪峰走到一起:冯雪峰其实也是个比较强势的人物。尽管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但当1955年风暴来临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出现隔阂。蒋传揭示:
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年里丁玲与冯雪峰各自生活、工作的环境不同,各自都有所变化,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那些年,丁玲在文艺界的地位,紧排在周扬之后,似乎是文艺界党内第二号人物,略高于冯雪峰。可能冯雪峰多少还有一点适应不了这一变化,因此,在相互关系上也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嫌隙。
蒋传还写到冯雪峰当年所写检讨中说感到丁玲骄傲了,在批判丁玲的发言中说丁玲“像家长,像贾母”,虽然这是特定形势下的事情,但蒋传认为“应该说冯说的是真话”,是“心里话”。而丁玲这时对冯雪峰也有了一些看法:她对蒋祖林说,冯雪峰担任《文艺报》主编后曾有情绪,认为丁玲虽然不在《文艺报》了,但影响还在,使他不好工作,“言下之意,冯雪峰这个人也不是怎么好相处的”。
然而,李传关于丁玲与冯雪峰爱情的叙述,却是另外一种面貌。据李传,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曾很狂热地追求过冯雪峰,说“丁玲与冯雪峰的恋爱,是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当初胡也频追求丁玲很狂热,丁玲被感动后,与之过起并无肉体关系的同居生活。冯雪峰是在这种情况下闯入他们生活的。冯雪峰对丁玲的吸引力超过胡也频,是因她感到冯雪峰能完全理解他,而胡也频不能;冯雪峰已是党员和革命者,而胡也频尚且不是。不过,胡也频发现他们的感情关系后反应激烈,曾大打出手。丁玲与冯雪峰这才决定中止交往。胡也频牺牲四五个月后,丁玲开始对冯雪峰发起热烈的爱情攻势。“雪峰则理智、矜持得多,家庭的责任、左联领导者的身份都约束着这个共产党员”,他们之间这段时间的这些通信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不曾收入《丁玲全集》)。李传上述叙述,除了据丁玲与他人的通信,还有丁玲晚年谈话录音记录稿为证,也属一手资料。
蒋传的叙述与此有所不同——在“四人帮”刚被粉碎的时候,蒋祖林夫妇去山西嶂头村看望母亲时,曾问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有没有想过与冯雪峰结合的事,丁玲予以否认,并说:“如果我想的话,我相信我可以把他抢过来,但我不愿意欺负弱者。”蒋传又以丁玲1985年3月1日致白滨裕美的信为旁证。笔者认为,蒋传与李传的叙述都有依据,都是可信的。丁玲晚年的说法,是因谈话对象关系,加上多年后人事的变化及个人理性反思,她有了新的感受和认识。但她也并未对儿子和儿媳明确否认自己那时对冯雪峰追求的主动和热烈;她只是暗示,如果她执意追求,不顾其他,她是有办法成功的。而蒋传强调丁玲“不愿意欺负弱者”(夺人之爱),同样是与李传关于丁玲在爱情追求方面比较强势的叙述及观点的“对话”。
丁玲和沈从文的早年友情与晚年纠葛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怨,是晚年丁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两人交往密切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初期,而最密切一段,是胡也频被捕至牺牲不久。李传较具体地写到了胡也频被捕前后沈从文对丁玲一家的关心和帮助。胡也频被捕前,虽然双方在政治上开始渐行渐远,沈从文在生活上仍然关心胡也频夫妇,主动把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胡也频穿;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很着急地找了徐志摩、胡适、蔡元培等人,试图营救,又陪丁玲一起去探监,陪丁玲去南京找邵力子,独自去找陈立夫、邵洵美。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陪丁玲将四个月大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写完这些后,特地加上一句评论:“在丁玲最困难时,沈从文挺身而出,全力相助,豪侠仗义,患难中见真情。”
蒋传写这段时,先写冯乃超曾答应帮助胡也频夫妇带孩子,写胡也频夫妇为此“感动得一夜没睡”,并引用丁玲回忆文章中的一句话“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求不到,而在革命队伍里,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感情”予以赞美。接着,也写到胡也频被捕那天“穿上暖和的海虎绒袍子就走了。这袍子是沈从文借给他穿的”,写到胡也频失踪后沈从文为之不安。
沈从文老友、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曾撰文说,1949年前后丁玲不念旧友情而冷淡沈从文,写得很具体:
大约是三月上旬一天,从文带着虎雏到北池子中段面对路东骑河楼那个大铁门去见丁玲。从文去找丁玲的目的,并不想向她祈求什么,还是想弄清楚心中那个不明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那样把他看作“反动派”。
从文带着微笑,走进铁门内那间充满阳光的二楼。从文原以为丁玲与他有多年友谊,能够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几句真心话,说明白人民政府的政策,向他交个底,让他放心。谁知道见了面,从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故旧,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军棉军装的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从文是个倔强的人,只好默默地带着小儿子走出那个大铁门。
对此,陈明迅即撰文澄清事实真相,说明刘文所说沈从文去见丁玲的1949年“三月上旬”丁玲根本不在北京,丁玲也从未住过刘文所说的那所房子。陈漱渝也曾于2007年撰文予以反驳。涂绍钧2012年出版的《图本丁玲传》则在引用陈明文章予以否认之后,用公开出版的丁玲日记和书信作为旁证。
李传和蒋传同样用可靠资料与严密逻辑反驳了刘文说法,说明直至丁玲被批判的1955年,丁沈二人仍保持联系,沈从文还曾向丁玲借钱,交情未断;二人产生隔阂,是在丁玲1979年读到沈从文写于1930年代的《记丁玲》并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以后。但在此之外,在对丁沈晚年交恶一事的评价及态度上,蒋传与李传却有明显差异:蒋传在指出了许多研究者“在立论所依据的材料上,取其所需,摒弃于己不利”,“甚至有些已被证明并非事实的事,却仍采取避而不见,一而再地引用论定”的错误做法之后,特别说明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在丁玲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几个点滴而已”,即对二人关系予以淡化,对“过分地渲染所谓沈、丁的‘友谊’,为之‘惋惜’,并将这‘友谊’终结的原因归之于丁玲”,表示大不以为然。李传则站在更超脱、更理性的位置,客观梳理了二人交恶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一方面指出沈从文当年写《记丁玲》完全出于好意,“既为宣传丁玲也为教育青年”,又根据丁玲对《记丁玲》的批注文字,指出丁玲是愤慨该作写胡也频丁玲夫妇与革命的关系时的态度,“沈从文固然好心,但他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自以为是的评说且不乏讥讽的态度激怒了丁玲”,丁玲“因此反应不免过于激烈”。并且指出,沈文提到冯达,这也是丁玲所忌讳的。对此,沈从文本人也有知觉。李传认为,沈从文《记丁玲》中对冯达的描述与评价,其实与丁玲自己在《魍魉世界》里所写“极其相似”;而关于胡也频,李传说沈从文“真是最理解丁玲与胡也频感情的一个人”。这与蒋传所说“沈从文也实在是算不上是胡也频的知己”之说似有矛盾,其实二者只是着眼点不同:蒋传侧重从沈从文对革命以及胡也频夫妇参加革命的理解来说,李传则是从沈从文对丁玲与胡也频、冯达为人性格的认识来说。李传又指出丁玲忌讳冯达,对于沈从文对革命的“庸俗”解读大为光火,也与她当时正为历史问题所困的处境有关。秦林芳的《丁玲评传》也曾表达过类似看法,只是秦著完全将丁沈的“相轻”归结为“政治功利”,完全不承认丁玲政治信仰的真诚性,这与李传有所不同。
蒋传还讲到一个细节——丁玲曾对蒋祖林说过她写《也频与革命》一文时的想法:当时她也是一再犹豫的,因为她也“顾及沈从文的健康和情绪”。但她又认为,还是趁沈从文健在的时候发表好,因为这能给沈从文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此事有丁玲1980年致赵家璧的信为证。蒋传还引用陈明1991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美国汉学家艾勃向沈从文探问他与丁玲的这段公案,当时沈从文回答:“过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说得有不一致的地方,以丁玲说的为准。”蒋传与陈明文章一样,对沈从文当时不作公开回应,只在私人信件里表达不满,而在丁玲、沈从文都已去世后的1990年,沈从文的两封信被公开发表,表示遗憾,因为死人已无法作答。
笔者对读沈从文给金介甫和康楚楚的信与丁玲给赵家璧的信,发现其实两人当时都还是有所顾忌,对对方都是既有不屑、不满乃至怨气,又有所怜悯的——丁玲觉得沈从文“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想到“我的文章的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也许有点不人道”,并说“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的”;沈从文说“她廿年受了些委屈,值得同情”,想到“她健康不大好,必然影响到情绪”,决定不与之争辩。在1979年丁玲首次读到《记丁玲》之前,1949年后二人再度相见时,沈从文为何一直不曾对丁玲提及这篇作品?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之后沈从文为何不直接作答?笔者以为,沈从文不愿提此作品,肯定不是把它忘了,而是他也觉得在新的环境下此文有些不合时宜,而且自己用了许多虚构,这些虚构丁玲肯定不会喜欢;他不对丁玲的文章直接作答,是因它涉及“革命”这个敏感问题,作为党外人士且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的他来说,也确实不好回答。即使两人公开交锋,也辩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从丁玲“左转”开始,双方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开始南辕北辙。沈从文认为丁玲与丈夫介入政治是由于幼稚无知,是“误入歧途”,丁玲则私下里认为老友沈从文庸俗、想做绅士,乃至有些“市侩气”。但过去友情尚在,政治观、艺术观的分歧尚不影响到生活上的互相关心和帮助。而这些不以为然,沈从文在《记丁玲》里确有明显流露。他当时以为丁玲已死,就无所顾忌,而在丁玲复出、并正奔波于历史问题平反的1980年,沈从文已知关于丁玲夫妇参加革命的动机及对革命的态度之事,对她来说非同小可,他即使有委屈,也只有对朋友私下发发牢骚了。而作为女性且多年蒙冤的丁玲,虽然尽力“强制住”自己,言辞还是过激了些,失去了分寸,这一点连陈明也承认。李传也直言丁玲“反应不免过于激烈”。在后革命年代,一些不曾亲历革命、投身革命的学者,在评论丁沈之间是非时,则不免倾向沈从文一些,因为他们对革命与文学的看法与沈从文更接近。
丁玲与沈从文围绕《记丁玲》的争议,若抛却个人意气之争及其他现实因素,其实也是一个有关传记、回忆录等纪实类文体写作中是否可以虚构,传记写作者如何表达自己对传主行状看法的一个理论性、专业性的问题。丁玲对沈作最大的不满,一是来自沈作中的虚构成分,二是其居高临下的议论显示的对革命者思维与行事逻辑的隔膜。由于前者,丁玲说沈作是“小说”;由于后者,丁玲骂沈从文是“市侩”。前述刘祖春《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一文写沈从文拜访丁玲受到冷遇一段之所以引起当事人亲属的不满,也是因为这段描述其实并无可靠的史料依据,作者并未对之进行学术性的核实查证。涉及传主人际关系与性格品质的重要史实不能虚构,这正是传记与历史小说的重要区别。沈从文自己也承认《记丁玲》有小说成分。所以丁玲研究者可以将其作为参考,但不可作为纯粹的史料不加旁证地使用。笔者认为,《记丁玲》中对丁玲、胡也频的议论无可厚非,因为读者明显可以看出它代表的仅是沈从文的观点。革命者与非革命者思维和行为逻辑不同,革命伦理与日常伦理迥异,所以,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夫妇这对原先的挚友在思想与事业上分道扬镳之后,竟都互相觉得对方可笑又可怜。感到“可笑”,是从自己的逻辑出发看对方;觉得“可怜”,则既有居高临下姿态,也与昔日友情分不开。
再说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与距离
在为涂绍钧、秦林芳2012年分别撰著的丁玲传记所写书评中,笔者已谈及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问题。而蒋传和李传在这方面较之前二者更具典型性。
作为儿子为母亲写的传记,作为传主生平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乃至直接参与者,蒋传在史料提供方面具有其他作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它有多处指出其他丁玲传记或相关研究论著的史料错误,甚至包括丁玲自己文章中与史实不尽符合之处。前述丁玲与瞿秋白关系即其一例。蒋传所指证的丁玲本人回忆文章或访谈中与史实不合之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避免引起猜疑和议论,丁玲故意为之,例如,蒋传指出《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访谈《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中“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一句实际应是“只有天上的梦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资格批评他”。这种修改应该是丁玲本人的意思。此外,丁玲在散文《冀村之夜》中隐去她自己当时的坦然勇敢行为,则是出于谦虚。蒋传一概予以还原。另有一些,是丁玲自己记错了,蒋祖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寻找旁证(比如相关的有据可查的标志性事件)予以纠正。这种纠正有的有一定目的,例如蒋传纠正了丁玲回忆文章中关于搬到文抗的时间的说法,是因认为“可能对澄清关于发表《野百合花》的责任这一历史问题有点儿意义”;有些则只为澄清史实,并无他意,例如关于胡也频一家三口唯一一张合影上的题字,蒋传以自己作为照片唯一保存者的身份,说明照片背面并无许多相关文章中所说的题字。
蒋传在史料方面另外一些值得重视之处,是作者作为丁玲唯一的儿子、作为传中与传主相关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一些重要历史关头个人见闻与心理的细致描述。比如丁玲被软禁在南京时,自己作为一个刚刚记事的儿童眼中的母亲。书中多次出现的母子夜话,很有史料价值,例如第244页写丁玲告诉儿子当年与彭德怀是否有恋情,自己为何没有选择彭德怀。第435页写1955年党组扩大会首次批判丁玲时陈明的表现,丁玲对儿子说“叔叔党性强着呢,知道是开斗争我的会后,他就向电影局党委提出,他是不是从多福巷搬到电影局去住。后来没有搬出去,但是对我的情况也不闻不问,更别说出什么主意了”,这虽然不能颠覆此前与此后丁玲与陈明之间的恩爱关系,却从历史一瞬看出当时压力之大,以及人的微妙复杂心理。再结合后面写丁玲晚年办刊时陈明的“夫人干政”,客观上投射出继子与继父(祖林兄妹一直称陈明为“叔叔”)之间时亲时疏的关系。蒋传还有一处,写到丁玲与儿子谈及胡家亲属时,“极少用你祖父、你祖母、你几叔这样的措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对家族血缘关系的西方式观念。有些段落,则可以与李传相关段落相互参照来读,让人看到这对特殊的母与子在特殊年代里的独特经历与心路历程。特别是1957年丁玲被调查时蒋祖林被询问的经过及被询问时的见闻与心理,丁玲被打倒后蒋祖林去苏联前母子告别时的情景及儿子的心理。第456页还写到自己当时压下不曾揭发的母亲的一些事。李传则写到1958年丁玲在北大荒收到蒋祖林寄自列宁格勒的关于暂时断绝与母亲联系的信件时,所受到的沉重精神打击,写到在绝望中是陈明又给了她温暖。李传既写到了丁玲此时的感受,又表示了对蒋祖林的理解。上述这些都是其他不含虚构与想象的丁玲传记所难以写到并写好的。
李传作者之一王增如为丁玲晚年秘书,除了文字资料,她也是丁玲晚年一些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同样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位置与距离优势。然而,与蒋传相比,李传具有另外一些特点:如果说蒋传采取的是传中事件亲历者或参与者视角,个别段落(例如涉及传记作者蒋祖林本人与母亲的关系部分)甚至有回忆录的特征,始终洋溢着歌颂革命、怀念母亲的浓郁情感,那么李传的特点是以后来者眼光审视历史,既同情地理解革命,又反思革命,以人性视角切入传中相关人物与事件,剖析事件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广收当事各方(包括对立一方)的资料,尽力作“平情如实之论”。
以对丁玲与王实味及胡风关系的叙述为例。王实味和胡风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艺界大批判中受冲击最大、蒙冤最重的人,总体而言与丁玲冤案不相上下,也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传作者也许出于多年政治运动的阴影以及革命战士的一贯立场与思维定势,在述及王、胡二人与丁玲关系时,给人以尽力淡化的印象。比如通过纠正丁玲对搬家到文抗时间的记忆错误,说明“《野百合花》不是丁玲组稿组来的,而是王实味自己送来的。丁玲与王实味毫无交往,而且在丁玲眼里王实味还算不上是作家”,以求减少其对发表王实味《野百合花》的责任。而对于胡风,则说“丁玲与胡风,也可说算是朋友,但不知心,主要是文艺思想方面有较多分歧的缘故”,“丁玲只好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胡风把她划为周扬一派了”。对丁玲与萧军的关系,则很少涉及。李传则说:“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丁玲的一些重要观点与王实味是相通的”,并通过对丁玲当时观点的分析得出结论:“这也就不难理解丁玲为什么要签发《野百合花》了。”李传引用黎辛和黄昌勇的文章,说明丁玲将发表此文的全部责任担起来,自有其道理。对于丁玲与胡风的关系,李传专列一节,说二人友谊可追溯到1932年底,说1949年1月28日“胡风在丁玲家谈了一天”,后来“胡风在沈阳停留不到30天,与丁玲长谈近10次,每次少则两三小时,多则整日长谈”,“他们一定是深层次的谈话,丁玲会把不轻易示人的意见也和盘托出”,“正是这些谈话,确定了二人的密切关系”。李传还引用在胡风被整、丁玲走红,二人开始分道扬镳的1950年元旦胡风致妻子梅志的信:“在这当局文坛,她还是一个可以不存戒心谈谈的人。”在晚年,丁玲还在与习仲勋谈话时为胡风彻底平反呼吁。李传写延安时期丁玲与萧军的交往用墨颇多,并引用萧军日记,写出了两人非同一般的友谊以及后来的分歧绝交、绝交之后又互相同情。
李传的史料来源,除了丁玲自己的文章、晚年谈话录音、作者亲眼见证,也有许多别的一手资料,包括当事各方的日记、书信、回忆文章,以及对各方人物的访谈。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尽量对矛盾各方予以“同情之理解”,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事件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然而,李传也并非没有立场、没有价值判断。在对各种丁玲传记都会大书特书的丁玲与周扬恩怨方面,李传不同于其他传记,不仅写到周扬偶尔也流露出一点歉意,还特别写到,1979年11月6日下午,在丁玲大会发言的前两天,周扬曾去木樨地丁玲家中拜访,但不巧丁玲不在家。李传认为“他一定是为丁玲而来”,“此来很可能是遵照胡耀邦讲话精神,想取得丁玲谅解”,感叹“历史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否则可能就没有丁玲两天后锋利泼辣的大会发言,可能他们后来的关系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又认为:“但如果周扬事先打个电话,丁玲决不会不在,所以,周扬究竟有几分诚意又值得怀疑。”个人与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和历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个人固然受环境制约,但人的个性和品格,还是有很大不同。这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历史的走向与进程。
李传写到了丁玲对革命逻辑、革命伦理的理解,他引用丁玲给儿子的信:“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某些人沾了一点便宜”,“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了。”由于采取了人性视角,李传给人的感觉是既同情地理解革命,又反思革命中的人性变异。关于丁玲晚年的表现,李传既写出丁玲革命信仰的真诚性、坚定性,也揭示其个人切身处境的因素,说明丁玲令外国人失望的访美言论,虽然不是“表演”,确也有“防身”考虑,并引用丁玲致宋谋玚的信予以佐证。此外,李传还以作者之一王增如的亲历,写到晚年丁玲面对死亡时各种细腻的生命感受与体验,这些也是其他丁玲传记所不太涉及的。
蒋祖林与李向东、王增如夫妇所写的两部丁玲传记,都是以一手材料见长、且互不可取代的著作。参照来读,当有更多收获。

晚年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