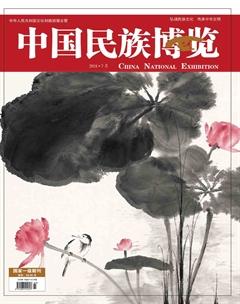试论“美术史”的重构
【摘要】美术史这一学科在今天已成为“跨学科”,不断与其他人文学科互动,例如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宗教性等。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导致对这种模式的怀疑逐渐加剧,这种趋势下学科将失去传统含义,转变成一种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在“图像时代”的大环境下,对“原境”以及“上下文历史”的重构在回归纯粹美术史的研究这一点上显得尤其重要。且只有史、论二者结合,对美术史的重构才可以摆脱某一单独学术立场的语境。
【关键词】传统;美术史;重构;原境;时空;“历史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一、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的不足
18-19世纪的研究者们通常以“风格”发展为主线来叙述美术史。这种美术史研究体系不足之处在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艺术与美术的发展单纯地概述为线性的发展脉络,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为一种直线型的“生物模式”。即把历史发展完全视为一条条线,各种复杂的现象成了互不干涉的存在,从而忽视了各艺术门类发展的总体规律以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①然而,不同时期的艺术品、艺术形态也并不平衡相似,并不是从低到高的进化这么简单,而是各有其突然的形式。这样的美术史研究虽然看似在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基于宏观的叙事模式,但不过是把美术形式的发展描述为“滥觞期——成熟期——衰落期”的三段式系列。其结果是把汇合了不同时段和艺术形式的一部美术史建构成若干这种系列的硬性综合,其以生物的成长、衰老和死亡为比喻的历史叙事是相当幼稚的。②作为人文历史学科,在保留独特的统观性和整体性之外,更应该融以更复杂、严密的叙事方式。
二、新时代的美术史研究
实际上,“美术史”这一外来学科在西方也从没被严谨的定义过。笔者认为,对于美术史的问题,应该从古今、远近、宏观微观多种角度引出对其的思考及想象。其具体研究内容应该在时间、地域甚至是社会层次等方面进行考察。美术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是广阔的,具有“全面性”甚至是“全人类性”的。史是全体的、人类的史,美术史同样也是全体的、人类的史。作为特定时期的发明,“美术史”应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特定语境相密切联系。例如,我国魏晋之前的艺术品或是被分类为关于艺术的制品,大都是为礼仪、实用目的而制作,这源于当时封建社会的重礼仪倾向以及落后社会普遍强调的实用性,而非纯碎欣赏,我们所看到的其商业价值、美术价值均为后世的附加和转化。而到了魏晋时期,礼仪和实用渐渐不被人们所需,就开始逐渐转向为观赏或为政教而制作。再到晚一些的文人画时期,观赏的目的也弱了,艺术创作甚至成为仅仅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所以说“美术史”的定义及内涵需放到时空中来把握。
然而,从20世纪以来,美术史已成为“跨学科”,不断与其他人文學科互动,例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图像学、宗教学等,这些学科逐渐向美术史这一学科渗透,不断形成新的研究点和研究角度。这种趋势下美术史这一学科将逐渐失去传统的学科含义,而演变成其他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甚至是成为其研究角度和手段。但如果从相对积极的角度考虑,一种全新学科的概念得以建立——不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而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任何与形象有关的现象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同时,其研究范围各个领域逐步扩展,这既代表了美术史学科影响力的壮大及对普遍人文社会相关学科的积极介入,又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逐步模糊不清的“轮廓”“面貌”及身份的丧失。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美术史的研究渐渐依赖于摄影、传媒、图像技术的发展。现代解读往往根据图像对原艺术进行“转译”,这成为解读艺术品或者美术史的先决条件,可以使原现场观看的许多视觉条件(周围环境)消失。其价值在于扩大了美术史家以及美术史研究者占有相关资料的范围和能力,改变了对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思维方式。同时,“比较式”论证法也由此兴起,即图像比较。照片资料使得美术史相关教学工作得以从“以语言基础”向“以视觉基础”转换,即由语言到视觉。“视觉”成为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唯一的联系,原对象被“碎片化”处理——肢解与重组,即由空间跳到视觉。这种研究模式很容易造成美术史的研究呈现“经典化”趋势。因为可获得的图像大多是“经典作品”,所以对美术史的研究很难达到所谓的“统观性”,美术史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基本的、牢固的内在框架支撑、没有自成系统的方法论和操作规则的新时代学科。而美术史研究者也因而处在两难之境,一方面,为提高研究效率与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可观性,而不得不使用图像这一工具;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史”的探索与知解只能通过图片、图像、影视这样的新途径,那这一学科无疑将沦为纯视觉文化的一部分。③
三、美术史的重构
美术史相关研究主要涉猎看的问题,以及历史物质性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传统的宏观叙事手段逐渐被解构,后现代主义学者也不愿意从整体上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那么美术史只能是被“肢解”,成为碎片的史。然而,作为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美术史的目的自然并不在此。④故而学术界提出的对美术史的重构,是基于对宏观叙事模式的解构主义而提出的新方法。从学科发展变化来看,其范围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由“自上而下”转而“自下而上”,由“形而上”慢慢转向“形而下”,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描述。美术史研究者过去研究的层面大多立于对学科总体的定位和描述,而今则转换到新的层次,即以观察的对象的本源为主,更加注重其单独的内涵、其相关的分支学科、关联领域以及结构概念总结,其研究方法和切入角度皆是依据研究指向的目的、对象而确立的,这些都需要放在重构的结构中去思考。所以说,美术史的重构也可以看作是对宏观叙述结构的一种解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艺术品及美术史的“原境”重构由图像转移重回作品本身或史实本身。这里的“原境”既包括形而上的时空中的“历史物质性”,也包括形而下的原物、环境。原物、原环境即代表该作品任何的功能、构图、色彩、欣赏方式等原始状态。而历史物质性是处于时空中不断变化的东西。重构即对其二者的融合,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研究考察方式。古代的绘画、壁画、雕刻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变换面貌、地点、功能,便被赋予了不同的、变化的历史物质性,我们将其看作是一种“历史再创造”。所以,不能仅仅对一件艺术品的原环境进行重构,也要对其形式、意义、上下文等层面在历史变化中进行寻找。将美术史看作一个独立的体系,对其“追根溯源”,使其与文化、宗教、政治发生关系,这是对“传统”的重构,是重构的“一级因素”,是宏观的。当然,在这一层面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其“时间性”,即时间轴,此为一种线性重构,以及一些空间因素。例如,地域特点则是此重构层面中的“二级因素”,是微观的。所以还要在一定程度之外打破这种线性研究,以超越空间地域的关系,由横向展开。巫鸿先生所谓的双向研究方式为“开与合”与“纵与横”,我们今后所研究与探索的美术史势必是纵横、开合中的美术史。⑤
四、结语
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重构”已然成为当代美术史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手法、途径甚至是目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例如考据、辩关、断代等技巧都日渐被削弱,一些西引研究法例如图形、心理、社会学甚至是性别主义逐步兴盛。重构具有不同的层次。从原历史的角度对美术史学科进行重构、思考,可以看成一种相互的启示,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美术史研究的回归。只有史、论二者结合,“以史带论”,“实物”和“理论”相互支持,对美术史的重构才可以摆脱某一单独学术立场的自我标榜,真正实现其意义。⑥美术史的重构显然也需要立足于时代的观念与文化,美术史的重构没有绝对统一的模式,只有在不同的观念与文化的变化要求下产生的不同的方法角度。因此,可以说,美术史的重构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常新的问题。
注释:
①刘允东.《全球史视野下美术史的重构》,《南京艺术学院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2).
②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1):126.
③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1):66.
④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⑤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1):80.
⑥朱志荣,巫鸿.《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巫鸿教授访谈录》,《艺术百家》,2011(4).
作者简介:梁嵩(1993-),男,汉族,山东德州人,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绘画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