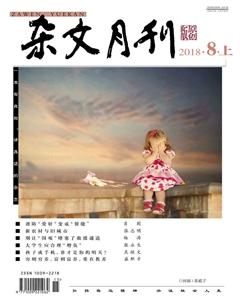最奇崛的文化大师辜鸿铭
鲁先圣
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文化界大师云集,文星璀璨,在遭受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时代,却诞生了几十位学贯中西的大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思议的时代奇观。
他们中间,可以说,辜鸿铭是最奇崛的一位。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中国的“东西南北人”。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他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鸦片战争开始之后,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在布朗那里,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到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在欧洲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
而与此同时,辜鸿铭奇崛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令西方人不可思议。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他。毛姆的朋友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无地自容。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是杰出的民族。他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因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他虽然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他留辫子,穿马褂,戴着傳统的瓜皮小帽子,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
而让人难以笑起来的一个故事是: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子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而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此言一出,所有在场的北大学生顿时无语。
对于辜鸿铭先生,李大钊先生曾经这样说:“愚以为中国2500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
吴宓先生的评价似乎更高:“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